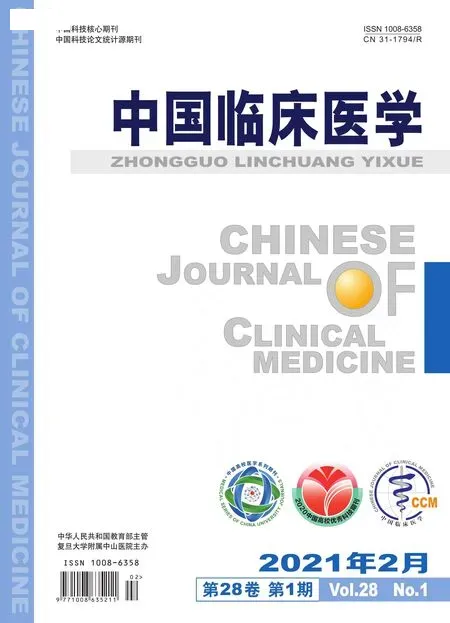超聲心動圖評價心肌作功的研究進展
李雪潔, 舒先紅
1. 復旦大學附屬中山醫院心超室,上海 200032 2. 上海市影像醫學研究所,上海 200032 3. 上海市心血管病研究所,上海 200032
常規超聲心動圖通過左室射血分數(left ventricular ejection fraction,LVEF)反映左室整體收縮功能。二維斑點追蹤技術(two-dimensional speckle tracking imaging,2D-STI)通過追蹤心肌超聲圖像的聲學斑點信號,定量評價左室整體及節段的收縮功能。但是,該應變成像技術存在不可忽略的局限性,即負荷依賴性,而后負荷的增高會造成應變值的降低,導致臨床醫師對心肌真實收縮能力的誤判。無創心肌作功技術通過結合2D-STI與后負荷測定,能夠客觀地評估整體及節段心室收縮功能,具有較大的臨床應用潛力,本文對此進行綜述。
1 心肌作功的概念
心肌作功的研究起源于左室壓力-容積環(pressure-volume loop,PVL)及壓力-長度環的概念。PVL由Suga等[1]在1979年提出,描述了一個心動周期中左室內壓力與容積變化的相互關系(圖1)。理論上,PVL能夠評估生理及各種病理狀態下的心臟功能及儲備能力。該技術不僅在動物實驗[2]中得到驗證,在多種心臟疾病如冠心病、二尖瓣狹窄中也得到了廣泛應用[3-4]。但是,PVL通過有創的心導管方法獲得,臨床應用存在一定局限性。

圖1 左室壓力-容積環示意圖[1]A:二尖瓣關閉;B:主動脈瓣開放;C:左室壓力峰值;D:主動脈瓣關閉;E:二尖瓣開放. 閉合的環內面積反映心臟搏出功;收縮末勢能反映心臟的貯備功能;充盈能是血液回流心室所產生的能量,其大小與心臟的舒張功能和搏出量有關. 收縮末勢能、充盈能與搏出功之和體現1次心動周期過程中產生的總能量。
2005年,Urheim 等[5]利用犬模型探討了根據應變多普勒超聲心動圖(strain Doppler echocardiography,SDE)和有創壓力得出的節段性心肌作功指數來量化區域功能的可行性。該研究通過頸動脈在麻醉犬左室置入微壓計導管測量左室壓力,分別用SDE和聲納微測量法測量心肌縱向應變,發現通過聯合左室壓力和SDE獲得的心肌應變可以估計局部心肌作功;在增加容積負荷和冠狀動脈閉塞等條件下,SDE方法顯示的環面積與超聲微測法測量的環面積有很好的相關性。但是有創的壓力測量限制了其臨床常規應用。
近期Russell等[6]提出將斑點追蹤超聲心動圖(speckle tracking echocardiography,STE)與估計的左室壓力曲線相結合,構建左室的無創壓力應變環(pressure-strain loop,PSL)來表示心肌作功。他們先在犬模型中使用微壓計進行有創性左室壓力(left ventricular pressure,LVP)測量,并使用心內膜下植入的超聲測微晶體測得心肌節段長度;使用STE記錄心肌應變,假設肱動脈袖帶記錄的收縮壓等于左室收縮壓峰值,通過調整參考左室壓力曲線的輪廓來生成估計的壓力曲線,使用軟件獲得估測的左室PSL,結果顯示估測的左室PSL和有創性測量的真實PSL具有良好的相關性(r=0.96)。該團隊在隨后的臨床試驗中證實,無創和有創PSL同樣顯示了良好的相關性(r=0.99)和一致性。
2 無創心肌作功的計算方法
在超聲心動圖測量之前用袖帶血壓計記錄收縮壓,應用2D-STI超聲心動圖測量應變,在心尖長軸、二腔和四腔觀中追蹤左室內膜邊界,假定左室收縮期峰值壓力和動脈峰值壓力相等,利用應變和血壓數據在EchoPAC軟件上構建左室PSL,并根據不同心臟周期階段的持續時間(根據主動脈瓣和二尖瓣啟閉時間確定等容收縮和射血期)調整標準化參考曲線。PSL是根據二尖瓣從關閉至開放期間左室壓力及應變之間的變化關系而形成的閉環(圖2)。二尖瓣關閉,進入等容收縮期,左室壓力急劇上升,而心肌應變無明顯改變;隨后主動脈瓣開放,進入射血期,左室壓力進一步升高,伴隨心肌細胞收縮,應變絕對值升高;主動脈瓣關閉,左室壓力開始下降,進入等容舒張期,在此階段左室壓力迅速下降而應變無明顯變化;當左室壓力小于左房時,二尖瓣開放,進入充盈期,此時左室壓力變化較小,心肌舒張,應變絕對值減小。

圖2 左室壓力應變環示意圖AVC:主動脈瓣關閉;AVO:主動脈瓣開放;MVO:二尖瓣開放;MVC:二尖瓣關閉
心肌作功為節段應變(%)與瞬時左室壓力(mmHg)的乘積(mmHg%)。心肌作功主要的測量參數:整體作功指數(global work index,GWI)、整體有用功(global constructive work,GCW)、整體無用功(global wasted work,GWW)及整體作功效率(global work efficiency,GWE)。其中,GWI為PSL內的總面積,是從二尖瓣關閉到二尖瓣開放的左室全部作功;GCW為有助于心室射血的作功,包括收縮期心肌縮短及等容舒張期心肌伸長;GWW為不利于射血的作功,包括收縮期心肌伸長及等容舒張期心肌縮短;GWE=GCW/(GCW+GWW)×100%。還可以根據17節段左室模型計算出每個節段的有用功(CW)、無用功(WW)及作功效率(WE)。
3 無創心肌作功的臨床應用
3.1 評估心肌能量代謝 Russell等[6]不僅證實了無創心肌作功的可行性,還證明了左室局部PSL面積和心肌葡萄糖代謝之間有很強的相關性。其在6例左束支傳導阻滯(LBBB)患者中,使用18-氟脫氧葡萄糖正電子發射斷層掃描(18F-FDG-PET)觀察心肌代謝,顯示室間隔心肌18F-FDG攝取值降低,而無創PSL區域局部心肌作功分布與糖代謝模式一致,所有患者的PSL面積節段值與局部FDG攝取之間均有很強的相關性(r=0.81)。該研究結果進一步支持PSL反映心肌作功分布的結論。
3.2 評估運動員及存在心血管危險因素人群的心血管風險 耐力訓練是否有益于心血管系統,一直存在爭議。目前已證實在業余運動員馬拉松訓練后左室整體縱向應變(global longitudinal strain,GLS)出現異常,產生亞臨床心功能不全,但GLS的負荷依賴可能導致研究結果偏倚。Sengupta等[7]對24例南亞業余運動員在參加半程馬拉松前、結束后2 h內和結束后72 h進行經胸超聲心動圖(TTE)檢查,結果顯示心肌作功出現了2種趨勢:第1組(n=11)在馬拉松前后GWI無顯著變化;第2組(n=13)GWI在運動期間增加,在結束后恢復基線水平。兩組之間的GWW、GWE及GCW沒有顯著差異;而第2組受試者運動后即刻心率及腦鈉肽(BNP)水平較高,提示心肌應激的存在。該研究顯示,無創心肌作功能夠識別耐力運動下的不同心肌功能變化,提示對于部分人群,耐力運動會隨著心率增加引起更高的心肌消耗,這可能是心臟應激的早期表現,其長期意義還需要進一步探討。
有研究[8]回顧性地納入了無結構性心臟病及心血管疾病(cardiovascular disease, CVD)危險因素的健康人120例,無結構性心臟病但有CVD危險因素(高血壓、高脂血癥、糖尿病、吸煙史、CVD家族史)的患者30例,無心力衰竭的心肌梗死(STEMI)患者30例,缺血性射血分數降低的心衰(HFREF)患者30例。研究顯示:總人群中GWE與LVEF顯著相關(r=0.80,P<0.001),存在CVD危險因素人群及CVD患者的GWE與LVEF無顯著相關性;健康人及僅有CVD危險因素的人群左室GWE為96.0%,STEMI組GWE下降為93%(P<0.001),而HFREF組GWE降低為69%(P<0.001)。結果提示僅存在CVD危險因素不會降低左室GWE,而無心力衰竭的STEMI和缺血性HFREF患者的GWE逐漸下降。GWE是否可以預測STEMI患者進展為缺血性心肌病,有待進一步研究。
3.3 預測冠心病 早期發現和治療冠心病(coronary atherosclerotic disease,CAD)至關重要,但是在CAD早期常規超聲心動圖參數常保持正常。Edwards等[9]對115例LVEF大于55%且無節段性室壁運動異常的患者進行TTE檢查,TTE檢查后3 h內行冠狀動脈(冠脈)造影,將一支或多支主要冠脈狹窄≥70%定義為顯著性CAD,結果顯示:所有CAD患者的GLS(P<0.05)和GWI(P<0.001)均顯著低于對照組,單支和多支血管CAD亞組間GWI無統計學差異;單支血管CAD患者與對照組間GLS無統計學差異,多支血管CAD亞組GLS明顯降低(P<0.001);GWI是顯著性CAD最強的預測因子(AUC=0.786),優于GCW(AUC=0.746)、GLS(AUC=0.693)和GWE(AUC=0.650)。這項研究表明,GWI能識別常規TTE參數無法識別的CAD患者,并能敏感地預測顯著的冠脈狹窄。
急性冠脈閉塞(acute coronary occlusion,ACO)能夠引起相應灌注區缺血和收縮功能障礙,該區域被稱為功能危險區(functional risk area,FRA)。Boe等[10]選擇了150例臨床診斷為非ST段抬高急性冠脈綜合征(NSTE-ACS)并計劃入院后3 d內行冠脈造影的患者,在冠脈造影之前行TTE,發現存在大于或等于 4個節段FRA MWI 1 700 mmHg%對于預測ACO顯示出良好的靈敏度和特異度(81%、82%)。這項研究顯示了局部WI對于識別NSTE-ACS患者ACO優于傳統參數,能為NSTE-ACS患者選擇早期冠脈造影及介入治療提供更多證據。
STEMI早期左室不良重構與心衰發生和死亡率升高有關。Lustosa等[11]納入了350例行介入治療的STEMI患者,在其入院后48 h和STEMI發生3個月時進行超聲心動圖檢查,記錄左室整體及罪犯血管局部的WI和WE,結果顯示:STEMI早期是否發生不良重構與罪犯血管位置無關,發生早期左室不良重構的患者在出院前已經出現GWI、GWE、GLS及罪犯血管區域WI和WE降低;罪犯血管區域WI降低對早期左室重構的預測優于常規超聲心動圖參數(如GLS和LVEF);局部WI小于1 129 mmHg%預示著早期左室重構,而局部WI大于1 460 mmHg%有高達89%的負預測價值。因此,使用罪犯血管區域WI有助于早期識別STEMI患者的不良左室重構風險,并指導隨訪和藥物治療。
3.4 評估高血壓病(HTN)和擴張型心肌病(CMP) 為了探究不同疾病的無創心肌作功模式,Chan等[12]前瞻性地招募了HTN和CMP患者及冠脈造影顯示無明顯冠心病的對照組,將HTN組分為HTN 1級組和HTN 2/3級亞組,CMP患者分為非缺血性CMP(CMPN-ISC)組和缺血性CMP(CMPISC)亞組。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HTN 1級亞組GWI和GCW均有升高趨勢(P=0.90,P=0.87),HTN 2/3級患者亞組GWI和GCW均升高(P<0.05,P=0.000 1);與對照組相比,CMPN-ISC亞組的GWI顯著降低、GWW顯著增加(均P<0.001),CMPISC亞組GWI進一步降低(P<0.001)、GWW無明顯改變(P=0.49)。該研究發現,在LVEF和GLS保留的HTN患者中,GWI會隨著后負荷增加升高,但是由于GCW和GWW按比例增加,GWE無改變,證實GWI比GLS能更敏感地反映后負荷的增加。
3.5 識別肥厚型心肌病(hypertrophic cardiomyo-pathy,HCM) Hiemstra等[13]納入了110例非梗阻性HCM患者及35例健康受試者,將HCM根據表型分為心尖肥厚型、向心肥厚型和室間隔肥厚型,中位隨訪期5.4(3.0~ 7.8)年;聯合終點事件:全因死亡、心臟移植、心衰住院治療、心源性猝死后幸存及植入ICD治療。結果顯示:與對照組相比,HCM患者平均GCW、GWE和GWI顯著降低,GWW顯著增加(均P<0.001);在整體及節段水平上,CW都是減少最顯著的心肌作功參數,且不同表型的HCM之間CW存在節段性差異,因此評價節段CW有助于鑒別HCM的類型;GCW與臨床不良結局顯著相關(P<0.001),提供了臨床上識別高危HCM患者的新思路。
Galli等[14]招募了82例非梗阻性HCM患者及20名健康人,其中70例HCM患者接受了心臟磁共振顯像(CMR),根據Maron分類法將HCM分為Ⅰ~Ⅳ型。結果顯示:盡管LVEF正常,但HCM患者的GCW仍較對照組降低(P<0.000 1),不同分型亞組之間GCW沒有差異(P=0.43);CMR顯示纖維化程度明顯的患者GCW明顯減少(P<0.000 1)。GCW是心肌纖維化的唯一預測因子,其預測心肌纖維化的截點值為1 623 mmHg% (AUC=0.80,P<0.000 1),靈敏度可達82%。GCW不僅能夠較敏感地識別早期心肌纖維化,還能評估心肌的代謝紊亂程度,有望成為評估心室纖維化的有效工具。
3.6 再同步化治療療效的評估 心臟再同步化治療(cardiac resynchronization therapy,CRT)是左室不同步性心衰患者的重要治療方法,然而30%~40%的患者對CRT無應答,這意味著目前的篩選指標還有局限性。為了探究無創心肌作功能否識別CRT無應答者,Vecera等[15]前瞻性地納入21例心衰患者,在基線及CRT后(8 ± 3)個月進行自身對照和組間對照,結果顯示:CRT后有應答者GWW和室間隔WW顯著減少(P<0.01),無應答組GWW及室間隔WW無明顯變化;基線室間隔WW水平是對CRT反應的唯一獨立預測因子(P=0.028),ROC分析顯示其預測CRT的能力(AUC=0.8)優于室壁運動評分指數(WMSI;AUC=0.63,P<0.05),兩者聯合預測CRT的能力進一步升高(AUC=0.86)。這提示心肌作功參數能為合理選擇CRT患者提供幫助,可能成為CRT適應證制定的有效指標。
4 小 結
無創心肌作功是最新發展的一項超聲心動圖技術,具有無創、簡便、敏感、可重復性高的優點,克服了后負荷對心肌形變的影響,能評估多種心血管疾病,有良好的應用前景。但是,PSL并不能完全等同于心肌作功,而僅是心肌作功的替代指標;用PSL計算心肌作功時未考慮左室的幾何形狀、室壁厚度和張力,也未考慮心室舒張期的心肌作功;在某些疾病如主動脈瓣狹窄、梗阻性HCM、外周血管病變等,肱動脈收縮壓與真實左室壓力之間誤差較大。目前缺乏中國人心肌作功各參數的參考標準,仍需要進一步探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