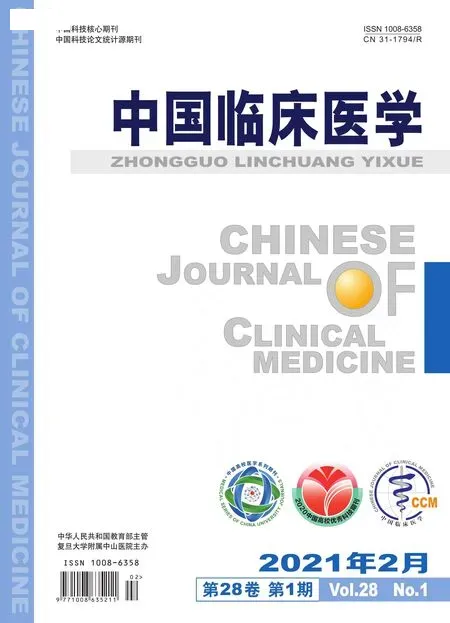妊娠繼發嗜血細胞綜合征1例報告
孫寒香, 葉偉萍, 高玉平
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婦產科,上海 200092
嗜血細胞綜合征又稱嗜血細胞淋巴組織細胞增多癥(hemophagocytic lymphohistiocytosis, HLH),是一組異質性疾病,其特征是T細胞、巨噬細胞和組織細胞激活失控導致的高炎癥狀態,并伴有細胞因子過度產生。HLH是成人最嚴重的臨床疾病之一,病死率為40%,年齡較大和血小板減少是患者死亡的主要影響因素[1]。目前關于妊娠合并HLH的相關報道較少,現將上海交通大學醫學院附屬新華醫院救治的1例妊娠繼發HLH報告如下。
1 病例資料
1.1 既往資料 患者女,36歲,生育史1-0-1-1,人工流產1次,2019年5月27日孕37周剖宮產1嬰。2019年5月19日,因“皮膚瘙癢1月”于當地醫院就診,查體見全身皮疹呈水腫樣突出皮膚,因膽汁酸及肝酶升高,考慮妊娠肝內膽汁淤積癥,予谷胱甘肽、熊去氧膽酸保肝利膽治療。2019年5月27日,治療過程中出現胎兒窘迫,故急診手術終止妊娠。患者術后3 h開始發熱,體溫37~41℃,考慮感染性發熱,予亞胺培南2 g q12h和甲硝唑0.5 g q8h抗感染;谷胱甘肽、熊去氧膽酸保肝利膽;低分子肝素抗凝。影像學檢查結果示兩側腋窩及縱隔見多發淋巴結腫大,雙腋下及頸部淋巴結腫大。產后B超示宮腔內混合結構,符合產后改變。腹部B超示肝臟增大,肝脂肪浸潤可能,胰腺增大,脾大,肝腎間隙積液。泌尿系統B超未見異常。孕期產檢(無創DNA、糖耐量、大畸形排查等)均未見異常,孕前身體狀況良好,無不良病史。
1.2 本次入院檢查資料 患者2019年6月3日下午13時因“剖宮產術后7 d,發熱7 d”轉入我院,入ICU。入院查體:營養中等,無貧血貌,無水腫,體溫38.1℃,脈搏102次/min,呼吸24次/min,血壓108/65 mmHg(1 mmHg=0.133 kPa)。心律齊,有力,各瓣膜聽診區未聞及雜音;雙肺呼吸音清,未聞及干濕啰音;肝脾增大;宮底臍下2指,惡露無異味,量中,色紅,乳汁少,乳頭凸,傷口滲出少,無紅腫。白細胞計數2.5×109/L,中性粒細胞絕對值1.3×109/L,血紅蛋白86 g/L,膽汁酸132.6 μmol/L,丙氨酸轉氨酶254 U/L,天冬氨酸轉氨酶641 U/L,降鈣素原0.79 μg/L。炎癥因子檢測示,IL-2受體6 009.0 U/mL,其余因子正常。鐵蛋白2 050 μg/L。宮腔、血、痰培養陰性,其余相關指標(免疫、腫瘤標志物等)均未見明顯異常。全身淋巴結(雙側鎖骨上、雙側頸部、雙側腋窩、雙側腹股溝)腫大。建議行淋巴結穿刺、PET/CT檢查,患者拒絕。磁共振胰膽管成像(MRCP)示膽囊大,肝右葉血管瘤。入院診斷:剖宮產術后,發熱待查,淋巴結增大待查。考慮:(1)感染性疾病(呼吸系統、消化系統、宮腔或泌尿系統的病毒感染),特別是肝膿腫可能;(2)血液疾病;(3)淋巴瘤;(4)風濕性結締組織病。
1.3 治療過程 治療方案:泰能(注射用胺培南-西司他丁鈉)1.0 g q8h抗感染,余治療方案同外院。入院后血紅蛋白從86 g/L降至72 g/L,故于2019年6月10日輸注2 μL紅細胞懸液支持治療,之后血紅蛋白維持90~105 g/L。患者自入院后體溫正常,丙氨酸轉氨酶、天冬氨酸轉氨酶、中性粒細胞絕對值也恢復正常,故轉入產科病區,繼續用泰能1.0 g q8h抗感染。2019年6月11日患者下午再次發熱,后體溫高達39℃(圖1),故調整抗生素,予泰能1.0 g q8h+萬古霉素1.0 g q8h治療,同時口服抗病毒口服液。再次建議查病原體,患者及家屬同意行PET/CT、淋巴結穿刺、骨髓穿刺、外周血二代測序(next-generation sequencing,NGS)檢查。

圖1 本病例入院后體溫變化圖
1.4 再次診斷過程 查體結果:中性粒細胞0.8×109/L,血紅蛋白72 g/L,鐵蛋白2 050 μg/L,IL-2受體2 493 U/mL,三酰甘油16.59 mmol/L,纖維蛋白原1.49 g/L。對照2004年HLH的診斷標準[2],滿足以下2條之一便可確診。(1)符合HLH的分子診斷,包括PRF1、UNC13D、Munc18-2、Rab27a、STX11、SH2D1A或BIRC4等基因突變。(2)滿足以下8條中的5條診斷標準:①發熱≥38.5℃;②脾腫大;③外周血細胞減少,并至少有血紅蛋白<90 g/L(小于4周的嬰兒為血紅蛋白小于100 g/L)、血小板計數<100×109/L、中性粒細胞<1×109/L;④高三酰甘油血癥(空腹三酰甘油≥3 mmol/L)和/或低纖維蛋白原血癥(纖維蛋白原≤1.5 g/L);⑤骨髓、脾臟、淋巴結或肝臟中有嗜血現象;⑥NK細胞活性降低或缺失;⑦鐵蛋白大于500 μg/L;⑧可溶性CD25(sIL-2R)≥2 400 U/mL。PET/CT結果(圖2)示:(1)全身多發淋巴結稍大伴代謝增高,肝脾腫大,脾臟代謝普遍增高,首先考慮綜上炎性感染性病變所致或HLH;(2)骨髓反應增生性改變;(3)肝臟右后葉稍低密度結節,脫氧葡萄糖代謝不高,良性可能大。2019年6月17日,淋巴結穿刺、骨髓穿刺病理結果均未見異常。2019年6月18日外周血NGS檢查結果示溶血葡萄球菌。

圖2 本病例各部位PET-CT圖片A: 肝臟低密度結節; B: 肝脾腫大; C: 腋窩淋巴結;D: 腹膜后淋巴結; E: 縱隔淋巴結; F:腹股溝淋巴結
1.5 再次治療過程及預后 2019年6月18日起使用萬古霉素,停用泰能,因中性粒細胞數較低,予吉粒芬(重組人粒細胞刺激因子注射液)、地塞米松靜推,改善炎癥反應后,改為口服強的松并逐漸減少用量。6月27日再次行B超檢查,結果(圖3)示雙側腋窩淋巴結可見,余均未見明顯異常腫大淋巴結,后訴耦合劑接觸部位瘙癢,次日開始出現散在鮮紅色斑片樣皮疹,予地塞米松、尿囊素外涂。7月3日體溫平穩后,強的松減量至15 mg qd,7月6日起強的松減量至10 mg qd。出院診斷:剖宮產術后,產褥期發熱,HLH,剝脫性皮炎,肝血管瘤,脂肪肝。出院后建議血液內科門診隨訪,調整激素用量。3個月后電話隨訪,產婦一般情況較好,已恢復正常生活。

圖3 本病例2019年6月27日B超影像A: 左側腋窩淋巴結;B:右側腋窩淋巴結
2 討 論
HLH是一種嬰兒期綜合征,但也有大齡兒童和成人病例,與感染性、腫瘤性和自身免疫性疾病有關[3]。臨床上將HLH分為家族性(原發性)HLH和獲得性(繼發性)HLH,淋巴細胞細胞毒性方面的遺傳缺陷已被確認為原發性HLH的主要原因[4]。然而,HLH也可在正常細胞毒性的情況下發展,例如符合孟德爾遺傳的炎性小體活動紊亂也是引起HLH的原因[5]。而繼發性HLH占HLH的大部分,與已知的遺傳缺陷無關,其高炎癥狀態是由感染性、自身免疫性或腫瘤性條件觸發的。HLH最常見的感染性病因為病毒感染,如EB病毒(EBV)、巨細胞病毒和細小病毒等。
原發性HLH的發病機制一般為基因功能突變喪失,包括PRF1、UNC13D、Munc18-2、Rab27a、STX11、SH2D1A或BIRC4等基因突變,導致抗原提呈細胞的持續過度激活和失控的高炎癥狀態。高度炎癥伴隨著高水平的細胞因子,包括干擾素γ、IL-6、IL-10、IL-12和可溶性IL-2R等,從而導致一系列指標異常。繼發性HLH的機制尚不清楚。一個合理的假設是驅動HLH表型的T細胞和NK細胞功能障礙由病毒感染或惡性腫瘤的慢性抗原刺激引起。最好的例子是EBV相關的HLH,EBV潛伏膜蛋白(LMP1)干擾T細胞適配器蛋白,即信號轉導淋巴細胞激活分子相關蛋白,反過來導致T細胞過度激活和Th1細胞因子分泌[6]。隨著全外顯子組和全基因組測序的出現及在這一罕見疾病亞組中的應用,未來很可能會發現新的遺傳驅動因素和修飾因子[7]。
目前HLH的基本治療原則是結合免疫抑制和細胞毒治療來針對高炎癥狀態。HLH-2004方案[7]是目前公認的HLH治療方案,還有單克隆抗體治療[8]、造血干細胞治療等。曾有報道[1]稱利妥昔單抗可作為EBV相關HLH患者的搶救治療方案。Brito-zerón等[9]也認為,抗腫瘤壞死因子治療是有效果的。開始導向治療之前,HLH病死率約為95%,中位生存期為1~2個月[10]。對HLH診斷的不確定性嚴重影響其預后評估和治療決策。因此,早期識別和治療至關重要,緊急轉診到血液科和腫瘤科也至關重要。
本病例符合HLH診斷,但考慮患者先行抗生素治療后體溫下降,后發熱,IL-2R下降,不支持腫瘤相關或EBV相關HLH,故予地塞米松減輕炎癥反應。NGS示溶血性鏈球菌,故予萬古霉素對癥治療,后患者體溫恢復正常,血象正常,全身淋巴結恢復正常。本病例感染病原微生物,又處于妊娠分娩期這一特殊時期,機體免疫功能受到抑制,誘發HLH。但找到感染病原體后,采用有效的抗生素行病因治療,同時采用腎上腺皮質激素抑制過度的炎癥反應,最后治療成功。而且本病例骨髓、淋巴結未發現嗜血現象,從側面提示該病例病情不是最兇險的,所以未使用依托泊苷化學療法及化療藥物也獲得痊愈。
綜上所述,妊娠婦女出現不明原因肝功能異常、發熱、血細胞進行性下降, 排除惡性實體腫瘤、淋巴瘤、風濕免疫性疾病后應考慮HLH, 且應及時行相關檢查,明確病因,并積極治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