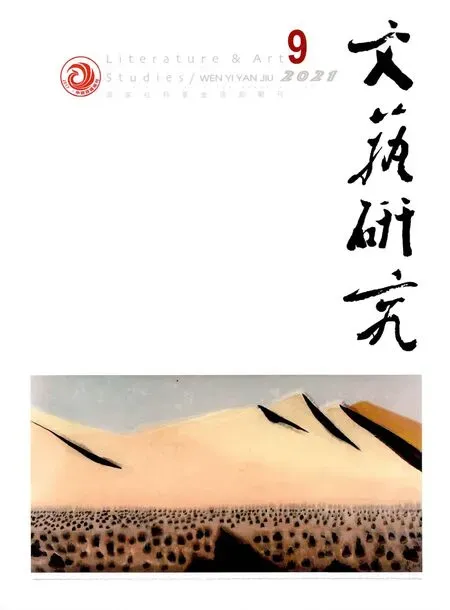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在新中國的確立與鞏固
張永清
一、問題的緣起
任何一門學科都有屬于自身的學科話語,但未必有屬于自身的學科話語體系。新中國成立以來,研究者們付出了諸多艱苦努力來構建文學理論,尤其是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的話語體系,著力凸顯其中國特色、中國風格、中國氣派。作為其中最基礎、最基本、最核心的問題之一,文學反映論在該體系構建中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整個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的建設與發展,在某種意義上,也是由反映論文藝觀的發展和應用所決定的反映論文藝觀的發展、變化、盛衰、得失,直接決定著中國現當代文藝理論的基本面貌與命運”①。
迄今為止,國內學界對文學反映論這一問題的重視程度、整體的研究狀況究竟如何?毋庸置疑,以周揚、朱光潛、蔡儀、以群、蔣孔陽、陳涌、陸梅林、程代熙、錢中文、童慶炳、王元驤、杜書瀛、董學文、朱立元等為代表的學者,以教科書、著作、論文、自述、訪談等形式,對文學反映論進行了多方面的深入思考與潛心研究,取得了令人矚目的累累碩果。他們有的側重于俯瞰反映論百年發展歷程中呈現出的總體問題,有的專注于探尋某一重要歷史時期發生的重大事件對反映論的關鍵影響,有的注重于探查某些重要人物在反映論發展過程中所發揮的核心作用,有的聚焦于反映論自身在某些方面存在的知識瓶頸,由此形成了問題切點迥然有別、各有側重的探索路徑②。上述概括可能掛一漏萬,但基本上有助于整體把握。
客觀而論,一段時期以來,文學反映論的整體研究狀況并不盡如人意。一些學者對此的批評切中肯綮。比如王元驤在21世紀初寫道:“現在學界對反映論文藝觀普遍地采取冷淡的態度,自以為棄之一旁、不予理睬,它就會自行消滅,我們的理論也從而就獲得新生,就會有新的創造。這想法未免顯得過于天真,甚至近乎自我蒙騙。”③十六年之后,他繼續寫道:“大家都覺得我國現在的文藝理論界比較浮躁,熱衷于追新逐異,對于一些重大的理論問題少有開展深入的探討,或往往熱了一陣子之后就不再有人問津,所以能真正解決問題和有理論建樹的成果微乎其微,對于反映論文藝觀的討論就是突出的一例。”④反映論在美學研究領域的命運也同樣如此。凌繼堯寫道:“新時期以來,常常有人對反映論有所詬病,把反映論說成是‘表征蘇聯模式的哲學符號’。我們認為,不能把美學研究運用反映論出現的偏頗和失誤歸咎于反映論本身。對于反映論,我們不能離開產生它的那些歷史條件來研究。”⑤不過,相當一部分學者甘愿為此付出畢生心血,比如王元驤就把自己六十年文藝理論研究的人生歷程簡括為“一條突破和超越傳統的反映論文藝觀的道路”⑥。
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的理論基石與方法論基礎自然是馬克思主義哲學。眾所周知,1949年以來,國內學界對馬克思主義哲學的理解與把握不盡相同:改革開放以前的三十年,它指的是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改革開放以后的四十年,除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一種意涵外,它還意指實踐唯物主義、實踐本體論、實踐的人道主義等。
一般而論,學界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視為馬克思主義哲學認識論抑或哲學反映論的同義語。與此相應,它是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的哲學根基與方法論基礎。在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思維與存在、基礎與上層建筑這兩大基本理論規范下,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形成了兩大基本理論命題:其一,文學藝術與科學一樣,都是認識現實、反映社會生活的特殊思想形式;其二,如果科學認識、科學反映是一種事實性、客觀性的認識、反映,那么文學藝術等對現實、社會生活的認識、反映則呈現出某種思想取向和某種價值立場,即哲學、文學等是屬于上層建筑的某一特殊意識形態。由這兩個基本理論命題還可進一步衍生出如下兩個論斷:首先,作為意識形態的哲學、法律等與作為意識形態的文學、美學等之間的區別,不在于所認識、反映的對象與內容的不同,而在于思維方式、表征形式上的不同,即前者主要是通過概念、推理、抽象等邏輯思維來完成對現實的認識、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以及對意識形態的表征,后者則主要是通過具體、可感、生動的藝術形象以及形象思維來達致對現實的再現、對社會生活的反映以及對意識形態的表征;其次,文學與繪畫、雕塑等其他藝術門類之間的區別,同樣不在于所認識、所反映對象或內容的不同,而在于各自媒介的不同,即文學不像繪畫、舞蹈、雕塑、建筑等藝術那樣可直接訴諸圖畫、形象,文學是語言的藝術,它主要是通過語言來描寫形象、塑造典型。換言之,馬克思主義哲學的兩大理論命題在文學領域推廣應用或具體轉換后,最終形成了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的三個基本論斷:文學是認識,認識即對社會生活的形象反映;文學是意識形態,文學是屬于上層建筑的一種特殊意識形態;文學是語言的藝術。上述命題、論斷可以凝練為一個極簡的表述:文學是以語言所描寫、塑造的藝術形象來認識現實、反映社會生活的特殊意識形態。
迄今為止,國內學界對“文學是語言的藝術”鮮有爭論,對“文學是意識形態”這一命題的討論也已較為充分,但對“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這一命題的相關討論尚顯薄弱。有鑒于此,本文擬從語境化與知識化雙重視角對“文學是社會生活的反映”進行總體審視。所謂“語境化”,就是從某一歷史時期的政治、經濟、文化等所構成的具體的整體中來審視相關問題的發生、發展、突變等的必然性緣由,進而把相關思想資源和理論淵源具體化、場景化、歷史化。所謂“知識化”,就是把現實中的諸多個別現象盡可能地予以征候化、問題化、譜系化,重點考察當時的現實需要與所給出的知識方案之間,即社會與思想、實踐與理論、問題與方法之間,產生了哪些共振,發生了哪些斷裂等。正如阿爾都塞所說:“為了認識一種思想的發展,必須在思想上同時了解這一思想產生和發展時所處的意識形態環境,必須揭示出這一思想的內在整體,即思想的總問題。要把所考察的思想的總問題同屬于意識形態環境的各思想的總問題聯系起來,從而斷定所考察的思想有什么特殊的差異性,也就是說,是否有新意義產生。當然,真實的歷史也在這一復雜過程中經常起作用。”⑦
基于語境化與知識化的雙重視角,筆者把新中國成立以來的文學反映論發展歷程概括為確立與鞏固(1949—1976)、反思與突破(1979—1999)以及綜合與超越(2000—2020)三大歷史時期,并在此基礎上對其存在的主要問題進行追本溯源式的剖析與探究。其中,從粉碎“四人幫”到十一屆三中全會召開前夕(1976年10月—1978年12月),這兩年處在“確立與鞏固”和“反思與突破”這兩大歷史時期之間,具有承上啟下的歷史性意義。在具體的論述過程中,本文擬以時間為脈絡,以基本問題為中心,以重點人物為節點,在語境化與知識化的交織、耦合、疏離、錯位等活動中,探尋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在1949—1978年的整體發展態勢,細察問題之間的深層轉換邏輯,反思其在發展過程中所面臨的主要困境。
無論從語境化還是從知識化方面看,蘇聯化(或稱“蘇聯模式”)不僅是確立與鞏固期不可忽視的重要因素,在某些階段甚至是文學反映論唯一合法的外來因素。由于文學反映論在這一時期深受蘇聯模式的深度塑造、深刻影響,我們在運用雙重視角探究文學反映論的過程中,就必須認真對待這一客觀情況,坦然面對這一無可爭辯的歷史事實。據此,本文以1958年為界,把1949—1976年這一歷史時期的文學反映論進一步細分為前期(1949—1957)與后期(1958—1976)兩個階段:前期為中蘇關系的“蜜月期”,后期為中蘇關系的裂痕—惡化—破裂期。
若從階段性特征和易于把握問題的理路等方面考慮,前期還可進一步細分為以蘇為師(1949—1953)、以蘇為鑒(1954—1957)兩個階段;后期還可進一步細分為激情躍進(1958—1960)、調整提高(1961—1965)、停滯不前(1966—1976)三個階段。
總體看來,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反映論在文學理論領域的一元性、指導性、引領性地位并非一蹴而就,而是走過了一條艱難、曲折的探索之路。換言之,文學反映論在前期經歷了由局部性、區域性到全局性、全域性的確立、鞏固,盡管這種確立還只是初步的,這種鞏固還只是基本的;文學反映論在后期得到了牢固確立、根本鞏固,盡管這種牢固性和根本性還附帶著那個時代不可避免的某種片面性和偏頗性。文學反映論在前期盡管發生了些許的中國化,但在全面學習蘇聯的時代氛圍中,其蘇聯化色彩十分濃厚;文學反映論在后期盡管十分自覺地突出了中國化并為此付出艱苦努力,但始終未能從根本上真正突破蘇聯模式,其蘇聯化色彩依然鮮明。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與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無疑受到了以季莫菲耶夫《文學原理》、畢達可夫《文藝學引論》等為代表的“蘇聯模式”的巨大影響,但它們確實是文學反映論在這一歷史時期“中國化”探索的典范之作。文學反映論在確立與鞏固期的相關探索,因而呈現出蘇聯化漸趨弱化、中國化逐步強化這樣一個發展態勢,體現出文學反映論話語體系建設中的某種理論自覺、文化自覺、民族自覺。
二、文學反映論的全面確立、基本鞏固
文學反映論在1949—1957年全面確立、基本鞏固的過程,其實就是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反映論的文學觀念被接受、被承認、被認同的過程。由于這段時期中蘇關系良好,反映論在文學領域的突出表現之一就是文學觀念、文學理論的蘇聯化,即蘇聯文論話語模式始終發揮著主導性作用。本文之所以格外強調“全面”與“基本”,是因為文學反映論盡管在新中國成立之前就已存在三十年,但始終只是局部性、初步性的存在;只有在新中國成立后,文學反映論才具有了全域性、總體性的存在、傳播、接受的可能性和現實性⑧。這種全域性、總體性特質經歷了一個較為艱辛的探索過程,主要通過“以蘇為師”與“以蘇為鑒”這兩種途徑來實現。
先來看“以蘇為師”階段(1949—1953)。“向蘇聯學習”其實是新中國成立前夕就已確立的大政方針⑨。新中國成立后,隨著《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1950年2月14日)的簽署,全社會掀起了“向蘇聯學習”的熱潮(1952年春);毛澤東在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國委員會第四次會議閉幕大會上(1953年2月7日)再次發出了“要學習蘇聯”的號召。對蘇聯的全面學習,范圍不僅涵蓋政治、經濟、軍事領域,而且涵蓋教育、文化、文藝等領域。比如,教育、文藝領域出臺的四大舉措,為文學反映論這一論題的全面確立、基本鞏固創造了必要的外部條件。舉措之一,頒布新《大學教學大綱草案》(1950年8月)。其中,文藝學教學大綱提出:“應用新觀點、新方法,有系統地研究文藝上的基本問題,建立正確的批評,并進一步指明文藝學及其文藝活動的方向和道路。”⑩大綱所說的“新觀點、新方法”指的是馬克思主義的哲學觀與方法論,即由斯大林1938年所闡發的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舉措之二,在高校、文藝界知識分子中開展思想改造運動(1951年9月—1952年9月)。這場運動對于清除舊思想,傳播馬克思列寧主義、毛澤東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導引作用。舉措之三,以《文藝報》為平臺,以呂熒等為主要批判對象,就《關于高等學校文藝學教學中的偏向問題》進行大討論(1951年11月—1952年4月)。這次大討論“批判了教學中的資產階級思想觀點,強調馬克思列寧主義思想在教學中的指導地位,強調理論聯系革命文藝創作和革命文藝運動的實際的重要性,樹立了馬克思列寧主義在教學中的指導地位,使文藝學教學產生了結構性的變化。之后,不少教師都努力運用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觀點來闡明文藝的性質、文藝的起源和發展、文藝的創作和批評等一系列文藝學的基本問題,使文藝學的教學有了很大變化”?。不僅如此,大討論還促使新中國成立前由西方引進或自編的相關文論教材等被停用、禁用,自此之后,西方文論話語在這一時期的文論話語格局中不再占有一席之地。舉措之四,對高等院系進行大規模調整(1952年秋—1953年底)。經過此次調整,新中國成立之前的英美教育體制被蘇聯教育體制取代。如果說教學大綱、思想改造運動、教學大討論等為文學理論的相關教學與研究劃定了必須恪守的范圍和邊界,具有不可逾越的學科強制性和規約性,那么院系調整等則為其提供了極為牢靠的組織性、機制性保障。
不過,上述四大舉措僅為文學反映論的全面確立、基本鞏固創造了必要的外在條件,而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觀念的傳播,還迫切需要一支高素質的專業人才隊伍和一批高水平的教科書、論著等內在條件的支撐。但出于各種各樣的原因,以群《文學底基礎知識》、齊鳴《文藝的基本問題》以及巴人的《文學初步》等,這些在當時影響較大的“本土”著作還遠遠不能滿足現實需要?。為解燃眉之急,國內學界對蘇聯哲學、美學、文學等方面的論著以及教科書的譯介、搬用乃至套用就成為了當時的必然之舉?。在所譯介的相關論著中,最具影響力的非季莫菲耶夫的《文學原理》莫屬。
值得注意的是,無論從理論資源的選擇還是文學觀念的接受看,“蘇聯”與“西方”這兩條道路在此期間呈現出一種典型的零和關系,即前者的“此長”與后者的“彼消”,最終結果就是新中國成立前的多元文學觀念逐漸被一元文學觀念即反映論文學觀所取代。換言之,文學觀念的蘇聯化昭示著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反映論在新中國的文學理論、文學批評與文學創作中的主導身份得到全面確立,其唯一者的地位得到基本鞏固。
再來看“以蘇為鑒”階段(1954—1957)的文學反映論。斯大林去世后,尤其是蘇共“二十大”之后,盡管中蘇兩國在一些問題上發生了爭執,產生了一些嫌隙,但整體上仍是友好、和諧的。這一時期國際或國內所發生的一些重大政治、社會事件對文學反映論產生了直接或間接的重要影響。比如,針對專業理論人才嚴重匱乏這一現狀,教育部于1954年聘請蘇聯專家畢達可夫、柯爾尊等來華講學,希望通過“文研班”這種組織化形式,以及面對面、規模化、現場化、專業化的授課方式,加快培養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人才的步伐,以期盡快擁有一支研究、講授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知識的專業人才隊伍?。相比較而言,畢達可夫及其講義《文藝學引論》產生的影響力更大。可見,對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等理論知識的獲取由個人自主轉變為集體授受,理論能力的培養、提高由自我選擇、個人自覺轉變為制度安排、國家導引。這不僅有助于文學反映論的確立與鞏固,也有助于馬克思主義文學理論人才隊伍的總體建設。
無論是譯自蘇聯學者撰寫的六種著作,還是國內學者編撰的七種文學理論著作,它們無一例外地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反映論作為其理論基石,并幾乎以相同的話語方式來闡述文學是認識現實、反映現實的特殊形式這一文學觀念?。比如,畢達可夫寫道:“關于存在與意識、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馬克思列寧主義學說,是解決這個問題的哲學根據。”“在文學里完滿地、全面地再現現實的問題,是文藝理論的根本問題之一。列寧的反映論,即有關人類認識的本質和規律的辯證唯物主義的學說,是科學地解答這個問題的根據。這個理論,提供了正確地理解和揭露通過文學或一般藝術認識現實的過程的科學標準。”?柯爾尊認為,列寧“創立了‘反映論’,創立了關于藝術的黨性的學說,關于在階級社會的民族文化中都有兩種文化的學說,以及關于批判地接受過去的文化遺產的學說”?。在畢達可夫等的影響下,鐘子翱、李樹謙等國內學者也做了大體相同的理論闡釋:“任何文學,都是反映一定歷史時期的社會生活,表達作者的思想感情的。”?“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認識論-反映論,從意識和存在的關系上,對于這個問題給予了徹底的、科學的解決。”?
此外,在意識形態與上層建筑的關系等問題的理解與把握上,國內學者的論著同樣深受當時蘇聯學者相關論爭及其觀點的影響:他們完全認同文學是一種特殊的社會意識形態這一論斷,但在文學是否必然屬于上層建筑這一問題上存在一定爭論。比如,冉欲達等認為文學既是意識形態也是上層建筑;劉衍文、蔣孔陽等則認為文學是意識形態但未必是上層建筑,堅持認為有的文學屬于上層建筑,有的文學則不屬于上層建筑,文學因而只具有上層建筑性?。
盡管蘇聯化是這一階段文學反映論的主色調,但其中國化色彩有所增強。并非所有學者皆亦步亦趨,乃至機械照搬、簡單套用蘇聯文論模式,部分學者在借鑒中有選擇,在接受中有創新,在對主要問題的闡釋過程中體現出一定的理論自覺性。這主要體現在以下四個方面。其一,對文學反映論哲學根基的闡釋重點有所不同。如果說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側重于辯證唯物主義之維,那么劉衍文的《文學概論》等則側重于歷史唯物主義之維。其二,以朱光潛、黃藥眠、蔣孔陽等為代表的少數學者在對文學反映論的論述過程中避免了多數學者存在的片面、機械、教條等傾向,持論相對公允?。其三,絕大多數學者較為自覺地把毛澤東有關哲學、文學方面的重要論述以及中國的文學作品等融入相關問題的論析,林煥平、劉衍文等在這方面有一定的代表性?。其四,在“雙百方針”的精神激勵下,劉衍文、李樹謙、蔣孔陽等比較重視對藝術力量、美學力量、美感形式在文學認識現實、反映生活中的作用和功能?。
毛澤東在《論十大關系》(1956)一文中論述“中國和外國的關系”時,明確反對學習蘇聯過程中盲目跟從、機械照搬等教條主義傾向,提倡要有分析、有批判地學習、借鑒?。但因時代氛圍和社會環境等諸多因素所限,有關文學反映論的多數論著還是不可避免地受到了教條主義的顯著影響,周揚對此問題有過明確論斷:“我們現在見到的蘇聯的教科書、一般的文藝理論書,資料豐富,但邏輯結構不太好,有的問題還沒有講清楚,又跳到另一個問題上去了。他們知識掌握得比我們多,但做學問的方法有缺點,條條羅列,條條之間沒有聯系,一般地講就是教條主義。”?在一些學者看來,蘇聯文論模式的教條主義缺陷在當時國內的相關論著中不僅未被有效克服,在某些情況下反而被擴大了?。
尤為可貴的是,朱光潛等極少數學者在這一階段就獨具慧眼地主張以“加法”的形式,即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的前提下,不再以認識論-反映論這一“單純”之眼來理解與把握美學、文學問題:“馬克思主義創始人是經常從生產觀點看文藝的。……從生產觀點去看文藝和單從反映論去看文藝,究竟有什么不同呢?單從反映論去看文藝,文藝只是一種認識過程,而從生產觀點去看文藝,文藝同時又是一種實踐的過程。辯證唯物主義是要把這兩個過程統一起來的。……因為依照馬克思主義把文藝作為生產實踐來看,美學就不能只是一種認識論了,就要包括藝術創造過程的研究了。”?朱光潛認為,不能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簡單等同于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反映論,同樣地,不能把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一理論圖譜中的文藝活動簡單等同于認識活動,它還可以被理解為一種生產活動、一種實踐活動。這就要求研究者不僅要從認識論、反映論觀點,而且也要從生產論、實踐論觀點來全面把握文藝問題。從這個意義上講,如果說美學、文學、藝術領域中的認識論、反映論是50年代的“時代強音”,那么其中的生產論、實踐論則是“空谷足音”?。
三、文學反映論的牢固確立、根本鞏固
如果說前期的“全面確立”意指確立的廣度,那么后期的“牢固確立”則意味著確立的深度;如果說前期的“基本鞏固”意味著鞏固依然有開掘與深化的空間,那么后期的“根本鞏固”則意味著它已獲得了無可撼動的“至尊”地位。文學反映論在后期所面臨的社會語境更為復雜,但在知識化方面卻簡單明了。為了更清晰地勾勒其中的變化,本文把后期進一步細分為激情躍進、調整提高、停滯不前三個階段。
1958—1960年是激情躍進階段。“大躍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不僅是“趕英超美”的經濟大躍進,也是激情四溢的學術大躍進,正如周揚所說:
一九五八年全國所卷起的一陣浮夸風、共產風和在知識界進行的所謂“拔白旗”的運動,也涉及了文藝界,使“左”的傾向又一度抬頭。我們在開展思想斗爭的時候,對一些文藝問題的解釋和處理,存在著簡單化、庸俗化的毛病,以致助長了理論上和創作上的公式化、概念化的傾向,產生了粗暴批評,損害了藝術民主。這個教訓是極為深刻的,我們應該引以為訓。?
受1958年“長波電臺”“聯合艦隊”等事件的影響,中蘇關系出現了明顯裂痕,蘇聯方面于1960年撤走援華專家的決定則使得雙方關系陷入了惡化狀態。為了應對與蘇聯在政治和意識形態等方面業已存在的巨大分歧與矛盾,我國隨即在經濟、文藝等各個領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其中包括弱化之前大力倡導的蘇聯化,強調堅定不移地走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發展道路。毛澤東于1958年提出了“革命的現實主義與革命的浪漫主義相結合”的創作方法(簡稱“兩結合”),孟繁華對此作了如下解讀:“無論‘兩結合’創作方法背后隱含了多么復雜的政治語義,有—點是相當清楚的,這就是它作為政治策略的—部分,雖然‘前無先例,后無成果’,卻承擔或完成了同蘇聯意識形態分歧后的表意形式,以它作為分界線,標示了中國與蘇聯文藝理論的疏離關系。它既諭示了中國重建獨立文化身份的決心,也在權宜之計中暴露了理論積累的不充分,它所有的資源從來也沒有離開過政治文化—步。”?中國人民大學文藝理論研究班(簡稱“人大文研班”)于1959年創辦,其絕大多數學員后來成長為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隊伍的骨干人才、學科領軍者?。又如,1960年的第三次文代會正式把毛澤東的“兩結合”確立為新中國社會主義文藝創作的最高準則,以取代第二次文代會所確立的、作為最高創作原則和批評準則的蘇聯社會主義現實主義。
在教育大革命、學術大躍進的時代激情驅策下,一批有關文學反映論的著作應運而生?。與前一階段相比,這些論著的哲學根基無一例外地堅持馬克思列寧主義的辯證唯物主義認識論-反映論,最顯著的變化莫過于闡釋重心存在著十分明顯的位移,即從蘇聯模式努力轉向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從而突出了毛澤東的理論貢獻。這種轉變主要體現在以下三個方面。
首先,從體例與結構看,這些著作以《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核心內容來組織和安排全書。比如,北京師范大學的《文藝理論教學大綱》和吉林大學等三院校的《文藝理論》均由“文藝的工農兵方向”“文藝如何為工農兵服務”等五講構成,兩者在結構與內容方面高度一致,區別僅限于個別章節的具體順序。再如,山東大學的《文藝學新論》(初版)和華中師范學院的《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初稿)均由“革命文藝在革命事業中的地位和作用”“文藝要為什么人服務”“文藝應該如何為工農兵服務”“馬克思主義文藝批評的任務和標準”等七章構成,兩者的論述對象完全一致,區別僅限于個別內容的具體組織。
其次,從對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毛澤東等著作的具體引證看,毛澤東的《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實踐論》《矛盾論》中的核心思想無可爭議地成為了這些著作的重要理論資源:“馬克思、恩格斯科學地解決了社會存在和社會意識、基礎與上層建筑的關系問題。這兩個問題的解決,給了文學科學以堅實的哲學基礎。”“列寧的反映論,對馬克思主義的文藝科學的發展有著非常重大的意義。”“斯大林在文藝科學方面的貢獻,是他在民族文化方面的論述。”?這些著作盡管強調上述理論命題,但是下述論斷才是它們的側重:“毛澤東同志以自己的天才著作《實踐論》《矛盾論》和《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和馬克思主義經典作家的哲學著作一起,奠定了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的哲學基礎。……毛澤東同志的《實踐論》準確地概述了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反映論,并且充實和發展了它的每一基本原理,以及馬克思列寧主義關于實踐在認識過程中的作用的原理,關于革命理論在革命實踐中的作用的原理。這一切,對于馬克思主義文藝科學的發展,有著極為重要的意義。”?“《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是《文藝理論》的中心教材。《關于正確處理人民內部矛盾的問題》《實踐論》《矛盾論》等文獻是指導本課學習的重要文獻。”?
再次,從對文學基本問題的闡發看,這些著作無一例外地把政治、階級、意識形態等置于認識論-反映論這一理論架構內,尤其把文藝為政治服務、文藝為階級斗爭服務等作為重中之重。文學是否屬于上層建筑這一問題,在前期的相關論著中還存在爭鳴與探索的空間,到了這一階段已成為不容置喙的定論。比如《文藝學新論》寫道:“有人認為:文藝觀點屬于上層建筑;而文藝本身只是社會意識形態,不屬于上層建筑。這是把社會意識和上層建筑、文藝和文藝觀點對立起來的錯誤觀點。……否認文藝屬于上層建筑,必然使文藝脫離經濟基礎,取消文藝的階級性和社會作用。這顯然是違背馬克思主義的一種十分有害的觀點。……文藝對基礎的反作用不是直接的,而是間接的,它必須通過政治才能反作用于基礎。”?
這些著作創立了一套既區別于英美文論話語也區別于蘇聯文論話語的新話語,即政策文論話語。誠如周揚所說:“編書不能離開黨的政策立場,就這點說,政策有決定作用。但是從另一方面說,教科書又與政策有區別。……教科書不能只講政策,要寫規律性的知識……教科書主要是要以規律性的知識武裝學生的頭腦,這同政策解釋、工作總結都不一樣。過去搬英美的理論,后來搬蘇聯的,后來又搬政策,這不行。”?在他給中央書記處呈送的報告中也明確寫道:“解放以后,大量采用了蘇聯的教材(有不少是來華專家編的),自己編寫的很少。一九五八年以后,教育革命,解放思想,青年人集體編了不少教材,出現了一種新氣象,但由于對舊遺產和老專家否定過多,青年人知識準備又很不足,加上當時一些浮夸作風,這批教材一般水平都低,大都不能繼續采用。”?一些學者極為中肯地指出了這些著作中存在的突出問題:“毛澤東文藝思想進入高校課堂是20世紀50年代后期文藝理論教材發展的重要標志。但是,由于我國1957年到60年代的特殊的政治環境,我國文藝學界沒有可能真正從學理上研究它,只強調其戰斗性,而忽略了其對理論的系統性和科學性的總結,這就是50年代后期文藝理論教材沒有長久流傳的原因。”?政策文論話語熱衷于以政治的宣示性、政策的圖解性、理論的戰斗性來取代思想的深刻性、論理的透徹性和學術的嚴謹性,最終導致某種程度上以政治取代學術、以生硬的政策圖解取代科學的文學闡釋。
1961—1965年是調整提高階段。為了克服“大躍進”運動給國民經濟所造成的嚴重困難,1961年初,八屆九中全會明確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高”八字方針。“科學十四條”“高教六十條”以及“文藝八條”等相繼出臺,正如周恩來所說:“三年來的工作中出現了一些毛病,需要調整、鞏固、充實、提高,精神生產方面也不例外,同樣需要規劃一下。”?1961年2月—1962年10月,周揚多次參加《文學概論》的編寫討論會,提出編寫工作的指導性意見:“先決問題是這本書講些什么,觀點就是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點、毛澤東文藝思想。我們這本教材要把毛澤東文藝思想貫穿在里面。毛主席的文藝思想是發展了的馬克思主義文藝觀點。”?之前創辦的“文研班”是文學理論人才隊伍建設方面的國家工程,而由以群主編的《文學的基本原理》和蔡儀主編的《文學概論》這兩部統編教科書則是文學理論著作建設方面的國家工程?;此前由國內學者編撰的文學理論教科書是編撰者的個人行為,而這兩部教科書的編撰則體現的是組織行為、國家意志,為文學反映論的牢固確立、根本鞏固提供了更加堅強的組織支撐、制度保障。此外,這一時期的社會氛圍較為寬松,一部分西方文論及其相關研究論著得以順利出版。俄蘇文論不再被視為唯一合法的外來思想資源,西方思想理論資源在有限時間內被有限地譯介、接受。
《文學的基本原理》《文學概論》這兩部著作與之前由蘇聯學者、國內學者編撰的相關論著一脈相承,始終把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反映論作為文學理論的哲學基石,始終秉持文學是一種認識、認識即以形象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觀念。比如《文學的基本原理》一書寫道:“馬克思列寧主義的反映論的基本原理,為我們正確地理解古往今來一切文學現象提供了一把鑰匙。”?再如《文學概論》一書寫道:“以形象反映社會生活的文學既是社會意識形態,也就是社會的上層建筑。”?毛澤東思想的重要性繼續得到凸顯。《文學的基本原理》“全書征引量最大的是毛澤東著作。全書注釋共引用毛澤東著作141次,占全書注釋總量的17.2%。以全書526頁計,平均每3.7頁就有一個毛澤東著作注釋出現。其中,《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的引用次數高達70次,占全書注釋總量的85%,為全書之最”?。
與之前的蘇聯文論話語、政策文論話語相比,《文學的基本原理》《文學概論》這兩部著作創立了一種“新”文論話語,即政治主導下的學術文論話語。它的“新”主要體現在體例結構、審美屬性、話語表述等方面,意味著對前兩種話語體系的某種突破和超越?。如果把這兩部著作與艾思奇在這一時期主編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1961)稍加對比,或許能更加清楚地把握各自領域的重要地位和理論貢獻。一些研究者對艾思奇主編《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作出了如下評價:
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中國版”正式誕生了。在此之前,盡管國內已出現一些哲學教科書,但都沒法取代蘇聯的教科書《馬克思主義哲學原理》的地位,現在,國產版的《辯證唯物主義歷史唯物主義》成為中國人對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最新理解和經典理解,以后的哲學教科書,盡管出現了幾百種,但大都沒能跳出它的套路。?
我們在此不妨把上述話語稍作修改,挪用到對這兩部著作的評價上:在體系編排基本方法的蘇聯模式化和體系基本內容及部分章節的中國化方面,如果說在此前的相關著作中還是發展趨勢,那么《文學的基本原理》《文學概論》則將其規范化和定型化;它們體現了中國學者對馬克思主義文學反映論的最新理解和經典理解,完全可以取代季莫菲耶夫的《文學原理》、畢達可夫的《文藝學引論》等蘇聯著作;在之后的很長時期內,絕大多數國內著作都未能跳出《文學的基本原理》《文學概論》所確立的理論范式與問題框架。
這兩部著作之所以能夠真正從學術上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的文學反映論中國化,真正從學理上突出毛澤東思想在馬克思列寧主義能動的、革命的、辯證的反映論中的理論貢獻,就在于撰寫者真正落實了周揚代表組織所提出的把馬克思主義、毛澤東思想貫穿始終、政治導向與學理探討有機融合的編寫原則。正如有學者所論:“周揚對教材編寫的指導原則大多都是符合文藝規律的,對文學理論教材編寫起了極大的促進和指導作用。……他當時的文學思想處于政治論的文藝學與認識論的文藝學之間,突出的還是文學反映論,反映論在上個世紀60年代初的歷史語境中就是中國文學思想所能達到的高度了。”?簡言之,《文學的基本原理》《文學概論》的問世,標志著馬克思主義的文學反映論在新中國得到了真正的牢固確立、根本鞏固。
無可回避的是,這兩部著作存在著諸如研究方法單一、對象特殊性被忽視等問題,并且,“政治性還是較突出,談文學藝術本身的規律太少,主要談論文藝與政治,文藝與社會的關系。……蔡儀把反映論理解得太狹窄,把反映論等同于認識論”?。但瑕不掩瑜,“這是歷史環境造成的,編寫者無法超越寫書的時代條件,我們不應苛求他們,指出缺陷的目的主要是為了總結歷史經驗”?。
1966—1976年是反映論的停滯不前階段。十年“文革”不僅對新中國的政治、經濟造成了巨大破壞,而且給文藝、文化、教育事業等帶來了巨大危害,文學反映論也不例外。在“極左”政治路線、思想路線、組織路線等的影響下,諸如“文藝黑線專政論”“三突出”等事件層出不窮。在這些阻滯性因素左右下,能動的、革命的、辯證的文學反映論淪為了機械的、庸俗的、片面的文學工具論,其豐富內涵被簡單化為對“極左”政治的單一圖解。若以最平和的語言來表述,文學反映論在十年“文革”中乏善可陳〔51〕。
綜上所述,無論從語境化還是從知識化視角看,蘇聯化、中國化是始終伴隨著確立與鞏固期文學反映論的兩種顯性存在。語境化具體體現為由倡導以蘇為師、以蘇為鑒向獨立自主、自力更生道路的轉變。知識化具體體現為由基本照搬蘇聯模式向努力構建《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模式轉換,受蘇聯化左右所形成的“三論模式”(本質論、作品論、發展論)轉向經中國化后所形成的“五論模式”(本質論、作品論、創作論、發展論、批評鑒賞論)。
還需要著重指出的是,確立與鞏固期的文學反映論自始至終把馬克思主義認識-反映論即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作為自身唯一的哲學根基與方法論基礎。不過,以朱光潛等為代表的少數學者堅持認為,在堅持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這一哲學前提下,在把文學、美學、藝術反映論看作其題中應有之義的基礎上,還可以從生產論、實踐論等角度探究文學、美學、藝術問題。因而,1949—1976年這一歷史階段雖然只存在一種馬克思主義哲學即辯證唯物主義與歷史唯物主義,但存在著文學反映論、文學生產論、文學實踐論等不同的理解方式與探究路徑,盡管前者始終居于絕對強勢地位,后者則始終處于絕對弱勢地位。順便提及,此種狀況在之后的兩個歷史階段得到了極大改變。
粉碎“四人幫”標志著十年“文革”的結束、新時期的開啟。一般認為,1976年10月至1978年12月是黨和國家工作“在徘徊中前進”的過渡時期。1977—1978年間,開新時期文學先河的《班主任》《傷痕》等作品陸續問世,學界展開了對“文藝黑線專政論”的批判,《毛澤東給陳毅同志談詩的一封信》(《人民日報》1977年12月31日,《詩刊》1978年第1期)的刊載乃至由此開啟的第二次形象思維大討論,以及圍繞文藝的真實性、典型、悲劇、莎士比亞化、席勒式等現實主義諸問題展開的相關討論等等,都十分有助于文學反映論在之后的創作、批評理論領域恢復其“本來面目”。1977年恢復高考,為文學反映論的進一步發展、深化等提供了人才保障,1978年圍繞真理標準問題的大討論更是為此后包括文學反映論問題在內的各種思想交鋒提供了以理服人的爭鳴典范。此外,《國外社會科學》《哲學譯叢》等刊物新啟了有關人道主義、異化、西方馬克思主義、東歐新馬克思主義、結構主義等文獻資料及其觀點的譯介工作。其中,在諸如《以色列學者談蘇聯一些學者反對反映論》《戰后的南斯拉夫哲學》《關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流派觀點和綜述》等相關譯介文獻里,對馬克思主義認識(反映)論的批判性立場與觀點已有所表露〔52〕。凡此種種無不表明,改革開放的時代大幕已緩緩拉起,多樣化的社會新格局正在孕育〔53〕。總之,過渡時期的文學反映論在其七十年發展歷程中具有承上啟下的重要意義。
① 朱立元:《對反映論藝術觀的歷史反思》,劉綱紀主編:《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第2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② 參見朱立元:《對反映論藝術觀的歷史反思》;劉鋒杰、尹傳蘭:《從“上層建筑”到“審美意識形態”——60年來文論教材中文學性質的再定義研究》,《文藝爭鳴》2013年第9期;夏中義:《蘇聯理論模式與中國學術重建——以當代文藝學學科的命運為例》,《學術月刊》2015年第3期;丁國旗:《列寧反映論與建國后我國文論的歷史緣分》,《山東社會科學》2015年第3期;汪正龍:《反映論:緣起、爭論與前景》,《安徽大學學報》2018年第6期。
③ 王元驤:《我所理解的反映論文藝觀——讀朱立元先生〈對反映論藝術觀的歷史反思〉所引發的一些思考》,劉綱紀主編:《馬克思主義美學研究》第3輯,廣西師范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
④ 王元驤:《論審美反映的實踐論視界》,《文學評論》2016年第3期。
⑤ 凌繼堯:《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哲學基礎》,《哲學研究》2017年第5期。
⑥ 王元驤:《文學原理》,浙江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309頁。
⑦ 路易·阿爾都塞:《保衛馬克思》,顧良譯,商務印書館2006年版,第57頁。
⑧ 比如蔡儀《新藝術論》一書堅持辯證唯物主義的認識論即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認為認識是現實的反映,藝術是一種認識的表現,藝術是現實的反映,藝術是現實的典型化(蔡儀:《新藝術論》,商務印書館1942年版)。
⑨1949年6月30日,毛澤東在《論人民民主專政——紀念中國共產黨二十八周年》一文中指出:“積四十年和二十八年的經驗,中國人不是倒向帝國主義一邊,就是倒向社會主義一邊,絕無例外。騎墻是不行的,第三條道路是沒有的。……在列寧和斯大林領導之下,他們不但會革命,也會建設。他們已經建設起來了一個偉大的光輝燦爛的社會主義國家。蘇聯共產黨就是我們的最好的先生,我們必須向他們學習。”《毛澤東選集》第四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473—1481頁。
⑩ 轉引自程正民、程凱:《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教學的歷史沿革》,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89頁。
? 程正民、程凱:《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教學的歷史沿革》,第105頁。
? 以群:《文學底基礎知識》,生活書店1949年版;齊鳴:《文藝的基本問題》,光明書局1950年版;巴人:《文學初步》,海燕書店1950年版。這三部著作的理論范式及問題框架基本取自維諾格拉多夫的《新文學教程》,比如以群《文學底基礎知識》被稱為“維諾格拉多夫《新文學教程》的中國版”。具體參見《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教學的歷史沿革》,第116—118頁。
? 當時出版的馬克思主義文學研究方面的論著、教科書主要有七種:葉高林:《斯大林與文藝》,水夫譯,海燕書店1950年版;蔡特林:《文藝學方法論》,任白濤譯,光明書店1950年版;蘇波列夫:《列寧的反映論與藝術》,朱譜萱譯,中華書局1951年版;阿拉伯莫維奇等:《文藝學教學大綱》,曲秉誠、蔣錫金譯,東北教育出版社1951年版;維諾格拉多夫:《新文學教程》,以群譯,新文藝出版社1952年版;季莫菲耶夫:《文學原理》,查良錚譯,平明出版社1953年版;《蘇聯文學藝術問題》,曹葆華等譯,人民出版社1953年版。
? 畢達可夫于1954年春至1955年夏在北京大學文藝理論研究班(簡稱“北大文研班”)講學,來自高校中文系的教師有霍松林、蔣孔陽、李樹謙、王文生、郝玉峰、呂慧娟等;柯爾尊于1956年夏至1958年夏在北京師范大學蘇聯文學研究班(簡稱“北師大文研班”)講學,來自高校中文系的教師有馬家駿、譚紹凱、雷成德、胡日佳、周樂群等。
? 馬克思主義文學、藝術、美學方面的主要譯著有六種:《蘇聯文學藝術論文集》第一、二集,《學習譯叢》編輯部譯,學習雜志社1955、1956年版;《美學與文藝問題論文集》,《學習譯叢》編輯部譯,學習雜志社1957年版;涅陀希文:《藝術概論》,楊成寅譯,朝花美術出版社1958年版;依·薩·畢達可夫:《文藝學引論》,北京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58年版;謝皮洛娃:《文藝學概論》,羅葉等譯,人民文學出版社1958年版;維·波·柯爾尊:《文藝學概論》,北京師范大學中文系外國文學教研組譯,高等教育出版社1959年版。若單從出版時間看,畢達可夫和柯爾尊的影響應在1958年之后,但實際情形卻是:由于他們倆先是課堂教學,之后才是課堂“講義”的出版,因此畢達可夫的影響力在1954年春就已產生,柯爾尊的影響力在1956年夏隨即發生,但其講稿的翻譯、出版略有滯后。國內學者在季莫菲耶夫、畢達可夫、柯爾尊等影響下編撰了七種主要論著:北京師范大學文藝理論組編:《文藝理論學習參考資料》,高等教育出版社1956年版;鐘子翱編:《文藝學概論》,北京師范大學出版社1957年版;霍松林編著:《文藝學概論》,陜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李樹謙、李景隆編著:《文學概論》,吉林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冉欲達、李承烈、康倪、孫嘉編著:《文藝學概論》,遼寧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劉衍文編著:《文學概論》,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版;蔣孔陽:《文學的基本知識》,中國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
? 依·薩·畢達可夫:《文藝學引論》,第20、40—41頁。
? 維·波·柯爾尊:《文藝學概論》,第6頁。
? 鐘子翱編:《文藝學概論》,第169頁。
? 李樹謙、李景隆編著:《文學概論》,第123頁。
? 參見冉欲達、李承烈、康倪、孫嘉編著:《文藝學概論》,第136—137頁;劉衍文編著:《文學概論》,第15頁;蔣孔陽:《文學的基本知識》,第14—18頁。
? 朱光潛認為,應持一種唯物的而非唯心的、辯證的而非機械的、總體的而非片面的馬克思主義認識論-反映論(詳見朱光潛:《美學怎樣才能既是唯物的又是辯證的——評蔡儀同志的美學觀點》,《人民日報》1956年12月25日);黃藥眠強調,應注重對創作過程中創作主體的體驗、情感和想象等作用的探討(詳見:《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教學的歷史沿革》,第152頁);蔣孔陽提出,不能把反映過程簡單化、機械化,反映中有選擇、有創造;不能把認識過程事實化,認識中有評價(詳見蔣孔陽:《論文學藝術的特征》,新文藝出版社1957年版,第40—41頁)。
? 林煥平的《文學概論》沒有像其他著作那樣,沿襲季莫菲耶夫、畢達可夫著作的體例、結構,而是突出了毛澤東文藝思想的重要性(林煥平:《文學概論》,廣西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3—6、213頁)。劉衍文在其《文學概論》的《后記》中寫道:“必須要多用我國的文學名著來做例證,以克服言必稱希臘羅馬而竟忘記自己老祖宗的偏向。”(劉衍文:《文學概論》,第267—268頁)
? 分別見劉衍文編著:《文學概論》,第19—20頁;李樹謙、李景隆編著:《文學概論》,第28頁;蔣孔陽:《文學的基本知識》,第14—18頁。
? 毛澤東:《論十大關系》,《毛澤東選集》第五卷,人民出版社1977年版,第288頁。
? 周揚:《在文科教材政治、哲學組匯報會上的講話》(1962年3月16日),《周揚文集》第四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1年版,第135頁。
? 程正民、程凱認為,教條主義下的蘇聯文論模式存在著四個方面突出問題:內容的哲學化和政治化,思維方式的簡單化,理論自身的狹窄化,以及研究方法的單一化(《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教學的歷史沿革》,第130—134頁)。
? 朱光潛:《論美是主客觀的統一》,《哲學研究》1957年第4期。
? 朱光潛:《生產勞動與人對世界的藝術掌握——馬克思主義美學的實踐觀點》,《新建設》1960年第4期。
? 周揚:《繼往開來 繁榮社會主義新時期的文藝》,《周揚文集》第五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177頁。
? 孟繁華:《中國20世紀文藝學學術史》第三部,上海文藝出版社2001年版,第180頁。
? 與“北大文研班”“北師大文研班”相比,“人大文研班”的授課專家完全立足國內,主要有余冠英、游國恩、何其芳、錢鍾書、羅念生、蔡儀、朱光潛、宗白華、李澤厚、王朝聞、周揚、林默涵、邵荃麟等。“人大文研班”前后舉辦了三期(1959—1961),總計培養了107名學員:第一期有王春元、繆俊杰、譚霈生等36人,第二期有張錫厚、李思孝、騰云等39人,第三期有李衍柱、潘必新、邊平恕等32人。此外,1962年還舉辦了人大文藝理論進修班,共招收邢煦寰、黃世瑜、王先霈等45人。參見《中國現代文學理論知識體系的建構:文學理論教材與教學的歷史沿革》,第161—170頁。
? 其中五種具有相當的代表性:北京師范大學編:《文藝理論教學大綱》(修訂稿),北京師范大學1958年編印;吉林大學、吉林師范大學、哈爾濱師范學院編:《文藝理論》上下,吉林師范大學函授教育處出版1958年版;湖南師范學院中國語言文學系文藝理論教研組編:《文藝理論》上,湖南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山東大學中國語言文學系文藝理論教研組編著:《文藝學新論》,山東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編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華中師院出版社1959年版。
?? 華中師范學院中文系編著:《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第5、13、17頁,第33—34頁。
? 吉林大學、吉林師范大學、哈爾濱師范院校編:《文藝理論》上,第1頁。
? 山東大學中文系文藝理論教研室編著:《文藝學新論》(修訂本)上冊,山東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6—7頁。
? 周揚:《關于〈教育學〉編寫工作的談話》(1961年8月16至18日),《周揚文集》第四卷,第72頁。
? 周揚:《關于高等學校文科教材編選情況和今后工作意見的報告》(1962年5月5日),《周揚文集》第四卷,第143頁。
? 毛慶耆、董學文、楊福生:《中國文藝理論百年教程》,廣東高等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204—205頁。
? 周恩來:《在文藝工作座談會和故事片創作會議上的講話》,《周恩來論文藝》,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第86頁。
? 周揚:《對編寫〈文學概論〉的意見》(1961年2月至1962年10月),《周揚文集》第三卷,人民文學出版社1990年版,第227—228頁。
? 《文學的基本原理》的編撰工作始于1961年5月,1963年2月出版上冊,1964年8月出版下冊,1978年被確定為高校文科教材,1979年出修訂版,1980年把上下兩冊合并印行。《文學概論》的編撰工作同樣始于1961年5月,1963年形成討論稿,但在當時未能出版,1978年修訂并被確定為高校文科教材,人民文學出版社1979年版。
? 以群主編:《文學的基本原理》下冊,作家出版社1964年版,第14頁。
? 蔡儀主編:《文學概論》,《蔡儀文集》第8卷,中國文聯出版社2002年版,第131頁。
? 支宇:《對以群主編〈文學的基本原理〉(1964年版)的社會學反思》,《文藝研究》2008年第9期。
? 毛慶耆等認為,這兩部著作打破了蘇聯教科書原有的“三論”即本質論、作品論、發展論的結構模式,形成了“五論”即本質論、作品論、創作論、發展論、批評鑒賞論的結構模式,它們對文學的審美屬性進行了比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它們在表達方式上是中國化的(參見毛慶耆、董學文、楊福生:《中國文藝理論百年教程》,第209—214頁)。
? 張秀琴:《走出與回歸——中國馬克思主義哲學體系的演化邏輯》,《四川師范大學學報》2001年第9期。
? 童慶炳主編:《20世紀中國馬克思主義文藝理論研究》,北京大學出版社2012年版,第426頁。
? 李世濤:《楊晦、周揚與文學理論教材建設——胡經之先生訪談錄》,《云夢學刊》2006年第3期。
? 劉夢溪:《十一論馬克思主義文藝學的發展問題——評五、六十年代流行的幾種文藝學教科書》,《學習與探索》1985年第6期。
〔51〕 這一時期已經難以就學術問題展開正常的學術討論,比如鄭季翹認為,形象思維論是反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體系(鄭季翹:《文藝領域里必須堅持馬克思主義的認識論——對形象思維論的批判》,《紅旗》1966年第5期)。此外,中蘇關系在這一階段處于全面破裂狀態,兩國之間甚至發生了“珍寶島事件”這樣的局部武裝沖突。
〔52〕 自信摘譯:《以色列學者談蘇聯一些學者反對反映論》,《國外社會科學》1978年第6期。M.施瓦爾茨:《戰后的南斯拉夫哲學》,《哲學譯叢》1978年第1期;徐崇溫:《關于西方的“馬克思主義研究”——流派觀點和綜述》,《國外社會科學》1978年第5期。
〔53〕 《哲學譯叢》1978年第5、6期刊載了T.A.哈薩羅娃《結構主義》、皮亞瑞《結構主義與哲學》、W.M.利奧格蘭德《對“青年馬克思”爭論的考察》、福格列爾《法蘭克福哲學-社會學學派基本思想的歷史發展》以及馬爾庫塞《當代工業社會的攻擊性》的譯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