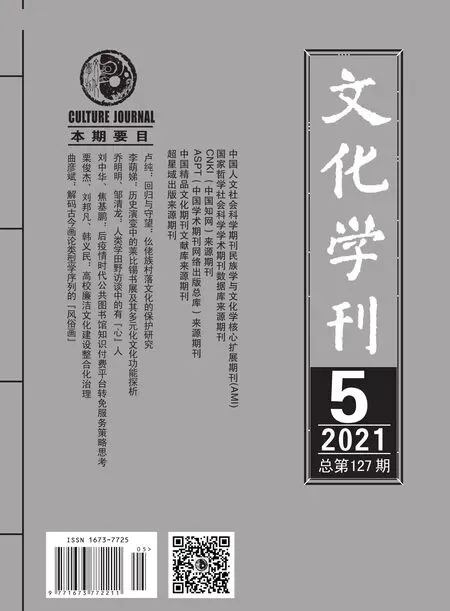獨特的自然觀對日本色彩文化的影響
白雪嬌 王悅悅
日本以溫帶和亞熱帶季風氣候為主,夏季炎熱多雨,冬季寒冷干燥,四季分明。日本是一個島國,四面環海,并且地處環太平洋火山地震帶,火山、地震活動頻繁,由地震引發的海嘯也高頻出現。在這樣極其不穩定的自然環境中,日本人逐漸形成獨特的自然觀,并對其色彩文化的構建產生了重要影響。
一、日本人的自然觀
寺田寅彥是夏目漱石的愛徒之一,在夏目漱石的作品《三四郎》中作為原型出現。寺田寅彥的杰作之一,就是《日本人的自然觀》這篇論文。在這部作品中,寺田寅彥提出日本的自然環境與西歐的自然環境是完全不同的。寺田寅彥曾在歐洲留學,因此,對歐洲特別是西歐的自然環境方面有諸多體驗感受。
就個人體驗來說,西歐的自然環境呈現一種十分穩定的特征。沒有地震、臺風、洪水、海嘯,自然災害發生的頻率低。因此,西歐國家的人們有機會在穩定的環境中探究并掌握自然界的構造,能夠理解、計算出相關的精確數據,進而能夠創造出合理控制和管理自然的方法。正是基于這一點,西歐的自然科學才得以誕生。進一步說,因為西歐自然環境天然的穩定性,近代西歐人才能夠征服自然。
與此相對,日本的自然則十分不穩定。地震、臺風、海嘯、洪水等自然災害頻繁發生,并且這種不穩定的狀況持續了幾千年。于是,日本人逐漸以自然為師,靈活地生活,塑造與自然和諧相處的生活態度,不斷積累生活智慧[1]。
二、從自然感受中誕生的“自然無常觀”
在對自然探索中,日本人了解到自然的兩面性。一方面,自然有其包容性;另一方面,自然有其嚴酷性。在這兩種特質所帶來的作用的沖擊下,日本人產生了“無常”的觀念。自然的無常是永遠橫亙在日本人心中的憂傷情結之源[2]。
有趣的是,日本人在自然中感受到的悲傷最終仍在自然中尋求治愈,并且是在孤獨、寂寥、哀傷、蕭條的環境情調中自我療愈。日本文化有三大審美意識——物哀、幽玄、侘寂:物哀是在靜默中由自然聯系到抒發人生無常的哀感;幽玄是追求自然中將物哀的官能之美提升至深奧、禪意、縹緲空寂的境界;侘寂是蒼涼、寂寥、歲月流逝的殘缺之美。三者共同點便是于自然中體味人生之“哀”與“美”。當日本人陷于悲傷的情緒中時不會尋求光明與希望,以正面積極的力量推動自身,而是尋求與自然共處悲傷的情境來治愈內心。因為悲傷是包容的、普遍的、永恒的情感力量。
寺田寅彥提出了自然信仰的觀念。即日本人看到的自然,并不是單純地認為是物質上的自然,而是通過種各種途徑與自然進行精神交流,進而深入了解自然,了解自己的內心世界[3]。在感知自然的過程中,日本人會以豐富多樣的表現形式反饋感知成果,諸如文學、繪畫、服裝、建筑、飲食以及色彩文化。
三、現代日本人自然理念——“野外文化”
日本人自古以來熱愛自然,敬畏自然,追求自然之美。在現代日本,甚至提出了“野外文化”這一概念。其中,“野外”不是指純粹的室內、室外的區別,而是指人類與自然共同生活的野性世界。一般意義上的文化具有傳統內質,可以分為外在物質文化和內在精神文化。從文化形成的動力出發,則可將其分為內源社會表層文化和外源環境基層文化。諸如音樂、美術、文學等文化體現于社會群體,具有流動性,為表層文化,這些是由人類共同的感性所培養并不斷發展的;衣食住行、語言、風俗習慣等基層文化,則是在經營社會生活、順應自然環境過程中形成的,具有很強的地域性及傳承性[4]。
日本人自古以來一邊順應自然生活,一邊不斷努力創造適合自己的環境,在長期發展中形成了緊密穩定的融合,現代日本人甚至要求社會成員以必要的基本行為和心理狀態去感知、了解自然。
由此可推知,日本人在長期與自然共生的經驗中,將“自然”劃分為兩層:一層是無人工雕琢的“大自然”,另一層是為了某種目的持續發展的“小自然”。“大自然”為“小自然”的誕生提供環境背景,“小自然”則是順應“大自然”的結果。從古至今,日本不斷地將“小自然”與“大自然”進行細膩巧妙的融合,達到人與自然共生一體的境界。
四、自然觀對日本色
(一)傳統色彩文化
日本人一直保持高度敏感的狀態去感知自然,與自然交流。在了解植物特征和名字之后,人們會對顏色命名。一片葉子、一朵花或果實的顏色特征都會展現出循環變化的四季之美。柳樹最美的時候是抽出了水靈靈的嫩芽之時,其顏色被稱為“柳色”,是春天的傳統色。盛夏在陽光沐浴下茁壯成長的青竹的翠綠色被稱為“青竹色”,單從顏色名便可以感受到其頑強的生命力。秋意漸濃,銀杏的樹葉變黃,楓葉也由綠轉紅,漸至枯黃,這些樹葉呈現出的暗淡的黃色被稱為“黃朽葉”,作為染色界的一色,頗受平安貴族們的喜愛。四季變遷傳達的不只是時間的流逝,同樣也表達自然之美、詩情畫意。自然使日本人磨礪出各種微妙柔婉的感情,培養出諸多復雜的文化。當季節更替,日本人感受到伴隨自然變遷而出現的美麗景象,將自然的色彩轉移到個體身上,由此發展出了獨特的日本傳統色彩文化,創造了豐富的色彩美學世界。如平安時代“十二單”的面料顏色和襯料顏色是根據四季植物、自然風景命名,并從季節、特定場合、性別、年齡等因素出發制定了詳細的配色原則。貴族們在此基礎之上適度調節顏色的濃淡,以此表現自己顏色的品位[5]。《枕草子》中有一段便記錄了女官們討論哪種顏色的衣服更加高雅。并且,在當時給意中人贈送和歌時會注重包裝用的薄紙和書寫紙顏色的搭配。例如經常使用的由紫藤花命名的“藤色”,多為高貴的紫色,也有白色和藍色。
黎明時東方天空的顏色被命名為“東云色”,這是江戶時代出現的顏色名。清少納言《枕草子》中寫道:“春天是破曉的時候‘最好’。漸漸發白的山頂,有點亮了起來,紫色的云彩微細地橫在那里,這是很有意思的。”[6]描寫的便是東云色的天空。
(二)日本人的色彩創新
日本人從對自然細致多感的觀察中感受季節更迭,個人或者群體都與自然緊密連接。在這樣的歷史中,人們辨識色彩之間的微妙差別,形成了獨樹一幟的色彩感知能力,能夠從萬千色彩中體會到不同的情感。
江戶時代色彩美學出現了重要的內容,即各種茶色系、鼠色系的顏色,總稱為“四十八茶百鼠”,用以表示其顏色變化豐富多樣。江戶時代中期,日本社會出現“富商”階層,百姓生活日漸富裕,對服飾有了更高的追求。但幕府為了增加國家財政的收入,要求百姓生活節儉,因此,陸續頒布了“奢侈禁止令”。禁令中對服裝的面料、質地、顏色做出嚴格規定——庶民只能穿由麻布或者棉布制成的衣服,顏色只能使用“許色”,即茶色、鼠色、藍色中的一種[7]。由此,百姓享受色彩鮮艷和圖案華麗的服飾的權利被剝奪。但平民百姓特別是富商階級并沒有限制自己對色彩的追求,他們憑借非凡的創造力和細膩的技術,使原本灰暗的茶色、鼠色變成了“瀟灑的顏色”,這種創造體現了一種返璞歸真的審美情致[8]。
江戶時代市民文化得到極大發展,歌舞伎成為市民文化中一項規模很大的娛樂活動。歌舞伎演員喜好的顏色稱為“役者色”,百姓會將喜愛的演員身著的顏色也穿在自己的身上,因此“役者色”成為了平安時代獨特的風尚。
諸如“團十郎茶”,是一種深紅色系的顏色,由澀柿果和牟柄(1)一種紅色顏料。制成。江戶初期的初代市川團十郎十分喜愛這種顏色,也是市川家荒事(2)日本傳統戲劇歌舞伎的一種角色,通常由成年男子扮演具有超人力量的正義勇者。表演的代表性劇目“暫”的服飾顏色。因此,“團十郎茶”可以說是團十郎家的象征色。再如“璃寬茶”,是一種深茶色,是江戶時代后期演員嵐吉三郎喜歡的舞臺服飾的顏色,“璃寬”是其俳號[9]158。而“媚茶”,名字來源于“昆布”(海帶),意為“像海帶一樣的茶色”。因日本方言中“昆布”的發音konbu接近kobi,也就是“媚”,因此后來稱為“媚茶”色[9]160。
除了茶色、鼠色,“一斤染”也允許庶民使用。“一斤染”是使用兩個人的和服用料制成一匹布,大約只有600克,因此,染出來的衣服非常淡。只要顏色比禁止使用的“禁色”淡,就都可以穿。因細膩的日本人在此基礎之上不斷調整濃淡比例,調制出許多新的顏色,如比櫻色暗淡一些的“灰櫻”,江戶時期被稱為“櫻鼠”[9]44。
五、結語
日本人順應自然,追求與自然和諧相處,但無常的自然正如無常的人生,永遠橫亙在日本人心中,成為憂傷的根結。日本人在意自然變化與自然之美,在體味自然的過程中漸漸形成了獨特的日本色彩文化并不斷創新。這是日本人獨特的觀念——承受自然帶來的傷痛,又以自然的力量治愈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