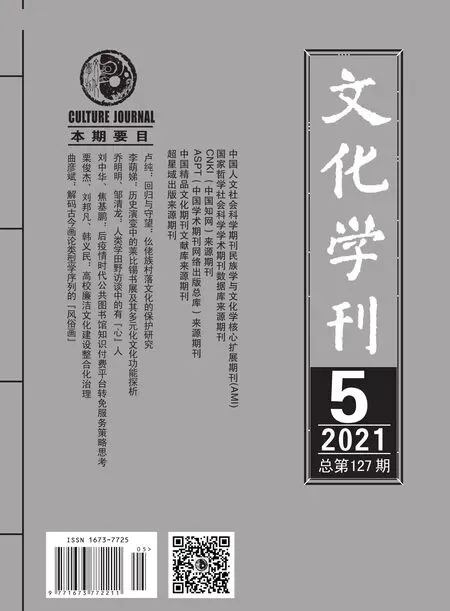論《我的帝王生涯》的敘事策略
胡仟慧
新歷史主義起源于20世紀80年代的英美文學界。美國學者史蒂芬·格林布拉在20世紀70年代就率先提出了“新歷史主義”的概念。新歷史主義主張歷史不是固定的,是生成的,文學沒有“背景”和“前景”之分,需將歷史研究帶入文學中。新歷史主義打破了傳統的歷史與文學之間的界限,是對形式主義、結構主義的反駁。新歷史主義作為一種不同于舊歷史主義的新的批評方式,因闡釋文學文本歷史內涵的獨特性而被認可和推崇,后成為文學批評的一種主要趨勢。中國的文學思潮受到西方的影響,在20世紀80年代后期,出現了新歷史小說的寫作潮流。新歷史小說不同于傳統的歷史小說,一改歷史寫實的特點,以虛構歷史的方式重寫歷史。但新歷史小說并不是歷史虛無主義,是對歷史以全新視角進行重新審視和書寫。代表作品如陳忠實的《白鹿原》、莫言的《紅高粱》、蘇童的《我的帝王生涯》。新歷史小說的寫作者,以轉型之后的先鋒小說作家和試圖拓展題材的新寫實小說作家為主,表達了他們關注歷史,希望用全新方式演繹歷史并借此完成他們寫作技巧轉變的意圖。
蘇童最初因為先鋒文學的創作而出名。《1934年的逃亡》和《罌粟之家》的發表,引起文壇注意,使他成為先鋒小說的領軍人之一。除了重視敘述視角的轉換、作品的神秘感等現代敘事技巧實驗,他也十分看重小說里“古典”的故事性,目的是保證故事的可讀性和流暢性。他后來創作的《妻妾成群》和《紅粉》關注“意象”的經營,注重對悲劇氛圍的營造和對女性細膩心理的刻畫,實驗性已明顯削弱,而被認為有“新寫實”小說和“新歷史”小說的色彩。再之后,他創作的《我的帝王生涯》用近乎魔幻和荒誕的筆法敘述了皇子端白的帝王生涯,被看作新歷史小說代表作。作為新歷史主義觀念影響下的產物,《我的帝王生涯》顛覆了傳統的歷史敘事方式,又借鑒了傳奇小說的寫法以及古典詩境的營造方法,增強了文本的可讀性。不可忽視的是,蘇童小說在敘事方面的安排不同以往,足以抓住讀者眼球。本文通過對《我的帝王生涯》的敘事模式、敘述視角和敘事結構等方面進行分析研究,探討蘇童在《我的帝王生涯》中所運用的敘事策略。
一、虛構歷史的敘事模式
《我的帝王生涯》以歷史為背景,用虛構歷史的方式來重新解讀歷史。“敘事文學用話語來虛構藝術世界。……這個話語的世界雖不等于現實本身,但卻能在更本質的層次上揭示社會現實的內在意義。”[1]23蘇童的小說多從歷史中取材,但歷史到了他筆下被虛幻化了,只保留了一點殘片。他曾坦言:“《我的帝王生涯》是我隨意搭建的宮廷,是我按自己喜歡的配方勾兌的歷史故事,年代總是處于不祥狀態,人物似真似幻,一個不該做皇帝的人做了皇帝,一個做皇帝的人最終又成了雜耍藝人,我迷戀于人物峰回路轉的命運,只是因為我常常為人生無常歷史無情所驚懾。”[2]這樣隨意搭建的方式,巧妙嘲諷了歷史的客觀性和規律性。
蘇童虛構了一個國家——燮國,懵懂的皇子端白在皇甫夫人的陰謀操縱下成了皇帝。本無意為王的端白完全不理朝政,即使是外寇侵犯,也只是平淡地交由皇甫夫人處理。在見過了宮中爭斗和血腥場面后,端白變得暴力嗜血、殺戮無常。后來真相大白,這一切不過是皇甫夫人與男人們開的一個玩笑,讓端白成為假燮王,只是為了更好控制從而主宰燮國。皇甫夫人死后,端白的昏庸無道還是迎來了燮國的末日。一代帝王淪落民間,成了“走索王”,最終選擇了歸隱和出家,實在令人啼笑皆非。在這樣一個虛構的歷史背景下,通過對歷史細化、縮小化書寫的方式,使讀者仿佛親歷歷史,又猜不透歷史的發展方向,激發了讀者的閱讀興趣,將歷史的風云變幻、捉摸不定的特點用虛構的方式呈現,道出了世事無常和人世荒涼。
二、內聚焦敘述視角
“‘內聚焦’的特點是敘述者只敘述某個人知道的情況,即從某個人的單一角度講述故事。內聚焦敘述的作品往往采用第一人稱敘述,敘述者通常是故事的一個角色。”[1]31內聚焦敘述方式有兩個主要特點:一方面,這個人物既是事件的參與者又是故事的講述者,把親身經歷的事件敘述給讀者聽,可以拉近文本與讀者的距離,也利于讀者理解故事內容;另一方面,雖然人物的敘述視角受到限制,只能講述他所知道的局限性部分,不如全知敘述那樣全面,但這種限制使敘述更加主觀,反而可以讓讀者仿佛身臨其境,體會其中逼真的故事情節。有些敘事作品以主觀心理描寫為主,往往會選擇這種敘述方式,可以起到透視人物的心理變化過程的作用。
在這個故事中,以第一人稱的內聚焦視角進行敘述。“我”意料之外地繼承了皇位。“我”本來作為故事的參與者,甚至是第一人稱視角,卻有種置身事外的感覺。“我”雖是最高統治者,其實不過是皇甫夫人手中的一枚棋子,無法掌控自己的命運。在“我”的帝王生涯中,我親身經歷了宮中暗斗、權利爭奪、外寇入侵、民生艱苦、后宮爭寵、民眾起義、戰爭紛亂、國家滅亡等一系列事件,卻始終用一種冷靜旁觀的態度來看待,最后選擇了隱逸山林,出家為僧。這些都應驗了僧人覺空的那句話:少年為王是你的造化,也是你的不幸。作者通過描繪一代帝王的心靈史,向我們再現了真實的宮廷生活和民間生活。這時,歷史不再是遙遠而神秘的事,是敘述者所處的環境,一下就拉近了讀者與歷史的距離,讓讀者能夠親近歷史。他虛構的這段歷史能在真實發生的歷史中找到類似案例,但那通常都是以史書記載的文字形式呈現,以內聚焦的敘述視角演繹出來,更加逼真而震撼人心。
三、災難和死亡的書寫
蘇童和其他的先鋒派作家余華、馬原一樣,熱衷于災難、血腥、死亡等的書寫。余華的《現實一種》,用一種近乎冷靜的筆調描寫親人間的相互殘殺,血腥、暴力與死亡充斥著文本。即使是他后期轉型的用溫和筆調書寫的《活著》,主人公徐福貴仍沒能擺脫苦難的厄運,還要悲痛面對身邊親人接連死去,只剩一頭老黃牛與他相依為命的命運。在這里面,死亡用以拷問人對苦難的承受能力和人為什么活著的永恒精神難題。
蘇童也偏愛書寫死亡和災難的敘事策略。苦難和歡樂在故事中交融,苦難的演變折射出人生的動蕩和起伏。毒與蜜、水與火的交錯統一完美呈現了人生的另一種形態。在小說中,死亡的重復發生,不僅能給人物以強大的心靈沖擊,還能給讀者造成巨大的震撼。端白作為燮王,卻總是重復著老宮役孫信那句不詳的咒語:“夜深了,燮國的災難也要降臨了。”文中處處散發著死亡的氣息,楊夫人公開揭露遺詔的騙局,卻被殘忍賜死,成為先王的殉葬品;楊松英勇報國,率領驃騎兵去鳳凰關援陣,在戰爭中受傷,被燮王下旨射殺;郭象兵敗紅泥河后,在京城城門口引咎自刎;祭天會首領李義芝被擒,被用十一種空前絕后的極刑處罰;弱小可憐的燕郎在彭國軍隊大肆進攻燮國的動亂中被殘忍殺害,以死來完成他對主人端白的忠心追尋。在免不了的災難中,死亡或許是解脫苦難最好的方式。死亡作為“災難”一種典型形態,把“人置于極端性的生存境界中進行冷酷的審視”[3],從而“檢測人性的畸變和生命的沉淪”[3]。端白多次夢見白色小鬼,表明他在目睹死亡場景之后內心的恐懼。這恐懼背后是無窮無盡的孤獨和悲涼。端白目睹死亡、制造死亡,卻又害怕死亡,足以顯示出人性深處的罪惡和荒涼。
四、換位的敘事結構
換位有兩種情況:第一種,兩個人在事態發展過程中逐漸演變,個體身份不變,但在進行著對方原有的生活狀態;第二種,故事里的兩個人互換身份,在對方的位置上體會在此身份下所能得到的經驗和具有的人生體驗。換位作為敘事中一條重要的情節鏈,加以體會,讀者便能進而明白作者的構思巧妙之處和所蘊含的深層寓意。
文中,“我”對歷代皇帝出巡時可能發生的危險既好奇又害怕,為了防止類似事件發生在“我”身上,“我”和燕郎玩兒了個換裝游戲。“我”讓燕郎穿上“我”的金冠龍袍騎在馬上溜圈。然而,穿上龍袍的燕郎仿佛就是皇帝,百姓對他行跪拜之禮,他也享受著做燮王的快樂。“我”對這次的換裝游戲非常不滿意,因為“我”和燕郎的衣服交換后,好似身份也互換了——“我”成了宦官,燕郎成了皇帝。身份是地位的一種象征,失去能證明身份之物后,人與人之間并無區別。蘇童這樣安排是想說明,在某種情況下,尊貴的帝王與平凡的百姓之間并無多大差距。這樣一下就把帝王拉下了神壇,和普通人無異,現出了真實面目。這只是個暫時的換位,以交換衣服的形式進行。其實文中有一條更深刻的換位線索,也就是端白因為皇甫夫人修改了遺詔代替了本該屬于端文的帝王之位。相當于端白代替端文體驗了帝王生活,體驗了本不屬于端白的經歷。端文在“池州之戰”勝利后攻占皇城,這才結束了端白二十多年的帝王生涯。也就是這時,兩人的換位才結束。蘇童啟示我們,歷史不完全是嚴肅的,它的可能性是我們想象不到的,它的戲劇性則令人出乎意料。
五、結語
到了蘇童筆下,歷史透視出存在皆偶然的虛無感,以及人們無法把握自己命運的無力感。蘇童剝掉歷史的神圣光環,將歷史殘酷的一面揭露給我們看。又用審丑的方式,讓血腥、災難、暴力和死亡充斥文本。這部作品展現了一個帝王的心靈史,揭示了人性的丑陋和存在的荒誕。蘇童非常擅長悲涼意境的營造,那些無可遁形的孤獨和悲涼是人對生存的試圖逃離以及精神的流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