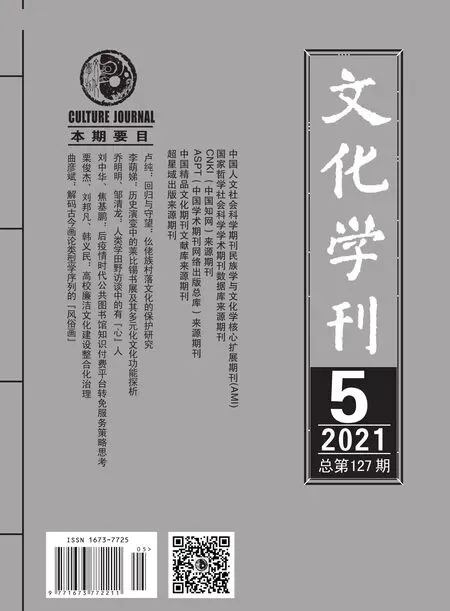論張棗詩歌的美學特征
顧 旭 何海峰
張棗作為中國當代文壇富有影響力的詩人之一,創作了許多令人難以忘懷的詩歌作品。《春秋來信》作為張棗生前出版的唯一一本詩集,該詩集包含63首詩。2010年,張棗逝世之后,其親友通過整理張棗的手稿,編排成書《張棗的詩》并通過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本書收錄了張棗生前創作的130余首詩。
病魔把張棗的生命定格在48歲,張棗的一生非常短暫,其創作出的許多作品也因為自己不滿意而遭到遺棄,但他為世人留下的極少部分詩作卻在中國當代詩壇刻上了不朽的印痕。
張棗作為后期朦朧詩的代表作家,其詩歌中極富個性化的意象構成、面具化的抒情特征與自信的抒情主體實現了巧妙融合,這也為后世學者研究張棗的詩歌、探索張棗詩歌中的美學特征留下了巨大的思考空間。
一、張棗詩歌的修辭美學
詩歌是語言的藝術,要求詩人能夠以精練的語言傳達出既富感性又蘊含哲思的過人見解。張棗作為后期朦朧詩的代表作家,十分重視修辭在詩歌語言中的作用。張棗通過對中國古典詩詞語言與結構的研究和雕琢,實現了與西方現代主義的巧妙融合。
《那使人憂傷的是什么?》這首詩,就體現出他對于中國古典詩學的研究,并為融入現代意識所作的嘗試。在本詩中,首尾兩句各出現“那使人憂傷的是什么?”這一問句,而這種首尾回環的結構正是對于古典詩詞中首尾運用相同意象的一種模仿,在漢語現代詩中運用這種回環結構,可以強化詩歌的情感表達力度,但單單是這種回環結構,顯然情感表達力度有限。與此同時,張棗在詩中加入了更親近現代化的個性意象組合,使讀者在閱讀詩歌時有耳目一新之感。例如,在此詩中,少女、葡萄藤、孤獨的英雄等意象的運用,在拓展閱讀者對于這些物事引發想象空間同時,也引發人們對于存在論更深的哲思。這則詩巧妙地告訴人們,那些過往進入你的生活又離開你的生活的人,他們依舊在記憶那端存在著,但卻又像被上了鎖。那些記憶好像那么親切,卻總保持著一絲不可切近感。全詩應用一系列陳述性意象,將記憶那種若即若離的感覺通過一系列諸如“你想”“你花”“你讓”“你感到”“你懷疑”等一系列復沓性的動詞蔓延至全詩的范圍,使詩的意象具有了整體性,同時也加強了全詩的整體情感力量。
在他的另一首詩《早晨的風暴》中,作者同樣運用回環結構,但在這里,不同于上首詩的首尾兩句進行相同的敘述,這首詩通過看星星這一件事完成了回環敘述。在詩中,作者把星象與人生的軌跡相聯系。當作者仰望天空中的一顆星時,感受到那顆星子與此時的作者內心是相呼應的,“孤單又晴朗”。“晴朗”的是作者知道人生是一場風暴,伴隨著起伏與不定。之后,作者將敘述的時間來回倒轉,從“昨夜”到“后半夜”,再從“后半夜”延續到“中午”,之后又從“中午”回溯至“早上”,最后回溯至“昨夜”。通過這樣的時間流轉與情感的波動相互呼應,使詩句所敘述的那種飄忽不定的人生感受與時間線條的游離感相互交錯,營造了一種微妙卻又流動的生命氣息。同時,從藝術結構上看,回環的結構與全詩那股捉摸不定的飄忽感相得益彰,在一定程度上使詩句的內容與形式得到較好的統一。
張棗在古典詩歌韻律的改造方面所做的努力也值得大家關注。張棗的詩歌很好地繼承了古典詩詞中音樂性特點,并在他的很多詩中能看到一種學習古典詩歌所留下的痕跡,這也體現在他對于詩的結構整飭的追求。如《麗達與天鵝》這篇詩作中,詩歌的結構組合就體現出張棗對于中國傳統詩學整飭風格的欣賞。在這首詩中,作者同樣把中國傳統詩學押韻的特征與現代漢語巧妙地結合起來,每一章進行首尾押韻,如“址”和“跡”;“號”和“島”;“磨”和“魄”;“象”和“反”。同時,兼具個性化與對稱性的意象拓展了詩文本的想象空間。除此之外,張棗創新了古典詩歌中的隱喻形式。在傳統古典詩歌中,隱喻手法的運用更像是為了在此物與彼物之間架設起無形的橋梁。在張棗的詩歌中,隱喻的作用得到拓展,并實現了隱喻、象征及意象三者的高度結合。如張棗喜用“鶴”這一意象,鶴不僅象征夢想與自由,同時在中國傳統觀念里,鶴兼具有清高、遺世獨立的形象。
二、張棗詩歌的對話美學
對話現象作為張棗詩歌中的一個重要特征,近年來受到許多研究學者的著重解讀。在張棗的詩歌中,經常出現對白似的片段。如他在《空白練習曲》這首詩中就曾寫下過這樣的詩句:“我啊我呀,總站在某個外面。從里面可望見我呲牙咧嘴。我啊我呀,無中生有的比喻。”張棗在詩中反復與自己對話,本質上是因為自身存在的不確定性所引發的,他渴望能夠重新定義自己的位置。在詩歌的世界里,張棗把自己分裂出去,他努力去找尋那個本我,這也是張棗在他的詩歌評論《十月之水》中寫下“我們所獵之物恰恰只是自己”一句的原因。一個迷惘的張棗在尋找一個本真的張棗,詩歌的寫作過程就是張棗重新發現自我的過程。在其另一首詩篇《天鵝》中,張棗就以詩的語言表現了自我的找尋過程,“尚未抵達形式之前,你厭倦自己。逆著暗流,頂著冷雨,懲罰自己,一遍又一遍”。這里寫的“尚未抵達形式之前”就可以理解為對于本真自我的找尋還未成功之時,迷惘的作者即使明知要歷經千辛萬苦,也要義無反顧。最終,作者找尋到了自我,“這個命定的黃昏,你嘹亮地向我顯現,我將我的心敞開,在過渡時,我也讓我被你看見”。在這首詩里,張棗向我們敞開了一個無比豐富的內心世界,他要找尋的是真正的本我,哪怕要歷經無比痛苦的內心掙扎,因為每一次尋找本真的過程,都是一次對于原有自我的否定。
張棗還善于利用視角的轉換來制造對話的迷宮。在他的詩歌《跟茨維塔耶娃的對話》中,張棗是以雙線條敘述的形式展開對話的,一條線條是張棗—元詩,另一條線條是張棗—茨維塔耶娃。詩的前些部分均是在想象茨維塔耶娃的情景,但伴隨著“他向往大是大非”這句詩中敘事視角的轉變,原有的單線條對話變得豐富起來。而這里的“他”,也指向了詩的寫作規則。之后,張棗又把敘事視角轉回茨維塔耶娃,并直接參與了與茨維塔耶娃的對話。但同時我們也能注意到,詩句中看似是寫張棗與茨維塔耶娃的對話,實際上,也是對另一個自我的對話。這是因為詩句中提及茨維塔耶娃對于祖國的思念,而張棗常年漂泊海外,對于祖國的思念同樣是詩人的隱痛。
三、張棗詩歌的生命美學
生命美學的概念最早出自學者潘知常的《生命美學》,他呼吁人們傾聽自己內心深處的呼喚,從生命相關的角度出發探尋美學本身。詩人一生坎坷,過著長期顛沛流離的生活,讓詩人對于生命充滿了一種虛幻感。面對命運,詩人常常有一種無力感。在這種情況下,理想自我與流亡、虛無相互交織,詩人對于命運的游戲流露出自己的深思。在他的詩《與夜蛾談犧牲中》,張棗高呼“你的命運緊閉,我的卻開坦如自然。因此你徒勞、軟弱,蕓蕓眾生都永無同伴。來吧,我的時間所剩無幾,燃起你的火來。人啊,沒有新紀元的人,我給你最后的通牒”。這段詩中,面對飛蛾撲火般難以逃脫的宿命,詩人時刻提醒著自己,與命運的搏擊注定是孤獨的,而軟弱會使人對人生產生無力感。在詩人的另一首詩《夜半的面包》中,面對命運的超驗性,詩人也發出過難以突圍的絕望:“我一生等待的唯一結果,未露端倪。如果我是寂靜,那么隔著外套,面包也會來吃我。”詩人對于命運的不確定性感到迷惘。他把自己比喻成寂靜,實際上是在形容他與命運的搏擊太過孤獨,周圍除了寂靜還是寂靜,這無疑會帶給人一種恐懼感。正如張棗所言:“異化的物質世界造成了主體的被壓抑。因為物大于人,對于物的消耗,對物的追求,以及對物的占有,成了人類的神。物成了神。”這種對于異化世界的懷疑讓詩人在思考關于人的存在本身是否受到物的支配。同時詩歌的邊緣化問題也是使張棗在創作中時常表現出無力與孤獨感的一大原因,這些情感相互交織,體現在詩人詩中的是一種與命運搏擊的猶疑感。
命運的捉摸不定與對于現實困境的無力,讓張棗嘗試從生活細微處的探尋中,找尋反抗命運的機會。長期的生活體驗讓張棗知道,生活中的苦痛往往是常態,而幸福則是小概率的事件。如若生活一直被痛苦所壓抑,而沒有用幸福去找尋這個世界更多的可能,那么生活將毫無希望。張棗在他的隨筆《秋天的戲劇》中,就曾表示出對于生活希望的努力追尋:“人的生活會一天天變美,變好。活著就是不斷地改掉缺點,走向完美。走向人生最英勇的高處,在高處,依然保持靈魂的崇高和身軀的健全。”不僅如此,他還極力呼吁人們“為幸福而歌”“尋找幸福,用虛無的四肢”。這里需要注意的是,張棗對于幸福的追尋,不同于海子那種將幸福寄予遠方的理想主義形式,而是將對于幸福的理解立足于生活,追尋的是一種生活細微處的幸福。正因如此,在《跟茨維塔耶娃的對話》這首詩中,詩人就用美好的詞匯,訴說著生活中簡單的幸福。
四、結語
張棗作為中國當代詩壇一位頗具影響力的詩人,其詩歌具有明顯的“化古化歐”、古典性與現代性相結合、對話性、哲思性等特點。他的詩歌情感流向平和而不偏激,既流露出對命運捉摸不定的無奈,也流露出對幸福追尋的渴望。張棗的詩歌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接續了中國古典詩歌的美學傳統,加之自我的生命感悟、情感體驗與時代沖擊,使得張棗的詩歌有著鮮明的個人印記和美學風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