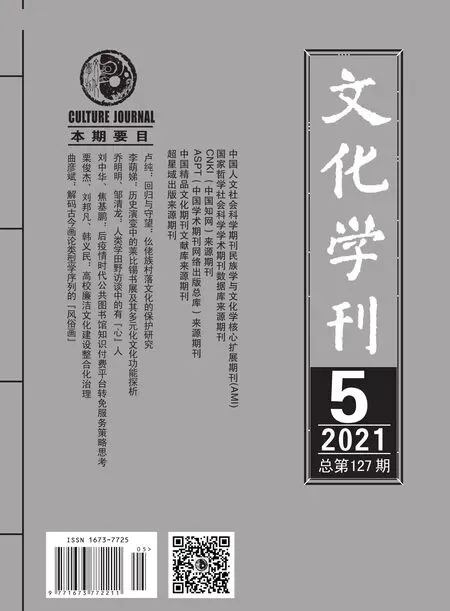淺談李清照懷鄉詞的特點
王藝璇 李春霞
懷鄉是文學創作中永恒不變的主題,歷代文人騷客圍繞“懷鄉”進行了不少創作。在中華民族的傳統觀念中,懷鄉情結是人與其靈魂歸于實地的故土情感。即便如此,不同的文人對懷鄉表達出了不同的情感內涵。由于每位文人的人生經歷與境遇截然不同,他們表達出來的懷鄉情結也是獨特的。李清照后期的懷鄉詞有其獨特歷史背景與特殊遭遇影響下的獨特一面。從她的經歷看,她的懷鄉情結源于家國破敗、流離失所、丈夫早逝及昔日光景消失不再。正因如此,李清照后期的懷鄉詞更多飽含著悲涼與失落,這也讓她的懷鄉詞的內涵更為飽滿與深刻。
一、漂泊顛離,感發家國之痛
家國本是一體。家,不僅是李清照生長與生活的地方,更是她溫情所生的場所。而她眼前的國與家,在“靖康之變”之后驀然間變成了故國與舊家,從被迫地遠離家園到無奈地失去家園,李清照表現出對故國舊家深深的眷戀與思念,但憑借她一己之力卻又無法挽回。
在漂泊不定的逃亡生活中,詞人又經歷了丈夫趙明誠病故,圖書金石喪失殆盡的巨大痛苦,這樣的劫難與打擊,讓李清照深深體會到家國淪喪帶來的痛不欲生的感受。這一連串的遭遇并沒有讓詞人生活的意志消沉,反而使其創作熱情更加高漲,并把眼光投到國家大事的關注上,寫下了“欲將血淚寄山河,去灑東山一抔土”[1]為出使金朝的韓肖胄和胡松年送行,強烈地表達出收復失地的愿望。在李清照心中,國破家亡對她造成的是傷害是久久不能平復的,她日夜懷念繁華璀璨的京都,懷念湖光山色的故土,有感而發,她寫出了一首首哀痛欲絕的詞。《菩薩蠻》中寫道:“故鄉何處是,忘了除非醉。”[2]3《蝶戀花》中寫道:“永夜懨懨歡意少,空夢長安,認取長安道。”《清平樂》中寫道:“看取晚來風勢,故應難看梅花。”[2]20這些都表達了詞人對國家淪喪、流離失所的深惡痛絕,對國家和人民命運深深地擔憂。這種懷鄉情結不僅僅體現在李清照的筆下,也是整個宋朝人民的心之所向。
家國情懷是愛國者情感的展現,故國之思則是國破家亡者最炙熱的表達。時代更迭不可避免,去國之悲更是在所難免。崔顥黃昏時分登黃鶴樓,寫下千古名句“日暮鄉關何處是,煙波江上使人愁”。屈原回首故國,淚干腸斷,寫出絕代佳作《離騷》。懷鄉情結是所處時代文人不可避免的話題,他們將對故國即將溢出的暢想躍然紙上,他們與李清照一樣,在作品中表達出強烈的愛國之情。但是,李清照更多地代表了宋朝底層百姓的呼喚與愿望,她后期的作品大都是在流亡時所作,身邊的流亡者所遭遇的一切她都看在眼里,她更懂得百姓的感受與需要。從名門望族到漂泊無依,從大家閨秀到國破家亡者,這一切都是因戰亂而起,時代所迫,這樣一連串的遭遇與打擊造就了后期的李清照,她后期的詞直白地寫出她對故國的思念與牽掛,對宋朝百姓的同情與擔憂。這不禁讓讀者的腦海里呈現一個這樣的鏡頭:詞人倚著欄桿,飲著酒,望著月,眼中泛著淚花。她執著追求自己的理想,她的理想就是國泰民安,人民安居樂業。她將自己的理想與宋朝百姓緊緊系在一起,她的家國之夢正是百姓所夢,她的憂國之思正是百姓所思,她的家國情懷代表著與她同時代、同遭遇的宋朝百姓的情懷。所以,李清照的懷鄉詞的特點之一是抒發愛國熱情,體現時代痛苦,表達百姓呼喚。
二、蒹葭之思,書寫喪夫之哀
夫妻雙方本就是相偎相依的,一方失去必然會對另一方造成巨大的痛苦,如果從這個角度界定懷鄉詞,就是通過對丈夫的思念、對美好家庭的向往來懷鄉。故懷人也是懷鄉。
李清照與趙明誠亦是如此。18歲的李清照與21歲的趙明誠在汴京成婚,兩人都喜歡圖書碑文,共同的愛好與興趣加深了兩人的情感。兩人婚后的生活雖然清貧,但是充滿歡聲笑語,用安靜、和諧、美好來形容也不過分。
好景不長,趙明誠英年早逝,多愁善感的李清照常常睹物思人。在她后期的作品中,也常常借景抒情,流露出她對丈夫的思念,以及自己孤獨無依的寂寞與無奈。正如她在《南歌子》中寫道:
天上星河轉,人間簾幕垂。涼生枕簟淚痕滋。起解羅衣聊問、夜何其。
翠貼蓮蓬小,金銷藕葉稀。舊時天氣舊時衣。只有情懷不似、舊家時。[2]42
詞人流離失所,追憶過去,感慨萬千,丈夫的病故讓她在痛苦與磨難中掙扎,就像她在詞中用“天上”與“人間”來寫出兩人天人永隔。夜幕降臨,家家戶戶都放下簾幕,已然入睡,只有自己輾轉難以入眠。正值涼秋,用“淚痕滋”三個字毫無保留地把自己的孤寂與悲傷宣泄出來。詞人睹物思人,看到舊衣上“貼翠羽”“金線刺繡”不由得想起丈夫,想起前塵往事。她回憶與丈夫在一起的那個時候,也是這樣的天氣,也是穿著這件舊衣服,只不過此情此景物是人非。正是這些看起來平平淡淡的話語,卻吐露出李清照無盡的辛酸與悲痛。
此外,李清照在《孤雁兒》中寫道:“一枝折得,人間天上,沒個人堪寄。”[2]45院內的梅花開得恰好,詞人信手采下一朵,轉頭一想,這梅花又贈予誰呢?在這人間已經無法找到可贈之人,那天上豈不是更難尋覓?詞人將筆落于梅花,而此前詞人與趙明誠將梅花作為他們表達愛意的信物,也是他們美好愛情的象征。因此,趙明誠逝世后,在梅花盛開的季節,過往的美好就會浮現在詞人眼前,她想起了與自己共同賞梅的夫君。詞人借“梅花”來懷念丈夫在世時的美好,深切地表達了她與亡夫趙明誠之間的深厚情感,抒發了她對趙明誠沉痛的悼念,這種強烈的失落感被她描繪得淋漓盡致。
從上面的兩首詞不難看出,李清照后期的懷鄉詞習慣性地用移情入景的手法抒發她對亡夫趙明誠的懷念,懷念兩個人的美好時光,這些思念現在只能通過詞來表達出來。飽嘗了山河淪喪的辛酸,丈夫的早逝對李清照來說無疑是重創,徹底擊碎了她想與丈夫白頭偕老的夢。她的精神最終失去了寄托,她的靈魂也失去了歸宿,詞人用最真摯的詞將這種辛酸的情感寫得淋漓盡致。因此,思夫是李清照懷鄉情結的表現之一,她的懷鄉詞的特點之一是懷念亡夫,用看似平和的語氣表達出了震人心魄的悲傷與思念。
三、韶光荏苒,感懷昔日之景
懷念舊時之景也是懷鄉的一種表現。人們潛意識里認為懷鄉更多著眼于空間層面的懷念,卻忽視了時間流逝留下的印記。舊時光留給人們許多不可磨滅的回憶,這些回憶會讓人們不由自主地想起往日美好,進而懷念故都。
李清照自幼家境優越,家中文學氛圍也十分濃厚,從小耳濡目染,自身天資聰穎,因此,李清照的文學才華開始嶄露頭角。生活在繁華璀璨的京師,更加激發了李清照的寫作靈感。后來與趙明誠成婚,雖為貴族子女,但兩人經濟獨立,并非大富大貴,生活積極向上,幸福和諧的。然而,金人南侵,徹底讓舊時好光景消逝不再。往日繁華璀璨的京都如今淪為一片山河破碎,滿地哀號的景象。詞人心中的一片凈土徹底淪陷,這種強烈的反差與落差感,讓李清照心里的防線徹底崩塌。正如李清照在《清平樂》中寫道:
年年雪里,常插梅花醉。挼盡梅花無好意,贏得滿衣清淚。
今年海角天涯,蕭蕭兩鬢生華。看取晚來風勢,故應難看梅花。[2]53
全詞以梅花為對象,先回憶自己與趙明誠共同賞梅的情景,常常陶醉在插梅的喜悅中,這陶醉不僅僅是詞人為梅花而醉,還是為當時的美滿生活陶醉,為當時安定的社會帶給他們美好的一切而陶醉,李清照將自己當時內心的喜悅情感通過插花表現出來。后來,雖有梅花在手,但只是漫不經心地把玩,沒有好心情去欣賞眼前的梅花。每一年花照樣開,人卻悄無聲息地發生了變化,昔日美好的一切,如今物是人非,怎能不叫詞人落淚呢?當年朝廷安定,詞人觀梅是一種興致;如今朝廷風云變幻,詞人愛梅的興致減弱,內心充滿了怨恨與憂傷。梅花年年綻放,今非昔比,此時的詞人兩鬢已經斑白,看見晚風正在吹打開放的梅花,落梅已盡,詞人很難再見到它的絢爛多姿了。詞人借用“風勢”一詞明指天氣,暗指政治。在當時,政治形勢極其不利,國家危難,詞人根本無心觀梅。山河破碎,國破家亡,寄托著詞人對正處于水深火熱的國家深深的擔憂。
由此不難看出,詞人在不同的生活階段對賞梅有不同感觸,而這些感受形成強烈的反差。從昔日的美好光景到如今的孤寂衰老,以昔襯今,寫出了詞人的生活經歷的翻天覆地的變化。因此,感懷昔日之景是李清照懷鄉情結的表現之一,她的懷鄉詞的特點之一是以昔襯今,通過對比的手法,感慨美好舊時光的消逝,以及對如今山河破碎的無奈。
四、結語
李清照的懷鄉詞題材廣泛,從多角度、多維度向人們表達出她對當年那個繁華璀璨的京都的懷念,對亡夫趙明誠的思念,對昔日無憂無慮生活的渴求。這些情感也恰恰表現出了詞人對山河破碎、國破家亡、百姓流離失所的無奈與感傷,表現出了她對故國舊家、宋朝百姓深深的擔憂與牽掛。李清照是那個年代的見證者,她記載了當時水深火熱的生活帶給她的痛苦與傷害,表達出了自己對故國舊家的懷念之感。縱觀李清照的懷鄉詞,她從情感出發,豐富了懷鄉詞的內涵,反映時代精神,同時推動宋代懷鄉詞向前發展一大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