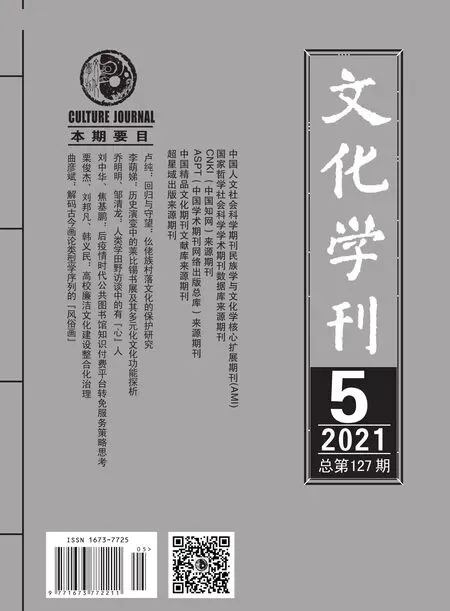蘇軾教育思想在高校思政課教學中的啟示
仲昭旭
一、蘇軾教育思想形成的文化底蘊
(一)家庭教育的影響
蘇軾其父蘇洵,自號“老泉”,是北宋中期大器晚成的文學家,熱衷文學,卻屢試不第。但蘇洵并沒有因此心灰意冷,反而從此醉心于學術,閉門求索,最終作有《嘉祐集》這等散文佳作,是蘇軾用心攻讀的榜樣。蘇洵告誡蘇軾,讀書、作文的目的是進能立功、退能立言:“推是以施之人,不為茍生也;不幸不用,猶當以其所知,著之翰墨,使人有聞焉。”這樣積極的教育思想深深影響了蘇軾,在日后的生活和教育實踐中,蘇軾謹記父親的教誨。每被貶到一處,蘇軾并不消極度日,而是積極改善當地教育事業,對弟子灌輸積極的學術精神。蘇洵常采用激勵教育法,從不吝嗇對蘇軾文章的贊賞和鼓勵,這樣的家庭教育讓蘇軾一生受用無窮,蘇軾在自己的教育實踐中也效仿父親的教育方法,采用啟發式、激勵式的教學方法,與學生在教學過程中采用平等的態度交流,取得了很好的教學效果。
蘇軾幼時,蘇洵常游歷在外,其母程氏就承擔起了教蘇軾識文斷字、講授史書的責任。程氏對蘇軾價值觀的樹立產生了巨大影響,她通過閱讀史書中的故事,向蘇軾灌輸了許多處世立身的經驗,向蘇軾灌輸了不畏奸佞的正直思想,對蘇軾的一生產生了重大影響。
(二)宋代文化的影響
宋代是我國封建社會發展過程中一個極其特殊的時代,“崇文抑武”的政治主張讓讀書成了選拔人才的重要標準,促使著文化教育的繁榮,教育改革成為當時的政治熱點。當時涌現出了一大批富有創造力的教育家、文學家,他們天馬行空的暢想為后人留下了無限財富。宋代“重文”的政治方針,讓讀書士子的社會和政治地位大大提高,學術思潮空前繁榮,后人將這個時期產生的思潮統稱為“宋學”。宋學不同于漢代經學的繁文冗雜,也不同于魏晉玄學的神秘浮虛,宋代學者更加崇尚哲理化的思辨思想,創立了以義解經的新經學,對自然、人性、社會等各個領域都做出了精辟的解釋。
宋學的另一個特點就是“三教合流”。不同于漢、魏晉、隋唐時期儒、釋、道水火不容的局面,宋代的思想家在發展中融合了儒、釋、道三家的思想精華,將其整合成一個更豐富、更系統的理論體系。在這個理論體系的影響下,蘇軾的教育思想體現了儒家入世的精神內核,兼具道家闊達、自然的心性追求與佛學眾生平等的觀點。
(三)從師經歷的啟發
蘇軾作為蜀中名門子弟,8歲就師從張易簡,開始了系統的學校教育。宋代的學校教育以科舉為目標,以經、史、子、集為主要教學內容,作為道士的張易簡還在此基礎上要求蘇軾學習《老子》等道家經典,為蘇軾教育思想中的道家思想奠定了理論基礎。蘇軾十余歲時,拜劉微之為師,劉微之根據蘇軾自學能力突出的特點,鼓勵蘇軾進行獨立的自主鉆研,培養其創造能力,但劉微之對蘇軾也不是全然的放縱。在自學期間,蘇軾常常縱情于山水,在游玩之中培養詩情,劉微之認為這樣并不利于安心做學問,就借李白“太白俠游到西川,磨針溪前悟前衍”的典故來敲打蘇軾,讓蘇軾明白了知行合一的道理。
二、蘇軾教育思想的主要內容
蘇軾針對教育目的、教育方法、教育內容、以及教育過程中的師生關系提出了一些具有創造性的觀點,值得我們研究、思考。
(一)教育目標
蘇軾認為教育的終極目的是培養儒家理想的君子,卻又不同于儒家對于君子的傳統評價標準,蘇軾對君子有著更為現實的要求。蘇軾在《上韓太尉書》中說:“古之君子,剛毅正直,而守之以寬,忠恕仁厚。而發之以義。”[1]1361蘇軾繼承了儒家對君子“學而優則仕”的看法,但對于君子與出仕的必然性中,又具有道家順其自然的精神內核。蘇軾在《靈璧張氏園亭記》中說:“古之君子,不必仕,不必不仕。必仕則忘其身,必不仕則忘其君。”[1]368蘇軾的教育觀更具有人本色彩,更加注重教育對人的成長作用,而不是為了培養國家官員忽略人性。
蘇軾對人性的推崇是建立在符合社會倫理道德基礎上的。蘇軾希望教育出的君子有許多優良品格。首先,必須要有擔當意識,在其位謀其政,不能過謙而喪失自身價值。其次,蘇軾認為君子的評價標準應該是“德才兼備、技道兩進”,反對王安石“德行取士”“經義取士”這種割裂德行與文化的主張。針對君子的德行操守,蘇軾注重“大節”而反對“過正”,反對“妄悖自然”的反人性標準。
(二)教育方法
在教學方法上,蘇軾認為前人的智慧、文明的積累是人成長的根基,必須要重視文化底蘊的積累,才能在此基礎上創新。重視實踐是蘇軾教育方法的又一特征。蘇軾認為實踐不僅是對前人經驗的驗證,也是進行創新的基礎。蘇軾采用“耳聞、目見、勤練”的教學方法,鼓勵學生在實踐中學習,而不能拘泥于書本之中。在創新中,蘇軾主張發揮學生的主體性,反對王安石要求別人學習自己文風的錯誤思想:蘇軾在《答張文潛縣丞書》中說:“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顏淵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學同天下!”[1]1427蘇軾鼓勵弟子寫文章要創新,不能呆板模仿。《石林燕語》曾經記錄過蘇軾對弟子陳師道的評價:“凡詩,須做到眾人不愛可惡處方為工。今君詩不唯可惡卻可慕,不唯可慕卻可妒。”[2]蘇軾肯定陳師道獨特的創作風格,同時鼓勵各個弟子向不同領域發展,其弟子最終在不同領域皆有建樹,這與蘇軾的教學方法是分不開的。
(三)教育過程中的師生關系
宋代“師道尊嚴”之風盛行,教師在教學過程中占據絕對地位,忽略了學生的主觀能動性。當時以王安石為首的新學派,甚至要求學生模仿他們的文風去寫作,打壓了學生創作的自主性。蘇軾十分反對這樣的師生關系,他曾在《書黃泥坂詞后》中自述過學生學習的狀態:“前夜與黃魯直、張文潛、晁無咎夜坐。三客翻到幾案,搜索篋笥。”[3]我們能夠清晰地看到蘇軾與其弟子是亦師亦友的關系,蘇軾為學生營造了平等民主、包容和諧的教學氛圍,有利于更好地激發學生學習的積極性和創造性,故蘇軾雖門徒眾多,但各有其風格,各有其長短。
三、蘇軾教育思想的現實啟示
(一)注重課程的實踐性
蘇軾重視實踐在教學中的作用,鼓勵學生在自然中感受真理,從而應用于書畫、詩詞創作中,對我國高校思政課具有啟示意義。在我國高校長期的教育實踐中,部分學校一味重視對學生理論知識的灌輸,忽視了在理論實踐中的應用,導致知識與實踐脫節。高校的思政課教師要及時轉變過去“以講為主”的教育方式,根據教學內容設計教學環節,活躍課堂氣氛,積極尋找“第二課堂”,培養學生發現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遵循求實原則,在實踐中獲得更好的教學效果。
教師要遵循求實原則,樹立強烈的求實精神,在實踐中檢驗知識,做到不唯上、不唯書、只唯實,做到認識與實踐相結合,根據學生特點開展教育工作,增強思想政治教育的針對性和有效性。在新時代,我們要在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引領下,將理論知識與實際行動結合起來,實現思政課程的“知行統一”。“知”是指要讓學生了解祖國歷史,了解黨的大政方針,培養學生的愛國情懷,引導大學生將個人理想追求同國家的前途命運結合起來,在實踐中踐行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行”是指將大學生在課堂中領會的道德認知,應用到社會實際問題的解決中去,從而做到課堂學習和社會實踐的緊密結合。
(二)樹立正確的人才評價觀
蘇軾通過分析宋代品行舉薦與科舉考試的關系,提出了“德才兼備、技道兩進”人才評價標準,在教學中同時注重對學生品行和才干的培養,對新時代的教育改革具有一定的借鑒意義。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目的是促進學生的全面發展,所以必然要摒棄傳統的“唯分數論”,要更加重視教學過程中對學生全面能力的培養,建立更為系統的人才評價體系。在日常的教學中,要引入對學生知識、技能、品行、交際能力、應變能力等多方面的考核因素,通過對學生評價方式的改變,激發學生主動提高個人素質的積極性。“要遵循思想政治工作規律,遵循教書育人規律、遵循學生成長規律,不斷提高工作能力和水平。”[4]此外,學校也應該積極推進學生評價機制的創新,改變過去只靠成績評獎評優的方式,可以根據實際情況將學生社會工作記錄、個人道德品行、各技能獎項納入評價方式之中,增強評價體系的科學性、合理性。
(三)構建以學生為主體的師生關系
蘇軾作為蜀學的集大成者,門下弟子眾多,成就頗豐,這樣的教學效果與蘇軾的為師態度是分不開的。蘇軾平等對待每一位學生,尊重學生的個性,鼓勵創新,不要求學生的文風與自己相同,蘇軾秉持的是一種“誠同守正”的教育觀念。而在我國長期的教育實踐中,教師一直在教育活動中處于主體地位,向學生灌輸理論,忽略了學生的主動性和創造性,這樣的師生關系不利于學生的個性發展。
在新時代背景下,我國高校的思政課要改變過去的“教師中心論”教學思維,向以學生為主體、教師為主導的新型教育模式轉變。在這個教育過程中,教師起到組織、引導、啟發和總結的作用,讓學生在參與、感受和踐行中發揮探究能力,促進學生道德健康發展。要堅定學生在教育過程中的主體地位,平等對待每一位學生,尊重每一位學生的個性需求。要充分發揮學生的主體作用,引導學生將觀念上的道德認知轉換成自身的道德行為,在遵循學生道德認知發展規律的基礎上,鼓勵、引導學生自主進行道德實踐,從而養成良好的道德習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