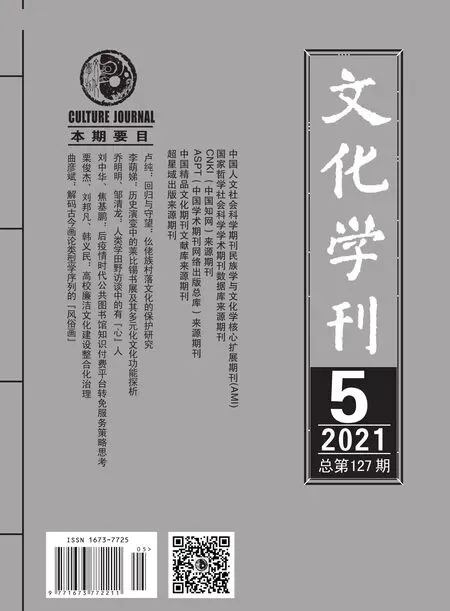中西方繪畫抽象表現性比較
——以梁楷《潑墨仙人圖》和德·庫寧《女人一號》為例
何璞詩如
本文選取梁楷《潑墨仙人圖》和德·庫寧《女人一號》這兩幅作品作對比有兩方面原因。一方面在于二者都是人物畫范疇。人物畫是最貼近人類自身的繪畫,是人的本質力量對象化的最佳體現。畫中表現出怎樣的人物,往往相較于山水畫、花鳥畫等能更直觀地反映藝術家的自我認知、精神取向以及這一時代所崇尚的風氣。另一方面在于二者的抽象性。中國繪畫不講“抽象”,而說“寫意”,但實質上與西方的抽象表現藝術有異曲同工之妙。中西方繪畫的“抽象”都并不如實寫照人物本身,而是加入自己的精神狀態和審美意趣,形成一種“再造”的形象,這種形象是模糊的、不確定的,能喚起欣賞者的幻想機制,代入接受者的生活經歷和審美經驗,可以引發更加強烈的“再創造”的欲望。
一、中西方繪畫創作背景及其相似性
(一)梁楷與《潑墨人圖》
古代人物畫的發展主要依靠統治階級和宗教的力量,宗教促成了一大批宗教人物畫家,如“四家樣”(南齊張僧繇所創的張家樣、北齊曹仲達所創的曹家樣、唐吳道子的吳家樣、唐周昉所創的周家樣);統治階級力量則形成以皇家宮廷為核心的“院派”和以文人士大夫為核心的“文人畫”。北宋設立翰林圖畫院,由宋徽宗親自指導,為人物、山水、花鳥等各種繪畫形式的發展奠定了堅實基礎,文人畫也由此興起。在梁楷之前,人物畫的線描技法已經發展成熟,著名的白描人物畫家武宗元、李公麟等,承接唐代吳道子“莼菜條”線描技法而有所發展。北宋風俗人物畫家張擇端有《清明上河圖》這一風俗人物畫,其線描極工致。還有燕文貴作《渡江圖》、蘇漢臣作《秋庭戲嬰圖》等,皆顯示梁楷以前的人物畫中線描技法的高超。前人皆重筆,梁楷則重墨。當寫實性的線描技法發展到一個極端,墨法的興起和運用便順理成章。梁楷是個生性放蕩的酒徒,不慕朝廷而慕山林,把皇帝賜予的金腰帶掛在枝頭,人稱“梁瘋子”。這種桀驁不馴的性格也成為其創作潑墨大寫意的前提和基礎。
文人畫的興起、前人技法的發展以及狂傲不羈的性格,梁楷的簡筆人物畫和潑墨大寫意在這種背景下應運而生。這幅《潑墨仙人圖》就是對其真性情、超然的精神狀態的最好詮釋,全畫用墨多于用筆,似墨筆隨意點畫而為之,細看幾乎看不清仙人的衣裳和五官,遠觀則能得其全貌,只可遠觀而不可褻玩,給人以整體氣勢,極其傳神。其用墨濃淡得當,干濕相宜,將仙人醉酒那種憨態可掬、悠然自得的神態描繪得淋漓盡致。畫中仙人步履蹣跚、滑稽輕浮的情態也充分反映了梁楷的孤傲及對權貴的嘲諷和蔑視[1]。
(二)德·庫寧與《女人一號》
20世紀中葉,西方陸續完成工業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混亂與機械工業化帶給人們內心的恐慌造成了繪畫線條和色彩的躁動,抽象表現主義就是在這種條件下產生的,德·庫寧是抽象表現主義的重要畫家。德·庫寧的“女人”既具象又抽象,他所畫的一系列女性形象由于過于抽象而難以辨識,甚至給人以“雌雄同體”的感覺,只通過色彩和線條表現女性特征,如用肉色、紅色與黃色表現女性陰柔的氣質,用加粗的線條表現女性胸部等。其中《女人一號》至《女人五號》算是介乎于德·庫寧“女人”系列中具象和純抽象之間的狀態,也是其最典型抽象表現主義代表作。這些“女人”均以正面示人,“被看”的視角最大化,仿佛在昭示自己的存在[2]。線條筆觸極其粗獷,色彩給人以視覺沖擊。“女人”自身的形象是抽象的,看不清具體形態與肢體。“女人”的背景往往也是模糊化的,這種模糊化給人以不確定性,正是如此,使它顯示出一種“自由度”,同時,這種過分的“自由”暗示了藝術家內心的躁動不安。
(三)《潑墨仙人圖》與《女人一號》相似之處
梁楷與德·庫寧的兩幅作品分別代表中西方人物畫的抽象性,二者有許多相似之處。首先,它們同為人物的抽象化表達。前文也講到,“人物畫”與“抽象性”是兩幅畫得以比較的前提和基礎,此處不再贅述。其次,從筆觸上看來,二者都較為自由狂放。中國繪畫從繪畫技法上分可以大致分為工筆、寫意和兼工帶寫,其中最具表現力、最自由狂放的一種形式當屬寫意,重在用墨。用墨是中國繪畫的一大特色,梁楷的大寫意充分利用水墨的特點創作,皴擦點染交互為用,從畫面的飛白、墨色看來,梁楷作畫時的行筆節奏是非常快的,如同行草書寫時如飛如動,更有利于傳達出創作者的情緒[3]。不像中國繪畫喜好用墨色變換表現無窮事物,西方繪畫更傾向于用色和用線。德·庫寧的“女人”系列用粗放明顯的筆觸和繁雜的賦色組合成一幅躁動的畫面,同樣傳達出創作者的欲望和激情。再次,二者的相似之處在于它們都能激起欣賞者情緒與“再創造”的欲望,這與上一點相輔相成。自由狂放的筆觸加強了畫面的動感,使之有一種沖破畫面與接受者對話的沖動,飛動的筆畫帶來節奏感與自由度。同時,模糊化的處理使其帶上了不確定性,若斷若連的筆畫使欣賞者動用“格式塔”心理模式去填補創作空白,欣賞者加入自己的主觀想象,不由自主地實現對作品的“再創造”[4]。
二、中西方繪畫抽象表現性差異
通過對梁楷《潑墨仙人圖》與德·庫寧《女人一號》兩幅代表性作品的分析,可以從三方面討論中西方繪畫抽象表現性的差異:從表現方式上看,中國求“簡”,西方求“繁”;從形象塑造方面看,中國求“神似”,西方則偏“符號化”;從情感表達方面看,中國往往通過所塑造的形象傳達瀟灑不羈的精神氣質,西方則傾向于表達躁動不安的內心及欲望。以下分別對三方面進行論述。
(一)表現方式
中國和西方在繪畫方面對于“抽象”等概念的理解不盡相同,但中西方的“抽象”都有一個共同的特點——潦草。在從繪畫寫實到“抽象”的發展過程中,中國書畫走的是“趨簡”的路方式。不僅繪畫,書法也是如此,書法從楷書演變為行草,線條逐漸簡化,一連串的復雜筆畫往往簡化為兩點一橫,甚至兩個相同連續的字只用兩點表示。書畫同源,中國書畫都是線條的藝術,所用工具都是這樣一支毛筆。用墨是在用線的基礎上發展成熟的,毛筆運行時,中鋒便成筆,側鋒便聚墨,中國繪畫對“筆墨”的靈活運用可以幫助創作者在僅僅使用最簡單的書畫用具的基礎上創作出最豐富的含義。“筆墨”在一定程度上促成了中國繪畫的“簡化”。西方繪畫的“抽象”走的則是“繁化”的方式。
從用色上看,中國的寫意畫幾乎不用過于豐富的色彩,講求“落墨為格”,從五代花鳥畫家徐熙到唐代山水畫家王維、王潑墨,再到明清文人畫家徐渭、八大山人等,都是以水墨為上。中國寫意畫對水墨的推崇主要來源于魏晉玄學的興起和文人畫家對老莊哲學的崇尚[5]。老子《道德經》中:“五色令人目盲”表明了中國文人畫不尚色彩的立場;而“墨色”即玄色,實際上照應了老莊推崇的“玄”,濃淡干濕之變化皆出于最單純的“玄色”,這一水墨特性使崇尚玄學的文人畫家著迷不已,對于這一點,唐代張彥遠也在《歷代名畫記》中有所敘述:“運墨而五色俱”,更肯定了中國文人寫意畫用單一墨色變幻出無窮可能的繪畫方式。而對于西方的許多抽象畫,人們的第一印象就是“色彩迷蒙”,各種繁雜鮮明的色彩、奔放的筆觸和點線交織構成一幅極富視覺沖擊力的畫面,傳遞給人一種動感和激情。除德·庫寧的“女人”系列,“滴灑繪畫”創始人波洛克的作品《迷蒙的薰衣草》以及“熱抽象”畫家康定斯基的“構圖”系列作品等都是體現西方抽象表現藝術風格和技法的典型之作[6]。
從用線上看,中國文人寫意畫崇尚的是“逸筆草草”,追求“聊寫胸中逸氣”,看似寥寥幾筆,但能用單純的墨線勾勒出人物神態,達到“傳神”。“求神似而不求形似”是中國“抽象”繪畫所追求的,是似亂而整、簡而有序的“抽象”;西方的“抽象”繪畫似乎因為急于展現藝術家狂熱的內心和激動的情感而使色彩線條如亂麻糾纏,單一的色線不足以充實畫面、表現情感,越是復雜的情感越是需要繁雜的色線相互交織的形態來傳達,這就造成了西方抽象繪畫的舍簡求繁。
(二)形象塑造
除去繪畫的基本表現元素,色彩和線條上的不同運用帶來中西方抽象表現繪畫的差異,在色彩和線條最終構成的藝術形象上也體現出中西方塑造形象的目標追求和審美差異。中國寫意繪畫在塑造形象之前就已“成竹在胸”,存在一個預設的“神”統領整個創作過程,“逸筆草草”所描繪的就是這個先于畫面形象而存在的“神”。因此,中國寫意繪畫所描繪的不是一個具體形態,而是直接抓住事物的“神”去描摹,其創作目的就是給這個“神”找一個恰當的形象來承載。對于“神”的描摹是虛幻的,塑造出來的形象越是具體,細節越精致,它離原本的“神”就越遠;筆意越是簡遠,留有的想象空間越多,離“神”越近。若要將頭腦中的意象盡可能保存其“神”而物態化到紙上,其塑造的形象需是簡而虛的,但虛中有實,得其神必然能得其形,這就是中國繪畫素來講求的“神形兼備”。相比之下,西方抽象繪畫不那么重視形體的塑造。相較于文藝復興時期對人體結構的精準把握,逐漸走向抽象化的西方繪畫刻意利用夸張變形的手段來扭曲完美的人體形象,造成一種視覺的陌生化,以獲得抽象的快感。西方抽象繪畫塑造的形象通常是極富象征意味的、非寫實性的,往往通過一些“符號化”的藝術語言來組織形體,如象征著女性的顏色、象征生殖部位的線條、色塊等[7]。總體來說,在形象塑造方面,中國大寫意注重整體表意,西方抽象繪畫則選擇局部安放象征意。
(三)表情達意
紙上的形象首先是存在于藝術家頭腦中的意象,經過藝術家的審美加工和篩選以及藝術語言的選用和表達,才最終變成物態化的藝術形象。這個意象物態化的過程也展現了中西方抽象繪畫的差異,即由于中西方表情達意角度的不同,造成情感物態化時藝術形象的兩種不同趨向:中國寫意繪畫中不論是取材還是人物形象的描繪都趨于“清高化”,如梁楷的另一幅簡筆人物畫《太白行吟圖》、李唐的《采薇圖》以及衛賢的《高士圖》等;西方抽象藝術中的人物形象則趨于“扭曲化”,如蒙克的《吶喊》和畢加索的《鏡前少女》等,其中的人物形象很明顯經過了夸張變形或視點轉換。同為草草的線條構成形態迥異的形象,其成因是多樣化的,其中較為深層的原因在于中西方對形象形成的情感期待不同。換言之,就是與中西方希望其繪畫中塑造的人物形象肩負著怎樣的表意功能,傳達出怎樣的思想情感有關。中國往往期待傳達出瀟灑不羈的精神氣質,這一傾向又與文人畫和老莊哲學有著千絲萬縷的關系。“重清談”和“尚意”是魏晉玄學和文人畫的核心理念和指導思想,這就使文人畫家在技法構圖上尚簡,在精神品格上崇尚清高、與世無爭,在思想上趨于隱逸。中國文人畫家對自我的最佳認知便反映到他們的繪畫中,他們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必定是充分反映自己的精神需求和品格標準的。而西方畫家往往表達躁動不安的內心和欲望,這與20世紀科技的發展與戰爭的恐怖帶給人們的緊張與不安有關。西方在極力追求理性到一個極點后,開始有意識地否定理性、否定藝術,在理性與完美發揮到極致的同時,開始反其道而行之,因而在恐慌與期待的心態之下他們渴望找到一種更富沖擊力的藝術語言,以便更好地表達內心。一言以蔽之,中國寫意人物畫可以用“悠然自得”來形容,西方抽象人物畫則可以概括為“躁動不安”。
三、結語
梁楷《潑墨仙人圖》和德·庫寧《女人一號》兩幅作品的創作不處在同一時期,甚至處于不同的文化背景中,但二者都為人物畫,都具有抽象性而具有可比性,正是不同的文化背景造成了這兩幅抽象人物畫各方面的差異。由這兩幅抽象人物畫的比較可以進一步探討中西方繪畫中抽象表現性的差異:“趨簡”“神似”與“清高化”為中國寫意人物畫的特征,“趨繁”“符號化”“扭曲化”為西方抽象繪畫的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