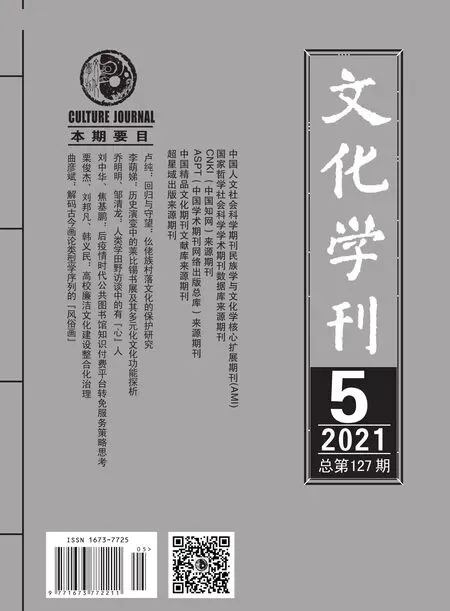淺論清儒關于“乾嘉三大考史名著”優劣的評判
王云燕
一、清儒對“乾嘉三大考史名著”的定位及評價取向
世人常將趙翼《廿二史札記》與錢大昕《廿二史考異》、王鳴盛《十七史商榷》相提并論,由此產生“乾嘉三大考史名著”一說。有并列就會有比較,比較中具有代表性的如梁啟超的論點。他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指出:“清代學者之一般評判,大抵最推重錢,王次之,趙為下。”[1]318與一般清儒的評判相反,張之洞對趙書推崇備至,《勸學篇》中明言:“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札記》。王氏《商榷》可節取;錢氏《考異》精于考古,略于致用,可緩。”[2]67梁啟超亦屬意趙書,如他所說:“錢書固清學之正宗,其校訂精核處最有功于原著者;若為現代治史者得常識、助興味計,則不如王、趙。”其中尤以趙書最值得稱贊,“陋儒或以少談考據輕趙書,殊不知竹汀(大昕晚年自號竹汀居士)為趙書作序,固極推許,稱為儒者有體有用之學也。”[1]318在錢、趙優劣問題上,張、梁二人的立場一致,與一般清儒尊錢(大昕)抑趙(翼)的取向截然不同。
按梁啟超的說法,不免給世人造成一種印象:錢大昕、王鳴盛做的是考據史學,趙翼做的是經世史學;趙書不善考據,故而為乾嘉學者所輕視,但趙書之可貴在于經世致用,此又勝過錢、王二書。事情果真如此?如此分類是否符合歷史實相?
將“求真”與“致用”判然兩分并不是中國的學術傳統,此為現代大學體制和職業學者出現以后的產物。古代學者并非如此,對于他們而言,“求真”與“致用”未嘗分離,“無用”是一句極重的罵人話。是以,說乾嘉學者因為沉迷于“求真”之考據學,所以輕視“致用”之《廿二史札記》,不啻以今概古,很難符合歷史實相。事實上,在清人眼里,《札記》從來都是與錢、王二書同列于考據史學。張之洞的《書目答問》就將三書并為“正史第一”條目下的“總考證”類,與“史評第十四”分屬不同條目[3]80。也正因三書同為考據學著作,才有相互比較的可能。
清代考據學相對于義理、詞章之學而言,所涉范圍很廣。考據宗旨或考據對象不同,其方法也可能大異其趣,本就沒有一個固定套路。清代學人對《廿二史札記》或有批評,但都局限于質疑其考證結論是否可靠,從沒有人將該書排除出考據學的陣營之外。其實梁啟超本人也一直將《廿二史札記》算在考據史學之列,而從未將其劃入他派。
民國以后,學術分類全然不同于清代,考據學的范圍大大窄化,其對應物不再僅僅是義理、詞章,而多為歷史解釋。在此背景下,似乎只有辨誤史實才算考據史學。故而周振鶴教授才會說:“《札記》之高并不在其考證的功力,趙翼是不擅長此道的,歷來的書目將其歸入考證類,并不合適。”[4]實則此處之“考證”已非清儒之“考證”了。
既然在清儒眼里,趙、錢、王三書都是考據書,那么《廿二史札記》與另兩書的區別就不在于是否考據,而在于用何種方法考據,考據的宗旨是什么。清楚這一點,我們才能明白三書地位之變化,以及張之洞為何青睞趙書。
二、錢、王、趙三書考據方式之不同
錢大昕在談及撰寫《廿二史考異》的緣由時曾說:
況廿二家之書,文字煩多,義例紛糾,輿地則今昔異名,僑置殊所,職官則沿革迭代,冗要逐時。欲其條理貫串,了如指掌,良非易事,以予佇劣,敢云有得?但涉獵既久,啟悟遂多,著之鉛槧,賢于博弈云爾。[5]
在他看來,正史之所以難讀,在于義例、輿地、僑置、職官等事項前后變化,名稱不一。撰述《廿二史考異》的宗旨就是要解決這些問題,讓世人能夠讀懂古書所言何事。因此,他采用了一種傳注經文的方式解釋正史。凡遇疑難之句便詳加注釋,集合各方材料,從文字訓詁到職官輿地無不注解,務求清楚明白。
王鳴盛考據的對象類于錢大昕,但他著書宗旨和考據方式則有所差異。如其所言:
學者每苦正史繁塞難讀,或遇典制茫昧,事跡樛葛,地理職官,眼瞇心瞀。試以予書為孤竹之老馬,置于其旁而參閱之,疏通而證明之,不覺如關開節解、筋轉脈搖,殆或不無小助也。[6]2
相比錢大昕的謙虛謹慎,王鳴盛的作風就顯得高調一些,其撰述方式也與錢氏不同。大抵王氏自比顧炎武,遂采用顧亭林《日知錄》的方法,將全書分為一個個小論題,引據史料,逐條證明。關于這些小論題的范圍,他明確指出:“書生匈臆,每患迂愚,即使考之已詳,而議論褒貶猶恐未當,況其考之未確者哉!蓋學問之道,求于虛不如求于實,議論褒貶,皆虛文耳。”[6]1言下之意,他本人不學那些史論家,隨便議論褒貶古人,而專事評議史實記載是否準確。
趙翼《廿二史札記》體例與王氏之書頗為相似,皆模仿顧亭林《日知錄》。他本人曾自謙地說:“或以比顧亭林《日知錄》,謂身雖不仕而其言有可用者,則吾豈敢。”[7]嘴上雖說“不敢”,但內心無疑是以《日知錄》為仿效對象。與王鳴盛不同,趙翼考據史學的內容主要不在輿地職官,而在鉤稽史實、排比史料。或者說,《廿二史札記》之所長,不在于商榷古書之誤,而在于把散落在古書各處的記錄按照特定論題集合起來,連綴成文,以見事情的來龍去脈,讀罷讓人有“紀事本末”之感。
這里需要特別強調,因為考據方法和考據內容有別,難易程度也不相同。楊樹達先生曾將“我國學者之治史籍者”分為兩派:“其一曰‘批評’,其二曰‘考證’。”這兩派都可以分為兩枝,就后者而言:
考證之第一枝曰考證史實,如錢竹汀、洪筠軒之所為是也;其第二枝曰鉤稽史實如趙甌北、王西莊之所為是也……于是考證派之兩枝于乾嘉之際,同時并起,而繼其后者,第一枝為盛……綜而論之,考證史實,為事較難,而所得反小;鉤稽史實,為之者較易,而收獲反豐。要之,非心思縝密,用力勤至者不能為,二者固無異也。[8]
這番話十分精妙地指出,趙翼與錢大昕、王鳴盛的區別是“考證派”內部的區別。錢大昕之“考證史實”與趙翼之“鉤稽史實”,其內容、方法不同,難易程度自然有所區別。清儒“最推重錢,王次之,趙為下”的理由,大抵就是錢書最難,趙書最易。周中孚在為錢大昕《廿二史考異》撰寫解題時便稱:
考史之書,至竹汀此編,誠所謂實事求是,得未曾有者也。同時王西沚(鳴盛)《十七史商榷》,考證輿地典制,頗不減于竹汀,惟其好取事跡加以議論,仍不免蹈前人史論之轍,且于《宋》《遼》《金》《元》四史未及商榷,其書究難與竹汀抗行。至趙云松(翼)《廿二史札記》,類敘事實,毫無發明,又別為一體,尤不可與是編相提并論焉。[9]
周氏之說只可作為楊樹達的論據。概而言之,錢、王、趙三書同為“考史之書”;錢、王同為一體,趙書“別為一體”;錢、王重于“考證輿地典制”,趙書則“類敘事實,毫無發明”。“類敘事實”較易,“考證輿地典制”較難,是故趙書尤不可與錢書“相提并論焉”。
換言之,趙書鉤稽史實較易,完全可以充當史學考據的入門讀物,錢書考證史實較難,卻只能供少數專家精研之用。《廿二史札記》的傳播范圍遠較《廿二史考異》廣泛,亦與此相關。周振鶴在評價趙書時,有一點睛之筆。
以今天的眼光看來,《札記》里的每一條實則一篇小論文,有些條目與今天的論文題目簡直一模一樣……而這種細致的踏實的功夫對于研究史學的人是一項必要的基本的訓練,因此《札記》在今天對青年學子依然有它的參考價值。但是《札記》的學術價值也僅在于此,不宜隨意拔高。如果說《廿二史考異》足以振聾發聵的話,《廿二史札記》則只是啟思開竅,不好同等看待的[4]。
對于史學研究而論,趙書為基本訓練,“只是啟思開竅”,錢書為專精研究,“足以振聾發聵”,當然前者更有普及價值。需補充說明的是,周振鶴所言“《札記》里的每一條實則一篇小論文”,這里的“小論文”不宜作狹隘理解。它不僅可以指今天撰寫的學術論文,更可以指清代樸學教育常用的“課藝文”。張之洞看重《廿二史札記》,就是因為它非常適合做考據學訓練的基礎讀物,尤其適合“課藝文”的體例。
三、張之洞對《廿二史札記》的推廣
1873年,張之洞簡放四川學政。一到四川就發現當地學風敗壞,讀書人不但終日埋首于時文小楷,而且異常迷信。他在《車酋軒語》中稱:“近今風氣,年幼方學,五經未畢,即強令為時文。其胸中常無千許字,何論文辭,更何論義理哉。”[10]196又說:“近年川省陋習,扶箕之風大盛。為其術者,將理學、釋老、方伎合而為一。”[10]198這些都是當年四川學風的真實寫照。
為改革四川學風,張之洞決心引入江浙考據學。他親自籌建尊經書院,意圖以此為陣地推廣漢學。他在《創建尊經書院記》中特別強調:“凡學之根柢,必在經史。讀群書之根柢,在通經。讀史之根柢,亦在通經。通經之根柢,在通小學,此萬古不廢之理也。”[10]371又說:“經是漢人所傳,注是漢人創作。義有師承,語有根據,去古最近,多見古書,能識古字,通古語,故必須以漢學為本,而推闡之,乃能有合。”[10]371尊經書院嚴格采用杭州詁經精舍的管理方式和教學模式。比如設立官、師考課制度,每月兩次,考課不用帖括時文,而是每課出四題,分別為經解、史論、雜文、詩賦各一題,限四日內交卷。
張之洞極力推崇顧炎武的《日知錄》,認為該書提供了訓練學術功底的不二法門。趙翼《廿二史札記》因模仿《日知錄》史學條目,而受到張的重視。《書目答問》中特意將《廿二史札記》與《翁注困學紀聞》《日知錄集釋》一同列入“考訂初學各書”,并稱“此類各書,約而不陋”[3]254。由此可見,張氏推崇《札記》主要因為它是乾嘉考據學的入門讀物。
《廖平年譜》載:“譚宗浚集尊經諸生三年以來課藝及下車觀風超等卷,刊為《蜀秀集》八卷。所刊皆二錢之教,識者稱為江浙派。”[11]《蜀秀集》第四卷收錄書院諸生“史論”課藝文,以下摘抄部分目錄:
卷四
秦郡縣/張祥齡
魏晉南北朝崇尚鄭學考/羅長玥
…………
史記列孔子于世家論/廖登廷
兩漢馭匈奴論/廖登廷
五代疆域論/廖登廷
其中“廖登廷”即廖平。以之對比《廿二史札記》條目,該書之教育功能,一目了然。正是在張之洞、譚宗浚等人的努力下,乾嘉漢學終于在光緒初年澤被蜀中,《廿二史札記》也因此得到四川學界的重視。
《書目答問》問世兩年后,唐友耕便開始在四川組織重新刊刻趙翼的全集。此后《甌北全集》重刊,時任四川總督丁寶楨、成都將軍恒訓、錦江書院山長伍肇齡等皆為之作序,竭力稱贊趙翼史學之成就。《廿二史札記》遂風行蜀地,成為蜀中士子讀史必備之參考書。
1898年,張之洞撰寫《勸學篇》,其中再次提到趙翼,稱“考史之書約之以讀趙翼《廿二史札記》。”尤為引人注目的是,此番趙翼的地位竟然越過了錢大昕、王鳴盛,“王氏《商榷》可節取;錢氏《考異》精于考古,略于致用,可緩”[2]67。不過錢、王、趙三書的位置再怎么重新排列,都不足以改變它們的基本功能。
張之洞說得很明確,史學教育首重趙翼《廿二史札記》,王鳴盛《十七史商榷》也可以選擇使用,至于錢大昕《廿二史考異》雖然學力深厚,作為專業研究也可,但不適合史學教育的當務之急。乾嘉學者評論三書“趙為下”,因為趙書最易;張之洞評論三書“趙為上”,同樣因為趙書最易。前者基于研究的需要,后者基于教育的需要。
與之相匹配,當年7月4日,張之洞、陳寶箴上奏朝廷,提議改革鄉試、會試,特別強調第一場要考中國史事,這當然不是讓人漫無邊際地空發議論,而是必須有本有據,論從史出。張之洞學宗乾嘉,深恨宋明史學游談無根,如今建議開設“中國史事”考試,自然要屏蔽一些令人炫目的史論性著作,《廿二史札記》的作用就更加凸顯。該書以考據學為本,路子純正,故不會導人以歧途,又淺顯易學,適合考官出題和學生作答,十分適合充當考試用書。庚子國變以后,清朝最高統治者下定決心實施新政,張之洞改革科舉制的夙愿終成現實。1901年8月29日,清廷正式頒布科舉改制詔令,規定:
著自明年為始,嗣后鄉會試,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二場試各國政治藝學策五道,三場試《四書》二篇、《五經》義一篇。[12]
為應付“頭場試中國政治史事論五篇”,趙翼《廿二史札記》遂成教輔,行銷海內。
綜上所言,清儒在錢、趙優劣問題上表現出兩種截然不同的評價取向,這與評論者的治學立場密切相關,可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值得注意的是,經由張之洞的推介,《廿二史札記》日益聲名鵲起,學術地位和影響力進一步擴大,逐漸超越錢、王,后來居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