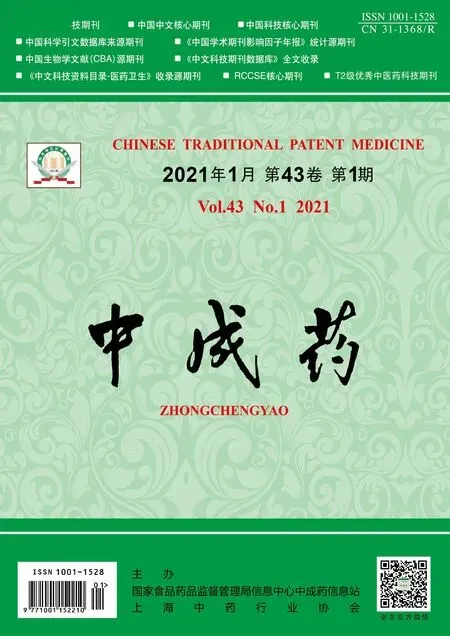基于現代驗案解析烏梅丸方證應用
高寰宇,王文寬,陳 聰,宋詠梅?
(1.山東中醫藥大學中醫學院,山東濟南 250014;2.山東中醫藥大學中醫文獻與文化研究院,山東濟南 250300)
烏梅丸出自《傷寒論·辨厥陰病脈證并治》,原文論其主治蛔厥、又主久利,清代醫家柯韻伯提出“烏梅丸為厥陰主方,非只為蛔厥之劑”,但多版《方劑學》 教材均將該方列入驅蟲劑,《中國藥典》(一部)[1]中首個適用病證也是蛔厥,眾多現代中醫醫師同樣未能準確理解應用該方。為此,本研究從現代中醫驗案著手,搜集應用烏梅丸原方或其加減方的成功案例,總結該方適宜病證的辨治特點,并探討它在中醫診療指南中的合理定位。
1 資料與方法
1.1 文獻、中醫醫案 文獻為中國知網(CNKI)數據庫中收錄的,中醫醫案為國內各類醫學期刊中發表的。
1.2 檢索策略 采用CNKI 高級檢索方式,檢索主題詞為“烏梅丸”and“驗案”or“舉隅”or“經驗”or“臨床”or“病例”or“病案”,根據本研究制定的納入、排除標準對文獻進行篩選。
1.3 納入標準 ①醫案中明確使用《傷寒論》 烏梅丸原方,或以其為主方加減;②醫案具備完整的首診資料,包括患者信息(性別、年齡)、癥狀描述、中醫診斷、辨證分型、治療原則、具體方藥;③醫案隨診療效需明確。
1.4 排除標準 ①醫案內容與烏梅丸、厥陰病無關;②醫案指出所用處方為烏梅丸與其他方劑合方;③治療措施聯用針灸、推拿、刮痧等中醫外治法或西醫治療;④醫案內容重復的只保留其中之一。
1.5 數據處理 基于本研究目的結合研究人員專業知識,對納入的醫案進行數據處理,提取重要文獻信息和醫案臨床資料,通過Excel 2007 軟件編制烏梅丸驗案信息采集表,分為文獻基本信息與醫案內容、具體組方用藥、數據規范化處理3 個副表,主要內容包括文獻來源、作者姓名、發表年限,患者性別、年齡,驗案中醫診斷、臨床癥狀、發作特點、辨證、治則,具體方藥組成及規范化后的診斷、辨證等。
1.6 個別信息處理 ①方藥劑型不區分顆粒與中藥飲片,統一為湯劑;②水煎方法不細分煎煮時間、湯液容量,統一為水煎內服;服藥頻次區別分服與頻服,不細分日二服、日三服;注明烏梅特殊處理、特殊藥引的應用;③統計數據時針對一藥多名的現象,參照“十二五”普通高等教育本科國家級規劃教材《中藥學》[2]進行規范統一,并根據相同版本的《中醫內科學》 《中醫婦科學》 《中醫外科學》《中醫耳鼻喉科學》 《中醫診斷學》 對原始中醫診斷、辨證分型進行規范化標注,如“久瀉”“腹瀉”“飧瀉”等表述大便次數增多,或糞質稀溏,或完谷不化的中醫診斷,統一規范為“泄瀉”;“寒熱錯雜”“上熱下寒”等表述寒熱癥狀兼見的辨證類型,統一規范為“寒熱錯雜”。
2 結果
本研究最終納入醫案220 則,來自139 篇文獻。
2.1 中醫診斷 共有65 種,以泄瀉頻次最高,其次是胃脘痛,頻率≥2.2%的高頻診斷共12 種,具體見表1。

表1 中醫診斷分布(頻次≥5,頻率≥2.2%)
2.2 病癥發作特征 共有83 條,主要為因情緒波動發作、發作有時間點性,具體見表2。

表2 病癥發作特征分布
2.3 中醫辨證 本研究中驗案涉及的中醫辨證方法包括六經、八綱、臟腑、氣血津液,有一些為2 種或2 種以上辨證方法的綜合應用。
2.3.1 六經辨證 共有28 則驗案,具體見表3。
2.3.2 八綱辨證 共有186 則驗案,其中寒熱錯雜出現頻次最高,其次是虛實錯雜,具體見表4。

表3 六經辨證分布

表4 八綱辨證分布
2.3.3 臟腑辨證 共有92 則醫案,以五臟為中心,有單論一臟,有關系兩臟,亦有少數涉及三臟、四臟,主要在肝、脾,具體見表5。

表5 臟腑辨證分布
2.3.4 氣血津液 共有19 則驗案,氣機逆亂出現頻次最高,其次是痰飲水濕,具體見表6。

表6 氣血津液辨證分布
2.4 泄瀉臟腑辨證 中醫辨證為泄瀉的醫案共有40 則,其中20 則采用臟腑辨證,主要涉及脾、肝,以肝脾不和者最多,具體見表7。
3 討論
關于烏梅丸的六經歸屬,古今醫家公認在厥陰[3],本研究立足于八綱、臟腑、氣血津液辨證,多方位解析烏梅丸方證內涵,并合理定義其功用類型。結果顯示,從八綱辨證角度出發,烏梅丸主治證型為寒熱錯雜、虛實錯雜;與辨證相應,大部分患者具備上熱下寒、虛實兼夾的證候群,而寒熱虛實之標本存在臨床差異,大多數以虛寒為本,兼見熱象,而且熱又有郁熱、濕熱、虛熱之分;針對該病機,本方用藥辛溫聯合苦寒,以達到寒熱平調之效[4]。大量驗案證明,烏梅丸不止為蛔厥專劑,更屬調和寒熱虛實之良方[5]。

表7 泄瀉臟腑辨證分布
在臟腑辨證中,以肝病最為突出,并且肝與其他四臟的辨證關系均有體現,臨床癥狀雖涉及各個系統,但其共通的病機均為肝失調達、客犯余臟。具體而言,肝氣失調,橫逆脾胃,因致痞滿嘔酸、腹痛急瀉;肝木郁結,化火刑金,常見逆氣喘悶、咽癢而咳;肝血虧損,竭乏腎本,一者頭痛眩暈、耳鳴目澀,再者遺精陽痿、痛經漏下;肝火升騰,上擾心君,故病心煩不寐、胸痹滯痛,或兼潮熱陣汗、口苦消渴,種種病癥龐雜無章,卻皆具數變、急迫、陣作等風木為病的典型特點,這是烏梅丸證以肝為中心、旁涉四臟的病機辨證關鍵[6]。研究顯示,情緒波動是發病的最主要誘因,人的精神情志活動除受心神主宰之外,還與肝的疏泄功能密切相關[7],即情緒是肝臟疏泄功能的具體體現[8],這也間接佐證了肝臟功能失調與本證發作的內在聯系。
氣機逆亂為氣血津液辨證之主要,揭示了厥陰為病的關鍵。劉力紅[9]教授認為,厥陰為闔,闔陰以升陽,司樞氣機升降,病則陰失其闔,妄瀉無度,龍雷相火攀升,表現為熱證;元陽不萌,君火無助,脾土弱而不固,表現為寒證,病久陰陽互損,致使表征寒熱相錯、虛實難辨。不僅如此,氣機逆亂、升降失常更直接表現為泄瀉、便秘、呃逆、咳嗽、喘哮、煩躁、不寐、手足厥冷、經帶不調、頭胸腹痛等病癥。烏梅丸組方諸藥溫清攻補之外,兼具氣化浮沉,酸苦內斂能降瀉,辛甘發散助升浮,對調和陰陽、恢復升降具有重要意義[10]。另外,本證發病有較為突出的時間點性,常在于丑至卯時,此值肝經當令,處厥陰樞機之位,重陰盡而一陽生,故多發“陰陽氣不相順接”之病[11],因此顧植山[12]教授主張,凡至厥陰經欲解時癥狀出現或加重者,可放手應用烏梅丸。
綜上所論,烏梅丸絕非專主蛔厥。《方劑學》 教材據治法分類[13],驅蟲劑對應消法。原著雖明言烏梅丸主治蛔厥,但用意卻非直接驅殺蛔蟲,而是平調寒熱虛實,并用剛柔補瀉,開通氣機升降,使陰陽氣平則蛔蟲自安,這種組方恰合歷代醫家對和法的共識。因此,本研究認為和解類方才是烏梅丸較為合適的歸屬。
4 結語
本研究基于臨床數據多角度分析烏梅丸方證內涵,從八綱而言,為寒熱、虛實錯雜;從臟腑而言,以肝為中心,旁及四臟;從氣血津液而言,主在氣機逆亂、升降失常。同時認為,在以治法分類方劑的體系下將烏梅丸列于和解劑,更能體現其中的病機規律與應用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