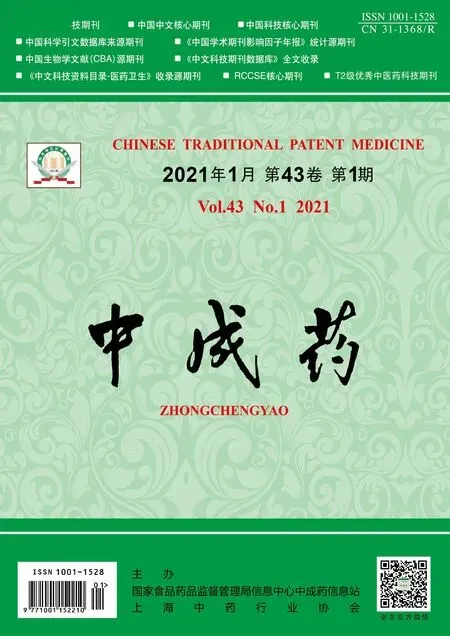基于網絡藥理學研究腦血疏口服液治療腦出血的作用機制
張友剛 李昊楠史永平 張姍姍李曉彬曾英姿韓利文田青平?劉可春
[1.山西醫科大學藥學院,山西太原 030001;2.齊魯工業大學(山東省科學院), 山東省科學院生物研究所,山東濟南 250103;3.山東沃華醫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山東濰坊 261205;4.山東第一醫科大學藥學與制藥科學學院,山東濟南250001]
腦出血(cerebral hemorrhage,CH)是一種常見的腦血管疾病,其通常是由腦內血管發生病變、壞死、破損引起,大多數患者不是由于腦出血導致原有病情加重,而是由于腦出血引起的一系列生理病理變化致殘致死[1-2]。腦出血一般發病較為突然,若不及時治療,輕則使患者留下后遺癥,重則導致患者死亡[3]。腦出血在臨床上病死率極高,受到了醫藥部門的高度重視,臨床上對于腦出血的治療包括西醫治療、中醫治療、中西醫結合治療,其中以中西醫結合治療的效果最佳。腦出血是影響我國國民健康的重大公共衛生問題,防治腦出血的發生、發展十分重要。
中醫認為,腦出血為“瘀血阻滯,脈道不利”,治療上多采用活血化瘀的方法[4]。腦血疏口服液是我國國家中藥保護品種,具有益氣、活血、化癖,通腑的功效[5]。腦血疏口服液由黃芪、大黃、牛膝、牡丹皮、石菖蒲、川芎、水蛭7 味中藥制成,是唯一一個治療腦出血的中成藥。臨床實驗表明腦血疏口服液可以顯著加快血腫吸收、具有顯著改善神經功能受損和臨床綜合癥狀的作用,對于腦出血患者的急性期和康復期具有良好的療效。中藥復方成分復雜,這種復雜性使得中藥復方的藥效物質基礎和作用機制不明確[6]。網絡藥理學是基于網絡生物學和系統生物學開發的一門新興學科,隨著與網絡藥理學相關的多學科的快速發展,國內外越來越多的學者運用網絡藥理學來探索疾病與藥物更深層次的關聯[7]。本研究利用網絡藥理學技術發掘腦血疏口服液治療腦出血的機理,通過建立“藥效成分-靶標-通路”網絡模型,深入探討腦血疏口服液治療腦出血的藥效物質、作用機制,為中藥現代化研究提供參考。
1 方法
1.1 腦血疏口服液化學成分信息的收集 通過TCMSP(http:/ /lsp.nwu.edu.cn/index.php)及文獻收集腦血疏口服液7 味中藥(黃芪、大黃、牛膝、牡丹皮、石菖蒲、川芎、水蛭)的全部化學成分,并通過TCMSP、Pubchem(https:/ /pubchem.ncbi.nlm.nih.gov/)以及查閱相關文獻獲得這些成分的化學結構,并保存Smiles 格式。
1.2 活性成分的篩選 口服吸收利用度(OB/%)和藥物相似性(DL)是藥物篩選過程中兩個重要的ADME 參數,常用于評價化合物的成藥性[8]。本研究選取同時滿足OB≥30%、DL≥0.18 的化合物作為潛在活性成分,結合相關文獻報道,對水蛭中不滿足以上2 個條件的活性成分也進行收錄[9]。
1.3 成分靶點的篩選、疾病靶標的收集 Swiss Target Prediction(http:/ /www.swisstargetprediction.ch/)服務器是基于分子的二維和三維結構與已知蛋白分子的作用程度來預測化合物的潛在靶標,從而精準的得到未知化合物的作用靶標[10]。將篩選得到的潛在活性分子的Smiles 結構導入該數據庫,并選定研究物種為人類(homo sapiens),導出潛在化學成分的靶標。以“cerebral hemorrhage”為關鍵詞,檢索GeneCards(https:/ /www.genecards.org)數據庫、DisGeNET(http:/ /www.disgenet.org/search)數據庫中腦出血相關基因,并去除重復基因。
1.4 “單味藥-活性成分-作用靶點”網絡的構建 根據以上預測結果,采用Cytoscape3.7.1 軟件構建“單味藥-活性成分-作用靶點”關系網絡模型,節點(node)代表單味藥、潛在活性成分與潛在作用靶點,邊(edge)用來連接單味藥與活性成分、活性成分與作用靶點,展現單味藥-活性成分-作用靶點之間的聯系。
1.5 交集基因的獲取及其蛋白質相互作用網絡的構建 將腦血疏口服液作用靶點基因和腦出血的相關基因分別輸入在線韋恩圖繪制網站(http:/ /bioinformatics.psb.ugent.be/webtools/Venn/)獲取交集基因,交集基因即為腦血疏口服液治療腦出血的潛在靶點。將獲取的交集基因導入String 數據庫(https:/ /string-db.org/),然后將獲取的交集基因信息導入Cytoscape 3.7.1 繪制交集基因蛋白質相互作用網絡。
1.6 交集基因的生物分子功能注釋 將獲取的交集基因靶點信息采用 David6.8 數據庫(https:/ /david.ncifcrf.gov/)進行GO 注釋分析和KEGG 通路分析。其中GO 注釋分析分為3 個部分,分別為生物過程分子功能(molecular function,MF)、細胞組分(cellular component,CC)和生物過程(biological process,BP)。利用David6.8 數據庫(https:/ /david.ncifcrf.gov/)進行通路富集分析,將通路富集分析的結果通過Omicshare(http:/ /www.omicshare.com/tools/index.php/)對富集分析結果進行可視化處理。
1.7 主要活性成分-靶點分子對接 LeDock 是蘇黎世大學趙洪桃在博士期間開發的一款跨平臺分子對接軟件,在速度和準確度上均呈現出強勁的優勢[11],它采用遺傳算法和模擬退火算法相結合的方法對配體的構象進行取樣[12],其蛋白處理過程十分方便,可實現水分子、雜原子、離子的去除,同時氫原子也可以自動加上。將“1.6”項下的主要活性成分通過Chem3D Pro 14.0 得到其MOL2 格式,通過Uniprot(https:/ /www.uniprot.org/)、RCSBPDB(http:/ /www.rcsb.org/)數據庫獲取主要活性成分作用于疾病靶點的PDB 蛋白晶體,并保存為PDB 格式,為分子對接做好前期準備。將靶點蛋白晶體及對應的配體先后導入LeDock 進行分子對接,保存對接后產生的DOK 文件用于展示對接結果。
2 結果
2.1 腦血疏口服液7 味中藥潛在活性成分及腦出血相關靶點 在TCMSP 數據庫中篩選出潛在活性成分,分別為黃芪20 種,石菖蒲4 種,牛膝20 種,牡丹皮11 種,大黃16 種,川芎7 種,合并去重后得到70 種,再查閱文獻發現水蛭45 種潛在活性成分,最終得到115 種,具體見表1。通過DisGeNET 數據庫搜集到疾病靶標66 個,在Genecards數據庫以Relevance score 的中位數的2 倍為卡值,獲得647 個疾病靶標,將2 個數據庫的疾病靶標去重,最終得到656 個。
2.2 “單味藥-活性成分-作用靶點”網絡 將單味藥-活性成分信息、活性成分作用靶點信息導入Cytoscape 3.7.1,采用Merge 工具繪制“單味藥-活性成分-作用靶點”圖,見圖1,一共有561 個節點、1 833 條邊。通過Network Analyzer 計算網絡拓撲參數,發現潛在成分作用靶點Degree值(網絡模型中每個節點與其相連節點的數目)>20 的有15 個,排名前5 的是TDP1、MAPT、CYP19A、MBNL、CA1,分別有69、57、26、26、24 個化合物與其發生相互作用。
2.3 交集基因及蛋白質相互作用網絡 通過在線韋恩圖,得到腦血疏口服液潛在活性成分作用靶點與腦出血疾病作用靶點的交集基因有66 個,見圖2。將其導入String 數據庫,經Cytoscape 3.7.1 處理后得到蛋白質相互作用圖,見圖3,包括66 個節點、和595 條邊,平均節點度值為18.03。

表1 腦血疏口服液中7 味中藥潛在活性成分

續表1

圖1 腦血疏口服液成分靶點網絡

圖2 腦血疏口服液成分靶點韋恩圖

圖3 交集基因蛋白質相互作用
2.4 生物功能通路分析 將66 個基因導入David 數據庫進行GO 分析,以P<0.01、錯誤發現率(false discovery rate,FDR)<0.05 為標準進行篩選,結果見圖4。由此可知,從生物過程層面上看,腦血疏口服液對蛋白質自磷酸化、平滑肌細胞增殖的正調控、肽基酪氨酸磷酸化、對脂多糖的反應、磷脂酰肌醇介導的信號傳導、血管生成、細胞增殖的正調控等影響較大;從細胞組分層面上看,腦血疏口服液對質膜、細胞表面、受體復合物、膜筏、胞質溶膠、細胞外間隙等影響較大;從分子功能層面上看,腦血疏口服液對酶結合、蛋白酪氨酸激酶活性、蛋白質結合、跨膜受體蛋白酪氨酸激酶活性、相同的蛋白質結合、絲氨酸型內肽酶活性、四氫生物蝶呤結合、血紅素結合等影響較大。前20 條通路見圖5。

圖4 腦血疏口服液治療腦出血候選靶點的GO 富集分析

圖5 KEGG 分析
2.5 腦血疏口服液活性成分-靶點-通路網絡模型 將富集分析排名前20 的通路所對應的腦血疏口服液潛在活性成分和作用靶點構建“活性成分-靶點-通路”網絡模型,見圖6,包括116 個節點、366 條邊。由此可知,ESR1、AKT1、AKT3、EGFR、PIK3CA 節點度值排名靠前,可能是腦血疏口服液治療腦出血的核心靶點。
2.6 分子對接 將活性成分-靶點-通路網絡中排名前五的化合物與其作用于腦出血的靶點進行分子對接,結果見表2,可知槲皮素與基質金屬蛋白酶3(MMP3)具有較好的結合活性,大部分活性成分與其作用的治療腦出血的靶點具有良好的結合性能。再將已知的能特定作用于MMP3 的抑制劑伊洛馬司他(Ilomastat,PubChem CID:132519)與1HY7 進行分子對接,其結合能為-10.39 kcal/mol。另外,槲皮素、伊洛馬司他都是通過疏水相互作用、氫鍵、配位鍵與1HY7 相互作用,以PyMol V1.8 和Ligplot+V2.1 展示對接結果,見圖7。

圖6 腦血疏口服液治療腦出血活性成分-靶點-通路網絡

表2 腦血疏口服液主要活性成分-作用靶點分子對接結果

圖7 1HY7 與槲皮素、伊洛馬司他的分子對接
3 討論
腦出血是指非外傷性腦內實質出血,腦出血后腦組織會發生一系列病理生理變化,分為原發性損傷和繼發性損傷,前者包括血腫增大、血腫機械壓迫,后者包括血紅蛋白毒性作用、炎性反應、凝血酶釋放、局部腦組織血流量減少等[13]。腦出血治療早期以消除血腫為主要治療目的,后期以繼發性損傷中的炎癥損傷為主[14-15]。
本研究系統分析了腦血疏口服液的有效成分,構建了化合物-靶點-通路網絡,在該網絡中起關鍵作用的是黃芪紫檀烷苷、槲皮素、漢黃芩素、川芎嗪、桉脂素等。在腦部血管的修復過程中,血管內皮祖細胞起著關鍵的作用。血管內皮祖細胞源于骨髓,被釋放至外周血液后根據需要可以分化成各種細胞,當分化成內皮細胞可以促進血管的新生以及內皮破損的修復在各種病理和組織工程學領域有廣泛應用[16-17]。孫軍[18]等研究表明,槲皮素能夠刺激血管內皮祖細胞的增殖與分化,從而促進損傷血管的修復。川芎嗪能夠保護受損的血管內皮細胞,且在一定濃度范圍內呈現出劑量依賴[19]。除此之外,川芎嗪具有較強的抗血小板作用,和一定的抗血栓作用[20]。川芎嗪可能通過抑制血小板聚集、降低血液黏滯度、改善腦部血管循環,從而達到避免腦部組織缺血缺氧的目的。腦出血后,缺血中心區將發生不可逆性的神經損傷,而缺血半暗帶發生的神經元細胞凋亡是可逆的[21]。漢黃芩素通過抑制小膠質細胞的炎癥激活來保護神經元細胞,而不直接作用于神經元細胞[22]。上述文獻報道與本研究通過網絡藥理學預測的槲皮素、川芎嗪、漢黃芩素可能的活性作用一致。除此之外,存在一些未被報道的活性成分,將成為未來研究腦出血治療腦出血的潛在方向,如黃芪紫檀烷苷、桉脂素等。
腦血疏口服液治療腦出血涉及多個靶點,成分-靶點-通路網絡提示,ESR1、AKT1、PIK3CA、AKT3、EGFR、PTGS2、MMP2、MMP3 等靶點在治療腦出血的過程中發揮著重要的作用。蘇氨酸蛋白激酶AKT1 和AKT3 能夠激活PI3K-Akt 信號通路,從而促進腦出血后局部腦組織缺血造成的損傷神經干細胞的增殖[23]。MMP2 和MMP3 同屬MMPs,二者的激活能夠誘發腦出血后炎癥反應的發生,炎癥反應導致血腦屏障的破壞以及腦部神經功能的損傷,抑制MMPs 的過表達能夠起到保護血腦屏障及腦部神經的作用[24]。除此之外,成分-靶點-通路網絡揭示了諸如PTGS2、NOS2、NOS3 等炎癥相關的靶點在治療腦出血時的重要性。在分子對接驗證過程中發現,槲皮素和伊洛馬司他與1HY7具有較好的結合能力,兩者結合位點相同,而且都能夠與MMP3 中的鋅形成配位鍵,抑制MMP3 的表達,從而驗證了靶點預測的可靠性。
本研究將所得到的靶點進行KEGG 通路分析得到與腦出血可能相關的通路,如PI3K-Akt、腫瘤壞死因子(TNF)、低氧誘導因子-1(HIF-1)、細胞凋亡(apoptosis)、ErbB、Rap1 信號通路等,與炎癥、代謝、血腦屏障功能、神經元保護及細胞凋亡密切相關。腦出血后,由于血腫等原因致使局部組織血流量減少,缺血部位組織細胞就會處于低氧狀態。HIF-1 信號通路的激活在缺血后細胞代謝中的作用發揮著重要的作用,參與重建細胞代謝途徑來實現對腦組織的保護[25]。腦出血患者發病幾天后血腫程度與TNF-α 水平呈正相關[26],其高表達是血腦屏障破損、炎癥反應、神經細胞凋亡等繼發性損傷的重要原因[15]。腦血疏口服液活性成分可能通過作用于TNF 信號通路相關靶點,抑制TNF-α 的過表達,從而達到保護血腦屏障、減少神經細胞的凋亡等目的。
綜上所述,腦血疏口服液通過多成分作用于多靶點,從而協同調控多種通路,從整體網絡層面發揮抗腦出血作用,展現了傳統中藥有別于小分子化藥的作用特點。關于腦血疏的關鍵活性化合物、作用靶點和通路還需要深入的驗證研究,為今后臨床治療提供理論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