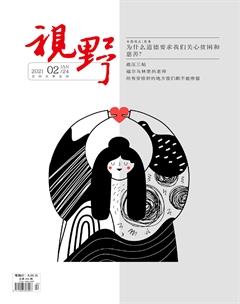生命好在無意義
木心
1
任何理想主義,都帶有傷感情調。
所有的藝術,所已有的藝術,不是幾乎都浪漫,是都浪漫,都是浪漫的,這泛浪漫,泛及一切藝術。當我自身的浪漫消除殆盡,想找些不浪漫的藝術來品賞,卻四顧茫然,所有的藝術竟是全都浪漫,而誰也未曾發現這樣一件可怕的大事。
2
上帝不擲骰子,大自然從來不說一句俏皮話。人,徒勞于自己賭自己,自己狎弄自己。
3
往常是小人之交甜如蜜,君子之交淡似水,這也還像個話,甜得不太荒唐,淡得不太寂寞。后來慢慢地就不像話了,那便是小人之交甜搶蜜,君子之交淡無水,小人為了搶蜜而撲殺,君子固淡,不晤面不寫信不通電話,淡到見底,干涸無水。
4
美國老太太,吹著口哨散步,我遇見過不止一次。轉念中國,幾千年也不會有此等事。種族的差異,可驚嘆的宿命。
5
在西方,下雨了,行人帶傘的便撐傘,無傘的照常地走,沒見有聳肩縮脖子的狼狽相。
在西方,道途兩車相撞,雙方出車,看清情況,打電話,警察來公斷處理(從出事起到警察到達之前,雙方不說一句話)。
僅此二則,立地可做的事,在中國,一百年后也未必能做得到。
6
自尊,實在是看得起別人的意思。
而在宇宙中,人的“自尊”無著落。人,只能執著“自尊”的一念。此一念,謂之生;此一念,謂之死。
7
猶太諺語:“人類一思索,上帝就發笑。”
上帝一思索,人類也發笑。
8
即使是聰明絕頂的人,也不可長期與蠢貨廝混,否則又多了一票蠢貨。
9
在精神世界經歷既久,物質世界的豪華威嚴實在無足驚異。凡為物質世界的豪華威嚴所震懾者,必是精神世界的陌路人。
10
“曠達”,僅是有情世界中所可能保持的一種態度,越出這個局限就不成其為態度。多少大智者都曠達到局限之外,竟從來沒有人指斥他們的失態、無度。
11
生命好在無意義,才容得下各自賦予意義。假如生命是有意義的,這個意義卻不合我的志趣,那才尷尬狼狽。
12
飽經滄桑而體健神清的人讀書最樂,他讀,猶如主演協奏曲,塵世的森羅萬象成為他的樂隊。
13
藝術是最虛幻不過的了,全憑人的領悟而存在,這樣地非物質,這樣地非附在物質上不可。
14
使愛情的舞臺上五光十色煙塵陡亂的,那是種種畸戀,二流三流腳色。一流的情人永遠不必殉隕,永遠不會失戀,因為“我愛你,與你何涉”。
15
愛了一個人,沒有機會表白,后來決計絕念。再后來,消息時有所聞,偶爾也見面——幸虧那時未曾說出口,幸虧究竟不能算真的愛上。
又愛了另一個人,表白的機會不少,想想,懶下來,懶成朋友,至今還朋友著——光陰荏苒,在電話里有說有笑,心中兀自慶幸,還好……否則苦了。
16
世俗的純粹“道德”是無有的。智慧體現在倫理結構上,形成善的價值判斷,才可能分名為道德。離智慧而存在的道德是虛妄的。如果定要承認它實有,且看它必在骨節眼上壞事敗事,平時,以戕賊智慧為其功能。
17
文學是可愛的。生活是好玩的。藝術是要有所犧牲的。
18
確有慧心的人,到了二十五、三十五歲時,回顧已逝的青春,必有所悔,必有所悟,因而很愿意對比他(她)小十歲、二十歲的朋友傾談衷款。能指點別人,是快慰的,如果聆者順從、感恩,那就愈加使大哥大姐為你盡心竭力。所以年輕者不必對年長者畏懼,盡可以開誠坦懷,企求年長者的提助。
19
“死”,不是退路,“死”是不歸路,不歸,就不是路,人的退路是“回到內心”。受苦者回到內心之后,“苦”會徐徐顯出意義來,甚至忽然閃出光亮來,所以幸福者也只有回到內心,才能辨知幸福的滋味。
20
所謂無底深淵,下去,也是前程萬里。
(丫丫摘自上海三聯書店《素履之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