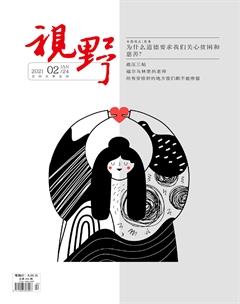我從未做過好學生
(一)

我從未做過成績優異、引人注目的“好學生”,其實我稱得上用功,早起晚歸,每日埋頭做題,但成績一直勉強維持在中等水平。
我們的物理老師有一次上課時直接說:“我只管前十名的學生,你們其他人愛怎么樣就怎么樣,只要不在我的課堂上搗亂就行。”這句話對我刺激很大,原來我們在他眼中就是不能提高升學率的廢物,隨你們自生自滅好了。
其他科目的老師雖然不會明說,但態度是一致的。
成績好的學生座位在最前面,成績中等的在中間,差的在最后,而我就常常坐中間靠后的位置。
成績好的不愿意跟我來玩,我也不愿跟成天睡覺的“差生”混,就是那么努力地往上爬又爬不上去,又不甘心往下掉。那種卡在中間的無力感只有我自己能體會,老師是看不見我的。
而這在當時和現在,都被視為正常。班級像是一個斗獸場,弱肉強食,弱者不配得到關注。就像是音樂劇《近乎正常》里一直被無視的女兒問:“他(哥哥)是光輝,是愛,是主角,我在哪里?我在哪里?”
這種哪怕就站在人們面前也被當成空氣的零存在感,很容易讓人連自己都不會愛自己了,連自己都嫌棄自己。我在哪里?無人在意。
(二)
小時候背課文,都是要去組長那里背的,背過了才能放學。每當我去組長那里背時,坐在一邊的小偉就故意透露出我接下來要背的字句,組長就說:“有人告訴你下面的了,不算!你要重背一遍。”于是我又重背,小偉又來搗亂,如此再三。
等到他來背,我也故意學他。誰知他立馬號啕大哭起來,說我欺負他,然后還告訴了老師。老師讓我在外面罰站。
我要解釋,老師說:“你看人家哭得那么兇!你也太過分了。”等老師走后,小偉又沖我笑了一下。那個笑,讓我第一次產生了毛骨悚然的感覺。
(三)
同學說起對我的印象:“你特別愛發言,看你會的不會的你都舉手。”我想了想,說除了喜歡出風頭愛虛榮這些心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原因是忍受不了尷尬。
“你想想老師提個問題吧,大家都埋著頭,現場會多尷尬啊!這個時候我就會飽受內心折磨,覺得不站出來,老師會尷尬,大家都尷尬,我自己也尷尬……”
(四)
讀高二的時候,一次模擬考試,數學只考了37分。我數學成績雖然不好,但從來都沒有考得這么低,心情真是非常沮喪。
分數都是老師在班級上一個個念出來的,念到我時,數學老師說:“鄧安慶這次沒考好,是因為他之前生病了。”當時我特別感激這句話,雖然我心里知道考得不好跟生不生病沒有關系。
(五)
記得大學教我們俄羅斯文學的老師,一學期都在給我們講那些偉大的俄羅斯作家們,有時候講著講著像是內心有很大的起伏,嘆口氣又接著講。
期末考試不發試卷,就是讓我們學會唱《國際歌》。文娛委員小聲地帶了個頭哼起來,大家稀稀拉拉跟著合唱。
聽著我們唱完,老師說了一句:“這其實是一首很悲傷的歌曲。”
(六)
睡著睡著特著急,一邊睡一邊想要遲到要遲到了,老師講的知識點我要錯過了,考試的題目還沒有來得及溫習,卻動彈不了,就是心里急得不行。
終于狠命睜開眼,窗外學校的鐘聲適時響起,學生喧嘩的聲音噗地一聲在耳邊響起。陽光在窗頭閃動,樹影婆娑,我忽然想起我不是學生了,現在不用上課了,真是太好了。
(緩緩摘自《優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