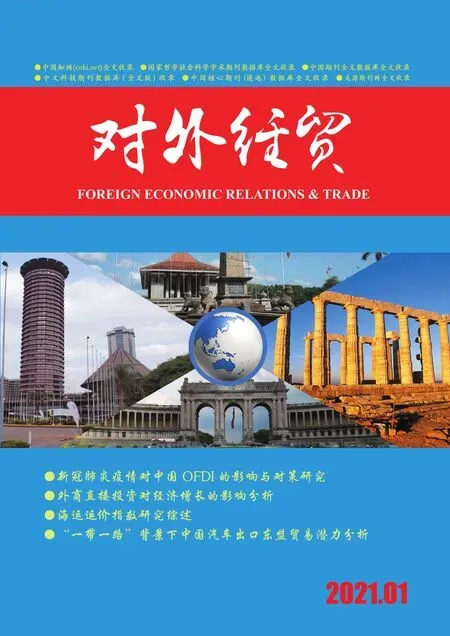全球價值鏈視角下我國制造業生產長度與產業動態調整
高理翔 苑鵬飛
(1.華東政法大學 商學院,上海 201620;2.中國社會科學院 研究生院,北京 100102)
一、引言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通過對外貿易與合作,在全球化的進程中創造了一系列舉世矚目的成績。隨著全球化的不斷深入,全球經貿體系不再是以傳統貿易分工為主導的區域范圍貿易模式,以全球價值鏈為核心的國際分工與區域產業模式逐漸興起。國際貿易模式的變化對我國擴大市場開放與產業結構的調整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鑒于國際化分工的相對固化,特別是在面臨環境污染以及勞動要素成本上升的背景下,針對勞動密集型產業,如何引導制造業產業轉型升級顯得尤為突出。2010 年以來,我國為擺脫產業分工的低端鎖定,正不斷改進粗放式的發展模式,特別是聚焦產業特點與經濟著力點的改變。根據《全球制造業創新指數白皮書》披露的數據來看,2019 年我國制造業在全球制造業創新評測中入選世界前15 強,制造業在技術與競爭力上的不斷增強,充分表明在制造業層面的轉型初具成效。
在價值鏈制造業增值生產長度不斷提升的背景下,結合《中國制造2025》的產業結構發展戰略,分析在全球價值鏈測算體系下我國制造業整體生產長度,技術型制造業相較于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是否具有一定優勢,亟待面臨轉型的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生產長度發展現狀。針對這些問題,采用Zhi Wang et.al(2017)[11]的復雜全球價值鏈測算體系,嘗試測算基于制造業加工生產所創造的增加值流向(前向聯系)與國內加工生產所需要的增加值來源(后向聯系)來分析在全球價值鏈中制造業的增值生產長度,由此對于我國如何動態調整產業結構逐步適應與緩解供求機制,保持制造業優勢,逐步將勞動密集型制造業逐步過渡到服務化、技術化的制造業提供相應的建議。
二、文獻回顧與問題的提出
價值鏈理論最早由Porter 在20 世紀80 年代《競爭優勢》一書中提出,最早主要針對分析行業間的產業分工理論。而后Kogut(1985)、Gereffi(2001)分別將價值鏈的研究主體從企業內部擴大到全球化價值鏈的范疇中,研究認為在全球化的發展背景下,一國制造業產出不僅僅局限于國內層面的生產、銷售、流通環節中,更是能夠跨越國界,從產品分工、增值的角度將各國的制造業生產納入到全球的價值鏈體系中。
目前,伴隨著全球價值鏈理論體系的不斷完善,學術界逐漸將全球價值鏈理論與一國產業的競爭力聯系在一起。特別是在全球化產業分工模式下,產品間的貿易關系不斷增強,傳統制造業依據產品出口、進口的核算指標存在著較高重復計算的情況,為有效核算在全球價值鏈中一國制造業生產長度的問題,貿易增加值核算方法逐漸成為全球價值鏈研究中的焦點問題。
Hummels(2001)[1]開創性地基于垂直專業化(VS)的測算方法對價值鏈進行核算。基于此類方法,張彬和桑百川[16](2015)在測算了我國制造業的出口垂直專業化水平后發現:我國制造業整體垂直專業化水平有所提升,尤其在資本和技術密集型行業中垂直專業化程度較高。在Hummels 理論模型的基礎上,Koopman(2012)[7]、Zhi Wang et.al(2013)[10]提出基于國家增加值出口分解的一國總出口分解測算方法(KWW 方法)與基于制造業加工生產所創造的增加值流向(前向聯系)與國內加工生產所需要的增加值來源(后向聯系)的價值鏈生產長度測算方法(WWZ 方法)。針對此類方法,劉琳和盛斌等(2017)[14]、戴翔等(2017)[13]測算后認為:我國制造業技術型行業的生產長度與競爭力正不斷提升,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競爭力較強,但在生產長度上仍舊稍顯不足。

圖1 WWZ 價值鏈貿易出口增加值分解模塊
從Zhi Wang et.al(2017)[11]的研究來看,上述方法主要聚焦于制造業企業在全球價值鏈中嵌入度分析。為更有效地將產業全球價值鏈的生產長度和生產位置進行綜合性分析,王嵐等(2014)[15]、戴翔等(2015)[12]提出了復雜價值鏈核算體系(WWYZ 方法),分析結果認為我國制造業整體得益于國際分工,在生產長度上有了較大的提升,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整體生產長度有了一定的提升,制造業層面存在一定的分化情況。在梳理了已有的文獻后,為更有效分析我國現行制造業在國際分工中所處的地位,本文嘗試將復雜價值鏈核算體系中的生產長度和制造業加工生產的生產增加值的流向相結合,以此來分析在我國制造業所存在的問題。
三、制造業增值生產長度現狀與存在問題分析
首先需要明確區分制造業生產長度中簡單與復雜價值鏈的生產過程以及前向與后向聯系。區分簡單與復雜價值鏈的關鍵在于明確在加工增值后不再被進口國再加工并通過貿易流動與加工增值再返還本國。我國制造業在要素生產中參與國際化分工的深入程度,體現在產業生產增值層面附加值的高低;而前向后向聯系則是從制造業加工生產所創造的增加值流向與來源進行劃分。簡單或是復雜價值鏈主要反映一國制造業加工生產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的嵌入度,而基于前向與后向聯系的分析主要刻畫了一國制造業加工生產整體的生產長度,反映制造業競爭力。故本文采用2016 年世界投入產出數據庫、ULBE GVC 數據庫測算了我國制造業在2000—2014年間的制造業生產長度數據,并根據《國際標準產業分類》第四版的劃分標準,測算了相應勞動、資本、技術密集型產業的價值鏈生產長度體系。
根據圖2 的測算指標來看,plv、ply 分別代表基于前向聯系與后向聯系的測算維度,而s、c 則是分別代表簡單與復雜價值鏈的生產過程。顯然,自2000 年以來,我國整體制造業的簡單價值鏈生產長度得到了較大的提升,尤其是在后向聯系的生產長度層面,整體制造業生產長度由2000 年的4.40 上升到4.76,而在勞動密集型產業層面,由2000 年的4.27 上升到4.61,這充分表明我國現行制造業專業化分工、嵌入度不斷提升;而基于前向聯系的維度來看,相較于后向聯系,增長速度相對較為平緩,由2000 年的4.83 上升到4.86。

圖2 基于不同項聯系的制造業與勞動密集制造業簡單價值鏈生產長度
主要可以從兩個方面看待制造業簡單價值鏈的生產長度的變化,一方面而言,在排除了2008 年國際金融危機以及自然災害對我國制造業造成的沖擊,整體制造業生產長度有了較大的提升,得益于我國所倡導的產能轉換與技術升級對于勞動密集型產業的政策引導,再加之東南亞國家勞動要素的優勢,這對于我國制造業加快結構升級、促進價值鏈攀升提供了源動力;尤其是在制造業生產增值流向來看,源源不斷的技術創新與人力資本需求的融合,對于促進制造業專業化生產,提升價值鏈生產長度帶來了新契機。從另一方面而言,如何看待基于前向聯系的簡單價值鏈生產長度增長速度相對放緩的問題。由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往往依賴于規模效率與結構紅利得以快速發展,環境問題一直成為勞動密集型產業的頑疾所在,自2012 年以來,綠色協同發展戰略正不斷提上政府議程,制造業在納入環境與要素利用率規制后,現有的結構基于產業發展的慣性,很難快速匹配綠色低碳的發展需求,因此在整體增長率上的增速趨于放緩。
在討論了簡單價值鏈生產長度后,結合我國宏觀政策的發展背景,為進一步考慮在加工后出口再進口的增值過程,即復雜增值過程,進一步分析基于前向、后向聯系下的復雜價值鏈生產長度,如圖3 所示。

圖3 基于前向聯系的整體制造業與勞動、技術密集制造業復雜價值鏈生產長度
由圖3 的測算結果來看,近些年東南亞國家借助其較大的勞動力市場潛力,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全球勞動力密集產業的遷移,因此無論在技術密集、勞動密集抑或是整體制造業國際化分工中都不斷攀升,在復雜價值鏈生產長度上有了一定的提升,尤其是在技術密集型產業中,我國借助技術與協同發展的相互融合,在較為高端的技術產業中有了較為快速的發展。但受限于粗放式發展所帶來的要素資源利用率及規模效率較低以及環境污染等問題,低附加值制造業產業結構優化的內生增長動力仍顯得不足。
從后向聯系的角度來看,以2008—2009 年為界,基于后向聯系我國制造業加工增值的生產長度有著顯著提升,在價值鏈中的地位有了較大的攀升,過去我國傳統制造業,憑借相對廉價的勞動力與人口紅利,在機械制造業等低附加值行業中得以快速發展。很大程度上在產品生產與增值貿易中更多的是參與到低附加值制造生產,尚未參與到高附加值與技術化的加工生產環節中,表現在生產長度上呈現為負。隨著宏觀政策的引導與綠色發展理念的深入,用人力資源與技術融合取代依賴粗放式要素堆積的制造業發展戰略,體現在后向聯系上呈現較大的攀升,反映了我國整體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體系中的不斷深入,在國際化分工中的位置正不斷前移。在這些成就的背后,一些問題也逐步凸顯,技術密集型制造業發展腳步加快,整體技術和效率得到了較大的提高。而在勞動密集型產業中相較于整體制造業、技術密集型產業仍有較大的差異。在我國現行的制造業發展歷程來看,盡管在低附加值制造業、技術密集型制造業有了較大的提升,但在整體的競爭力上仍具有一定的差距。如何在綠色發展理念下,與數字化、信息化發展相互融合,引導傳統勞動密集型制造業向服務化轉型是我國亟待解決的問題。

圖4 基于后向聯系的整體制造業與勞動、技術密集制造業復雜價值鏈生產長度
四、提升價值鏈層面制造業增值生產長度的路徑選擇
在制造業層面,如何引導新舊增長動能轉化,培育制造業新競爭優勢來帶動制造業增值生產長度是經濟新常態下所著重聚焦的熱點問題。鑒于我國各省份發展情況差異較大,無疑對于調整制造業轉型帶來了較大的難度。從現代產業結構的發展需求來看,促進勞動密集型產業轉型為服務化與技術相融合的產業是高質量經濟發展的關鍵環節。結合價值鏈的發展現狀來探究制造業轉型的路徑選擇:
(一)深化人工智能與互聯網融合,引導制造業服務化轉型
考慮到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整體技術能力在國際化競爭中實力相對較弱,很難快速培育出制造業的內生增長動力。伴隨著數字經濟與互聯網在產業環節中的線上與線下活動的形式與組織逐漸多樣性,服務型產業發展作為新貿易格局下演化與發展過程較快的產業,更有利于傳統制造業在全球價值鏈的過程中不斷深化與創新。根據數據顯示,我國制造業服務化發展更多通過制成品出口而增加出口,而非通過服務貿易出口的方式。利用互聯網、智能終端、個性化云設計與制造,既能夠彌補傳統制造業層面的供給需求,同時能夠滿足產品的個性化定制,實現制造業的服務化外包。由此不難發現,通過信息化與數字化的勞動密集制造業的協調機制,不失為推動制造業服務化轉型,實現向價值鏈增值生產中高端攀升的新路徑。從政府層面上看,由于推進勞動密集型制造業服務化與技術化,服務化轉型是提升我國整體制造業增值維度提升的重要手段,作為地方政府更應該提升政策的引導機制,擴大數字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協調管理。
(二)加強技術與人力資本融合,深化技術密集型產業路徑選擇
從價值鏈增值生產的聯系上看,相較于過去以低附加值加工貿易為主的制造業,在價值鏈體系中的復雜程度正在不斷提升。我國制造業面對西方發達國家高端制造業的回流以及東南亞國家低附加值制造業的發展,對我國制造業的發展造成了一定的沖擊。一方面而言,針對我國先進制造業發展的瓶頸期,應該基于制造業自身的優勢通過對外投資與交流充分吸納海外的技術與人力資本開展產業深度融合,在國際交換與融合中邁向價值鏈的中高端維度;更重要的是在國際化分工中轉向,重視將技術與資本要素整合融入到和服務貿易維度中,充分發揮數字經濟與人工智能的優勢中,更契合工業4.0的現實發展需求。
(三)提升綠色協同發展理念,打造高效要素利用率的制造業體系
鑒于在制造業層面,無論是數字經濟的發展帶動制造業服務化,亦或是技術培育動態的產業優勢都離不開如何將傳統粗放式發展演化為更為低碳、高效的先進制造業綠色協同發展體系。正如2016 年《全球環境績效(EPI)評估報告》,在產業層面的要素利用與環境保護上,我國仍處于相對較低的位置,特別是在能耗與污染治理上。目前我國在產業綠色發展戰略中,已經建立了相應的政策法規與相應的政策激勵制度,在一定程度上引導了制造業產業對于較高能耗、較高污染的綠色發展轉型。在下一發展階段,尤其是在制造業較為密集的區域更應該擴大政府層面的監督與引導,從產品的設計、要素資源的利用、環境規制環節中,制定一系列的綠色制造、綠色發展的政策與管理規范。而在政府、制造業企業與社會層面提升制造業綠色發展的溢出機制,促進綠色產品、綠色產業、價值鏈維度的協同發展新體系的建立。
五、結論與對策建議
通過梳理投入產出機制下的全球價值鏈測算體系發展歷程。嘗試采用Zhi Wang et.al(2017)的復雜價值鏈生產長度的測算體系,分析了我國基于制造業前向聯系后向聯系的制造業增值生產長度。研究發現:我國產業嵌入度在不斷提升在價值鏈中均有上升的趨勢;勞動密集型產業在整體生產長度上要弱于技術密集型產業;基于后向聯系來看勞動密集型制造業的相對位置盡管有上升的趨勢,但距離技術密集型產業仍有較大的差距。這不僅僅是由于我國勞動密集型產業發展的慣性所致,更是在于在短時間內快速培育技術與人力資本深度融合的產業發展模式仍較為困難。嘗試從制造業轉型的角度入手,由于提升技術與要素資源利用率的綠色協同發展層面,低能耗、低排放與高技術的制造業發展需求正是價值鏈體系攀升的關鍵核心。通過環境規制與綠色發展理念的不斷深入,我國在制造業層面已經逐步擺脫“污染天堂”的產業外部環境,形成價值鏈攀升、產業分工升級與綠色協同發展的新產業格局。尤其是在數字化時代發展的背景來看,針對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突出問題,互聯網與數字經濟發展正是引導制造業服務化轉型的一劑良藥。總的來說結合價值鏈增值生產中我國所處的位置與分工格局,在新舊產業調整的過程中通過數字化與技術化的融合,更能在對外開放與對內發展過程中,謀劃制造業多元化的轉型發展,更易打造一套具有中國特色的動態發展機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