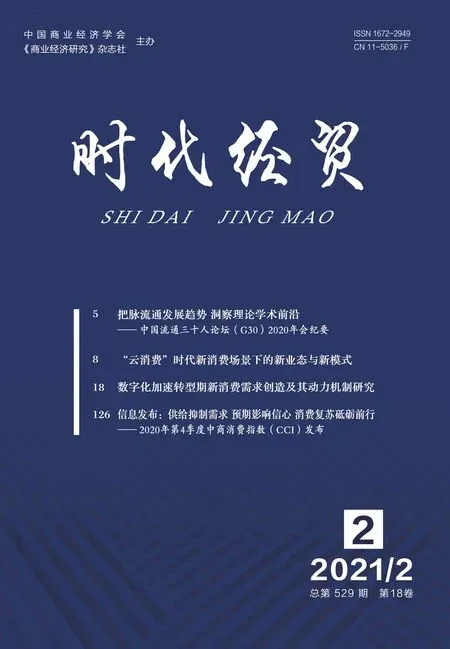中國湖南與非洲合作中的金融風險防范探討
吳 楠
(中共湖南省委黨校經濟學教研室 湖南長沙 410011)
引言
2019年6月,中非經貿博覽會機制永久落戶湖南,為湘非合作增添新平臺。就平臺規格而言,這是目前中非合作論壇下唯一的國家級對非經貿落地機制;于湖南省而言,這是第一個國家級、國際性對外開放平臺。平臺可以助力湖南充分發揮“一帶一部”區位優勢,積極融入“一帶一路”建設,為開放崛起添翼增輝。非洲發展最緊迫的問題就是讓各項資源和要素活化為經濟增長的內生動力,金融在其中發揮的作用不言而喻。目前湘非在金融方面的合作尚處于淺層次,一方面由于在金融發展上非洲整體較為滯后,缺乏統一的金融市場;另一方面我國提供的金融合作以政策性金融或開發性金融為主,合作中市場經濟主體的參與度不高。在高水平合作平臺的推進下,可以預見的是伴隨湘非經貿合作的深化,金融往來也將愈加緊密,金融合作必將日益深化。與發展中經濟體的金融合作關鍵在于對風險的把控,整個合作過程從某種角度而言就是經營風險的流程。風險把控得當,則互利雙贏;把控不當,則一方受損或雙方受損。因此,中國湖南與非洲合作中的金融風險防范成為必須關注和研究的課題。
一、文獻綜述
學術界對非洲大陸的金融風險研究主要囊括在整體風險研究之中。姚桂梅(2018)在對中非經貿論壇的綜述中全面概括了中非共建“一帶一路”的主要風險,即政局動蕩風險、本幣貶值風險、債務違約風險、恐襲風險、國際競爭風險;趙蜀蓉(2019)等運用PEST分析工具,從政治、經濟、社會及技術四個角度對中國企業在非洲面臨的風險做了實證性質的調研,并對如何應對調研結果中的主要風險給出了對策與建議。金融與投資緊密相連,文獻分析也表明較多學者都從投資角度對非洲大陸風險進行了分析。FADILOU(2008)用綜合模糊評價模型衡量了在非投資風險,并列出了高中低風險國家的排名[1];安迪雷(2009)研究認為對非投資時不能將非洲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風險,而是應該對每個具體國家和區域進行風險分析;田澤(2014)從東道國視角構建評價指標體系對南非、蘇丹等非洲10國進行了投資風險實證研究,編制指數[2]并繪制雷達圖供投資企業參考;周經等(2017)從投資動機視角出發,發現中國對非投資整體上對政治風險態度模糊,實證研究中分樣本數據顯示:市場尋求型的投資對政治風險相較于整體平均更加不敏感,資源尋求型投資則對經濟和政治風險不敏感,但對文化風險選擇規避;劉惠好(2020)較全面的分析了中國企業在非投資面臨的五大風險,即政局不穩治安不良、營商硬軟環境不佳、融資難債務高、文化沖突人才匱乏、第三方干擾,并針對性的給出了對策建議。具體到金融經營角度而言,張小鋒(2013)指出中非金融合作還處于起步階段,應該以多邊開放金融機構為平臺,繼續深化金融業的合作,完善金融服務體系;葉永剛等(2018)選取多樣化宏觀經濟環境指標,采用層次法和熵值法組合確定指標權重,構建了中非銀行風險評價和預警指標體系;薛志華(2018)從金融自由化的兩面性出發,建議雙邊合作在釋放合作潛力的同時,要深化跨境金融監管,維護金融穩定;王珊珊等(2020)通過面板數據研究發現外商直接投資、進出口商品額、資本項目開放這三個指標對非洲金融市場發展的作用是正向顯著的,接受官方援助指標則影響大小和方向不穩健,說明對非洲金融市場發展而言市場化的投入相較于援助更加有效。
從學術研究可見,中非合作中的風險點從整體角度、投資角度和金融經營角度已經研究較為全面且深入。“湖南渠道”的對非合作同樣面臨著這些風險,企業應該如何把握?政府層面要怎樣考量?成為推進湘非合作的試金石。基于此,本文試圖從省域層面出發,分析湘非合作中直接面臨的各類金融風險,并從政府、企業、金融層面就如何合理有效防范金融風險給出可行的思路和建議。
二、湘非合作中面臨的直接金融風險分析
金融是內嵌于現代經濟體系的資金樞紐,從整體視角來看,任何能影響經濟運行的因素都會影響到金融,但金融又由于其特殊性,某些因素對其影響非常直接且明顯。本文探討的范疇為直接影響金融風險的因素,結合文獻綜述中的觀點,主要從政局、融資、債務和貨幣結算四個角度來分析湘非合作中直面的金融風險。
(一)政局不穩定引發的金融風險
政局穩定是一個國家吸引外資能力的基礎。從目前的情況來看,非洲政局總體趨于穩定,多數國家為謀求發展制定了優化投資環境、吸引外資的政策,但少部分國家和地區仍陷于反政府武裝、恐怖主義、種族和宗教沖突的威脅之中。湖南企業在走進非洲的過程中已經歷過利比亞內戰帶來的損失、津巴布韋“本土化”引發的不安。政局動蕩引發的金融風險幾乎是毀滅性的,任何投入基本完全成為沉沒成本,即使后續宏觀環境緩和再進行合作,前期的損失也難于挽回。對政局的正確研判成為規避此類大型風險的重要依據。
(二)融資困難帶來的金融風險
目前非洲國家普遍儲蓄率比較低,同時金融市場欠發展,外來企業想要在本地獲得資金支持很困難。而在國際上,非洲國家的信用評級偏低,投資企業也無法以當地資產為抵押從國際金融市場獲得融資,這就導致湘企在非發展要么靠自有資金,要么從中國政策性銀行獲得貸款,這使得資金的政策依賴性強,缺乏市場自主自發性。如果國內由于某些原因政策性資金回縮,就容易導致在非企業資金周轉困難或斷流。
(三)債務違約可能性引發的金融風險
非洲國家的債務問題長期存在,早在2005年就進入了債務積累的明顯拐點,當時多數非洲國家負債率、債務率和償債率大幅提高,部分國家逼近甚至超過國際警戒線。從2012-2019年非洲年平均經濟增長率達3.82%,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但必須要正視非洲經濟快速增長在一定程度上是依賴于大量外資的流入。由于全球經濟進入緩增長期,大宗商品價格下跌,2017年非洲整體外債規模達5350億美元,平均負債率則從 2011 年的30%增長到53%,非洲債務問題再次進入國際視野,國際社會對非洲外債的擔憂涉及所謂的“中國債務陷阱論”,不僅不利于債務存有隱憂的非洲國家,亦不利于中非長遠的利益訴求。具體到在非項目和企業而言,償債壓力增加會影響政府及企業的決策,減少基礎設施建設項目或壓縮現金流,因此部分項目在還本付息、款項支付可能面臨延期、拖欠甚至違約風險。(非洲國家整體債務余額與外債占GDP比例可見圖1)

圖1 2000-2019年非洲國家總體外債狀況
(四)貨幣結算困局隱含的金融風險
外匯短缺是非洲國家普遍面臨的問題[3],在大宗商品價格低迷背景下,非洲外匯市場可謂承壓嚴重。2017年,非洲有30多個國家貨幣貶值,其中幾個經濟大國更是外匯貶值嚴重。目前中非經貿合作進展穩定,2018年和2019年我國對非直接投資分別為33億美元和30億美元,但其中以人民幣計價的投資不到1%。這就意味著非洲貨幣貶值對中國可能帶來雙重匯兌損失。對中資企業而言,原材料進口計價、生產運營、收益回流都會產生較大影響,這加大了體現在財務報表上的匯兌損失。
三、湘非合作中的金融風險防范對策
(一)政府層面,湘非合作要有大局意識,提高整體風險預警能力
湘非合作必須服從中非合作整體安排。地方政府外事一方面要配合、服從和服務于國家總體外交,另一方面也可以作為國家總體外交去修正、補充或試驗部分尚未得到充分重視和研究的領域。從理論角度,美國學者Duchecek(1986)提出“次政府外交”一詞,認為次政府外交是地方政府所從事的“平行于中央或中央外交的國際活動”,這些活動通常與中央外交互相合作、補充,但不排除也有沖突的時候。湖南省作為地方政府在與非洲的合作中特別需要對國家大方針戰略有正確的理解,樹立大局意識,和國家整體行為保持一致。如,從中非關系長期可持續發展角度考慮,國家對非總體外交基礎是政治和經濟兩個支柱,伴隨全球開放思潮的轉變,日益強調社會和安全兩個新支柱,由此需要在非洲的人文、社會、安全等領域加強合作與投資,湖南省也應該在這些領域發揮自己的優勢,拓展與非洲的合作范圍。
湘非合作中要升級地方政府對非投資的風險預警能力,完善投資風險預警機制。湘非合作的具體行動要落到每一個參與企業中,這些企業有央企、地方企業和私企,不論哪種企業“走出去”都需要全面準確的把握海外投資國或投資地區的風險。但部分企業并不具備進行海外盡調與全面衡量風險的能力,此時地方政府有責任和義務把關企業海外投資的安全性,從而幫助企業把控風險。對于非洲這片局勢多變的大陸,企業獲得的信息可能滯后甚至不確實,政府如果能組建專業研究和盡調團隊實時跟蹤政局動向、經濟走勢,對于湘企“走出去”的策略選擇必然大有幫助。
(二)企業層面,對非投資合作要協調布局,提升企業“走出去”的內外把控能力
湘企在與非合作中應遵循“既符合對方需求也與自身能力匹配”的原則,合作方向方式有的放矢,才能打破原有一味援助而產生路徑依賴的困境。湖南是裝備制造大省、農業大省、傳媒強省,從某種程度而言,目前的產業結構非常適合與非洲合作。非洲國家普遍基礎設施薄弱,農業水平低,礦產資源豐富但開采能力不足,而湖南在農業、基礎設施建設、礦產品開采與深加工等領域都有著獨特的優勢,如隆平高科、三一重工、中聯重科、湖南建工、湖南路橋等企業,非常契合非洲各國的需要。需要注意的是,合作的成功不僅僅依賴雙方資源的匹配,更需要在進程中不斷磨合和尊重雙方需要,這是對企業綜合協調能力的考驗。如贊比亞的銅礦資源吸引了我國企業“扎堆”到贊比亞開采礦藏,各方面因素引發當地社會不滿。其中,湖南到贊比亞投資銅礦開采的企業就有8家,一省多個企業涉足同一領域,一方面存在重復投資的可能,另一方面也可能導致內部惡性競爭,風險相伴而生。在此情境下,企業之間、企業內部如何協調顯得尤其重要。
湘企在與非合作中要采取多元化合作模式來分散和化解融資風險。如與其他企業合作投資,分散風險。合作模式可以是國企+國企、國企+民企、國企+外企、民企+外企,這有利于雙方各自發揮優勢,稀釋風險、共創雙贏。還可以嘗試“投建營一體化”,從項目設計、建造到運營管理全程長時間段參與[4],充分發揮項目的經濟效益和社會效益,同時致力于手把手教會非洲當地人員如何管理運營項目,以“授人以漁”的精神參與到非洲國家的發展建設中,長時間駐留當地對湘企在海外發展的內外協調把控能力將有極大提升。
(三)金融層面,深入推進各項金融業務合作,利用“造血金融”化解風險
金融合作是中非“十大合作計劃”之一,習近平總書記在2015年中非合作論壇約翰內斯堡峰會開幕式上致辭:“中方將同非洲國家擴大人民幣結算和本幣互換業務規模,鼓勵中國金融機構赴非洲設立更多分支機構,以多種方式擴大對非洲投融資合作,為非洲工業化和現代化提供金融支持和服務”。可見,未來5-15年,深化中非“功能性”金融合作成為計劃的主題。如銀行證券保險業合作、建全貨幣互換機制、參與區域債券市場建設和支付清算體系建設等。金融業需要合理布置和配置業務資源,優先支持戰略亟待的項目,逐步構建起多層次金融服務體系,加強與非洲相關金融機構的合作,共享信息、分享利潤、共擔風險,為市場的拓寬順暢凝聚合力。如2019年在湖南舉辦的中非人民幣國際化論壇上,就提出了以論壇研討為契機,加快推進中非跨境人民幣中心建設,為中非合作發展提供堅實金融支撐。
金融風險的識別與管理在合作中顯得非常關鍵。因此在開展金融業務時,應緊密關注所在國當地政治經濟形式,考慮市場風險、國別風險,建立完善的資產質量和重大風險事件報告制度,嚴防當地系統性、行業性、區域性風險。在應急處理機制上,要根據當地情況因地制宜,提前制定應急預案,及時處理陷入困境國家的風險暴露,提高應對國別風險突發事件的能力,使湘非合作中的金融生態呈現一種“造血”能力,而非傳統西方援助帶去的發展“制度性依賴”,造成非洲各國本身內生發展能力缺失[5]。也即言,要通過深入推進各項“功能性”金融業務的合作,力求促生和增進非洲國家自身發展能力的特質,發揮金融在提高資源配置效率上的重要作用,通過支持基礎農業項目、工業化項目、公共基礎設施來實現經濟增長,為非洲國家的脫貧與發展提供兼具市場和普惠效用的金融思路和工具。
注釋:
[1] 高等風險國家:岡比亞、幾內亞比紹、幾內亞、塞拉利昂、利比里亞、尼日利亞、蘇丹、索馬里、剛果(民)、安哥拉、赤道幾內亞、坦桑尼亞、馬拉維、莫桑比克、馬達加斯加、科摩羅等。中等風險國家:利比亞、馬里、尼日爾、多哥、乍得、喀麥隆、中非、剛果、埃塞俄比亞、吉布提、烏干達、贊比亞等。低等風險國家:埃及、突尼斯、阿爾及利亞、摩洛哥、毛里塔尼亞、塞內加爾、布基納法索、科特迪瓦、加納、貝寧、加蓬、厄立特里亞、肯尼亞、津巴布韋、納米比亞、博茨瓦納、南非、萊索托、斯威士蘭等。
[2] 對非投資風險由低到高依次為 :毛里求斯、南非、阿爾及利亞、埃及、尼日利亞、民主剛果、贊比亞、蘇丹、安哥拉、埃塞俄比亞。
[3]彭博數據顯示,非洲各國平均外匯儲備僅為58億美元。
[4]因為原來中國在非洲的“交鑰匙”工程部分經營慘淡。
[5]《援助的死亡》一書中提到:撒哈拉以南非洲國家60多年來獲得了總額超過一萬億美元的援助資金,在全球各地區中比例最高,卻“沒有產生東亞地區(那樣)的經濟增長,而且還形成了對西方援助的制度性依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