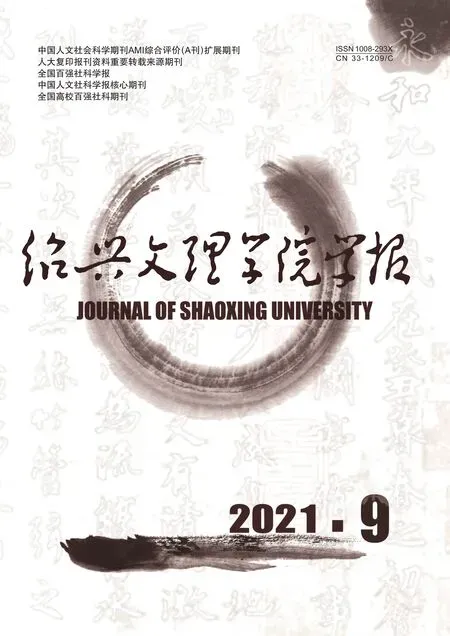民國《平陽縣志》摩尼教資料新考
[美]馬小鶴
(哈佛大學 哈佛燕京圖書館,美國 麻州 劍橋 02138)
民國《平陽縣志》不僅發現了摩尼教新資料,即今蒼南縣括山鄉下湯村的元碑《選真寺記》和元代陳高所撰《竹西樓記》,而且作了初步考證。隨著福建霞浦文書和日本藏摩尼教繪畫的發現,近年來中國東南摩尼教的研究進展迅速,對這些資料可以作一些新的分析。本文先著錄民國《平陽縣志》的有關資料,再介紹這些資料的收集和考據者劉紹寬,并以20世紀初中外摩尼教研究為背景,評估劉紹寬考據的得失。再簡要回顧20世紀80年代以來對這些資料的研究,進而對資料中講到的“食必紅蕈”“蘇鄰”以及“七時”等內容,作一些新的探索。
一、民國《平陽縣志》摩尼教資料著錄
民國《平陽縣志》卷四十六《神教志二·佛教》小序曰:
……此外有明教者,陸務觀謂:“始自閩中,有明教經甚多,妄取道藏中校定官名銜贅其后。燒必乳香,食必紅蕈。男女不親授,遇婦人所作食則不食。”(《老學庵筆記》十)陳高謂:“相傳自蘇鄰國流入中土,甌閩人多奉之。其徒齋戒持律頗嚴謹,日一食,晝夜七時唄詠膜拜。”(《不系舟漁集·竹西樓記》)孔克表亦稱“為蘇鄰國教”。(《選真寺記》石本)蓋即末摩尼教。(《老子化胡經》云:“我乘光明道氣,至蘇鄰國,降為太子,號末摩尼。”)今萬全鄉尚有其教,大較流為優婆夷、塞(1)優婆夷,音譯梵語Upāsikā,中譯為“女居士”,即信佛的在家女子;優婆塞,音譯梵語Upāsaka,中譯為“居士”,即信佛的在家男子;合稱“優婆夷、塞”。矣。……《老學庵筆記》引徐常侍《稽神錄》云:“有善魔法者,名曰明教。”是明教亦為魔。[1]卷46,1-2
又記載:
選真寺:在彭家山,元至正(1341—1370)間重建。清嘉慶、同治間(1796—1874)重修。
并引邑人孔克表《選真寺記》略云:
□平陽郭南行百十里,有山曰鵬山,彭氏世居之。從彭氏之居西北,有宮曰“選真寺”,為蘇鄰國之教者宅焉。蓋彭氏之先之所建也。故制陋樸,人或隘之。彭君如山奮謂其侄德玉:“愿力事茲役,汝其相吾成。”乃崇佛殿,立三門,列左右廡;諸所締構,演法有堂會,學徒有舍,語處食寢有室,以至廚井、庫廩、湢圊之屬,靡不具修。都為屋若干楹。即寺之東廡,作祠宇以[奉]神主。又割田如干畝,賦其金用供祀饗。繼德玉而相于成,君之孫文復、文明、文定、文崇、文振也。君名仁翁。[1]卷46,17
又記載:
潛光院:在鹽(炎)亭,為明教浮圖之宇,見陳高《竹西樓記》(《不系舟漁集》)。[1]卷46,28
卷三十七《人物六》有孔克表傳[1]卷37,5。孔克表(1314?—1385?)元明均擔任過官職,學問淵博,尤精于史學。
卷六十四《文徵內編二》引元陳高《不系舟漁集》卷十二《竹西樓記》載:
溫之平陽,有地曰炎亭。在大海之濱,東臨海,西南北三面負山;山環之,若箕狀。其地可三四里,居者數百家,多以漁為業。循山麓而入,峰巒回抱,不復見海;其中得平地,有田數百畝,二十余家居之,耕焉以給食。有潛光院在焉。潛光院者,明教浮圖之宇也。明教之始,相傳以為自蘇鄰國流入中土,甌閩人多奉之。其徒齋戒持律頗嚴謹,日一食,晝夜七時唄詠膜拜。潛光院東偏,石心上人之所居也。有樓焉,曰竹西樓。當山谷之間,下臨溪澗,林樹環茂。樓之東植竹,其木多松、櫧、檜、柏,有泉石煙霞之勝;而獨以竹名焉者,蓋竹之高標清節,學道者類之,故取以自況云。鄉之能文之士,若章君慶、何君岳、林君齊、鄭君弼,咸賦詩以歌詠之。斯樓之美,與竹之幽,固不待言而知矣。石心修為之暇,游息于是。山雨初霽,冷風微來,如挹瑯玕之色,聽環珮之音焉。而又仰觀天宇之空曠,俯瞰林壑之幽深,翛翛然若游于造物之表,而不知人世之為人世也。石心素儒家子,幼讀六藝百氏之書,趣淡泊而習高尚,故能不汨于塵俗而逃夫虛空。其學明教之學者,蓋亦托其跡而隱焉者歟?若其孤介之質,清修之操,真可以無愧于竹哉!樓建于某年。石心之師曰德山,實經營之。石心名道堅。至正十一年(1351)七月望記。[1]卷64,7-8
卷三十六《人物五》有陳高傳[1]卷36,23-24。陳高(1314—1367)為平陽金舟鄉人,著名詩人。
一般方志眾手成書,不易確定具體部分出自何人之手。不過,此書的這些資料,應該可以確定編纂者為劉紹寬(號厚莊,1867—1942)。
二、方志專家劉紹寬
平陽自清乾隆二十三年(1758)纂修縣志以后,168年未曾修志,民國初年,劉紹寬等“懼邑志曠缺日久,典章堙廢,益難為理”,1915年開修纂縣志會議,王理孚為修志主任,符璋為總纂(后受聘往上海,實未親任其職),劉紹寬為副纂,主持實際工作。劉紹寬為近代浙南地區杰出的教育家和著名學者,一代經學大師、地方志專家。蘇步青、夏鼐、鄭振鐸等大批知名學者都出自他門下。遺著有《厚莊詩文鈔》《厚莊詩文續集》等。民國《平陽縣志》比乾隆志增三分之二,選真寺的資料明確注曰“增”。乾隆志只著錄了“《不系舟漁集》[元]陳高著”,新志則將《竹西樓記》全文錄入。此志不僅篇幅增加,而且質量上乘,《浙江方志考》譽之為“近代浙江方志之佳作”[2]428-429。
劉紹寬將《〈平陽縣志〉篇目序(子目小序附)》收入《厚莊詩文續集》,其中有《神教志》序,附有神祀、佛教、道教、基督教小序[3]卷1,33-36,可以確證《神教志》為其所親撰。摩尼教資料的收集與考據當出自其手。劉紹寬等擬定的凡例曰:“舊志祠祀并入寺墓,而仙釋列于人物。今立神教一志,神廟寺觀及仙釋列傳并合為篇,所謂各從其類也。墓祭本非古禮,況古墓不皆列祀,入古跡庶稍合耳。”[1]卷首,凡例全縣分設采訪十有四人,而劉紹寬也親自采訪,根據其《厚莊日記(手稿)》,為了編《神教志》,1916年曾有一日跑了15處。隔日,又跑了11處。到處奔波,不辭辛苦,如其所言“閱書史,訪碑碣,無非為修志搜集材料”[4]1076。元碑《選真寺記》的發現與摘錄就是其成果之一。
符璋對劉紹寬的評價是:“君于學無所不窺,于鄉賢哲遺書無不博覽及之。……其修《平陽志》也,每考一事,陳書滿案,孜孜孽孽。”[5]序2,4劉紹寬撰有《繕校〈不系舟漁集〉附記》[5]卷1,30-31,熟悉此書自不待言,他是指出《竹西樓記》包含明教資料之第一人。
陳澹然(1859—1930)為《厚莊詩文鈔》作序言曰:“獨其詩登臨贈答,雅類劍南,身世之間,或多凄涼,私竊嘆之。”[5]序1,1劉紹寬對《劍南詩稿》作者陸游《老學庵筆記》中的資料自然能信手拈來。《老子化胡經》在元忽必烈下令禁毀之后,無完帙存世。但劉紹寬所引的段落,仍可見于《佛祖統紀》轉引的《夷堅志》等著作。
劉紹寬所引用的數種明教資料:《選真寺記》《竹西樓記》都是他首先發現的,但《老學庵筆記》及其所引《稽神錄》與《老子化胡經》則在法國漢學家沙畹、伯希和以及王國維、陳垣的摩尼教研究中都已經引用,劉紹寬是否可能參考過他們的論文呢?劉紹寬于光緒二十九年(1903)曾入上海震旦學院,就學于馬相伯;次年游歷日本,考察學務,著有《東瀛觀學記》;他“湛深經術,淹達時務”,不無這種可能。不過要確定其是否吸收了1925年以前摩尼教研究的成果,則尚需簡要回顧一下這段研究史。
三、初期摩尼教研究與方志
伯希和1908年在敦煌獲取大量文書,次年8至9月間,到北京購書,隨身攜帶的敦煌藏經洞的一些珍本使中國學者認識到了藏經洞寶藏的巨大價值,促使清政府把藏經洞所余經卷悉數運京。羅振玉1911年在《國學叢刊》第二冊上刊布了一份敦煌寫經的抄本,題曰《波斯教殘經》(后常稱京藏《摩尼教經》)。這份文書今藏北京的中國國家圖書館,舊編號“宇字第56”,新編號“北8470”,近來編為“北敦00256號”。羅振玉將這一冊《國學叢刊》送給日本學者羽田亨,羽田亨于次年在《東洋學報》上發表論文,考訂此經為摩尼教殘經[6]。這件文書可謂伯希和在敦煌藏經洞揀選文書中的最大失漏,他急忙和老師沙畹研究其抄本,翻譯成法文,詳加注釋,附以敦煌發現的“伯希和文書”(后來確定是《摩尼光佛教法儀略》,簡稱《儀略》的下半截)、《老子化胡經》殘卷,并廣泛收集有關摩尼教的漢文史料,包括陸游《老學庵筆記》、徐鉉《稽神錄》,并翻譯為法文。1911年和1913年分三次發表在《亞洲報》上,題為《中國發現的一部摩尼教經典》[7]。1931年馮承鈞將此文研究漢文史料的部分翻譯為中文發表。
沙畹、伯希和的摩尼教研究激起了王國維的回應,在其基礎上,新增11則史料,但未發展為正式論文,以《摩尼教流行中國考》為題,于1921年發表[8]。此后,陳垣也有意參加這場學術爭勝,向王國維請教英國不列顛博物館所藏摩尼教文獻《下部贊》的內容,王國維回信云:
右摩尼經贊目,倫敦博物館所藏唐寫殘卷,反面寫《大唐西域記》卷一,次《往生禮贊文》一卷(比丘善導愿往生禮贊文廿二拜),次《十二光禮懺文請佛作梵》(此二段疑亦摩尼教經),見日本矢吹慶輝《敦煌出佛書解題》,惜所錄未完。然其中人名頗有與何喬新(“遠”字之誤)《閩書》所載參證,忙儞具智王即《閩書》之具智大明使,忙儞即MANI之音譯也。[9]262
《下部贊》是斯坦因(Marc Aurel Stein,1862—1943)帶至大英博物館的敦煌文書之一,直到1916年夏,才為日本學者矢吹慶輝認定為摩尼教經,但很長時期內中國學者并無研究。1923年陳垣發表《摩尼教入中國考》[10],即引用了方志《閩書》。給學界的印象是《閩書》的此條材料由陳垣首先發現的。根據此信,極有可能是王國維最先注意到《閩書》中的摩尼教材料[11]。陳垣接著發表《摩尼教殘經一、二》,點校、刊布了京藏《摩尼教殘經》和《儀略》[12]。伯希和得知《閩書》這條資料后,又補充了何喬遠《名山藏》中關于摩尼教的資料,于1923年發表《福建摩尼教遺跡》[13]。這進一步引起學術界對福建摩尼教遺跡的注意。
陳垣發表《摩尼教入中國考》之后,1924年胡適也為他提供了重要史料。胡適提出宋代黃震《黃氏日抄》中包含了一篇《崇壽宮記》,記載了一座摩尼教寺演變為道觀的史實[9]201-202;[14]。陳垣回信感謝胡適提供資料,還說友人告知《嘉定赤城志》中有知州李謙《戒事魔詩》十首,可以推定宋代閩浙沿海地區盛行摩尼教[9]202。此友人當即王國維,王國維1921年發表的《摩尼教流行中國考》中并未引用《戒事魔詩》,而在此文收入其《觀堂別集》第1冊時,增補了這條資料。王國維、胡適為陳垣提供的資料與意見等于間接回應了沙畹、伯希和在摩尼教研究上的挑戰。
劉紹寬看來沒有接觸到這些學者的研究成果。如果他通過陳垣之文知道《閩書》關于華表山的記載,應該知道“‘末’之言大也”,因此不會稱此教為“末摩尼教”,而應該像王國維、陳垣一樣,稱此教為“摩尼教”。他如果知道摩尼教實際上是一種獨立于佛教之外的世界宗教,恐怕就不會將其視為佛教異端,放在《神教志二·佛教》中討論,應該另列一類。從上述學者之間的爭勝與交流中,可以看到在東方摩尼教研究這個新領域中,何等重視一條方志資料的發現。可惜,他們都未能注意到民國《平陽縣志》中的《選真寺記》和《竹西樓記》。
劉紹寬發現新資料對摩尼教研究的意義固不待言,但尚需對這些新資料定性。
四、新修方志與摩尼教研究
繼承王國維、陳垣學術傳統的劉銘恕先生于1940年發表《火祆教與摩尼教的新史料(未完)》,刊布了火祆教新史料,但未見續篇[15]。他意欲刊布的摩尼教新史料中或許就包括《竹西樓記》。他于1958年發表《泉州石刻三跋》,節錄了《竹西樓記》,首先將此史料定性為摩尼教資料[16]61。劉南強先生于1977年將《竹西樓記》全文英譯發表[17]。莊為璣于1983年也征引了這則史料[18]81。三位學者可能是直接從陳高《不系舟漁集》中檢出的。1985年,林悟殊先生據民國十五年(1926)重刊本(民刊本)將《竹西樓記》標點刊出[19]。四位學者均未提及民國《平陽縣志》。
20世紀80年代中國大陸開始修志,創造了一個地方史料更多地進入史學研究視野的大環境。林順道先生為新修《平陽縣志》副主編,當熟讀民國《平陽縣志》。林順道不同于劉紹寬的地方在于,他不再只以傳統考據方法研究地方宗教史料,而是利用當時學術界對宋元東南沿海摩尼教的研究成果來解讀民國《平陽縣志》中的史料。
林順道指出:今鰲江下游之南,當地習慣稱為“江南”。1981年,原平陽縣析為平陽、蒼南兩縣時,“江南”劃歸蒼南,萬全劃歸平陽。民國《平陽縣志》沒有提及明教在萬全的遺跡,但卻完整地保存了明教在“江南”的兩座寺廟的有關史料。“江南”是摩尼教由閩入浙的重要據點。潛光院所在地炎亭和選真寺所在地彭家山分別位于現在金鄉鎮東西兩側,古代金鄉是閩浙重要通道上的重鎮。明代中葉以后,溫州的明教已和佛道或其他秘密宗教相混雜,因此,民國《平陽縣志》又說:“今萬全鄉尚有其教,大較流為優婆夷、塞矣。”根據民國《平陽縣志》的記載,林順道1988年在蒼南縣括山鄉下湯村彭家山山麓找到了選真寺遺址,并在寺前田野中找到了《選真寺記》碑。他也確定了潛光院遺址當在現蒼南縣炎亭鎮洪家行政村岙底自然村大崗山山麓[20]。
1990年周夢江將碑記抄錄發表[21]75。1993年版《平陽縣志》在人物方面介紹了陳高、孔克表,說明《選真寺記》與《竹西樓記》是研究平陽明教傳播的珍貴史料[22]831-832。1993年版的《蒼南縣志》,在宗教方面設專章介紹摩尼教,在人物方面介紹了陳高,在藝文方面著錄了《竹西樓記》和《選真寺記》(林順道錄文)[23]692,745-746,846-847。1998年版《溫州市志》宗教方面也設專章介紹摩尼教,附《選真寺記》;人物方面介紹了孔克表與陳高[24]477-478,607-608。林順道又將碑文校補標點,刊布于《中國文物報》1997年7月27日第3版上的《摩尼教〈選真寺記〉元碑》中。2005年金柏東發表此碑的一個更新錄文[25]18。林悟殊以多個不同版本參校,對《竹西樓記》與《選真寺記》作了新的錄文校勘,推測選真寺、潛光院應為宋時物[26],[27]242-252。林順道通過分析溫州姓氏史志、譜牒資料以及溫州方言狀況,認為摩尼教傳入溫州,可上溯至唐季五代大量閩東移民入溫時。選真寺應是北宋時所建[28]。
眾多學者的努力為進一步研究奠定了基礎。下文嘗試對民國《平陽縣志》中的有關資料作一些新的分析。
五、“食必紅蕈”
民國《平陽縣志》所引陸游《老學庵筆記》關于明教的記載當出自陸游親身觀察。他于紹興二十八年(1158)冬季出任福州寧德縣(現寧德市)主簿,次年調官為福州決曹;三十年(1160)自福州北歸,在都下任閑職。三十二年(1162)上《條對狀》,其第七條請禁民間“邪教”,陰消異時“竊發”之患[29]64-97;[30]80-89。其中講道:“伏緣此色人等處處皆有,……福建謂之明教、揭諦齋,名號不一。明教尤甚,至有秀才、吏人、軍兵,亦相傳習。……以祭祖考為引鬼,永絕血食,用以沐浴。其他妖濫,未易概舉。燒乳香則乳香為之貴,食菌蕈則菌蕈為之貴。”[31]125
賈文龍認為宋人描述江南地區的秘密宗教信仰時,沒有沿襲“食素”這個俗語,而是使用了“吃菜”一詞,稱之為“吃菜事魔”。“吃菜”的由來并不僅因為素食,而是因宋代摩尼教的特殊教儀促成[32]。他引述著名人類學家克勞德·列維-斯特勞斯的名著《結構人類學》中譯本之《文化中的蘑菇》一文,講到陸游譴責摩尼教徒食用紅蘑菇(紅蕈)和以人尿為儀式用水(“以溺為法水,用以沐浴”),而圣奧古斯丁也曾譴責他們喜歡蘑菇[33]228-230。《文化中的蘑菇》是對美國民族真菌學家羅伯特·高登·華生之《蘇摩:不朽的神圣蘑菇》一書的書評。華生是通過沙畹、伯希和的《中國發現的一部摩尼教經典》一文而知道陸游譴責摩尼教徒嗜食蘑菇的。他指出,福建盛產一種可食用的紅蘑菇[大紅菇,Russula rubra (Krom.) Bres],福建人采集它們,供本地人和外地人食用。這應該就是陸游所說的“紅蕈”[34]71-76。華生將陸游與圣奧古斯丁對摩尼教的譴責作了比較。圣奧古斯丁指責他們,以為一個人[=選民]只要吃蘑菇、米飯、塊菌、糕點、葡萄汁、胡椒和咖喱,就不會發現其違背三印(即神圣的戒律)[35]82。
紅蕈(菌蕈、蘑菇)無疑是福建“吃菜事魔”者所食之“菜”中最重要的一種,由于他們人數眾多,經常吃紅蕈,以致紅蕈的價格上漲。吃蘑菇是東西方摩尼教徒的共同特征之一。“吃菜”其實就是摩尼教的圣餐,有重大的宗教含義。摩尼教教義認為,素菜中含有大量光明分子,選民(僧侶)吃下素菜,能把素菜中的光明分子解放出來。摩尼教社團生活就是選民與聽者(俗信徒)之間的互惠關系,聽者向選民布施瓜果素菜,使選民能將光明分子從中釋放出來。聽者則根據其布施的程度,靈魂獲得不同的歸宿,信教者免下地獄,重新輪回,投胎為選民,再得到解脫,而最虔誠者則可以直接飛升天堂。漢文資料提供了中國摩尼教圣餐儀式的證據。唐代《儀略》“寺宇儀第五”列舉的五堂之一為“齋講堂”,即布施、食齋、講經之堂,“齋”意為“素食”“布施”,這里就意為摩尼教的圣餐。“法眾……每日齋食,儼然待施;若無施者,乞丐以充。”每寺詮簡三人,其三為“遏換健塞波塞”,是伊朗語rw’-ng’n‘spsg的音譯,“譯云月直,專知供施”,就是專門負責圣餐的供應與布施之事[36]521。京藏《摩尼教經》說選民“年一易衣,日一受食,歡喜敬奉,不以為難”,北宋宣和二年(1120)臣僚言:“今來明教行者各于所居鄉村建立屋宇,號為齋堂,如溫州共有四十余處。”[37]第14冊,8325“齋堂”類似《儀略》所說的“齋講堂”。陸游說:“至有士人宗子輩,眾中自言:‘今日赴明教齋。’予嘗詰之:‘此魔也,奈何與之游?’則對曰:‘不然,男女無別者為魔,男女不親授者為明教’。”[31]第11冊,481-482“明教齋”即明教的圣餐儀式。
宋代“吃菜事魔”后來泛指素食、崇拜非正統神祇的宗教社團,也包括了白蓮菜、白云菜等佛教異端團體。到了元代,明教徒似不再諱言“吃菜”。新發現的日本奈良大和文華館藏《冥王圣幀》榜題曰:
東鄭茂頭保弟子張思義偕鄭氏辛娘喜舍冥王圣幀恭入寶山菜院,永充供養,祈保平安。愿(圣?王?)□□(安?)日(以下殘)。[38]96-98
“菜院”之“菜”,即“吃菜”之“菜”,“菜院”即“吃菜”之齋堂。陳高說明教“其徒齋戒持律頗嚴謹,日一食”,“日一食”應該就是“吃菜”。
粘良圖先生從《青陽科甲肇基莊氏族譜》中發現一篇莊惠龍(1281—1349)的墓志銘,說他“晚年厭觀世諦,托以蘇鄰法”,意即皈依摩尼教。莊氏族譜記“天德,惠龍三子,從空,葬菜堂地基”。“從空”意為出家作僧人,天德卒后葬于自家的“菜堂”,亦即齋堂[39]48-50。
六、“自蘇鄰國流入中土”
民國《平陽縣志》所引《竹西樓記》說:“明教之始,相傳以為自蘇鄰國流入中土。”《選真寺記》說:“有宮曰‘選真寺’,為蘇鄰國之教者宅焉。”摩尼與蘇鄰的聯系見于20世紀初發現的敦煌寫本《老子化胡經》卷一:
后經四百五十余年,我(即老子)乘自然光明道氣,從真寂境,飛入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王室,示為太子,號末摩尼。[40]第1冊,7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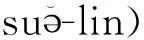

其實,蘇藺、蘇剌薩儻那就在泰西封,完全可以用對音法來確定蘇鄰國的真實地理名稱。根據泰伯里用阿拉伯文寫的《歷代先知和帝王史》、波斯沙普爾一世中古波斯文、帕提亞文、希臘文三語碑銘、納爾西一世中古波斯文和帕提亞文雙語碑銘和菲爾多西用波斯文寫的《列王記》,薩珊時代,波斯國都所在的中央省區的名字,希臘文作’Aσσυρια,帕提亞文、中古波斯文作’swrstn,讀作Asūristān,阿拉伯文、新波斯文作Sūristān。漢文音譯為“宿利”“蘇利”“蘇藺”“蘇鄰”“蘇利悉單”“蘇剌薩儻那”,實際上都指薩珊波斯首都塞琉西亞-泰西封(馬達因)為中心的地區,古稱巴比倫。這一地區正是摩尼出生和活動的中心[48]320-335。
本文就“蘇鄰”問題欲再加探討的是白居易“蘇鄰之詩”的可能性,及其與霞浦文書之關系。先著錄南宋志磐《佛祖統紀》的有關記載:
述曰:嘗考《夷堅志》云,吃菜事魔,三山尤熾。為首者紫帽寬袗,婦人黑冠白服,稱為明教會。所事佛衣白,引經中所謂“白佛,言世尊”。取《金剛經》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為第五佛。又名末摩尼,采《化胡經》“乘自然光明道氣,飛人西那玉界蘇鄰國中,降誕王宮為太子,出家稱末摩尼”,以自表證。其經名《二宗三際》。二宗者,明與暗也;三際者,過去、未來、現在也。大中祥符興道藏,富人林世長賂主者,使編入藏,安于亳州明道宮。復假稱白樂天詩云:“靜覽蘇鄰傳,摩尼道可驚。二宗陳寂默,五佛繼光明。日月為資敬,乾坤認所生。若論齋絜志,釋子好齊名。”以此八句表于經首。其修持者,正午一食,裸尸以葬,以七時作禮。蓋黃巾之遺習也。(原注:嘗檢樂天《長慶集》,無蘇鄰之詩。樂天知佛,豈應為此不典之辭?)[49]第3冊,1143
芮傳明先生在《白居易之“摩尼教詩”的可能性》中指出摩尼教盛行于白居易時代,“安史之亂”后,唐肅宗請求回鶻軍隊的援助,剛成為“國教”的摩尼教借助唐廷對回鶻的“優惠待遇”而得以在中國廣泛傳播。憲宗元和二年(807),回鶻使者請于河南府、太原府置摩尼寺三所,許之[50]351-353。
白居易的翰林制誥中就有元和三年(808)撰寫的《與回鶻可汗書》,也講道:“其東都、太原置寺,此令人勾當,事緣功德,理合精嚴。又有彼國師僧,不必更勞檢校。……所令帝德將軍安慶云供養師僧請住外宅,又令骨都祿將軍檢校功德使,其安立請隨般次放歸本國者,并依來奏,想宜知悉。今賜少物,具如別錄。內外宰相及判官、摩尼師等,并各有賜物,至宜準數分付。內外宰相、官吏、師僧等,并存問之。”[51]第3冊,1174-1177此處之可汗即保義可汗,存世的突厥、粟特、漢三語哈拉巴喇哈遜(Kara Balgasun)碑即其記功碑。東都即河南府,東都、太原所置之寺即摩尼寺,師僧即摩尼師。《與回鶻可汗書》還講到唐朝與回鶻的絹馬貿易,陳寅恪在《元白詩箋證稿》討論白居易新樂府《陰山道》時曾加以引用。《陰山道》曰:“五十匹縑易一匹,縑去馬來無了日。養無所用去非宜,每歲死傷十六七。縑絲不足女工苦,疏織短截充匹數。藕絲蛛網三丈余,回紇訴稱無用處。”陳寅恪謂:“又史籍所載,只言回鶻之貪,不及唐家之詐,樂天此篇則并言之。是此篇在新樂府五十首中,雖非文學上乘,然可補舊史之闕,實為極佳之史料也。”[52]261-267,[53]349-352
白居易還撰有多篇與回鶻有關的中書制誥:穆宗即位,派鄭權為入回鶻告哀使,長慶元年(821),白居易撰《入回紇使下軍將官吏夏侯仕戡等四十人授卿監賓客咨議》,擢升隨鄭權出使回紇的軍將官吏。同年回紇毗伽保義可汗薨,白居易撰《祭回鶻可汗文》。四月,白居易撰《冊新回鶻可汗文》,冊封君登里羅羽錄沒密施句主錄毗伽可汗,此為回鶻九世可汗,亦稱崇德可汗。接著又撰《冊回鶻可汗加號文》,加冊其為信義勇智雄重貴壽天親可汗,并告訴他“請仍舊姻,誓嗣前好”。保義可汗生前曾遣使求婚,唐朝答應過,五月,崇德可汗遣使請迎所許公主。朝廷遂封穆宗第五妹為太和公主以降[51]第2冊,603-611、836-837。白居易顯然熟知回鶻與摩尼師的情況。
白居易撰寫過“蘇鄰之詩”還有旁證。宋末四明(寧波)崇壽宮主持張希聲告訴儒生黃震:“吾師老子之入西域也,嘗化為摩尼佛。……吾所居初名道院,正以奉摩尼香火,以其本老子也。”他請黃震為崇壽宮寫記。黃震認為“吾儒與佛老固冰炭,佛與老又自冰炭,今謂老為佛,而又屬記之于學儒者,將何辭以合之,且何據耶?”因書詰之。張希聲回答時給出的一個證據是:“白樂天晚年酷嗜內典,至其題摩尼經,亦有‘五佛繼光明’之句,是必有得于貫通之素者矣。則釋氏之據如此。”[54]第7冊,2311-2313張希聲為了說服儒生黃震為此宮寫記而將“蘇鄰之詩”作為證據,說明他確信此詩是白樂天之作;黃震看到張希聲的多重證據之后,欣然為其寫《崇壽宮記》則說明他并未懷疑“蘇鄰之詩”乃白樂天詩。志磐說其“假稱白樂天詩”,且加上雙行夾注來論證其“假稱”,恐怕是出于對摩尼教的偏見。
霞浦文書《摩尼光佛》的刊布,為此問題的深入探討提供了新的證據與角度。《摩尼光佛》多處將摩尼與蘇鄰聯系在一起:“志心信禮,長生甘露王(即摩尼)。從真實境下西方,跋帝蘇鄰國,九種現靈祥。”[55]60這顯然套用《儀略》。“摩尼佛下生時,托蔭于蘇鄰。”“一,那羅初世人;二,蘇路神門變;三,釋迦托王宮;四,夷數神光現。[眾和]救性離災殃,速超常樂海。一,摩尼大法王;二,最后光明使;三,出現于蘇鄰;四,救我有緣人。”[55]66,72根據《摩尼光佛》,可以肯定“蘇鄰之詩”中的“五佛”,對應上文“一佛、二佛、三、四、五佛,以為第五佛,又名末摩尼。”但是與《金剛經》無關。摩尼教五佛各有自己的活動地域:一佛那羅延(簡稱那羅)“降神娑婆界,國應波羅門”,二佛蘇路支(蘇路)“以大因緣故,說法在波斯”,三佛釋迦文(釋迦)“四生大慈父,得道毗藍苑(藍毗尼園)”,四佛夷數和(夷數)“無上明尊子,降神下拂林”。又說:“第一那羅延,自洪荒世下西方。”“第二蘇路支,救凈風性下波斯。”“第三釋迦文,下天竺國號世尊。”“[第四]夷數和,……神通驗,拂林國,圣無過。”[56]81-84那羅延為印度婆羅門教之大神,故稱“國應波羅門”。蘇路支即瑣羅亞斯德,其活動地域是波斯;釋迦文即釋迦牟尼,其活動地域為天竺,即印度;夷數即耶穌,其活動地域為拂林,即羅馬帝國。二、三、四佛都是在摩尼教文獻中反復頌揚的摩尼的先驅者,活動范圍都是可以用對音法來確定其真實地理名稱。教主五佛摩尼的出生和活動中心蘇鄰,更加應該是一個可以用對音法來確定的真實地理名稱,即古代的巴比倫,薩珊波斯首都所在的直隸省,而不是一個道教杜撰的烏托邦。
七、七時
民國《平陽縣志》所引《竹西樓記》說:“其徒齋戒持律頗嚴謹,日一食,晝夜七時唄詠膜拜。”民刊本作“晝夜七時咸瞑拜焉。”《敬鄉樓叢書》本作“晝夜七時誦膜拜”,另據校注,一本作“晝夜七時唄詠膜拜”。《四庫全書》本作“晝夜七時詠膜拜”[27]147。哈佛燕京圖書館藏清代據明成化元年序刊本抄寫的精鈔本同四庫本。“七時”見于多種摩尼教資料。《七時偈》是《宋會要輯稿》宣和二年(1120)“臣僚言”中所列舉的明教經文之一。志磐也說道:明教徒“以七時作禮”。白玉蟾在《萬法歸一歌》中說:“明教專門事滅魔,七時功德便如何?不知清凈光明意,面色萎黃空自勞。”[56]《摩尼光佛》也說明教僧“七時禮懺”。根據比魯尼的記載,摩尼教選民每天要做七時禮懺,時間是:拂曉、日出、中午、下午三點左右、黃昏、半小時后和子夜[57]。
八、余論
京藏《摩尼教殘經》與民國《平陽縣志》的明教資料相比,包含的信息量相去懸殊,但是,兩者的發現、定性、研究仍有可比之處。1911年羅振玉刊布京藏《摩尼教殘經》時,在按語中寫道:“然考火祆、摩尼與景教頗類似,未易分別,且皆由波斯流入中土,故姑顏之曰波斯教經,以俟當世之宗教學者考證焉。”[58]1265他未能確定此文獻之宗教屬性。劉紹寬在1925年出版的《平陽縣志》中披露并考證有關資料時,稱之為“末摩尼教”,也并未厘清其宗教屬性。
但是,兩者此后的遭際卻大相徑庭。所謂《波斯教殘經》立即被羽田亨、沙畹、伯希和諸人考定為摩尼教經文,沙畹、伯希和的精深研究很長時期無人能夠超越,陳垣又很快刊出了此文獻的校點本。民國《平陽縣志》中的相關資料卻被冷落了半個世紀,直到20世紀80年代新修方志的環境下,才重新引起重視,定性為摩尼教資料,得到研究與探討。
20世紀90年代,對京藏《摩尼教殘經》的研究有了比較大的進展。德國學者宗德曼檢出與京藏《摩尼教殘經》內容相關的安息語、粟特語殘卷凡四十九號,著成《〈[明使演說]惠明經〉——東傳摩尼教的一部說教作品:安息語和粟特語本》[59],系統地探明了《摩尼教殘經》的伊朗語原本。最近,劉南強、米克爾森、埃克爾斯等學者吸收其成果,將漢文與相應的安息文、粟特文、回鶻文相對照,翻譯成英文,詳加注釋,已出版了第一卷[60]。這是國際摩尼教研究領域的一項重大成果。
同時,民國《平陽縣志》中的摩尼教資料也尚有進一步研究的余地,本文就是在這方面所做的一個嘗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