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論語》翻譯看抵抗式翻譯的取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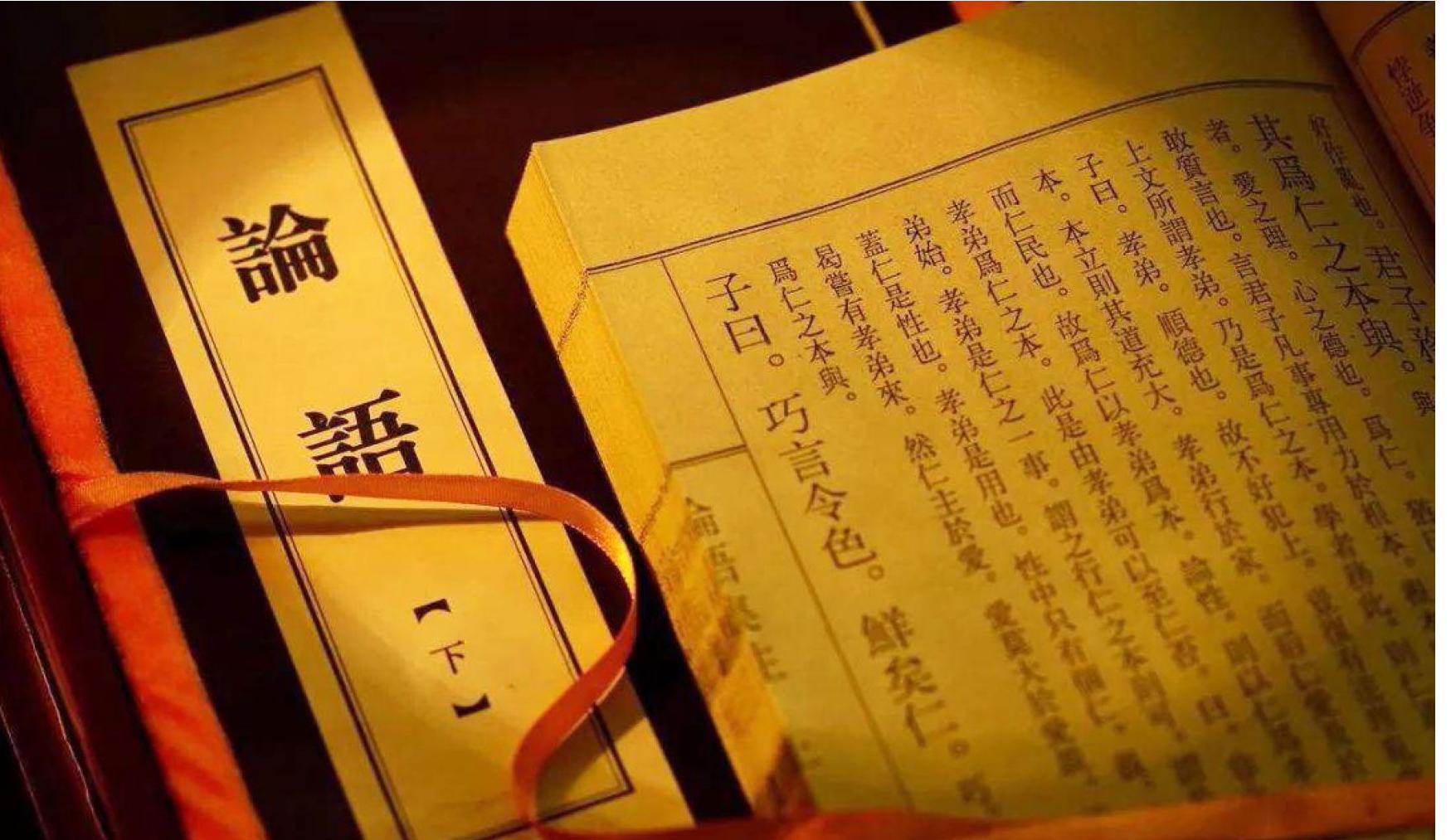

摘要:抵抗式翻譯是韋努蒂通過衡量譯者地位以及翻譯中所包含的文化、語言關系所提出的一種翻譯策略。這種翻譯策略旨在實現提高譯者地位的愿望并打破英美主流文化在翻譯中的強勢壟斷,同時旨在促進文化的傳播。本文通過分析《論語》不同版本的翻譯來探究翻譯中的文化抵抗,來探討《論語》翻譯的文化傳播功能及抵抗式翻譯的取舍。
關鍵字:勞倫斯·韋努蒂;抵抗式翻譯;文化傳播
“抵抗式翻譯”一詞最早見于勞倫斯·韋努蒂主編的《反思翻譯》中,并豐富于其著作《譯者的隱身——一部翻譯史》。《譯者的隱身——一部翻譯史》中通過梳理翻譯歷史進程,揭示單純以通順這一原則作為評價翻譯唯一標準的不合理性,以及譯者隱身的不合理性,因此針對性地提出抵抗式翻譯。這一理論現已廣泛運用于中譯英的具體實踐中。本文將通過對具體文本的分析來探討該翻譯策略的實際運用,并探討文化的傳播。
一、抵抗式翻譯
韋努蒂認為,抵抗式翻譯主要運用異化的翻譯原則,即保留源語文本的語言文化風格,要求譯者在翻譯過程中凸顯語言之間的差異,從而實現抵抗目的語的主流文化與價值觀的目的。此外,抵抗式翻譯反對以通順作為翻譯的唯一標準,要求凸顯翻譯痕跡,即提倡譯者顯身[1]。實現這種抵抗式翻譯的途徑主要有兩種:其一,運用與目的語所流行的迥然不同的語言來進行翻譯,如運用古語來進行翻譯,以打破譯者隱身的狀況;其二,選擇與目的語主流文學不同,甚至相悖的外國文學作品來進行翻譯。將這樣的要求應用在中譯英中,那就是要去選擇凸現中西方文化差異的文本進行翻譯,或者刻意運用風格迥異的語言風格來進行翻譯。
韋努蒂通過引入這一翻譯手段主要想打破譯者隱身的傳統。在當時的英美文化中,學者、讀者評判翻譯好壞的標準是翻譯文本的通順與可讀性。如果一部作品過于通順,而讓讀者感受不到翻譯的痕跡,就可以說譯者是隱身的。針對譯者的隱身性,作者主要從兩方面來進行批評。第一是譯者的地位。在譯者隱身的同時,原作者與原作的內容得到了凸顯,這樣一來沒有翻譯痕跡,譯者的地位也被隱去了。由于地位沒有得到凸顯,本來處于邊緣地位的譯者則更難以為人注意。第二是文化傳播的角度。在文化迥然不同的兩種語言之間,譯者如果在翻譯過程中將弱勢文化的語言風格抹去,并以強勢文化的語言風格作為替代,這種行為是一種文化霸權行為。
二、抵抗式翻譯的時代價值
20世紀以來,隨著交流工具先進化,廣告業、娛樂行業得到發展,語言的使用也更加工具化。借用美國詩人查爾斯·伯恩斯坦的話來說,由于各行業的需要,他們無法自由選擇工作所需要的語言風格,于是親自體會了經濟價值對翻譯、寫作透明風格的決定性影響。對于這樣的時代來說,譯者的隱身已是大勢所趨。韋努蒂坦言,當時不少暢銷的英譯小說作品都無法感受到譯者翻譯的痕跡,且這些作品的唯一標準就是通順。可以說,在20世紀,譯者的隱身蔚然成風,翻譯通順的譯者會被贊揚,反之就會被批判。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韋努蒂獨特的抵抗式翻譯思想如同一面戰旗,向譯者隱身的潮流發起了挑戰。
韋努蒂通過提出抵抗式翻譯旨在強調譯者的主體地位,批判英美文化的排外主義[2]。隨著21世紀的到來,全球經濟得到進一步發展,全球化的特征越來越明顯,文化也成為全球化的一部分。在這樣的全球化趨勢下,無論是要促進各文化平等交流,還是要促進各自文化、語言的發展,排外主義都會是一大阻礙。隨著中國與英語國家的交流越來越密切,彼此的文化交流也越來越頻繁,各種中國經典的典籍被外翻為英文版本,因此如何合理運用抵抗式翻譯促進中國經典作品走出去,仍值得我們認真思考。
三、《論語》翻譯中的文化抵抗
《論語》為中國儒家的經典典籍,是譯者進行外翻的熱門對象。作為儒家經典,《論語》緊貼中國的傳統文化,將這樣的典籍進行外翻,有利于實現中國文化走向世界。但是,翻譯的手段決定著翻譯是否能實現這一目標。因此,本文將對《論語》不同版本的翻譯做對比分析。
(一)文本的選擇
上文提到,實現抵抗式翻譯主要有兩種途徑,即語言與文本的選擇。抵抗式翻譯觀的前提是文化有差異[3]。中西方之間擁有明顯的文化語言差異,這使得抵抗式的翻譯在中英翻譯之間有了討論的價值。韋努蒂明確表示,應該選用與目的語主流文化不同,甚至相悖的文本來進行翻譯。中國本土有著諸多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且這些作品與西方文化的價值觀截然不同,如中國的儒家文化、道教文化、武俠文化等作品,甚至還有由外傳入并在中國傳播數千年的佛教文化作品。選擇富有民族特色的作品進行翻譯,有助于促進該民族的文化走出國門,為世界所熟悉甚至認可,也可以促進不同文化之間的交流。誠然,隨著中國對外交流的頻繁,不少有識之士將許多經典著作英譯版帶出國門,如古代名著《論語》《詩經》,近現代小說《邊城》《阿Q正傳》,甚至是現代武俠小說《射雕英雄傳》等。但是由于翻譯者進行翻譯的目的、概念不同,同一部翻譯作品可能擁有截然不同的翻譯風格。換句話說,即使譯者選擇了一部富有民族特色的文本進行翻譯,但結果可能是異化的,也可能是歸化的。下面以中國經典外翻典籍《論語》為例。
例一:
子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
理雅各譯: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Chün-tsze and
the small man.The Master said, “The superior man is catholic and not partisan. The mean man is partisan and not catholic.”
辜鴻銘譯:Confucius remarked, “A wise man is impartial, not neutral.A fool is neutral but not impartial.”
吳國珍:The Master said, “The virtuous people widely unite but not gang up; the virtue less people gang up but not widely unite.”
同一篇《論語》,卻有許多種不同的翻譯風格。這三篇翻譯各有特點,但總體來說,前兩篇翻譯風格更加相近。首先是對君子與小人含義的翻譯,理雅各版本給出了一個音譯來的外文表達:Chün-tsze,這樣的音譯與直接使用中文的拼音不同,這樣的表達完全西化,是西方讀者完全能夠接受的翻譯表達方式,可以說是一種歸化翻譯的態度。而后面的兩篇翻譯,譯者均采用直接翻譯文字意義的方式進行。 作為一名傳教士,理雅各的翻譯難以剝離宗教的外殼,因此其選用了catholic與partisan兩個宗教性質濃烈的單詞來對該句進行翻譯,非但不能正確傳達原句句意,反而使其嚴重西化,反而橫生了與《論語》完全無關的西方宗教的風格。在批評理雅各翻譯失真的前提下,辜鴻銘作為中國早期的學士,有志于將中國儒學經典西傳,于是有了第一部由中國人翻譯的《論語》。辜鴻銘翻譯版本的《論語》能夠較為準確地傳達原文句意,有助于將中國典籍的意義西傳。相較理雅各的翻譯版本,其更能直觀反映中國文化的精髓。作為現代學者,吳國珍翻譯版本的《論語》于2012年出版,在研究了諸多《論語》翻譯文本后,吳國珍的翻譯可以說更加中化,這不僅體現在用詞上,也體現在句式表達上。如前兩個翻譯版本,譯者均采用主系表的鏈接方式,并在句號分割前后形成兩句進行表達,前后兩句均為未采用或者未完整采用原文句式,可以說這樣的翻譯風格明顯屈從于英語的形合特點,因此更加符合西方人的閱讀習慣。而吳國珍版本前后采用主謂賓的句式,由兩個but進行原文“而”的表達,既符合原文意義,又貼合原文表達,可以說是中式化的表達方式。由此可以看出,三個版本的抵抗式翻譯痕跡在遞增。
(二)語言的選擇
異化翻譯意味著外國文本的不同,但只是通過破壞流行于目的語中的文化符號來做到這一點[4]。前文提到,選擇文本十分重要,但是翻譯所選用的語言對于抵抗式翻譯來說則更為重要。如果采用目的語流行的語言風格,那么即使文本選擇得當,意義傳譯準確也無法使得原文文本的文化與語言風格得到傳遞,更遑論促進文化地傳播了。翻譯如果只是譯出原文的意義,不表現原文的文化內涵,就會丟失掉很多有價值的東西[5]。從這個角度來看,尊重原語的文化風格與語法內容,進而實現抵抗式翻譯是有意義的。
例二:
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為人謀而不忠乎?與朋友交而不信乎?傳不習乎?”
理雅各譯:How the philosopher Tsang daily examined himself, to guard against his being guilty of any imposition.The philosopher Tsang said, “I daily examine myself on three points:-- whether, in transacting business for others, I may have been not faithful;-- 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 I may have been not sincere;-- whether I may have not mastered and practiced the instructions of my teacher.”
辜鴻銘譯:A disciple of Confucius remarked,“ I daily examine into my personal conduct on three points;firstly, whether in carrying out the duties entrusted to me by others, I have not failed in conscientiousness; secondly, whether in intercourse with friends,I have not failed in sincerity and trustworthiness ;thirdly ,whether I have not failed to practice what I profess in my teaching.”
吳國珍譯:Zengzi said, “I ask myself several times in my daily introspection: Am I not dedicated when handling affairs for others? Am I not faithful in association with friends? Have I not reviewed the lessons taught by the teacher?”
具體分析:我們首先來探討曾子人物名字的翻譯,理雅各版本給出的是一個音譯的英文的名字,這樣一來西方讀者更能夠接受這樣的翻譯風格,可以說是一種歸化翻譯的態度。辜鴻銘版本則直接省去對曾子名字的翻譯,以一個籠統的“弟子”形象進行傳譯,雖然表義正確,但卻沒有緊貼原文信息,以譯文讀者更能接受的方式進行翻譯,仍然屬于歸化的翻譯態度。吳國珍版本則以漢語拼音的方法對人名進行翻譯,這是一種以原文為中心的翻譯態度,異化明顯。另外,在前兩篇的翻譯中,譯者運用歸化的翻譯態度來行文,如第一版本的各種連字符與插入語、第二版本的數字順序行文,都以英語的形合特點進行翻譯,十分照顧英語語言讀者。而在第三版本的翻譯中,吳國珍完全根據原文的句式進行行文,以三個反問句進行直譯,既保留了原語言的行文風格,又準確地對文章意義進行了傳達。最后,《論語》中的對話式道德教育方法是一種啟發式教學,對話方式本身沒有一定之規,完全出于對話的實際需要[6]。作為一種對話式的教育文本,《論語》原著的風格以口語化為特點,那么相應的翻譯也應該流暢自然,以簡單對話的形式出現,而不應繁復化、書面化。在這三個文本當中,只有第三個翻譯文本做到了這個要求。因此,在中譯英的翻譯過程中,除了要考慮文本的選擇外,語言因素也應該著重考慮,以防止翻譯文本的西化,阻礙民族文化的傳播。
四、抵抗式翻譯的舍
(一)精英主義思維
“想要在翻譯過程中保存源語文本中的語言、文化差異的譯者只能在受過良好教育的精英群體中獲得讀者。”韋努蒂的精英主義是他自己用于回應對抵抗式翻譯質疑的觀點。他認為由于抵抗式翻譯對譯文通順性的批判,從而喪失龐大的支持群體,因此這一翻譯準則只能為少數受過良好教育的人所接受。可是韋努蒂對于精英主義沒有更多詳細的論述,到底如何去評價一個人是否屬于所謂的“精英”,只能從他是否受過良好的教育來思考。這一評價標準過于主觀,難以對其精英主義進行精準定位,這是其精英主義的第一個弊端。此外,精英主義立場使差異倫理有遠離大眾的危險[7]。由于群眾基礎的斷裂,其翻譯思想本就難以受到更多人的關注,從而就更難形成一種人人想要遵從的社會風尚了。因此,在中翻英的過程中,譯者需要審慎對待所謂的精英主義觀念,更要做到在推崇本國的文化風尚的同時去獲得良好的讀者基礎。否則,讀者基礎的缺失,勢必會導致翻譯文本的閱讀量受限,這樣一來更加難以談及語言與文化地傳播了。
(二)對于通順的大肆批判
韋努蒂認為,一部翻譯作品越是通順,那么譯者就越是隱身。因此韋努蒂大肆批判通順對于翻譯的評價準則,這一觀點與魯迅的“寧信而不順”有著相似之處。然而,如果全盤接收其抵抗式翻譯的觀點,那么文本一旦選定,譯者在語言、文體、韻式、節奏、敘事模式等方面背離主流以求新立異,這種與翻譯傳統斷然決裂的譯文文本一時很難為大量的讀者接受[8]。要求文本的可讀性與流暢性并不是一個錯誤的觀念,因為文本的可讀性與其讀者基礎息息相關,而傳遞原文文本的文化語言風格,就是要讓其走入異域人的視野中,本不應該與抵抗式翻譯的目的相斥。因此,在中譯英的過程中,盡力保持文本的通暢性也應受到譯者的充分考慮。
(三)審慎對待“極端”
對于韋努蒂的抵抗式翻譯理論來說,其要求的異化程度可以說是極端的。前文提及,韋努蒂抵抗式翻譯的兩大弊端是精英主義與對譯文通順的不合理批判。這兩點都是源自其對于“抵抗”的極端追求。弱勢文化的譯者在翻譯過程必須面臨著兩難的抉擇,要尋求歸化和異化之間的一個平衡點[9]。從前文《論語》翻譯的例子來看,如果以韋努蒂的要求來進行翻譯,翻譯文本必定晦澀難懂且語意不通,讓讀者難以產生閱讀的興趣,這更不利于文化的傳播。那么,在歸化和異化之間尋找平衡就是一個非常好的解決辦法。對于“度”的把握需要考慮兩個方面,即不可因運用抵抗式翻譯使得文本難以閱讀,也不可完全傾向于西方讀者的閱讀習慣,致使文意背離,文章西化。
五、結語
時至今日,抵抗式翻譯在中英的翻譯中仍然擁有重要意義。隨著中外的廣泛交流,越來越多的中國經典文本需要走出國門,為促進中外文化交流做出貢獻,因此這一翻譯策略也勢必在未來煥發出新的生機。但是韋努蒂有關抵抗式翻譯的觀點并不應該被全盤接收,我們需要在翻譯過程中摒棄其不合理的,保存其擁有價值的,做到對韋努蒂關于抵抗式翻譯理論的有舍有取,才是繼續運用這一翻譯策略的正確態度。
作者簡介:閆傲(1996- ),山西人,天津大學外國語言與文學學院研究生。
參考文獻:
〔1〕Venuti Lawrence. The Translator,s Invisibility:A History of Translation[M]. Shanghai: Shanghai Foreign Language Education Press,2004.
〔2〕付仙梅.試論韋努蒂翻譯理論的創新與局限[J].上海翻譯,2014(3):75-77.
〔3〕高慧.論勞倫斯·韋努蒂的抵抗式翻譯策略[J].時代文學,2012(3):48-49.
〔4〕封一函.論勞倫斯·韋努蒂的解構主義翻譯策略[J].文藝研究,2006(3):39-43.
〔5〕譚振華.簡論異化翻譯[J].時代文學,2009(14):30-31.
〔6〕馬忠,黃建軍.《論語》中的對話式道德教育方法研究[J].中國大學教學,2013(4):68-72.
〔7〕楊鎮源.論韋努蒂的文學翻譯倫理思想之局限性[J].當代文壇,2013(6):37-39.
〔8〕任淑坤.解構主義翻譯觀芻議 ——兼論韋努蒂的翻譯思想和策略[J].外語與外語教學,2004(11):55-58.
〔9〕張萬防.后殖民主義譯論的“文化霸權”解構策略的反思[J].外國語文研究,2018(4):77-8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