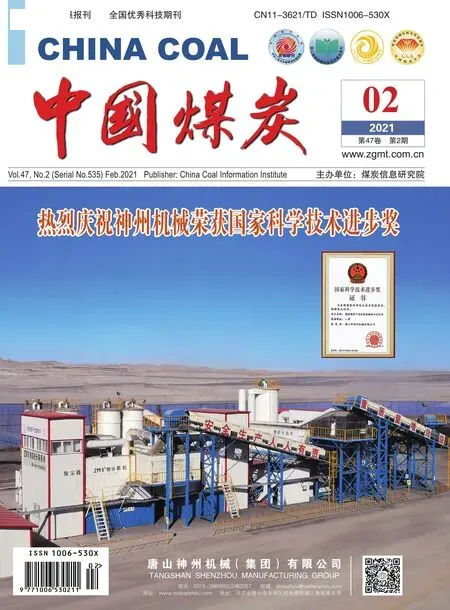我國化石能源固碳利用新途徑探索及研究
朱維群,王 倩,郭宇恒
(1.山東大學化學與化工學院,山東省濟南市,250100;2.山東大學國家膠體材料工程技術研究中心,山東省濟南市,250100)
2020年9月22日,在第75屆聯合國大會一般性辯論上,我國鄭重承諾將提高國家自主貢獻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CO2排放力爭于2030年前達到峰值,努力爭取2060年前實現碳中和。這一目標的宣布在國內外立刻引起了強烈反響[1]。為實現21世紀內將溫升控制在2 ℃之內的目標提供了可能性,也使全球向控制溫升1.5 ℃的目標邁進了一步。為了實現我國2030年前碳達峰和2060年前碳中和的目標,我國需要付出比發達國家更大的努力。從碳達峰到碳中和,發達國家過渡期有50~70 a的時間,而我國只有30 a的時間,能源和經濟轉型、CO2和其他溫室氣體減排的速度和力度都要比發達國家大得多。因此,研發切實可行的CO2減排路徑是我國各界研究學者廣泛關注的焦點。
1 實現碳中和的技術路徑分析
目前,碳基能源仍然是我國能源結構的主體,化石能源的消費占比超過80%,其中煤炭占比高達55%。因此要實現碳中和的最終目標,應當是盡可能減少化石能源利用產生的CO2排放,開發新的綠色低碳排放技術。
低碳排放技術大致可分為3類,源頭控制的“無碳技術”,即綠色能源技術;過程控制的“減碳技術”,即現有工業過程的節能減排技術;末端控制的“去碳技術”,即捕集封存利用CO2技術(CCS/CCUS)。
1.1 “無碳技術”——綠色能源技術
綠色能源一般具有能量密度低的缺點,其發電系統的涉網能力與安全防護能力不足,增加了電網運行風險。未來隨著我國綠色能源應用逐步進入“無補貼”時代,非技術性成本的不利影響將成為制約風電和光伏發電等綠色能源發電的重要因素,甚至可能影響風電和光伏發電進入“無補貼”時代。當前清潔能源的發展還面臨著電網接納、經濟性、清潔能源的利用技術亟待突破、標準體系不完善等系列問題[2],短時間內還不能成為能源主力。
1.2 “減碳技術”——節能減排技術
降低化石能源的使用對減少溫室氣體排放的影響比較顯著[3],但2019年煤炭占我國能源消費的比例仍然高達58%,據預測,直到2050年,化石能源將繼續在我國的能源結構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首先,倪維斗院士[4]認為:以煤為主是我國資源稟賦不可變化的事實,其他替代能源只能是輔助能源,而不可能成為主力;其次,我國現有的工業技術已經發展的比較成熟,由于技術路徑鎖定效應[3](行為習慣、思想意識、體制機制、基礎設施、既有產能),現有工業過程節能減排的潛力有限;最后,工業過程的節能減排還面臨著來自工廠企業和國家的投資、民眾環保意識較為薄弱、基礎設施和產能鎖定、短時間難以大規模變革等一系列挑戰。
1.3 “去碳技術”——CCS/CCUS技術
CO2捕集封存利用技術(CCS/CCUS)目前尚未展現出足夠的商業化可行性[5]。目前國內進行了多個CO2捕集及封存項目,CO2總量不到100萬t。根據目前情況測算,煤電應用CCUS將使能耗增加24%~40%、投資增加20%~30%、效率損失8%~15%,綜合發電成本增加70%以上。因此,CO2捕集封存利用技術在煤電領域難有大規模的應用,而且在生產過程中排放大量CO2,再去捕集、封存及利用,在實際過程中可能得不償失,也就是說捕集封存實施過程耗能所排放CO2的量可能大于所封存的CO2量。
總之,目前我國低碳排放技術的發展及應用現狀是:綠色能源和綠色碳匯的快速發展受限、現有工業過程的節能減排潛力有限、現有工業過程排放的CO2難于封存利用。因此,為了實現全球碳中和的目標,急需開發新的低碳排放工業路線。
2 化石能源固碳利用的新途徑
CO2主要是在化石能源利用過程中排放的,例如火電是將化石燃料通入空氣(N2、O2)燃燒產生高溫,然后將能量轉化為電力,CO2作為煙氣排放,其化學反應式見式(1):
CHn+N2+O2→CO2+N2+H2O
(1)
式中:n——不同化石燃料分子中H的占比,一般為0.8~4,CH0.8代表煤炭,CH4代表天然氣。
如煤電煙氣中的CO2濃度一般為10%~20%。雖然全世界對現有煤電排放CO2的捕集封存利用進行了廣泛深入的研究開發,但目前還沒有找到比較經濟可行的技術路線。
2.1 固碳利用的能源工業路線
筆者提出了將化石能源的能量和物質同時高效利用的科技開發路線,即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氣)采用空分出來的純氧氣化(O2+H2O)反應生成CO2,在能量釋放后將所產生的CO2直接轉化為CO2固定量最高的穩定固體產物1,3,5-均三嗪三醇(C3H3N3O3,簡稱三嗪醇),過程中釋放的能量和剩余氫作為清潔能源進行利用,從而實現化石能源能量和元素成分的同時高效利用,形成化石能源固碳利用的能源工業路線。以煤炭為例,其總的化學反應式見式(2):
3C+1.5N2+0.75O2+1.5H2O→C3H3N3O3
(2)
該反應為放熱反應,放熱量為327.7 kJ/mol。
其中包括的主要化學反應見式(3):
(3)
與化石燃料空氣燃燒相比,能量釋放可能有所減少,但實現了CO2和部分N2等物質的利用,同時也是CO2固定利用最可行的方式。化石能源固碳利用的能源工業路線示意圖如圖1所示。

圖1 化石能源固碳利用的能源工業路線示意圖
這樣化石能源固碳利用新途徑不僅減排了CO2等污染物,而且還提高了化石能源總的利用效率,綜合經濟效益更好,可以作為應對全球氣候變化經濟可行的技術途徑。
筆者對三嗪醇的生成反應過程進行了500 kg/h的中試,在一定壓力、溫度和催化條件下,得到三嗪醇固體產品和可循環利用的副產物——氨氣。三嗪醇產品為純白色固體,質量良好,單程轉化率為75%,產品純度為90%。從反應過程來看,該過程具有實現大規模工業化生產的條件。
2.2 技術路線優勢
化石能源固碳利用新途徑具有以下多方面的優勢。
(1)三嗪醇是CO2固定量最高的穩定固體產品,生成1 t三嗪醇需要消耗1 t的CO2,這是固定利用CO2最有效的化學反應[6-7],其生產過程也是氫耗量(能量消耗)最少的一種固定CO2過程。
(2)在此過程中CO2生成即固定,減少了CO2氣體的熵增過程。現有工業生產過程中排放出的CO2,再去捕集、封存或利用,往往得不償失。
(3)由化石能源生成三嗪醇是反應熱較大的工藝過程,不僅可以促進整個工業過程的自發進行,而且還能釋放大量的能量。
(4)在此路線中化石能源在純氧氣化工藝過程中沒有NOx產生,原料中的硫在反應過程中轉變為硫磺,CO2直接轉化到產品中,實現了化石能源元素成分的高效利用。
(5)不同化石能源(煤、石油、天然氣)在CO2固定后有不同的能量釋放,可根據應用場景按需設計,可以采用燃氣輪機、廢熱鍋爐、燃料電池等各種能量轉換技術。
(6)該技術可以在現有化石能源工業利用過程裝置的基礎上進行改造、革新,投資相對較小,經濟上完全可行。
(7)在全球化石能源中,石油和天然氣占70%,煤炭占30%,該技術的開發可以保持全球能源的供需平衡和社會經濟的平穩發展。
(8)該技術路線不僅減少了在化石能源利用中CO2等污染物的排放,而且提高了化石能源總的利用效率,綜合經濟效益更好。
(9)三嗪醇產品固碳周期長,而其它CO2固定產品如醇類、酯類、碳酸酯類、尿素等,其生命周期通常局限在6個月內,較容易降解并釋放出 CO2重返到大氣中[7]。而三嗪醇是穩定的固體產品,可以實現長時間的固定CO2,而且三嗪醇產品用途廣泛、附加值高。
該能源工業路線可以說是IGCC(整體煤氣化聯合循環發電系統)和煤化工的結合,它可以實現化石能源能量的梯級利用,高位端的能量優先用于發電,低位端的能量用于化工合成,通過系統集成提高了化石能源的能量和物質利用效率,減少CO2排放。化石能源的固碳技術利用原理如圖2所示。

圖2 化石能源的固碳技術利用原理
2.3 化石能源固碳利用技術路線部分應用場景
2.3.1化石能源固碳利用技術的制氫技術
氫能作為一次能源的一種二次能源利用方式,應該詳細分析其產業鏈總的能源利用效率和污染物排放。通過來源于風能和太陽能的可再生能源電解水制取氫,不但受制于發電成本,而且能源轉化效率低,最好直接利用綠電;通過煤炭、天然氣等化石燃料制取氫,再通過CCUS技術對CO2進行捕集封存利用的可行性也不高。
可以采用化石能源固碳利用技術的方式制氫。如天然氣制氫的設計見式(4):
6CH4+2O2+3N2+6H2O→2C3H3N3O3+15H2
(4)
化石能源固碳利用的方式制氫可應用于氫能開發、分布式能源及清潔供熱等應用領域。
2.3.2三嗪類高固碳材料的開發
高碳資源(化石能源)只有生產高固碳產品(在生產和應用過程不排放或少排放CO2)才更有利于實現低碳排放的工業利用。朱維群等[8-11]研究人員以三嗪醇為原料合成得到了一類低成本、低碳排放、低內能的三嗪類高固碳材料,該專利方法比現有三嗪類材料生產工藝減少1倍的原料消耗,中間物料和中間過程大幅減少,產品純度更高且工藝操作簡易、過程能耗低、固定資產投資少。該類材料具有無毒無味、耐腐蝕、耐溫性強、阻燃、質輕、有較強的耐用性等綜合性能,廣泛應用于建筑裝飾、交通車輛、航空航天、機電設備、工業吸音保溫等領域。
3 結論
化石能源固碳利用的新途徑是將化石能源利用過程中所產生的CO2直接轉化為固碳產品三嗪醇,過程中釋放的能量和剩余氫可作為清潔能源利用,從而實現化石能源能量和元素成分的同時高效利用。
化石能源固碳利用新途徑不僅減排了CO2等污染物,而且提高了化石能源總的利用效率,綜合經濟效益更好;三嗪醇固碳產品也可以繼續開發得到一類低成本、低碳排放、低內能的三嗪類高固碳材料,為我國實現碳中和目標提供一條經濟可行的能源和材料技術路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