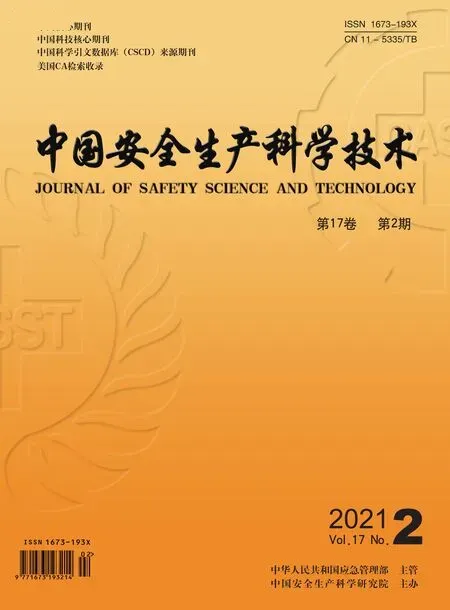基于海洋環境要素的動態航行風險評估*
杜 沛,任利鋒,劉善偉,曾 喆
(1.中國石油大學(華東) 海洋與空間信息學院,山東 青島 266580; 2.中國石油集團 東方地球物理勘探有限責任公司海洋物探分公司,天津 300457)
0 引言
海洋運輸作為各國貿易往來主要方式,其航行安全也成為全球性重要議題[1],定量評估航行過程中影響因素意義重大。航行風險評估模型建立以專家經驗數據與事故統計數據為基礎,主要考慮船舶、船員、海域環境3種影響因子,利用貝葉斯網絡法從事故數據中挖掘風險信息[2-3]。利用可拓學方法研究人為、船只、環境和管理因素,評估跨海客滾運輸船的航行風險[4];基于灰色關聯分析方法建立航行環境風險評估模型[5-6],但該模型僅體現靜態分析結果,海域空間探討及風險預警能力欠缺。快速制圖技術在風險評估、災情跟蹤、響應及部署等方面發揮重要作用[7]:洪水風險、滑坡風險等均可通過快速制圖方式實現風險動態可視與風險預警[8-9];層次分析法被廣泛應用于GIS決策與航行風險評估領域,但存在主觀性較強的弊端[10-12];為削弱主觀因素影響,提出基于模糊層次分析法(Fuzzy-AHP)模型,通過利用多組專家經驗獲取評估因子權重,并實際應用于中國南海航行風險評估研究[13]。本文為進行航行風險動態評估,提出均衡權重與時序權重概念,并采用有序加權法對評估因子要素與時序進行優化AHP定權,研究評估因子對航行風險影響,提高動態航行風險評估效率。
1 動態航行風險評估
基于海洋環境要素,動態風險評估過程包括以下3個步驟:海洋環境要素數據采集、數據預處理,動態航行風險評估。其中,數據預處理以時間、空間維度插值計算和去量綱化為主。動態航行風險評估流程如圖1所示。
1.1 原始數據
動態海洋環境要素主要包括:風場、海浪、海流、海溫,靜態要素為海底地形,數據信息見表1。
建立數據庫(MongoDB),對各類環境要素數據進行動態更新與維護。動態數據來源于美國國家海洋和大氣管理局。

圖1 動態航行風險評估流程Fig.1 Flow chart of dynamic navigation assessment

表1 數據信息Table 1 Data information
1.2 數據預處理
因航行風險評估數據空間與時間維度分辨率不統一,評估前需對數據進行空間與時間插值,統一時空分辨率。為保證評估賦權可靠性,用統一標準將數據無量綱化。
1)數據空間處理
用于評估的各類數據呈現整齊格網分布,為確保局部環境數據分布特征不發生改變,采用雙線性插值法處理空間數據。插值數據由臨近4個角點計算得到。雙線性插值計算如式(1)所示:

(1)
式中:f(x,y)為坐標(x,y)插值結果;坐標對(x1,y1)、(x1,y2)、(x2,y1)、(x2,y2)分別為臨近(x,y)左上、左下、右上、右下4點坐標;f(x1,y1)為坐標(x1,y1)要素值。
插值計算可統一數據空間維度分辨率,使評估結果在空間具有連續性。
確定每個評估因子縮放比例,使不同空間維度數據量綱保持一致。例如:根據經驗可知,當風速達到7~8級時,客滾船與貨船被禁止出海,已出海船只需尋找臨近避風港,以7級風速作為歸一化標準,歸一化后風速如式(2)所示:
(2)
式中:α,α′分別為歸一化前后風速,m/s。
2)數據時間維插值
不同數據在時間維精度不同,評估前須利用差值法統一分辨率。插值法存在一定誤差,但相對海洋環境要素,在小范圍時間、區域發生劇烈變化的概率極其微小,總體變化趨勢平滑。采用線性插值補充時間尺度缺失數據,計算公式如式(3)所示:
(3)
式中:xt+i×T為2個時間節點間空缺數據值;T為新的時間分辨率;i為索引值;xt,xt+n分別為時間節點兩端數據。
結合式(3),將不同時間分辨率的數據統一精度,取點位[84°E,10°N],在2020年9月22日洋流流速30 h預報值,時間分辨率為3 h,插值法前后洋流預報數據如圖2~3所示。由圖2可知,數據存在缺失,經插值計算得到圖3。由圖3可知,洋流預報數據總體變化趨勢較平滑,時間分辨率為1 h。
1.3 評估方法
動態航行風險評估方法主要包括層次分析法(以下簡稱AHP法)、權重優化和動態風險制圖。AHP法將專家經驗知識轉化為因子權重值,代表決策過程中各因子的相對重要程度[14]。對23位航海經驗豐富的專家進行問卷調查,統計調查數據,對數據統一均值處理并進行AHP方法定權。AHP方法定權主要包括以下4個步驟:

圖2 插值前洋流預報數據Fig.2 Forecast data of ocean current before interpolation

圖3 插值后洋流預報數據Fig.3 Forecast data of ocean current after interpolation
1)采用一致矩陣法構建判斷矩陣。
2)計算矩陣特征值,取最大特征值所對應特征向量,進行歸一化處理。
3)對歸一化特征向量進行一致性檢驗,計算一致性比率。
4)當一致性比率小于0.1時,通過一致性檢驗,并將歸一化特征向量作為權向量,否則重新構建判斷矩陣并重復步驟1)~4)。最終得到每個風險評估因子權重值,評估因子權重見表2。

表2 評估因子權重Table 2 Weights of assessment factors
AHP法主觀性較強,各評估因子權重存在較大差異,評估過程中,固定權重無法體現較大變化因子的重要性:T1時刻海上某點風速15.1 m/s,浪高2.3m;T2時刻該點風速15.2 m/s,浪高4.3 m,由于風速因子權重較大,浪高因子權重較小,AHP法得到的權重無法很好體現浪高突增帶來的風險。本文采用有序加權法,在因子和時序間進行2次權重計算,分別為均衡權重和時序權重:均衡權重用于平衡各因子原本存在的權重差異,在評估因子間展開計算;時序權重用于突出動態變化因子對航行風險的影響,在評估因子時序間展開計算。最終優化權重為均衡權重與時序權重乘積。
1)均衡權重計算

(4)

(5)

2)時序權重計算

(6)

(7)

最終優化權重wt,m為均衡權重與時序權重乘積,如式(8)所示:
(8)
根據式(4)~式(8),在每個柵格像素上計算優化權重。不同區域不同時間權重值均根據區域海洋環境要素時空分布動態調整,避免單一定權模式。最終風險值如式(9)所示:
(9)

將風險值劃分5個層次,分別代表不同航行風險程度,危險層次劃分見表3。

表3 危險層次劃分Table 3 Division of risk levels
2 實例分析
2.1 試驗區域簡介
試驗區域為孟加拉灣南部[80°E,97°E,3°N,14°N],西臨斯里蘭卡,東側通過馬六甲海峽與南海相連,是海上絲綢之路重要航行區域,該區域中尺度漩渦較多,同時受夏季風和熱帶氣旋影響[15],多變的天氣對航行影響較大,試驗區域如圖4所示。

圖4 試驗區域Fig.4 Experimental area
2.2 動態風險評估
為更好體現動態航行評估效果,本文開展2組試驗:第1組表示航行風險評估模型遭遇惡劣海況時評估效果;第2組表示數據插值后評估連續性。
試驗1以2020年12月4日8∶00孟加拉灣氣旋風暴“布列維”通過研究區域的時間段作為研究對象,此時氣旋中心風速20 m/s,浪高5.5 m,海事部門禁止船舶出海航行,氣旋風暴經過研究區域模型評估結果如圖5所示。由圖5可知,00∶00到15∶00高風險區域在每個時間段的空間分布以及風險隨時間的變化特點。據海事局報道,2020年12月4日08∶00時,氣旋風暴在斯里蘭卡東南部生成,由09∶00時評估結果可知航行風險在空間中聚集位置,且高風險區域逐漸向東移動。整體航行評估數據采用2020年12月4日00∶00時預報數據,對船舶航行具有較強預警能力,船員可根據風險空間與時間分布,合理規劃躲避氣旋風暴。
試驗2評估數據選取間隔為6 h的預報數據和插值處理后間隔為1 h的預報數據。試驗2航行評估結果如圖6~7所示。由圖6可知,以6 h為間隔進行評估時,風險變化幅度較大,沒有體現出航行風險隨時間演變過程,風險動態連續性展示效果不明顯;由圖7可知,局部航行風險生成及消退過程整體風險評估值變化較小,局部區域隨時間變動明顯,評估結果能較好體現風險變化連續性。
對2組試驗結果進行分析發現,淺水區航行風險值較高,評估結果能體現淺水區對船舶航行影響;當未出現惡劣海況時,風險值隨風場、洋流、海浪和溫度局部變化較明顯,但整體動態變化較小;當遭遇惡劣海況時,評估結果能體現高風險區風險生成與變化趨勢。因此,評估方法能夠很好地描述海域航行風險在空間與時間維度上分布與變化。

圖5 2020年12月4日氣旋風暴經過研究區域時評估結果Fig.5 Assessment results of cyclone storm passing through research area on December 4,2020

圖6 2020年9月22日6 h間隔航行評估結果Fig.6 Assessment results of 6-hour interval sailing on September 22,2020

圖7 2020年9月22日1 h間隔航行評估結果Fig.7 Assessment results of 1-hour interval sailing on September 22, 2020
3 結論
1)通過對數據空間和時間維插值計算統一數據分辨率,制定不同評估因子歸一化標準。
2)提出均衡權重和時序權重,結合AHP方法為評估因子定權,更好體現航行風險的動態效果。
3)航行風險模型能夠體現航行風險空間與時間維度上分布,對遭遇惡劣海況時的航行風險有足夠預警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