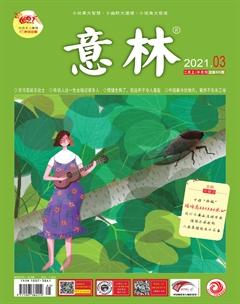剪婆婆
聶鑫森

出閣前,她叫“剪妹”;洞房花燭后,她叫“剪姐”;有了兒女,她叫“剪嫂”;兒女成家立業了,她順理成章地被稱作“剪婆婆”。
《百家姓》《千家姓》里,沒有“剪刀”的“剪”這個姓。只有一個“翦”姓,比如大學者翦伯贊,就是此中的翹楚。
“剪”并不是她的姓,她姓劉,叫劉蘭芳,是古城湘潭鄉下的青山鋪人。那地方的婦女,從小到老,都喜歡剪花(也就是剪紙)。剪什么樣式的都有,人生禮儀的“禮花”“喜花”“壽花”,歲時節令的“窗花”“墻花”,還有用于服飾居住、文藝游戲、祭祀祈祝形形色色的“花”。劉蘭芳六歲就開始學剪花了,心靈手巧,總是在同齡人中頭角崢嶸。到了被人稱為“剪婆婆”的時候,她的作品自成一格,構圖宏大,多剪大場景畫面,花草、山水、人物匯于一體。而且她不用起稿子,運剪凌厲,常采用折剪重復的手法,于對稱中求變化、規整中見性靈,作品多次參加市、省和全國大展,成了名副其實的民間藝術家。人們認為她是為一把剪刀而活著的,只有她配得上在稱謂前冠一“剪”字。盡管她有忙不完的農活、家務,但只要一有空閑,就是剪紙。在細細脆脆的剪刀聲中,她六十有五了,青發間有了白發,臉上有了皺紋。
日子越過越順心哩,名也有了,錢也有了——城里的各個旅游商店都爭著訂購她的作品,而且價格不菲。可她還是農婦打扮,該干的農活、家務照干,然后才是剪紙。
丈夫是耕田、種菜的里手,而且身體很好,常對她說:“你就專心剪紙吧,別的事不用你動手。”
她搖搖頭,說:“人一懶,心就蠢,手就笨。”
女兒、女婿是公務員,兒子、兒媳是私營企業家,挺孝順,老往她手上塞錢。他們都勸她:“剪紙幾個錢賺得太辛苦,沒那個必要。”她氣也粗了,說:“不是為賺錢,是為自己賺快樂,也給別人快樂!”
有一天,剪婆婆感到長期握剪刀的右手大拇指疼痛不止,摸上去還有一個硬塊,剪刀也握不穩了。若是身體其他部位出了再大的毛病,她絕不上醫院,人哪有這么金貴呢?但這是要握剪刀的手。在家人的前呼后擁下,剪婆婆去了湘潭一家最好的醫院。
測體溫、驗血、照片……有經驗的醫生說,是骨癌,必須做截指手術!
剪婆婆急了,一個月后市里有個改稿會,她送審的表現農村改革開放新氣象的大幅剪紙《日子越過越開心》,已獲通過,但還要進行修改,截除了大拇指,怎么握剪刀?她只好向大夫陳述她的苦衷,能否只截去大拇指有硬塊的第一個關節?
醫生嘆口氣,同意了。
一個月后,剪婆婆出院了,高高興興去參加改稿會。作品一路過關斬將,到北京去參展了,還得了個金獎。
半年后,剪婆婆動過手術的大拇指又開始劇痛,上面又長出了一個腫塊。醫生勸她把大拇指或手截掉,以絕癌細胞的擴散,這樣可以多活幾年。
剪婆婆慟哭起來,又是搖頭,又是擺手,這樣的手術她堅決不能做。她哽咽著說:“好日子過夠了,死算個什么。就是花沒剪夠,沒有手了,怎么剪?不能剪花了,要那么長的壽做什么?”
不管家人怎么勸怎么求,剪婆婆都不答應。她突然從口袋里掏出一把剪刀,狠狠地說:“你們硬要截我的手,我就先剪斷我的喉管!”
醫生只好改變醫療方案:先做刮骨手術,再做化療。
剪婆婆開心地笑了。“我能活多久就多久,再剪些花留在世上,就心滿意足了。”
一年后,剪婆婆辭世。
臨終前,她只有一個要求:把她常用的剪刀,放在骨灰盒里。到了另一個世界,她還要剪花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