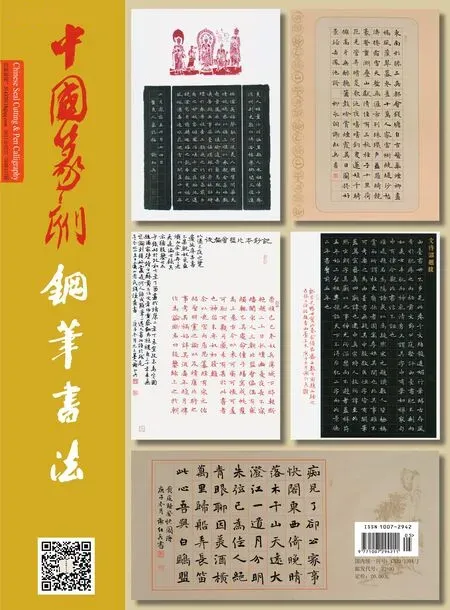與筆墨結伴而行
楊文瀏

楊文瀏,1971年生,安徽長豐人。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國家二級美術師、安徽省書法家協會篆書委員會秘書長、合肥市書法家協會副主席,第三屆中國書壇蘭亭雅集“蘭亭七子”之一,安徽省十大青年書法家,中國書法家協會第四屆“國學修養與書法”全國青年書法創作骨干高研班成員。先后于合肥、洛陽、臨沂、桐鄉、無錫等地舉辦個人書法作品展。
近年作品被推選參加中國書法家協會“理想與現狀”當前書法創作學術批評展暨烏海論壇、“源流·時代”以王羲之為中心的歷代法書與當前書法創作暨紹興論壇,獲全國第四屆扇面書法展、全國首屆書法小品展、首屆中國普洱茶鄉全國書法展優秀獎(最高獎),全國首屆行書展提名獎;入展中國書法家協會主辦的第五屆中國書法蘭亭獎、全國第十屆書法篆刻展、全國首屆篆書展等20余次。
我出生于瓦埠湖畔,少年時最深的記憶莫過于家鄉的偏僻落后與連年的水患。家里有三間出檐的草房,最亮堂的照明是馬燈,有我與弟弟的一間沒掛門簾的屋子,可那時不知書法為何物,更不知深宅大院里書房的情狀。故鄉這片土地三面環水,播種四季未果,唯一一條土馬路通往十余里外的繁華。現在,當我以一個走出農家、走出閉塞的“母親的驕傲”再去審視這片土地時,怎么也想不出自己怎么會倘佯于黑白世界而不能自拔?
九十年代初,有幸以全鄉第一名的成績考入師范,成為遠近幾個村莊第一個“魚躍農門”的學子,端上了令人艷羨的“鐵飯碗”。進入師范后,無端地愛上書法,練字就在教室,買字帖、收報紙,今天顏,明天柳,牙縫里省下的飯菜票大多涂抹于筆端。畢業后分到鄉下小學,土墻瓦頂,半間宿舍,玻璃窗用報紙糊上,明月清風自然被關在窗外,現實把風雅照得無處藏身——這也許就是理想與現狀吧。一桌一椅一床,還有一個煤油爐,買菜要到兩公里外的集市,生活頗有幾分魏晉風度,單純簡約、平和簡靜,最大的樂趣可能就是來個同學在酒桌上“清談”了。所幸學校有電,比老家現代,開始趕硬筆的熱潮,拿起鋼筆在亮堂堂的電燈下臨帖,感覺也挺聚氣。那時最期待的是一周來一次的郵差,一般都有我的報紙、雜志或信件,或是廣告、或是書友來函、或是展賽回復,回到寢室,拆信讀札、翻閱書報應該是最幸福、最愜意的時光了。
后來調到鎮上,沾愛人的光有了個帶院子的房子,終于可以與清風明月親近了,也有了自己的一間兼做儲藏室的小書房。便讓土木匠弟弟打制了一方書案,批發了幾刀毛邊紙,又拿起了毛筆。就在兼做儲藏室的小書房,在與古人的耳鬢廝磨中,我漸漸對書法有了新的理解與體悟,筆下的橫豎撇捺漸漸有了法度與情性。那就一個勁地寫吧,直寫得晨曦臨窗,直寫得星斗滿天,時光不知不覺在指縫間流淌,書法填充著我生活的另一個頁面。
2002年底,因書結緣,由小鎮搬入縣城。環境的改變,眼界的拓寬,縣城良好的藝術氛圍使我對書法有了更深的理解與認識。我開始靜下心來,對傳統進行重新的審視、梳理與強化,臨帖、創作、作文幾乎占去了我全部的業余時間。漸漸地,我的參賽作品不再是“黃鶴一去”,陸續在一些比賽中入展、獲獎。同時,寫的一些隨筆、論文亦能時常見于報端,更讓我感到無比欣慰的是,2007年終于加入了夢寐以求的中國書協,成為小城中為數不多“有證”的書法家。
近些年,書法的學習重心逐漸轉向教學。首先在本縣開設了“點墨齋書法公益班”,二三十號人每月因為書法聚那么兩天,研究筆墨之道,在小城中也算是一群風雅之士。又在安徽省書協培訓中心、江西省書協培訓中心、河北美院等兼帶書法課,平日工作之余的事基本都是圍繞書法展開的,臨帖、創作、分析、思考、備課、聚會等等。教學相長,不亦樂乎。
去年聽說家鄉瓦埠湖作為“引江濟淮”工程的河道,水面要抬高幾米,河水又要漲了。故鄉的村莊早已被移民工程推為平地,兒時的棗樹、池塘、老屋,所有的參照以及關于“炊煙”的記憶已蕩然無存,惟有那條河還在,她靜謐、安詳、澄澈、無私,歷史的年輪在她的臉頰上寫滿了皺紋,我想那其間也一定有一輪對應著我的軌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