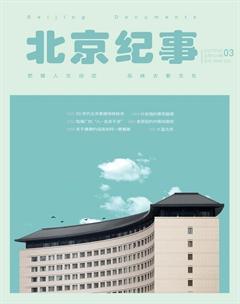況晗:寬線條下濃縮的北京胡同
宋冰華

盡管面前的是一張樸素的鉛筆畫,然而,強烈的光影對比,讓我感受到了陽光的耀眼。靜謐而灰色的磚墻上爬滿了絲瓜葉子,每一片葉子都在努力投射出陽光的溫度。水缸、花盆、斜倚著墻的自行車……甚至門口站立的那只小狗都讓這幅只有灰白色彩的畫作產生了極強的動感。仿佛我就站在這老北京院落的門口,勃勃的生機與古老的青磚灰瓦瞬間立體起來,下一刻我就要走進那古老的胡同中。
這就是況晗寬線條鉛筆畫中北京胡同的魅力。看似畫的是景,透過線條,撲面而來的卻是濃濃的老北京人文情懷。每一張畫仿佛都有著生命,帶著魔力,述說著老北京胡同的厚重歷史感,描繪著老北京人的生活態度。
扁頭鉛筆里的北京味道
1989年,大學畢業后的況晗來到了北京工作。和那時候的大多數異鄉人一樣,他也在北京租房子住。最開始他住在三元橋牛王廟。1991年,單位給他在北新胡同找了間只有9平方米大小的房間住下,對于一直生活于南方的況晗來說,陌生的環境、迥然不同的氣候給他帶來了不小的壓力。然而,北京城用它的包容,胡同用它的質樸,大雜院的大媽們用她們的溫暖,緩解了況晗心中的不安與惆悵。讓他不僅適應了北京的生活,更在日常的茶米油鹽、鄰里的互相照應下慢慢體會到了老北京胡同里瑣碎卻溫情、古老卻生動的氛圍,并愛上了北京。
況晗在這里生活了6年。朝夕相處的大雜院的人們就像沒有血緣關系的家人。而他兒子的第一句話更是非常的“胡同”。“那時候,胡同里天天都有收廢品的、賣菜的、修鎖的、磨剪刀的一路吆喝著走過。有一天我領著兒子剛到門口他就說了一句拖著長聲的‘啤酒二鍋頭……哈哈哈,那是他人生說的第一句話。”“老北京人對于北京文化的傳承,有些已經進入骨髓,就像我們北新胡同小院里的居民,雖然多數已經搬走了,但親情還在,有空的時候還是會找個地方聚聚,那感覺像我們又一起住在胡同里一樣。”
“ 作為藝術家, 筆墨當隨時代。”用畫筆記錄下生活中的事物是一種職業的習慣,更是內心世界的表達。從況晗的胡同系列畫作中,人們能夠感受到畫家對北京胡同的濃濃眷戀。那時的況晗擔任某出版社的美術編輯,工作之余,他幾乎跑遍了整個北京城,收集著有關胡同的點點滴滴。

況晗的某位小學同學曾在博客上介紹說,況晗從小就熱愛畫畫,而最擅長的是水彩畫。而況晗的整個《北京胡同系列》全部使用了木工的扁頭鉛筆,用大塊面的筆觸,表現出細膩的老北京胡同里厚重的人情味。對此,況晗說:“我是師范生,什么畫種都要來幾筆,但也有喜好,水彩畫就是我的喜好。開始也是用水彩畫去表現,感覺與灰磚灰瓦的胡同搭配在一起總是有點別扭。偶然翻到自己以前練習的寬線條風景畫,就用它來試試,這一試就讓我試了半輩子。法為畫,畫不為法。技法是為畫服務的,而不是畫為技法服務。一方面,胡同的靜謐時光與灰色調正好與鉛筆的灰色相融合。另一方面,那時候我還在上班,沒有時間一氣呵成地畫水彩。鉛筆畫不用擔心時間的安排,可以慢條斯理、不慌不亂、條理清晰地去安排自己的時間。”
1995年,國家藝術博覽會上,況晗將《北京胡同系列》畫作展示在眾人面前,受到了藝術鑒賞家和收藏家的注意。
和推土機賽跑的異鄉人
1995年朝陽門北小街墨河胡同拆遷,而況晗才剛描完它的輪廓。他第一次意識到畫筆趕不上推土機的速度,于是拿起照相機開始邊拍邊畫。
一臺相機, 一個軍綠色帆布畫板,一個裝著鉛筆盒的布袋,就是靠著這一身簡單的行頭,30年間,況晗走街串巷,記錄下北京城的1000多條胡同,把那些正在消失和已經消失的胡同留在了畫紙上。看著胡同一天天的減少,他必須抓緊時間把逝去的胡同留在紙上,手已經磨出了老繭,有時肩周炎讓他抬不起胳膊。這個被稱為和推土機賽跑的異鄉人已經拍下近萬張照片,也用一支鉛筆畫出了青磚灰瓦、木窗石階,畫出四合院的動靜春夏,和最地道的北京底色。
從某種意義上說,胡同可以說是老北京的代名詞。在北京城里縱橫交錯的數不清的胡同里,京腔、京調、京味隨處可見。王府、會館、名人故居遍布全城,更有數不清的感人故事流傳其中。況晗說:“不管到哪里寫生,旁邊的大媽大爺、街坊鄰居都會告訴你,你畫的房子是誰誰曾經住過的。在北京,你畫哪一個地方,胡同里的人都能跟你講半天的故事。所以,我始終說,北京的一塊磚都有著說不盡的故事。”
隨著北京城市規劃的需要,許多胡同的風貌只能在況晗的畫作中再現昔日的輝煌。從這個意義上講,他的作品不僅具有藝術欣賞性,更是珍貴的文化遺產。胡同里上學的孩子、逗弄孩子的老人、傍晚推著自行車進門的人、院門口圍坐吃飯的人們……閑適的小狗、晾曬的衣服、布滿爬架的葡萄藤、墻壁上肆意生長的絲瓜藤蔓、在窄小胡同里錯車的三輪車與自行車、雪后的胡同、瓦上的茅草、院中間的大棗樹……從他筆下的門樓、房舍、街景等日常景物中,你會發現平凡生活的詩意、濃得化不開的人情味,還會體會到濃厚的歷史文化感。
將昔日胡同留存在藝術之中
1998年,況晗的作品《京都紀事》入選中國美協第十三屆新人新作展;1999年,組畫《城市變遷》入選第九屆全國美展;2000年,況晗出版了個人畫集《留住胡同——況晗寬線條鉛筆畫作品選;2002年《拆遷之前》入選《紀念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講話發表六十周年》全國美術作品展并獲優秀作品獎;同年,先后在中央美術學院美術館、北京云峰畫苑舉辦“留住胡同——個人寬線條鉛筆畫展”;2008年,出版《消失的胡同——鉛筆畫中的北京風貌》;2020年,出版了《樹影·鴿子·人——胡同北京的生趣與鄉愁》三本胡同專著。
況晗的作品得到了人們的喜愛,在業界更獲得了極高的評價。《北京晚報·新視覺畫廊》評價道:在他(況晗)的寬線條鉛筆畫下,勾勒出線面組合的物體,在自然光的照射下,暗色、灰色、亮色相互融合拼湊,匯合成古樸北京城里最日常的生活、街道、胡同,得益于寬線條筆觸帶來的質感,讓灰色的鉛筆畫多了一份西洋油畫般的立體效果。

舒乙在為《消失的胡同——鉛筆畫中的北京風貌》作序中寫道:況晗的作品……屬于有相當藝術價值的圖冊,史料之外,又多了一層美學欣賞價值,分量大不相同……寬筆鉛筆畫是一種新畫種。寬筆鉛筆畫可以說是況晗的發明,此前僅有個別外國人拿來作速寫,真正當一種正規的藝術創作手段的還沒有……這種寬筆鉛筆畫講究筆觸,一筆是一筆,不可涂抹,頗像中國畫、中國書法、木刻和水彩。畫時手臂必須很用勁,一筆下去,畫紙上會留下一個凹溝,摸起來頗有立體的質感。這種畫吃功夫,不大的一張畫,要耗時整整7 至10天。況晗是個壯漢,連續畫畫,7天下來,竟大病一場,可見耗精力之大。如此看來,這部圖集可算是一部身心投入的力作了。
況晗筆下的很多胡同已經被鋼筋水泥取代,他最擔心的是以他現在每日一幅的創作速度,畫到100歲也畫不完。“金融街的那一片,就因為它拆得比較早,我沒有留下什么資料,我真后悔。作為南方人,當年我首次看見胡同,很有感覺。那灰磚灰瓦、那精雕細琢的門樓、那飛檐走壁、畫梁雕飾,處處都是先賢給我們留下的寶貴財富。隨著城市的變遷,這些會不會消失殆盡?想起來就讓人心疼不已。就這樣看著它們消失而無動于衷嗎?當年,我就想著用繪畫的方式留下、記錄下這些。用藝術的手法讓它們在畫紙上重現。讓歷史與現代城市有個銜接,讓后人知道我們的根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