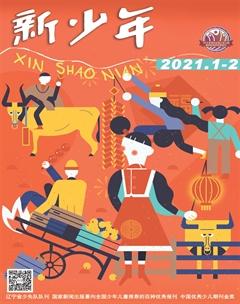遇見劉胡蘭
王云浩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期一個初冬的傍晚。
“曉——鵬,曉——鵬!”母親在大街上喊我,拉著長長的調子。村莊的樹木和房屋漸漸遮擋住夕陽的余暉,遠處的烏鴉“哇哇”地叫著歸巢。下午期中考試放學后,我滾著鐵環剛來到村委會大門前,看著大人們蕩秋千時,聽到母親在喊我。
母親站在不遠的地方,我應了一聲,滿頭大汗地滾著心愛的鐵環跑向她。這個鐵環是我不知跟爺爺說了多少好話,爺爺才答應給我制作的。鐵環是用小拇指粗的圓鋼筋彎成一個如臉盆大小的鐵圈,焊接而成;鐵鉤是用一根粗鐵絲折好,再用細繩子系在小木棍上作為手柄。玩兒的時候鐵鉤推著鐵環往前滾,人也跟著跑。我和小伙伴兒經常比賽看誰跑得快,走“8”字形看誰的鐵環不會倒。滾鐵環需要大腦快速反應,手腳協調配合,是我們最愛玩兒的游戲之一。
“回家吃飯!”母親帶有責備地說,“天黑了,也不知道回家,瘋個啥!”說完,拉住我的小臟手就往家走。
我跟母親回到家里,本以為桌子上會擺放好香噴噴的油餅和稀粥,沒想到放的卻是我的作業本,而父親就坐在桌子旁。我看著沒有書皮兒的課本,心想這下壞了,父親又該揍我了。我今年十歲,本來該升入三年級,可因為考試成績不及格留了級。為此我挨了不少父親的訓斥和巴掌,屁股上的疼痛往往剛下去沒幾天,接著又有了新的巴掌印。
“你過來!”父親說。
我磨磨蹭蹭地來到桌前。
“書皮兒弄哪兒去了?”還沒等我回答,父親用手指著書本說,“課本還沒學完書皮兒就沒有了!你看看書角卷成啥了!”
我站在那里默不作聲。我記得是用書皮兒折疊了兩架戰斗機,和伙伴兒們玩兒飛行來著。至于兩個書角,怎么翻卷成老綿羊的羊角那樣,我就不知道了。
父親翻看了幾下作業本說:“你看看,不是大叉子就是對一半,你是咋學的?再做一遍!”看著父親生氣的樣子,我只好老老實實重做老師布置的作業,然后才敢吃晚飯。
一學期很快在滾鐵環游戲中度過。到了期末,我的成績和期中考試一樣沒有進步,母親說:“你爹是老師,學校領導常年讓他教畢業班。他教出了許多尖子生考上了重點高中,年年被評為優秀教師。”母親仰臉望了一眼堂屋的后墻,我順著她的目光望去,墻上貼著一排十分醒目的獎狀,我知道這都是父親的榮譽。
父親一直對我沒有笑容,白天除了做家務就讓我做寒假作業,晚上也不讓我出去玩兒,我的寒假生活瞬間變得枯燥無味。
到了臘月二十,過年的氣氛漸漸濃起來,父親不再管我那么嚴了,我又恢復了自由。
小孩兒們都愛過新年,能穿新衣,走親戚。大年初一,母親包著餃子對我說:“初二咱們去你外婆家。”
我一聽手舞足蹈,嘴里露出了剛掉的門牙豁口。
初二吃過早飯,父親騎著自行車,車后座上坐著母親,車梁上坐著我,車把前掛著去外婆家買的禮品點心。一路上,我像路邊樹梢上飛來飛去的小麻雀,嘰嘰喳喳地說個不停。
臨近中午,我們來到了外婆家。 吃午飯的時候,外婆對母親說:“明兒村里有戲,別走了,在這兒看戲吧。”
外婆住的村莊人口多,村子大,每年農歷正月初五是廟會,常常以唱大戲的方式來祝賀,周圍十里八村的人都蜂擁而至。戲一般唱三天,初三開始,前兩天算是預熱,初五是正會,所謂好戲在后面。
我和母親留在了外婆家,連著看了兩天戲。初五的早晨,金色的陽光暖暖地照在戲場里,看戲的人明顯比前兩天更多,戲臺周圍賣零食的也多起來,甘蔗、膨香酥、花米團、冰糖葫蘆,花樣繁多。我和母親、外婆、三舅興高采烈地來到戲場,當天的壓軸大戲是《劉胡蘭》。
戲臺上的劉胡蘭留著一條長辮子,雖然年紀輕輕,可一舉一動都顯露出英雄氣概。
“娘,劉胡蘭是不是咱這里的人?”
“劉胡蘭是山西人,像你這般大就參加了村里的兒童團,為八路軍放哨送情報。她為了保護八路軍,被敵人抓住,受到嚴刑拷打也沒投降,犧牲時才十五歲。”
母親說到這里停頓了一下又繼續說:“是很多像劉胡蘭這樣的英雄,用自己的生命換來了我們的幸福。你也不能光瘋玩兒了,要想想怎么做才是報答先烈……”
母親講著講著,用手帕不住地擦眼睛。我把目光從母親身上轉移到戲臺上,看著雄赳赳氣昂昂的劉胡蘭,想起不愛學習的自己,怎能對得起小英雄的犧牲,我羞愧地低下了頭。
過完春節,新學期開學后,我除了給家里養的豬羊割些青草外,其余時間就專心讀書寫作業。我把心愛的鐵環放在了床下面,也不疊飛機了。
自從看了《劉胡蘭》,劉胡蘭就成了我心目中的英雄。每當我不愿學習時,她好像就站在我面前,激勵我努力學習。
初春的一天,我做作業時,聽見父親對母親說:“曉鵬比以前知道學習了!”母親說:“自從春節在他外婆家看了《劉胡蘭》后,改變了不少,這多虧了劉胡蘭哪……”
父親一改冰冷的態度,現在對我如雪后出現的太陽,溫暖了許多。
到了暑假升三年級的時候,我得了入學考試以來的第一張獎狀。母親把它和父親的獎狀貼在了一起。在燈光的照耀下,我看著金光閃閃的兩個大字——“獎狀”,它好像變成了一條金色大道,指引我大步向前……
(責任編輯? 李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