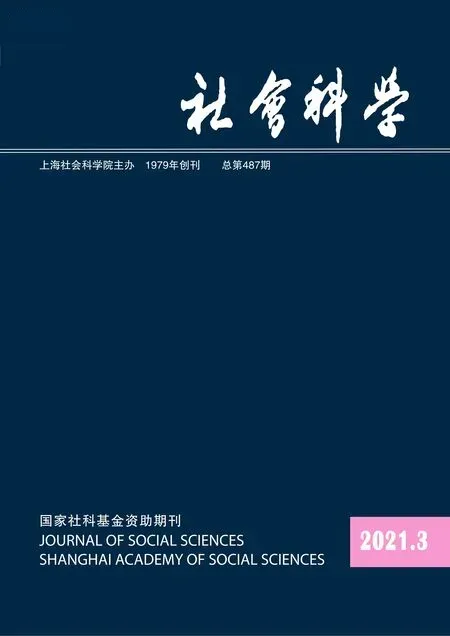城市治理新動能:以“微基建”促進社區(qū)共同體的成長*
劉淑妍 呂俊延
一、問題的提出
社區(qū)作為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交匯的重要場域,是城市發(fā)展的活力源泉,其本質(zhì)是居民生活共同體。伴隨著西方市場經(jīng)濟的興起,人們對共同體的認同方式隨之變遷。無論是滕尼斯對“本質(zhì)意志”與“選擇意志”(1)[德] 斐迪南·滕尼斯:《共同體與社會:純粹社會學的基本概念》,林榮遠譯,北京大學出版社1999年版,第146-170頁。的分殊,還是涂爾干對“機械團結”與“有機團結”(2)[法] 埃米爾·涂爾干:《社會分工論》,渠東譯,生活·讀書·新知三聯(lián)書店2013年版,第91、214頁。的對比,都可以歸結為現(xiàn)代市場經(jīng)濟發(fā)展對共同體格局的分野。這些二元對立共同體的深層邏輯,體現(xiàn)著人們對其認同方式的差異。傳統(tǒng)的共同體一般以自然情感為紐帶,是彼此密切聯(lián)系且具有一定排他性的血緣、地緣和精神共同體。現(xiàn)代化以來,隨著時間的“逝去”與空間的“隱遁”,資源的自由流動與選擇造成了一個“脫域”的共同體(3)[英] 安東尼·吉登斯:《現(xiàn)代性的后果》,田禾譯,譯林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頁。,并從血緣和地緣認同轉(zhuǎn)向了個人利益認同。可見,工業(yè)化對傳統(tǒng)共同體的一大挑戰(zhàn)是將人們從“定型”社會(4)[美] 喬治·梅歐:《工業(yè)文明的社會問題》,費孝通譯,商務印書館1964年版,第8頁。中脫嵌出來,并使其孤身面對復雜的現(xiàn)代世界。現(xiàn)代高壓生活造成人們的孤獨感與焦慮感,又迫使我們重拾傳統(tǒng)共同體的積極價值,以慰藉人們的精神世界。
聚焦到中國社區(qū)場域,市場化和工業(yè)化對社會結構格局變遷的影響同樣清晰可見。傳統(tǒng)鄉(xiāng)土中國被編織在差序格局之中,屬于熟人關系下的禮俗社會結構(5)費孝通:《鄉(xiāng)土中國》,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版,第7頁。。改革開放以來,市場機制的引入對血緣和地緣合一的傳統(tǒng)社區(qū)存續(xù)構成了挑戰(zhàn)。現(xiàn)代社區(qū)不再由“生于斯、死于斯”、因緣固定的群體組成,而是市場機制指引下公民選擇意志的聚合。這一現(xiàn)代社區(qū)形態(tài)缺乏有機團結的紐帶(6)Sampson Robert, “Local Friendship Ties and Community Attachment in Mass Society: A Multilevel Systemic Model”, American Sociological Review, Vol.53, No.5, 1988, pp.766-779.,并且也沒有及時供給適應性的社會交往道德。因此,在社區(qū)治理過程中,“公共物品難以有效供給”(7)張雷:《構建基于社區(qū)治理理念的居民自治新體系》,《政治學研究》2018年第1期。“共同體困境”(8)鄭杭生、黃家亮:《論我國社區(qū)治理的雙重困境與創(chuàng)新之維——基于北京市社區(qū)管理體制改革實踐的分析》,《東岳論叢》2012年第1期。等問題開始顯現(xiàn)。上述文獻均可見轉(zhuǎn)型后社區(qū)共同體缺失帶來的問題,但對如何營造一個符合社區(qū)多元利益主體的共同體格局卻都語焉不詳。
當下,社區(qū)共同體的價值日益彰顯。2019年11月,習近平總書記在上海考察工作時,提出“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為人民”的城市治理理念(9)習近平:《城市是人民的城市,人民城市為人民》,《人民日報(海外版)》2019年11月4日。。在“人民城市”建設中,只有積極吸納人民參與其中,才能在促進城市現(xiàn)代化建設的同時,提升人民的獲得感。與此同時,社區(qū)中“互不相鄰”的鄰里關系格局(10)桂勇、黃榮貴:《城市社區(qū):共同體還是“互不相關的鄰里”》,《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卻不利于激發(fā)居民的參與意愿。對此,既有研究多從國家與社會對立的角度開出藥方:要么站在社會中心論的立場上,強調(diào)培育社會主導力量以杜絕國家力量對社區(qū)的“侵蝕”(11)Gene Barrett, “Deconstructing Community”, Sociologia Ruralis, Vol.55, No.2, 2014, pp.182-204.;要么站在國家中心論的立場上,主張社會問題的解決必須依賴于國家指令或動員(12)侯利文:《行政吸納社會:國家滲透與居委會行政化》,《深圳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19年第2期。。雖有部分文獻看到了社區(qū)共同體培育的“憑借機制”(13)吳曉林、謝伊云:《國家主導下的社會創(chuàng)制:城市基層治理轉(zhuǎn)型的“憑借機制”——以成都市武侯區(qū)社區(qū)治理改革為例》,《中國行政管理》2020年第5期。和國家的“助推”(14)熊易寒:《國家助推與社會成長:現(xiàn)代熟人社區(qū)建構的案例研究》,《中國行政管理》2020年第5期。作用,但缺乏對中國場域下國家助推社區(qū)共同體成長的必要性的分析,且對其發(fā)揮“橋接”作用的微觀機制也著墨不多。
評價一個社區(qū)治理成功與否的指標不能局限于物理空間的改善,而應聚焦于社區(qū)居民共同體意識的生成(15)楊貴華:《社區(qū)共同體的資源整合及其能力建設——社區(qū)自組織能力建設路徑研究》,《社會科學》2010年第1期;陳友華、佴莉:《社區(qū)共同體困境與社區(qū)精神重塑》,《吉林大學社會科學學報》2016年第4期。。因此,本文旨在厘清在社區(qū)居民共同體意識不強的背景下,為何要發(fā)揮國家的助推作用,以及國家通過何種方式來增強居民對社區(qū)共同體的認受度。基于2020年6月至12月間在上海市楊浦區(qū)和靜安區(qū)10個街道16個社區(qū)的田野觀察、問卷調(diào)查和電話補充訪談,我們發(fā)現(xiàn),社區(qū)可以通過營造“微基建”,并以此為紐帶促進社區(qū)共同體的生成。基于此,本文首先界定了社區(qū)“微基建”的內(nèi)涵,并在重塑社區(qū)共同體的維度上探討社區(qū)“微基建”何以必要和可能。
二、社區(qū)“微基建”的三維內(nèi)涵
2020年3月4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務委員會召開的會議上,決策層強調(diào)要加快推進國家規(guī)劃已明確的重大工程和基礎設施建設,其中,要加快5G網(wǎng)絡、數(shù)據(jù)中心等新型基礎設施建設進度。自此,新型基礎設施建設再次成為熱議詞匯,并被認為是中國未來經(jīng)濟增長的新引擎。城市社區(qū)建設離不開“硬件”支撐。社區(qū)中的各類硬件設施作為看得見、摸得著的物體,是實現(xiàn)公民參與必不可少的外在條件。新基建的發(fā)展戰(zhàn)略也為提升社區(qū)治理的現(xiàn)代化水平提供了技術支撐和硬件保障。但是,新基建是發(fā)力于科技端的基礎設施建設,且由大型企業(yè)承擔建設任務,其耗資大、受益遲等特點阻隔了社區(qū)主體參與意識和互助精神的培育。
因此,社區(qū)治理對接新基建,應著力營造社區(qū)“微基建”(16)葛天任、王拓涵:《社區(qū)更新“微基建”的公平規(guī)劃與合作治理——以北京“清河實驗”的YG社區(qū)為例》,《華東理工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5期。。社區(qū)“微基建”與新、舊基建各有側(cè)重、互為補充,借以提升社區(qū)的治理水平和城市發(fā)展活力。具體而言,社區(qū)營造“微基建”要與新基建、舊基建三管齊下(見表1),共同推動城市治理革新,既要繼續(xù)推進以“鐵公基”為代表的舊基建,又要加強以數(shù)字化為代表的新基建,還要以中國城市的15分鐘生活圈為中心,營造好社區(qū)“微基建”(17)諸大建、孫輝:《人民城市人民建,戰(zhàn)略性推進社區(qū)更新微基建》,《文匯報》2020年6月2日。。社區(qū)“微基建”項目對高質(zhì)量的社區(qū)發(fā)展至關重要,既能改善民生環(huán)境,又能有效對接“六保”“六穩(wěn)”的戰(zhàn)略考量,從根本上鞏固社會、經(jīng)濟和環(huán)境可持續(xù)發(fā)展的基礎,促進社區(qū)發(fā)展的良性循環(huán)。

表1 舊基建、新基建與“微基建”的特點和應用場景
可見,社區(qū)“微基建”是對新、舊基建的補充與超越,旨在加強社區(qū)設施配套建設,實現(xiàn)基礎設施和基本服務均衡化。社區(qū)“微基建”可作為聯(lián)系社區(qū)個體與共同體的紐帶,以“硬件”——小微基礎設施建設促進“軟件”——公民參與意識的生成。社區(qū)“微基建”還將精準提高居民生活品質(zhì),滿足居民“最后一公里”的需求,并可視為新時代提振社區(qū)治理的重要引擎。社區(qū)“微基建”與新、舊基建一脈相承、相互補充,可賦能社區(qū)治理,實現(xiàn)社區(qū)主體間的協(xié)同治理。具體而言,可以從價值、目標和手段三個維度進一步詮釋社區(qū)“微基建”。
(一)價值維度:以“人民城市”理念為價值指引
“人民城市”價值理念集中體現(xiàn)為從增量擴張的權力型、資本型城市轉(zhuǎn)向提質(zhì)升級式的人民型城市。推進社區(qū)營造“微基建”,既是對“人民城市”重要理念的貫徹落實,同時也是適應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常態(tài)化、提升城市治理現(xiàn)代化水平的現(xiàn)實要求。當前,中國國家治理正處于前現(xiàn)代與后現(xiàn)代交織疊加期,社會共識難以達成。政府發(fā)展理念常常錯位(18)朱光磊:《“兩化疊加”:中國治理面臨的大難題》,《北京日報》2016年10月24日。。改革開放四十余年實現(xiàn)了經(jīng)濟的飛躍發(fā)展,國庫逐年充盈。但是,這種經(jīng)濟趕超式的大尺度發(fā)展往往顧及到了國家發(fā)展的“面子”,卻疏漏于城市發(fā)展的“里子”——社區(qū)的發(fā)展不均、鄰里隔離、公共空間缺失等問題突出。新時代國家發(fā)展的戰(zhàn)略更應該落實到富民、強民上,而聚焦到基層就需要以精細化的治理方式解決社區(qū)居民的有效需求,并推動人民的積極城市建設。
社區(qū)“微基建”對標“人民城市”治理理念和城市治理現(xiàn)代化的戰(zhàn)略目標。在“人民城市”的價值指引下,激活人民參與社區(qū)治理的重要性、必要性與可能性(19)劉士林:《人民城市:理論淵源和當代發(fā)展》,《南京社會科學》2020年第8期。。首先,在治理導向上,社區(qū)“微基建”以人民的需求為指引,將增強居民對社區(qū)共同體的價值認同作為出發(fā)點與落腳點。其次,在治理的內(nèi)容上,社區(qū)“微基建”要不斷內(nèi)化社區(qū)居民的生存、發(fā)展與幸福等多層次的服務需求,在滿足居民最基本訴求的基礎上,創(chuàng)新服務方式,并以精準性、包容性的服務方式,實現(xiàn)社區(qū)居民對美好生活的追求。最后,在治理路徑上,社區(qū)“微基建”通過激發(fā)利益共同體的參與意識,進而增強社區(qū)居民的主體價值,使社區(qū)居民能夠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生活。在此基礎上,社區(qū)通過營造“微基建”以引導投資轉(zhuǎn)向民生領域,并進一步探索社區(qū)公共物品供給的新策源和新模式。
(二)目標維度:以“韌性社區(qū)”培育為任務旨歸
疫情是一次大考,但同時也給社區(qū)營造提供了新契機。在傳統(tǒng)的社區(qū)微更新的基礎上,進一步拓展思路,以現(xiàn)代化社區(qū)基礎設施與公共服務建設推進社區(qū)營造“微基建”,這是疫情后建設“韌性社區(qū)”的內(nèi)在需求。“微基建”以15分鐘步行圈為基準,著力營造社區(qū)居民生活必需的基礎設施和公共服務,其中包括出行、居住、工作、休閑等方面。可見,如果“微基建”配備齊全,整個城市就能夠以小區(qū)甚至更小單位為矩陣,高效應對風險社會帶來的挑戰(zhàn)。
《上海市城市總體規(guī)劃(2017-2035年)》提出的“15分鐘生活圈”對社區(qū)營造“微基建”具有指導意義。首先,社區(qū)“微基建”需要加強社區(qū)健身、社區(qū)醫(yī)療等方面的基礎實施配套。其次,社區(qū)“微基建”需要精準把控老人、青年、小孩等不同主體的需求,并因人制宜地進行查漏補缺,助力實現(xiàn)各年齡層基礎設施和基本服務的均衡化。最后,社區(qū)“微基建”要彌合城鄉(xiāng)公共物品供給差距,實現(xiàn)城鄉(xiāng)一體化發(fā)展。社區(qū)“微基建”通過實現(xiàn)基礎設施齊全配套、基本服務均衡供給以及城鄉(xiāng)公共物品一體發(fā)展,筑牢城市社區(qū)安全底線,并以“韌性社區(qū)”建設確保“人民城市”能夠安全順暢地運行。
(三)手段維度:以多元主體協(xié)同共治為實踐導向
長期以來,我國社區(qū)規(guī)劃和建設多以政府為主導。但是,自上而下的運作模式存在著資金短缺、社區(qū)主體培育不足等弊端,這一模式不利于培育社區(qū)多元主體參與的積極性。應當看到,在快節(jié)奏的現(xiàn)代化生活中,社區(qū)居民對社區(qū)公共事務的冷漠表現(xiàn)常常是“理性”選擇的結果(20)熊易寒:《社區(qū)共同體何以可能:人格化社會交往的消失與重建》,《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一方面,在高壓的城市生活中,讓朝九晚五的社區(qū)居民騰出時間參與社區(qū)事務,這是不切實際的。另一方面,目前社區(qū)自治組織的事務也相對較少,且多為例行化的“瑣事”。當缺乏與公共利益相關的公共事務時,“搭便車”的行為也就不可避免。當個人利益沒有受損時,社區(qū)居民就很難主動投入到社區(qū)自治的實踐之中。
社區(qū)以營造“微基建”為突破口,搭建與社區(qū)居民利益攸關的基礎設施項目,將多元主體有效地整合進社區(qū)治理之中。“微基建”的營造不再由政府全盤兜底,而是通過政府、居民和企業(yè)間多維交互以形成治理合力。具體而言,“微基建”營造可劃分為三大類型:第一,偏政府性的“微基建”營造。這一模式主要針對政府運營為主、社會參與為輔的“微基建”項目。如在社區(qū)文化活動中心、社區(qū)衛(wèi)生服務中心等領域,應由政府發(fā)揮主導作用。此類“微基建”公共性較強,需要政府完善治理規(guī)則,借此提高公共物品的供給效率。第二,偏企業(yè)性的“微基建”營造。對于一些具有較強市場效應的“微基建”項目,如社區(qū)智能快遞柜、智能充電樁等,應交由企業(yè)參與運營。此類“微基建”只需政府保證招標的公開透明并做好后勤保障工作。第三,偏社會性的“微基建”營造。社區(qū)花園、弄堂客廳等社會性較強的“微基建”,主要依靠社區(qū)居民的志愿意識來培育公益精神。可見,社區(qū)營造“微基建”可將多元主體吸納到社區(qū)治理實踐中,實現(xiàn)社區(qū)公共服務的共同生產(chǎn)(21)Elinor Ostrom, “Crossing the Great Divide: Coproduction, Synergy and Development”, World Development, Vol.24, No.6, 1996, pp.1073-1087.。
三、社區(qū)“微基建”何以必要:雙層嵌入下社區(qū)共同體的迷失
中國的社區(qū)治理發(fā)軔于20世紀90年代初,并成長于2000年中共中央辦公廳、國務院辦公廳轉(zhuǎn)發(fā)的《民政部關于在全國推進城市社區(qū)建設的意見》。自此,國家強化了社區(qū)的服務功能,并突出社區(qū)在維護政治穩(wěn)定和群眾自組織建設等方面的作用。中國城市社區(qū)的發(fā)展,不能忽視國家、市場和社會三重邏輯的交互影響。一方面,中國社區(qū)發(fā)展本身就是國家權力驅(qū)動和資源注入的結果。其中,國家始終扮演著主導者的角色,不論是“全能主義模式”(22)鄒讜:《二十世紀中國政治——從宏觀歷史與微觀行動的角度看》,牛津大學出版社1994年版,第3頁。還是“選擇性治理”(23)吳理財:《以民眾參與破解選擇性治理》,《探索與爭鳴》2009年第4期。,都是國家在城市發(fā)展的不同階段中權力運作的反映。因此,考察中國城市社區(qū)治理,不能忽視其成長歷史的路徑依賴性,并從中窺探出社區(qū)治理的國家邏輯。另一方面,中國自1978年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經(jīng)濟的推行使得原先壓抑已久的市場活力迸發(fā)出來。聚焦到社區(qū)治理,也日益形成了強大的資本力量,這是影響社區(qū)治理的市場力量。社區(qū)作為社會領域的一個微觀場域,在國家力量和市場力量的雙層嵌入下,逐漸形成社區(qū)共同體迷失的格局。
(一)行政嵌入:行政主導下的社會參與缺失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后,面對內(nèi)部重建社會秩序和外部局勢緊張等壓力,“單位制”應運而生(24)何海兵:《我國城市基層社會管理體制的變遷:從單位制、街居制到社區(qū)制》,《管理世界》2003年第6期。。這一社會管理體制具有政治整合和資源配置等方面的效率優(yōu)勢,因而在短時間內(nèi)對國家政權的鞏固、經(jīng)濟發(fā)展和社會秩序的恢復等方面起到了突出作用。作為聯(lián)結國家和個體的紐帶,單位向上承接國家的方針、政策,向下組織單位成員,并進行政治動員和思想建設。整個社會則明顯地分化成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大量分散的、封閉的單位組織;另一部分是高度集權的國家和政府(25)Andrew Walder, Communist Neo-traditionalism: Work and Authority in Chinese Industry, Berkeley and 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6, p.153.。國家通過單位來實施其分配資源的權力,并形成對社會成員的控制和動員,“單位人”由此塑造形成。“單位人”對單位產(chǎn)生了強烈的依賴感,而對其所處的社區(qū)則充滿冷漠感,對社會及社會生活的認識和實踐更顯得模糊而生疏。國家對單位組織全能化、“小而全”的職能設置,在提高單位內(nèi)部運行效率的同時,卻抑制了社會的組織發(fā)展和功能發(fā)育,導致社會參與不足。
改革開放后,中國經(jīng)濟體制逐漸向市場經(jīng)濟轉(zhuǎn)變。市場經(jīng)濟要求實現(xiàn)人口、資金等要素的自由流動,進而對“單位制”的管理模式造成沖擊。城市社會面臨著龐大的新增人口就業(yè)壓力,而既有的單位體系無法承擔這種急劇出現(xiàn)的就業(yè)和福利需求,社會穩(wěn)定形勢面臨嚴峻的挑戰(zhàn)。基于此,國家啟動基層管理體制的改革,以強化基層社區(qū)的功能。國家逐漸放松對單位的控制,而單位相對于國家的依附性減弱、獨立性增強。由于體制外企業(yè)的發(fā)展,單位的優(yōu)勢被削弱,個人也逐漸脫離單位,尋找新的庇護場所。這一轉(zhuǎn)換主要通過政府授權社會,并通過建立自治組織吸納社會力量、進行社會整合,進而形成了一個“社區(qū)制社會”(26)徐勇:《論城市社區(qū)建設中的社區(qū)居民自治》,《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1年第6期。。但是,社區(qū)在誕生之初就扮演著“雙重角色”,在行政與自治的定位之間游移,是國家基層政權制度設計的產(chǎn)物。社會控制和行政服務始終是這一時期居委會的前置職能,社區(qū)服務和居民自治則處于序列后位。在實際運作中,政府對居委會的指導關系很容易演變成行政上的領導關系,居委會處于政府的干預甚至控制之下,影響了社區(qū)居民的參與積極性。在缺乏參與感的社區(qū)中,居民對其認同感自然也無從談起。
在國家主導的理念下,各種剛性制度安排的影響直接且明顯:社會意愿和訴求長期不能得到聲張、社會成員和群體的自主性和獨立性缺失、民眾自主決策和管理公共事務的能力偏弱、社會發(fā)展缺乏活力。近些年,社區(qū)治理方式的一大創(chuàng)新——網(wǎng)格化管理,試圖尋找并配置更為微觀的“網(wǎng)格”組織,并賦予其穩(wěn)定的管理和服務職責。但這種思維和實踐的導向,依舊是國家強力推動下的行政組織向社會層面的單向度擴張,也始終沒有擺脫自上而下的控制思維(27)姜曉萍、焦艷:《從“網(wǎng)格化管理”到“網(wǎng)格化治理”的內(nèi)涵式提升》,《理論探討》2015年第6期。。“社區(qū)行政化”造成了“無緯式”的偏向性發(fā)展,即作為“經(jīng)”的縱向政府系統(tǒng)俯拾即是,而作為“緯”的橫向社會自組織網(wǎng)絡則寥寥無幾,“行政社區(qū)”(28)劉君德:《中國大城市基層行政組織社區(qū)重構——以上海市為例的實證研究》,東南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37頁。也就應運而生。最終結果就是行政的嵌入影響了社區(qū)居民的參與意愿,最終阻隔了社區(qū)共同體的培育。
(二)市場嵌入:市場進入后社會共同體的侵蝕
卡爾·波蘭尼(Karl Polanyi)的“雙向運動”理論,為考察市場“嵌入”和社會“脫嵌”提供了很好的分析框架。在波蘭尼看來,一直到19世紀之前,西方的經(jīng)濟都是嵌入在社會之中的,其主導運行模式不是等價交換,而是互惠、再分配和家計原則。在這種生產(chǎn)模式下,人的經(jīng)濟目的從屬于社會目的,且人的行為動機首先是為了維護他的社會地位和社會關系,而不是占有盡可能多的物質(zhì)財富。在傳統(tǒng)社會中,人在共同體中的社會地位、社會聲望和社會網(wǎng)絡,顯然比占有物質(zhì)資源更重要。但在19世紀,市場突然從人類社會中“脫嵌”出來,“使社會的實存本身從屬于市場的法則”,“自然界將被化約為它的基本要素,鄰里關系和鄉(xiāng)間風景將被損毀”。市場從社會中剝離后,人類社會逐漸成為經(jīng)濟體系的附庸。造成這種結果的原因,主要不在于經(jīng)濟上的剝削,而是社會資本和社會文化的解體。這些勞動者被從他們依賴的鄉(xiāng)村社會網(wǎng)絡中連根拔起,拋入了“文化真空”。在這樣的背景下,19世紀出現(xiàn)了聲勢浩大的社會保護運動,席卷整個歐洲(29)[英] 卡爾·波蘭尼:《大轉(zhuǎn)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jīng)濟起源》,馮鋼、劉陽譯,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48、54、73-76、85頁。。這些運動的目的指向同一個方向,就是阻撓自由市場的運作,保護社區(qū)共同體免受自由市場的侵蝕。
中國自1980年代以來,也經(jīng)歷了一場“雙向運動”(30)王紹光:《大轉(zhuǎn)型:1980年代以來中國的雙向運動》,《中國社會科學》2008年第1期。。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至1984年間也是一種倫理經(jīng)濟。這一階段,經(jīng)濟增長固然重要,但卻服從于以社會主義為代表的倫理經(jīng)濟原則。經(jīng)濟關系必須服從于一套社會價值,即基本保障和平等,因而分配成為社會整合的主要形式。地方政府與單位之間以及下級政府與上級政府之間的關系皆是“軟預算約束”。第二個階段是1985年到1998年,其發(fā)展的特征是“效率優(yōu)先,兼顧公平”,但常常是效率壓倒公平,呈現(xiàn)出早期資本主義經(jīng)濟的發(fā)展態(tài)勢。改革開放后,社會形成了批評絕對平均主義的風潮,并逐漸從倫理社會轉(zhuǎn)向市場社會。為了追求更快發(fā)展,寧愿容忍一些不平等,并堅信只要實現(xiàn)經(jīng)濟騰飛,其他一切問題都會迎刃而解。此時,市場經(jīng)濟的原則開始侵入非市場領域,成為整合社會生活甚至政治生活的基準。人與人之間的關系變得越來越商品化、市場化,普通的民眾享受到的福利越來越少,所以,各種各樣的不平等逐漸顯現(xiàn)。第三個階段從1999年至今,社會政策開始出現(xiàn)。從市場社會向社會市場轉(zhuǎn)變也就意味著“雙向運動”正式開啟。在社會市場里,市場依舊發(fā)揮著高效配置資源的作用,但與此同時,政府也積極介入,并以再分配的方式實現(xiàn)部分民生領域的“去商品化”。
聚焦到社區(qū)治理場域,市場邏輯的進入正是中國式“雙向運動”第二階段之后的結果。現(xiàn)代社區(qū)以價格手段為中介,其居住空間受市場調(diào)節(jié),并形成了公民自由選擇的商品房小區(qū)。20世紀90年代中期以后,無償或者低償?shù)母@址空咧饾u廢止。政府著手推行住房公積金制度改革,大力推動房地產(chǎn)市場的發(fā)展。自住房商品化之后,資本開始參與城市空間的安排。資本與市場的邏輯視新興封閉式住宅小區(qū)的私密性為商品房的附加值,即一個住宅區(qū)的封閉性越強,越能將外來者拒之門外,這樣的住宅區(qū)的房價往往也越高。小區(qū)的私密性被資本包裝為一種高端的商品,服務于利潤最大化的需要;而私密性又導致社交的最小化,增加了彼此之間的“相遇成本”。新型商業(yè)住宅“陌生人”的社區(qū)歸屬感、認同感的缺失,直接誘使社區(qū)居民之間的共同體網(wǎng)絡不復存在。
(三)雙層嵌入、三重邏輯與社區(qū)共同體的迷失
盡管不同學者對社區(qū)的定義迥異,但有一個基本的共識,即社區(qū)是一定地域范圍內(nèi)經(jīng)由特定紐帶而形成的居民生活共同體。在這個社區(qū)共同體中,紐帶聯(lián)結以及社區(qū)認同是社區(qū)存續(xù)的核心要義(31)Seymour Sarason, “The Psychological Sense of Community: Prospects for a Community Psychology”,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Vol.132, No.3, 1974, pp.306-307;[美] 歐文·桑德斯:《社區(qū)論》,徐震譯,黎明文化事業(yè)股份有限公司1982年版,第16頁。。否則,作為共同體的社區(qū)將不復存在。但是,在中國的城市社區(qū)場域中,社區(qū)共同體在國家邏輯、市場邏輯與社會邏輯的交互作用下,卻呈現(xiàn)出迷失的狀態(tài)(32)桂勇、黃榮貴:《城市社區(qū):共同體還是“互不相關的鄰里”》,《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6年第6期。。其中,行政化代表國家的邏輯,是動員和組織城市社區(qū)的外在力量。與西方現(xiàn)代社區(qū)萌生于社會要素變化的內(nèi)生型發(fā)展路徑不同,中國的現(xiàn)代社區(qū)發(fā)展并非社區(qū)衰落和社會資本下降的結果(33)吳曉林:《中國城市社區(qū)建設研究述評(2000-2010年)——以CSSCI檢索論文為主要研究對象》,《公共管理學報》2012年第1期。,而是自始至終都具有行政化主導的傾向。社區(qū)作為國家在基層社會塑造的新單元,服務于國家政權建設和維護社會穩(wěn)定的實踐。在國家強行政邏輯的嵌入下,社會空間擴展有限,社會自組織能力弱化,進而影響社會共同體的培育。
中國城市社區(qū)場域中的市場邏輯發(fā)酵于“98房改”。自此,國家推行以居民住宅貨幣化、私有化為核心的住房制度改革。房改后,商品房社區(qū)成為城市社區(qū)的主要居住形態(tài)。與之相伴隨的是住房階層(Housing Class)的興起,房價逐漸成為一個區(qū)分不同階層的顯著標志。因此,將具有相似社會地位和生活方式的人群聚攏在一起的封閉式小區(qū)應運而生。然而,小區(qū)的封閉化催生了城市中產(chǎn)階級的“領地”意識(34)肖林:《“后院”政治:城市中產(chǎn)階層的“領地”意識》,《文化縱橫》2016年第6期。,住房作為一種象征社會地位的商品,推動了社會群體邊界意識的再生產(chǎn)(35)張海東、楊城晨:《住房與城市居民的階層認同——基于北京、上海、廣州的研究》,《社會學研究》2017年第5期。。同時,市場天然的逐利趨向又強化了商品房社區(qū)封閉性的領地屬性。商品房社區(qū)通過邊界意識的生產(chǎn),逐漸異化為一個業(yè)主利益的聯(lián)合體。這一形態(tài)淡化了社區(qū)共同體的營造,進而造成人格化社會交往的缺失(36)熊易寒:《社區(qū)共同體何以可能:人格化社會交往的消失與重建》,《南京社會科學》2019年第8期。。這樣的社區(qū)不再是一個具有人情味的互助共同體,而逐漸成為階層分化、社會區(qū)隔(37)在布迪厄看來,人和人之間分屬不同的群體,這種群體的區(qū)隔方式可以是資本、場域或者習性。參見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4。的“制造廠”。
以上分析表明,在國家邏輯與市場邏輯的雙層嵌入下,社會邏輯受之調(diào)控,并催生出一個“夾心層”狀態(tài)下的社區(qū)共同體(見圖1)。這一“夾心層”的社區(qū)共同體具有以下表征:第一,城市社區(qū)的產(chǎn)生和發(fā)展具有濃厚的國家推動色彩。無論是以“單位制”為基礎、街居制為配合的管理體制,還是“單位制”解體后社區(qū)制的普遍建立,抑或是社區(qū)服務和社區(qū)建設的興起,都是政府占主導地位并服務于國家政權鞏固的需要。城市社區(qū)治理扮演著“雙重角色”,在自治與行政之間游移。社區(qū)行政化不僅不利于社會自主空間的拓展,也抑制了社會主體意識的提升。因此,出現(xiàn)“行政區(qū)-社區(qū)”的社區(qū)形態(tài)。第二,住房商品化改革后,市場的逐利趨向塑造了社區(qū)居民的“領地”意識,造成社區(qū)認同與鄰里互助意識薄弱。第三,在國家維穩(wěn)趨向和市場逐利趨向的雙層嵌入下,社區(qū)共同體難以有效發(fā)揮守望相助和情感溝通的作用。

圖1 “夾心層”狀態(tài)下社區(qū)共同體的生成
分析社區(qū)共同體的迷失這一問題,應當從國家與社會關系、市場與社會關系中探求其癥結。一方面,國家高強度控制與治理績效之間往往并不呈現(xiàn)正相關的關系,只有實現(xiàn)國家與社會的相互聯(lián)結才能實現(xiàn)有效治理(38)邵春霞、彭勃:《國家治理能力與公共領域的合法性功能——論國家權力與社會結構的相互聯(lián)結》,《南京社會科學》2014第8期。。在單一化的社會背景以及復雜的國際環(huán)境下,國家運用專斷權力維持社會秩序具有合理性。但是,當社會主體日益多元、利益訴求日益分化,國家要實現(xiàn)有效的社會治理就必須更好地發(fā)揮國家的基礎性權力。邁克爾·曼(Michael Mann)將國家權力分為專斷權力(Despotic Power)和基礎權力(Infrastructural Power)兩個方面(39)Michael Mann, “The Autonomous Power of the State: Its Origins, Mechanisms and Results”, Europe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25, No.2, 1984, pp.185-213.。應當看到,任何國家為實現(xiàn)有效治理都需要將專斷權力和基礎權力有機結合。但是,現(xiàn)代國家治理應該更多地尋求社會力量的支持與合作,在國家有機“嵌入”(40)Peter Evans, Embedded Autonomy: States and Industrial Trans-formation,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5.社會的過程中探求國家與社會的相互交融。另一方面,波蘭尼的“雙向運動”指明,市場的逐利傾向追求自發(fā)調(diào)節(jié),但當社會遭受“市場有害行動”影響時,要通過“保護性立法、限制性社團和其他干涉手段”來尋求保護(41)[英] 卡爾·波蘭尼:《大轉(zhuǎn)型:我們時代的政治與經(jīng)濟起源》,馮鋼、劉陽譯,當代世界出版社2020年版,第140頁。。
此時,國家的邏輯、市場的邏輯以及社會的邏輯三者耦合,催生出中國社區(qū)治理場域下以國家助推社區(qū)共同體生成的必要性。區(qū)別于波蘭尼所描述的“自下而上”尋求保護的西方邏輯,中國社區(qū)共同體的迷失還有國家邏輯的作用。在中國,國家的強勢入場并始終在場使得社會力量發(fā)育不足。因此,在這一大前提下,中國社區(qū)共同體的成長以及為社區(qū)賦能(42)Sheila Watt, Cassie Higgins and Andrew Kendrick, “Community Particip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Services: A Move towards Community Empowerment”, Community Development Journal, Vol.35, No.2, 2000, pp.120-132.的諸多舉措,可能無法脫離政府的作用(見圖2)。但與西方相同,中國城市社區(qū)共同體的迷失同樣呼喚信任、互助、自治式鄰里關系的營造。

圖2 中西方社區(qū)共同體的生成路徑
社區(qū)內(nèi)的認同感和歸屬感來自于居民對社區(qū)行動的信任與認可,并隨著參與度和滿意度的提升逐漸營造出一個社區(qū)生活共同體。這一共同體締造的關鍵是形成一個利益團結的紐帶,以助推其成長。紐帶發(fā)揮著聯(lián)結社區(qū)內(nèi)個體和群體的作用,既可能是物質(zhì)形態(tài)的,也可以是心理層面的(43)袁方成:《國家治理與社會成長:中國城市社區(qū)治理40年》,上海交通大學出版社2018年版,第21頁。。社區(qū)通過營造與居民生活休戚相關的基礎設施,搭建一個社區(qū)主體相互交往的平臺。因此,社區(qū)“微基建”作為物質(zhì)形態(tài)的紐帶,在運作與實施過程中可以形塑公民心理層面的共同體意識。在營造社區(qū)“微基建”的同時,注重民眾自主參與、社區(qū)民主自治精神和公共精神的培育,重塑社區(qū)共同體。在社區(qū)營造“微基建”的過程中,政府始終保持著在場的狀態(tài)。
四、社區(qū)“微基建”何以可能:多維賦權重塑社區(qū)共同體
城市社區(qū)在行政化和市場化的雙層嵌入下,面臨著社區(qū)共同體日益迷失的困境。因此,需要尋找將社區(qū)居民組織起來的力量,以增強居民對其所在社區(qū)的價值認同與利益關懷。社區(qū)通過營造“微基建”,向社區(qū)社會組織和居民賦權,進而重塑參與者的互助精神和共同體意識。向社區(qū)賦權(Empowerment)旨在賦予社區(qū)治理參與者自治的權力(44)[英] 羅伯特·亞當斯:《賦權、參與和社會工作》,汪冬冬譯,華東理工大學出版社2013年版,第20頁。,讓其在參與中獲得社區(qū)治理所需的行動能力,并輔之以協(xié)商途徑,實現(xiàn)主體間利益的協(xié)調(diào)與一致。從賦權主體和結構動因的角度看,社區(qū)賦權可具體劃分為“自助”賦權和“他助”賦權兩種模式(45)范斌:《弱勢群體的增權及其模式選擇》,《學術研究》2004年第12期。。社區(qū)“微基建”作為聯(lián)結紐帶,通過技術賦權、機制賦權和主體賦權三重維度,以“他助”促進“自助”,重塑社區(qū)共同體。
(一)技術賦權:以“微基建”設施搭建居民參與的技術平臺
智能技術的引入,可以實現(xiàn)社區(qū)自動化、科學化與智能化升級,并以網(wǎng)絡化和信息化的平臺為媒介,為多元主體參與社區(qū)公共事務提供具體的方法與渠道。社區(qū)治理過程中的技術可具體劃分為自然意義上的和社會意義上的。“微基建”設施在供給自然意義上的治理技術之余,還可以作為社會意義上的治理技術運作平臺,為居民社區(qū)參與權利的落實奠定基礎。上海市靜安區(qū)臨汾街道為應對新冠肺炎疫情對基層治理的沖擊,與同濟大學智慧城市研究所合作搭建“智慧臨小二”平臺,以完善社區(qū)基礎信息化平臺建設。“智慧臨小二”在政府出資、社區(qū)自治、時間銀行三大運作理念的基礎上,以區(qū)塊鏈技術為底層架構,綜合運用人工智能等智能化技術,為社區(qū)居民提供智慧化的一站式服務。
“微基建”搭建居民參與的技術平臺,可有效提升政府對社區(qū)居民訴求的回應性以及居民對社區(qū)事務的自治能力。以“智慧臨小二”為例,一方面,在社區(qū)居民利益表達和政策議程輸入處理端,“智慧臨小二”使政府對多源異構問題的反應更加敏捷。它在搭建居民民意敏捷反應平臺的同時,也使得社情民意能在系統(tǒng)中及時被呈現(xiàn)并得到處理。另一方面,在社區(qū)議題討論端,“智慧臨小二”以區(qū)塊鏈技術保障社區(qū)自治。例如,利用區(qū)塊鏈技術對社區(qū)投票過程、結果進行加密,使投票全程可溯。“智慧臨小二”還提供居民預約居委干部走訪的功能,讓社區(qū)自治更加多樣。在技術手段的賦權增能下,居民參與社區(qū)治理有了平臺支撐。在對社區(qū)事務的積極參與中,社區(qū)居民的責任意識和共同體意識得以生成。
(二)機制賦權:以“微基建”模式創(chuàng)新保障公民的參與質(zhì)量
機制賦權是通過治理模式創(chuàng)新,賦予社區(qū)治理主體自主決策權和參與社區(qū)事務的職責權限,促進基層社會自治的規(guī)范化、合法化和專業(yè)化。為社區(qū)賦權,不應僅停留在居民能力上的扶持,還應關注社會政策、資源供給和運作機制的供給。因此,提倡基層社會自治,并不意味著政府角色的退出,而是要求政府集中精力掌舵,提高對機制模式的供給能力。社區(qū)營造“微基建”要實現(xiàn)公民參與質(zhì)量的持續(xù)提高,離不開社區(qū)運營機制的創(chuàng)新。資金、人員和組織作為“微基建”運轉(zhuǎn)的基礎性資源,唯有通過穩(wěn)妥的機制安排,方能營造合法的運作環(huán)境(46)尹浩:《城市社區(qū)微治理的多維賦權機制研究》,《社會主義研究》2016年第5期。。
上海市殷行街道通過PPP模式開展智慧車庫(棚)改造,將市場運營模式引入到“微基建”的營造中。殷行社區(qū)現(xiàn)有非機動車庫(棚)193個,大多建于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原來由物業(yè)、業(yè)主委員會委托收取管理費,聘請專人負責車庫(棚)的車輛看管和保安保潔工作。在傳統(tǒng)的管理和運行模式下,車庫(棚)內(nèi)物品丟失、車輛被盜事件屢見不鮮。因此,對老舊車庫(棚)進行改造升級有其客觀需求。對此,無論是中央層面還是地方政府層面,都要求基層工作者以治理精細化、智能化的工作方式,創(chuàng)新性地解決社區(qū)居民的實際問題。
傳統(tǒng)非機動車庫(棚)改造有兩種模式。其一是完全由政府包攬。該項做法主要面臨政府財力供給不足以及后期維修責任難以落實等難題,因此難以有效推廣。其二是完全由社區(qū)居民出資建設。此舉適用于中高檔商品房住宅區(qū),通過調(diào)動社區(qū)居民參與公共事務的主動性,公開募集資金。但對那些以低收入居民為主體的小區(qū),社區(qū)居民出資意愿低、溝通成本高,難以有效募集資金。
針對上述兩難選擇,上海市殷行街道打破行政化思維,探索黨建引領下的“政府引導、居民主體、市場運作”的聯(lián)席會機制。首先,政府通過引入合格供應商、設立財政引導資金等方式,搭建智慧車庫(棚)多方合作的機制。其次,街道將改造車庫(棚)的相關事宜均交由居民和企業(yè)商量。在反復磋商的過程中,社區(qū)居民把決定權掌握在自己手中,這有利于培養(yǎng)居民的自主意識。最后,車庫(棚)的改造、運營和維護采用BOT模式。企業(yè)主要負責車庫(棚)的規(guī)劃建設,并通過社區(qū)居民在使用過程中產(chǎn)生的費用來回收成本。前五年維持原收費價格不變;后五年按照合同規(guī)定,企業(yè)與業(yè)主委員會共享收益;十年后,相關設備的所有權轉(zhuǎn)向業(yè)主委員會,同時,企業(yè)享有提供維修維護服務的優(yōu)先權。
殷行街道通過將PPP模式引入社區(qū)老舊車庫(棚)改造,有效地盤活了社會資本(47)劉春榮:《國家介入與鄰里社會資本的生成》,《社會學研究》2007年第2期。,對于智能車庫(棚)的營造,社區(qū)居民也有支付意愿。如果政府部門能有效搭起合作治理的平臺,就能解決集體行動的困境。殷行街道通過BOT模式建設社區(qū)智能車庫(棚),一改過去由政府包攬改造、阻礙該領域市場發(fā)育的現(xiàn)象,實現(xiàn)“政府監(jiān)場、企業(yè)進場、居民主場”。如果將該模式推廣,既有利于企業(yè)間形成良性競爭,又有利于車庫(棚)更快地建、更好地管,最終實現(xiàn)政府、企業(yè)、居民共贏的局面。在BOT模式的保障下,居民有效地參與到社區(qū)服務的共同生產(chǎn)中(48)Victor Pestoff, “Citizens and Co-production of Welfare Services”, Public Management Review, Vol.8, No.4, 2006, pp.503-519.。在前期意見征求階段,關于“要不要改、怎么改以及改造后的權益與責任”等問題,都充分調(diào)動了居民的參與和協(xié)商。社區(qū)居民參與社區(qū)公共事務的質(zhì)量和責任獲得提升,這有助于其內(nèi)生出對所屬社區(qū)的歸屬感。
(三)主體賦權:以“微基建”營造激發(fā)居民的參與意識
主體賦權是以社區(qū)“微基建”為紐帶,以外部助推的方式,激發(fā)多元主體參與公共事務的動力,促進社會支持網(wǎng)絡和社區(qū)認同的培育。社區(qū)主體培育不足、組織化程度低是影響和阻礙社區(qū)治理現(xiàn)代化推進的重要因素(49)鹿斌、金太軍:《國家治理現(xiàn)代化進程中的社會治理創(chuàng)新》,《天津社會科學》2016年第2期。。激發(fā)社區(qū)居民的組織化程度,可以通過外部催化與內(nèi)部生發(fā)兩種路徑。社區(qū)“微基建”涉及凝結居民共同利益的各項基礎設施,因此,可作為激發(fā)居民參與意識的紐帶,從外部催生居民的參與意愿,并助力社區(qū)組織合力的生成。“微基建”營造可以將分散在社區(qū)中的治理主體有效組織起來,以社會能人(50)羅家德等:《自組織運作過程中的能人現(xiàn)象》,《中國社會科學》2013年第10期。和小微企業(yè)等為代表的多元主體積極投入到社區(qū)治理實踐中。
社區(qū)花園作為城市景觀“微基建”,以參與式社會創(chuàng)意為運作核心,有利于實現(xiàn)“人民城市”建設從最后一公里到最后一米的跨越。在《上海市城市總體規(guī)劃(2016-2040)》中,政府規(guī)劃著力強調(diào)了生態(tài)之城與人文之城的營造。新冠肺炎疫情爆發(fā)后,更加彰顯出與自然和諧相處以及與社區(qū)內(nèi)成員之間睦鄰友好的重要性。如何提升社區(qū)居民的居住空間品質(zhì),調(diào)動社區(qū)民眾共同參與設計、維護、管理,這是“人民城市”建設中亟需解決的問題。對此,上海“創(chuàng)智農(nóng)園”通過在城市化的景觀中引入田園風光,為高密度中心城區(qū)建成社區(qū)花園提供了很好的實踐借鑒。
“創(chuàng)智農(nóng)園”位于上海市楊浦區(qū)五角場街道創(chuàng)智天地園區(qū)內(nèi),毗鄰上海四大城市副中心之一的五角場商圈(51)劉悅來、尹科孌、魏閩、范浩陽:《高密度中心城區(qū)社區(qū)花園實踐探索——以上海創(chuàng)智農(nóng)園和百草園為例》,《風景園林》2017年第9期。。通過政府主導決策、差異化的包容性設計以及參與式建設,“創(chuàng)智農(nóng)園”建設借由社會組織和社區(qū)居民的高度參與,改善公共空間品質(zhì),加強多元主體間的互動融合。首先,在“創(chuàng)智農(nóng)園”的實施中,街道政府通過購買社會組織服務,多渠道地推動民眾參與社區(qū)建設,并為項目的落地提供政策監(jiān)督以及指標核準服務。其次,“創(chuàng)智農(nóng)園”設計團隊基于深入的調(diào)研,為社區(qū)公共物品的供給提供了專業(yè)化、科學化以及合理化的知識,充當著“城市空間醫(yī)生”的角色。最后,“創(chuàng)智農(nóng)園”日常運營和維護則主要由社會組織以及社區(qū)居民負責。在政府的引導下,社會組織和社區(qū)居民以共建共享的方式打造社區(qū)綠地空間。
“創(chuàng)智農(nóng)園”將共建共享的理念帶入到社區(qū)空間中。在政府對多元主體的賦權下,“創(chuàng)智農(nóng)園”為社區(qū)居民和社會組織參與社區(qū)生態(tài)空間營造提供了開放的途徑。這一公共空間的生產(chǎn),為互不相識、少有往來的社區(qū)居民提供了彼此“了解型信任”(52)帥滿:《從人際信任到網(wǎng)絡結構信任:社區(qū)公共性的生成過程研究——以水源社區(qū)為例》,《社會學評論》2019年第4期。建構的場所。以“創(chuàng)智農(nóng)園”這一公共空間為媒介,有著共同興趣愛好、社區(qū)參與理念的群體,在互動、磋商以及共建中逐漸形成對社區(qū)共同體的認知。“創(chuàng)智農(nóng)園”的營造將一個冰冷的陌生人社區(qū)變成一個有溫度的熟人社區(qū)。社區(qū)居民在公共空間中有了交流的媒介與需求,進而促進社區(qū)共同體的生成。
基于上述分析,可以看出,無論是偏公共性的,還是偏市場性的,抑或是偏社會性的“微基建”營造,都離不開政府的助推作用。以社區(qū)“微基建”為紐帶,并在政府“元治理”(53)Bob Jessop, “Governance and Meta-governance: On Reflexivity, Requisite Variety and Requisite Irony”, in Henrik Bang, Governance, as Social and Political Communication, Manchester: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3, pp.142-172.的作用下,通過技術賦權為多元主體參與社區(qū)治理提供了具體的手段和途徑;通過機制賦權為多元主體參與社區(qū)治理提供了合法性基礎、資源支撐和制度保障;通過主體賦權培植社區(qū)社會資本以增進公共福祉。社區(qū)以“微基建”的空間生產(chǎn)方式,調(diào)動了多元主體參與公共事務的積極性,并讓人與人之間形成了有意義的關聯(lián)(54)Elinor Ostrom, James Walker and Roy Gardner, “Covenants with and without a Sword: Self-Governance is Possible”, Th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6, No.2, 1992, pp.404-417.。正是以社區(qū)營造“微基建”這一中介機制,完善了作為國家權力運作基礎的社區(qū)組織網(wǎng)絡,并通過社區(qū)主體的自我管理和自我服務,塑造居民的認同感和共同體意識。
結 語
黨的十九屆五中全會審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四個五年規(guī)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明確提出,要“完善社會治理體系,健全黨組織領導的自治、法治、德治相結合的城鄉(xiāng)基層治理體系”,“加強和創(chuàng)新市域社會治理,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xiàn)代化”(55)《中共中央關于制定國民經(jīng)濟和社會發(fā)展第十四個五年規(guī)劃和二○三五年遠景目標的建議》,http://www.gov.cn/zhengce/2020-11/03/content_5556991.htm,2020-11-03。。新時代的社區(qū)治理應著力于讓社會運轉(zhuǎn)起來,并通過擴大居民參與,營造一個有凝聚力和向心力的社區(qū)治理共同體。但是,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來,伴隨著現(xiàn)代國家的正式權力有組織的滲入以及改革開放以來市場的逐利動機的侵入,城市社區(qū)共同體在雙層嵌入下逐漸迷失。如何在國家強勢入場和始終在場的情況下,消解市場與資本對城市社區(qū)共同體的侵蝕,并塑造一個兼具社區(qū)認同和鄰里互信的社區(qū)共同體,這是創(chuàng)建“人民城市”和推進市域社會治理現(xiàn)代化亟需解決的問題。
中國的國家與社會之間的關系不是西方社會中心論式的此消彼長,而應實現(xiàn)二者的相互重疊與相互滲透。實踐經(jīng)驗表明,在既有的格局下,中國社區(qū)共同體的成長不可能外在于國家,這一過程應浸透著國家的身影和力量。但是,如何平衡與區(qū)分國家和社會的力量,實現(xiàn)二者相互賦權,這是現(xiàn)代國家建設的主線。社區(qū)治理是觀察國家與社會互動的微觀場域。行政力量與社區(qū)自治力量并非此消彼長,相反,應呈現(xiàn)出一種共生共長的態(tài)勢。因此,國家應通過嵌入式治理的方式,改變國家權力與社會結構的聯(lián)結方式,實現(xiàn)國家權力與社會權力的相互交織。社區(qū)“微基建”作為一種嵌入機制,是一種聯(lián)結國家與社會不同行為主體的紐帶。對于“微基建”的營造,既萌生于社區(qū)居民的內(nèi)在需求,又需借助國家資源的下放和制度的供給,還需要市場主體的積極參與。在國家的助推下,社區(qū)“微基建”將激發(fā)多元主體的參與動力,增強社區(qū)居民的價值認同,并生成社區(qū)命運共同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