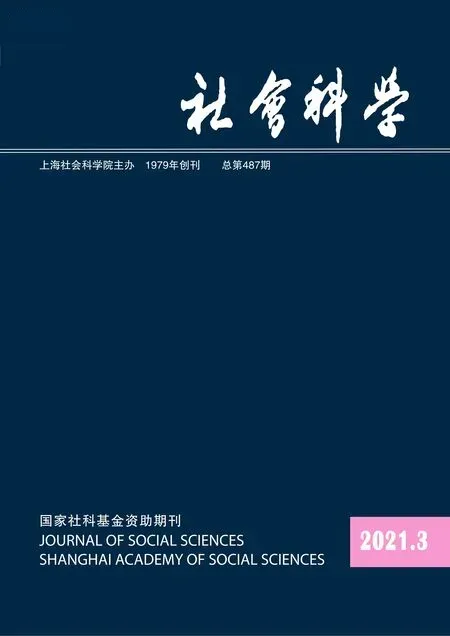經(jīng)史子集與中國文論的兼性闡釋
李建中
按照朱自清先生《詩文評的發(fā)展》一文的說法,現(xiàn)代學科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其“名”(即“文學批評”一語)是舶來的,其“實”(經(jīng)典、理念、方法、演變等)則出自《四庫全書總目》(以下簡稱《總目》)集部的詩文評類。(1)參見朱自清《朱自清古典文學論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45頁。筆者曾著文,將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百年嬗變描述為“從‘學出集部’到‘識通四庫’”。(2)李建中:《從“學出集部”到“識通四庫”——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的范式演進》,《暨南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4期。“經(jīng)史子集”不僅僅是傳統(tǒng)文獻的分類方法,還是學術(shù)研究的思維方式和批評方式,更是漢語學術(shù)的知識學譜系和理論范式。同理,《總目》不僅僅是一部文獻學或目錄學經(jīng)典,更是一部具有明顯的“兼性”特征(3)國內(nèi)學界較早論及文學之“兼性”特征的,當推欒棟《辟文學別載》,《文學評論》2010年第4期。的闡釋學或批評學經(jīng)典。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無論是兼通四部的“中國古代文論”,還是學出集部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均淵源有自、順理成章地帶有經(jīng)史子集及其《總目》的兼性闡釋之特質(zhì)。
在現(xiàn)代性語境下,中國文論的兼性闡釋正面臨兩大挑戰(zhàn):一是“以西律中”或“以中證西”的強制闡釋,二是“分科治學”或“專業(yè)主義”端性思維。二者合謀將中國文論從其兼性闡釋的學術(shù)傳統(tǒng)中剝離出來,從其經(jīng)史子集的有機整體中切割開來,從而釀成當下中國文論研究的“無根化”和“標本化”的雙重困境。如何在經(jīng)史子集之知識學譜系與中國文論之闡釋學理論的深度關(guān)聯(lián)的基礎(chǔ)上,重新清理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學理依據(jù)、古典形態(tài)、現(xiàn)代嬗變和當代價值,對于突顯中國文論的“中國性”,對于在文學理論研究領(lǐng)域重塑中國方案、中國范式和中國特色,有著重要的理論意義和實踐價值。
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學理依據(jù),既植根于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又生長于“兼”“通”互訓之語義根柢,從而在兼性主體、兼性思維和兼性文本的邏輯層面有機生成兼性闡釋的學術(shù)內(nèi)涵及學理框架。“中國文論”又稱“中國古代文論”和“中國文學批評史”,三千年的“中國古代文論”,與“經(jīng)史子集”的范式生成基本上同向同行、同體同構(gòu),從而在文獻的互文性、學派的交融性和心態(tài)的“平心而論”等不同層面建構(gòu)起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古典形態(tài)。近百年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從“學出集部”到“識通四庫”,分別在“集”奠其基、“史”開其局、“子”拓其疆和“經(jīng)”聚其力的不同領(lǐng)域交織成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現(xiàn)代嬗變。對經(jīng)史子集與闡性闡釋之學理依據(jù)的重構(gòu),對三千年古典形態(tài)的重塑,對近百年現(xiàn)代嬗變的重建,最終是為了揭示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當代價值:如何行之有效地將中國文論的兼性闡釋用之于文論典籍“新四部”和大學教育“新文科”的建設(shè),如何在鏡鑒西方、通變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重建文論話語的“中國性”,于文學理論領(lǐng)域重塑中國方案、中國范式和中國特色。
一、兼性闡釋的學理依據(jù)
討論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學理依據(jù),需要從“兼”這個關(guān)鍵詞說起。
西語有詞根,漢語也有詞根,而漢語的“詞”之“根性”有二:一是決定這個詞之根本義的字,二是這個字最早的釋義。就本文的關(guān)鍵詞之一“兼性闡釋”而言,“兼”這個漢字是它的詞根,“兼”最早的釋義(手持兩禾)則是它的詞根之詞根。“手持一禾”者,固守一端,偏于一方,是《莊子·天下篇》所說的“方術(shù)”,或稱為“端性思維”或“端性闡釋”;“手持兩禾”者,兼和包容,會通適變,是《天下篇》所說的“道術(shù)”。依照《天下篇》的描述,上古文明史之嬗變是“兼”在前而“秉”在后,“悲夫!道術(shù)將為天下裂”。在漢語闡釋學的語境下,中國文論研究如何從“方術(shù)”返回“道術(shù)”,如何從“以西律中”的強制闡釋和“專業(yè)主義”的端性思維返回到傳統(tǒng)文論的兼性闡釋,正是本文所要探討的核心問題。
生長于“兼”“通”互訓之語義根柢的中國文論的兼性闡釋,其理論的邏輯維度有三:一是主體身份之兼性;二是思維方式之兼性;三是文本纂集之兼性,三者有著密切的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兼性主體具備兼性思維,兼性思維創(chuàng)生兼性文本。分述如下:
(一)兼性主體
中國學術(shù)史上,第一次對闡釋主體作類型學區(qū)分的當推《莊子》,其《天下篇》將上古學術(shù)史之流變描述為“道術(shù)”向“方術(shù)”的裂變,“道術(shù)”之主體是“四通六辟”“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的圣人、至人、神人和真人,而“方術(shù)”之主體則是“不該不遍”“得一察焉以自好”的“一曲之士”。(11)(清)郭慶藩:《莊子集釋》,中華書局2016年版,第1073頁。后莊子(或者說前學科)時代漫長的歷史時期,中國并沒有職業(yè)的文學家,更沒有職業(yè)的文學理論家或批評家,賦詩作文或者品詩論文并非是文學家或文論家單一的立身之道或謀生之途。就社會身份而言,文學家亦官亦民:達時為官,窮時為民;出仕時為官,隱遁時為民;天下有道時為官,天下無道時為民。就文化身份而言,文學家亦學亦文:“辨章學術(shù)”時為學者,“獨抒性靈”時為文人;撰著《新唐書》時為學者,閑談《六一詩話》時為文人;出任四庫館臣時為學者,退居草堂閱微時為文人。就學者身份而言,文學家又悠游于經(jīng)史子集之間:于經(jīng)部立天下公理,于史部識前車轍痕,于子部拓展視野,于集部涵養(yǎng)性情。闡釋主體這種一身而數(shù)任、一人而多能的兼性特征,成功地超越了《莊子·天下篇》所說的“方術(shù)”而返回到“道術(shù)”,從而成就了三千年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的博雅多元和文備眾體。
(二)兼性思維
有什么樣的闡釋主體,就會有什么樣的思維方式,中國文論的兼性闡釋,其主體身份的或仕或隱、亦學亦文和學通四部,直接釀成思維方式的會通適變、惟務折衷和彌綸群言。《文心雕龍·雜文篇》:“智術(shù)之子,博雅之人,藻溢于辭,辯盈乎氣。”(12)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254頁。劉勰字彥和,俊彥之士,協(xié)和眾說、等觀三界,既于時空層面兼通古今、兼和佛華,又于邏輯層面敷理舉統(tǒng)、籠圈條貫。前者就是《通變篇》所講的“望今制奇,參古定法”,因其通而亙古亙今,因其變而日新其業(yè)。天下之理,不可以不通;古今之道,不可以不變。后者則是《序志篇》所特別標舉的“擘肌分理,惟務折衷”。就《文心雕龍》的文本而言,劉勰諸多文論范疇如體性、風骨、情采、奇正、比興、通變,等等,都是“惟務折衷”的結(jié)果,亦即叩其兩端或多端以作深度辨析和辨證,從而揚棄、超越兩端或多端之局限或偏頗,在更高的層面達成新的融通和統(tǒng)一。若將《文心雕龍》置于“長時段”(即幾千年中外文學理論批評史)來考察,劉勰文學理論批評的“解析神質(zhì),包舉洪纖,開源發(fā)流,為世楷式”(《題記一篇》)(13)魯迅:《魯迅全集·集外集拾遺補編》,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年版,第332頁。也是“惟務折衷”的結(jié)果。就思維方式而言,劉勰之所以撰寫《文心雕龍》是有感于在他之前和與他同時代的論文者大多只能“詮序一文”,只能“各持一隅之解,欲擬萬端之變”,“各照隅隙,鮮觀衢路,所謂東向而望,不見西墻也”(14)范文瀾:《文心雕龍注》,人民文學出版社1962年版,第726頁。。針對這種流行的“端性思維”的方式,劉勰主張“彌綸群言”,主張“籠圈條貫”。從根本上說,宗經(jīng)征圣的劉勰是繼承了經(jīng)學的傳統(tǒng):“籠圈”源于《周易》的經(jīng)緯天地、苞舉宇宙,“條貫”源于《周禮》的整飭六官和《尚書》的洪范九疇。清代章學誠《文史通義》比較司馬遷和班固,稱“遷書通變化,而班氏守繩墨”,“遷書體圓而用神,……班書體方而用智”(15)葉瑛:《文史通義校注》,中華書局2014年版,第59頁。,說的也是思維方式的“兼性”與“端性”之別。
(三)兼性文本
對于學術(shù)書寫而言,有什么樣的思維方式,就會有什么樣的理論文本。太史公的思維方式是“體圓而用神”,故《史記》才能“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劉舍人的思維方式是“籠圈條貫”,是“惟務折衷”,故《文心雕龍》才能“彌綸群言”,才能“體兼四部”。就后者而論,劉勰的《文心雕龍》是一個典型的兼性文本:《隋書·經(jīng)籍志》將之收入集部的總集類,后來的《總目》將之收入集部的詩文評類,在從7世紀到18世紀的千年歷史中她都屬于“集部”,此其一;劉勰有著濃厚的圣人情結(jié)和自覺的宗經(jīng)意識,《文心雕龍》從“文之樞紐”到“論文敘筆”,從“割情析采”到“才略知音”,全書一以貫之的以“論文”的方式“述經(jīng)”,以至于成為中國古代文論的經(jīng)學闡釋之范式(16)李建中:《中國文論的經(jīng)學范式》,《武漢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此其二;《文心雕龍》大到理論體系的建構(gòu),中到分體文學史的演繹,小到作家作品的評騭,無不遵循“原始以表末,觀瀾以索源”的史學路徑,此其三;劉勰既有“博明萬事,適辨一理”的子學方法,更有“融通儒道,等觀三界”的子學胸襟,故《文心雕龍》的子學特征同樣鮮明昭著(17)關(guān)于《文心雕龍》的子學特質(zhì),請參見游志誠《文心雕龍五十篇細讀》,(中國臺灣)臺北文津出版社2017年版。,此其四。不惟《文心雕龍》,古代文論經(jīng)典文本的詁訓傳譯、層累纂集,既有文獻學之版本考證,又有目錄學之系譜厘定;既有文字學之語詞詁訓,又有歷史學之源流考鏡;既有義理學之求微言大義,又有文章學之辨奇正華實……真正是體兼四部,文備眾體,交互交匯,兼和兼通。
二、兼性闡釋的古典形態(tài)
“中國文論”之一名二指已如前述:或偏于研究領(lǐng)域(中國古代文論),或偏于學科命名(中國文學批評史)。若放在歷史時空中考察,則“中國文論”的一名二指又有三千年之“古典形態(tài)”與近百年之“現(xiàn)代嬗變”之別。本文的二、三兩節(jié)將分別討論: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與三千年古典文學理論批評的兼性闡釋,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與近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兼性闡釋。
作為漢語知識學譜系的經(jīng)史子集,首先是一種文獻分類方法。中國古典學術(shù)的文獻分類,雖然劉歆《七略》的“六分法”早于荀勖《中經(jīng)新薄》的“四分法”,但前者亡佚,后者則藉隋志庚續(xù),至《總目》而集大成。從隋志到《總目》,四部的總體特征就是“兼性”。《總目》卷首《凡例》:
闡明學術(shù),各擷所長;品騭文章,不名一格。兼收并蓄,如渤澥之納眾流,庶不乖于《全書》之目。
《總目》集學術(shù)之大成,既不乖于“全書”之名,亦不有違“兼收并蓄”之實。《總目》卷一一《書類敘》亦稱:
尺短寸長,互相補苴,固宜兼收并蓄,以證異同。
只有兼收并蓄,方能取長補短、補苴罅漏,方能求同存異、各得其所。《總目》從卷首之《凡例》到四部之總敘,從44條類敘到近萬條提要,不僅有自覺的“兼收并蓄”意識,而且始終貫穿著兼性闡釋的理念和方法。如果說,作為一部文獻學和目錄學經(jīng)典,《總目》是對“四分法”的總歸和集大成;那么,作為一部文化和文學批評學經(jīng)典,《總目》則是對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的一次最為成功的兼性闡釋。就后者而言,不僅《總目》自身即是兼性闡釋的古典形態(tài),而且《總目》的理論和實踐又是對經(jīng)史子集之兼性闡釋范式的檢驗和確證。
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所特有的兼性闡釋,對包括《總目》在內(nèi)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的影響是深刻而廣泛的。分而論之,兼性闡釋從三個方面鑄成中國文論的古典形態(tài)。
(一)典籍的互文性
《總目》所賡續(xù)并定型的文獻四分,雖然典列四庫,其實四大部典籍之間具有明顯的互文性特征。《總目》卷九一《子部總敘》:“自六經(jīng)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這就公開宣稱“經(jīng)”之外的“子”“史”“集”是相通或相同的。其實,子書與經(jīng)書也有相通之處,比如《論語》和《孟子》,原本為“子”,后來升格為“經(jīng)”。“經(jīng)”中不僅有“子”,“經(jīng)”中還有“史”與“集”:“經(jīng)”中之“史”如《尚書》《春秋》,“經(jīng)”中之“集”如《詩經(jīng)》。《尚書》和《春秋》分別為最早的記言體和編年體史書,《詩經(jīng)》則為最早的詩歌總集。章學誠《文史通義》講“六經(jīng)皆史”,則是要以“史”之德、才、法,既融通經(jīng)、子、集,又兼和考據(jù)、義理、辭章。
古典形態(tài)的中國文論,在文獻類分上的最大特征就是典籍的互文或互通。近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即下一節(jié)要討論的“現(xiàn)代嬗變”),受西方“純文學”觀念和“分科治學”方法的影響,不僅要區(qū)分“純文學”與“雜文學”,還要區(qū)分“文學”與“批評”,落實到文獻類分上,就有了“文學文體”與“批評文體”之別。但這種區(qū)別或類分在古典形態(tài)的中國文論中并不存在,《總目》卷一九五《詩文評類敘》稱“建安黃初,體裁漸備,故論文之說出焉,《典論》其首也”(18)(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下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779頁。,可見《典論·論文》之前的先秦兩漢并沒有“批評文體”或“文學理論批評文獻”意義上的“論文之說”,關(guān)于文學理論和批評的種種言說,還是“寄生”在經(jīng)、史、子、集四大類文獻之中:被譽為“中國文論開山綱領(lǐng)”的“詩言志”首見于《尚書》,影響中國文論幾千年的“發(fā)憤著書”出自《史記》,原始儒、道兩家的文論散見于先秦諸子,《詩經(jīng)》中的以詩論詩則可視為首部詩歌總集中的文論……濫觴期的中國文論,其文獻的互文性表現(xiàn)為一種特殊的“寄生性”形態(tài)(19)關(guān)于早期中國文論相關(guān)文獻的寄生性特征,可參見李建中、閻霞《從寄生到彌漫——中國文論批評文體原生形態(tài)考察》,《華中師范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2004年第5期。,既是批評文體的“文備眾體”,又是批評文獻的“文兼四部”。三千年的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其典籍的互文性從早期的“寄生”到中后期的“彌漫”,既是經(jīng)史子集四部文獻的互滲互透,又是文論文獻與四部文獻之間的互文互通。這種典籍的互文性從古代延續(xù)到現(xiàn)代,直接鑄成近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學出集部”與“識通四部”。
(二)學派的融通性
中國傳統(tǒng)學術(shù)以經(jīng)學為綱紀,而經(jīng)學之流變又以漢學與宋學為統(tǒng)系。《總目》卷一《經(jīng)部總敘》先是清理歷代經(jīng)學的六變與六弊:兩漢之“拘”、魏晉之“雜”、兩宋之“悍”、明初之“黨”、晚明之“肆”和清初之“瑣”。在此基礎(chǔ)上總括經(jīng)學“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為勝負。夫漢學具有根柢,講學者以淺陋輕之,不足服漢儒也;宋學具有精微,讀書者以空疏薄之,亦不足服宋儒也”。顯然,經(jīng)學六弊和漢宋之爭,皆為端性思維而遠離兼性闡釋的海納眾流、兼收并蓄。如何既消除經(jīng)學六弊,又超越漢宋之爭?《經(jīng)部總敘》主張“消融門戶之見,而各取所長,則私心祛而公理出,公理出而經(jīng)義明矣。蓋經(jīng)者非他,即天下之公理而已”(20)(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上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頁。。這個“公理”,從闡釋學的層面論,就是“兼性闡釋”之理,也是張江所說的“公共闡釋”之理。
《總目》對漢學與宋學的折衷或融通,是中國文論兼性闡釋之古典形態(tài)的典型案例或?qū)W術(shù)范式。“消融門戶之見”既是經(jīng)學闡釋的任務,更是文論闡釋的使命,三千年的中國古代文論,大體上表現(xiàn)出一種“學派融通”的大趨勢和大氣魄。在《莊子·天下篇》所描述的“道術(shù)”時代并無學派之分或門戶之見,即便是在百家爭鳴的“方術(shù)”時代也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就“言意觀”而言,老子講“大辯無言”,孔子講“天何言哉”;莊子主張“得意忘言”,孟子主張“不以辭害志”:儒、道兩家皆有“言不盡意”之體認。從根本上說,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綱紀性知識客體是“經(jīng)”,融通性闡釋主體是“圣”,故《說文解字》稱“聖,通也”,“聖,通而先識”(21)(漢)許慎撰,(清)段玉裁注《說文解字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版,第592頁。《說文解字》中“圣”與“聖”是兩個不同的字,前者從“土”,而后者從“耳”,本文指后者,特此說明。。鄭樵《通志·總序》:“惟仲尼以天縱之圣,故總《詩》《書》《禮》《樂》而會于一手,然后能同天下之文;貫二帝三王而通為一家,然后能極古今之變。”(22)鄭樵:《通志二十略》,中華書局1995年版,總序第1頁。一個“惟”字,或可見出在鄭樵的心目中,自有書契以來,能夠識“會通”“融通”或“兼通”之大義者,孔子為第一人,故可稱“天縱之圣”。司馬遷心儀孔子,“雖不能至,心向往之”,作《史記》而“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史記》之后,尊孔子為“圣”而通變古今、消融門戶者代不乏人,如“隨仲尼而南行”的劉舍人,不屑古今也不屑佛華,而是彌綸群言,惟務折衷。被譽為儒家詩圣的杜工部,“不薄今人愛古人”“轉(zhuǎn)益多師是汝師”(《戲為六絕句》)。直到“但丁式”終結(jié)古代文論并開啟現(xiàn)代文論的王靜安,更是主張“學無新舊也,無中西也”(《〈國學叢刊〉序》)。古代文論兼性闡釋的學派融通性,在最高的層面融通了“經(jīng)”(闡釋對象)與“圣”(闡釋主體),因為“經(jīng)”之“消融門戶”也就是“圣”之“中庸為德”,這也是以劉勰為代表的古代文論家如此執(zhí)著于“征圣宗經(jīng)”的闡釋學緣由之所在。
(三)批評態(tài)度和方法的“平心而論”
有學者將《總目》文學批評的特征與方法分別概括為“全知批評、官學批評、書籍批評”與“貫通批評、打通批評、通觀批評、雙向度批評”(23)何宗美:《〈四庫全書總目〉的文學批評》,《中南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1期。:就前者而言,《總目》的文學批評帶有明顯的官方色彩和權(quán)力意志;就后者而言,《總目》的文學批評大體上是兼通、兼容和兼和的。讀《總目》,發(fā)現(xiàn)四庫館臣在撰寫各種提要時最愛用的一個詞是“平心而論”。《總目》卷一五一《樊川文集》條:
平心而論,牧詩冶蕩甚于元、白,其風骨則實出元、白上。其古文縱橫奧衍,多切經(jīng)世之務。(24)(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下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96頁。
《總目》關(guān)于樊川詩文的“平心而論”,針對的是杜牧詩歌評騭中的“冶蕩”之譏。杜牧有“十年揚州夢”,故難免“青樓薄幸名”;但杜牧更有《赤壁》《河湟》《泊秦淮》,故被劉熙載《藝概》贊為“雄姿英發(fā)”,雖生于晚唐卻不乏盛唐風骨。“平心而論”的批評態(tài)度和方法,用在具體的作家品評上,是了解之同情,是求同而存異,是劉勰所說的“見異唯知音耳”;用在文學史的通變上,則能識大體,通大道。《總目》卷一四八《別集類敘》推論歷代別集的存佚之因:
文章公論,歷久乃明。天地英華所聚,卓然不可磨滅者,一代不過數(shù)十人。其余可傳可不傳者,則系乎有幸有不幸,存佚靡恒,不足異也。(25)(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下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271頁。
若無“平心而論”的心態(tài)和方法,是很難總結(jié)出如此通達又如此明暢的“文章公論”的。
就學術(shù)研究的具體方法而言,經(jīng)史子集,各有各的方法:諸如經(jīng)學方法的“字以通詞,詞以通道”,史學方法的“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子學方法的“博明萬事,適辨一理”,集部方法的“討論瑕瑜,別裁真?zhèn)巍薄=?jīng)史子集知識譜系的這四種方式,在古代文論的兼性闡釋中都有成功的運用;或者反過來說,正是經(jīng)史子集的四種方法構(gòu)成古代文論的兼性闡釋。劉勰《文心雕龍·序志篇》將自己“論文敘筆”(即文體論)的方法概括為“四項基本原則”:原始以表末,釋名以章義,選文以定篇,敷理以舉統(tǒng)。劉勰的這四種方法,分之為“經(jīng)”“史”“子”“集”,合之為“平心而論”。“釋名以章義”是經(jīng)學方法的名物詁訓、詞以通道,“原始以表末”是史學方法的溯源尋根、考鏡源流,“敷理以舉統(tǒng)”是子學方法的博通萬事、自成一家,“選文以定篇”是集部方法的淘沙汰滓、別裁真?zhèn)巍K姆N方法總而合之、兼而通之,則是《總目》卷一《經(jīng)部總敘》所說的“參稽眾說,務取持平”,也就是四部館臣念茲在茲的“平心而論”。
從方法論的意義上講,經(jīng)史子集各有一套成熟的方法,合起來就是兼性闡釋的方法;而在四種(或四套)方法之上,則是“平心而論”。這既是《總目》卷一《經(jīng)部總敘》所標舉的“天下之公理”,更是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之兼性闡釋在方法論上的總體特征。“平心而論”的兼性闡釋方法和心態(tài),近而言之來自《總目》,遠而言之則根源于孔儒的中庸和中道。《總目》所舉經(jīng)學六弊,或為“過”,或為“不及”;漢學與宋學的互為攻訐,亦為批評方法和心態(tài)的偏于一端。孔子喟嘆:“中庸之為德也,其至矣乎!民鮮久矣。”(26)(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91頁。所以莊子后學要浩嘆“道術(shù)將裂”,劉勰要標舉“惟務折衷”,四庫館臣要主張“平心而論”。
三、兼性闡釋的現(xiàn)代嬗變
本文二、三兩節(jié)分述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古典形態(tài)”與“現(xiàn)代嬗變”,其中的“古典”與“現(xiàn)代”之分,既是時間層面更是研究主客體及研究內(nèi)容層面。就研究主客體及研究內(nèi)容的區(qū)分而言,“古典”之中國文論指的是古代文論家對古代文學的批評及理論總結(jié)(故又稱“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現(xiàn)代”之中國文論則專指現(xiàn)代學者對古典文學理論批評的研究(故又稱“中國文學批評史”)。這一區(qū)分,放在本文的研究視域(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與中國文論兼性闡釋之關(guān)系)來考察,其各自的特征就較易辨識了:“古典”之兼性闡釋,中國古典文學理論批評與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是同向同行、同體同構(gòu)的;“現(xiàn)代”之兼性闡釋受西學沖擊和影響,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則在兩個不同的層面展開,一是以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為內(nèi)核的本土范式與外來西學范式的博弈與融通,二是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在百年批評史研究歷程中的潛行與嬗變。關(guān)于前者,筆者另有專文論述,下面著重討論后者。
經(jīng)史子集,作為自本自根、原汁原味的知識學譜系,構(gòu)成近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思想靈魂、歷史本末、文化精神和批評方法。站在21世紀回望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百年歷程,可以將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在近百年批評史研究歷程中的“潛行與嬗變”概括為四句話:“集”奠其基、“史”開其局、“子”拓其疆和“經(jīng)”聚其力。以“集”之詩文評性質(zhì)的各體批評和各種方略奠其基,以“史”之重新書寫和各種理念、風格及體量之史著的再度輝煌開其局;以“子”之多元文化視野的思想爭鳴和博明萬事的知識纂集拓其疆;以“經(jīng)”之“文以載道”式的本體闡釋和“詞以通道”式的范疇辨析聚其力。
(一)“集”奠其基
20世紀初葉,處于開創(chuàng)期的中國文學批評史,有兩大學術(shù)事件值得大書特書:一是1914年至1919年黃侃在北京大學開壇講授《文心雕龍》并作《札記》31篇,二是1927年陳中凡出版《中國文學批評史》,前者可謂“‘集’奠其基”,后者則為“‘史’開其局”。《總目》集部的五大類,一頭(楚辭)一尾(詞曲)是狹義的文學,第四類(詩文評)是狹義的文學批評,而二、三兩類(別集和總集)則是廣義的文學和文學批評。因此,集部的五大類文獻,對于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而言,既提供了研究對象(文學文本),又提供了研究范式(經(jīng)典文本、核心理念、話語行為和研究方法)。在這個意義上甚至可以說,無集部則無中國文學批評。黃侃在北京大學講授集部詩文評的代表作之一《文心雕龍》,作為中國文學批評史草創(chuàng)期的標志性事件,則是“‘集’奠其基”的有力證據(jù)。
對于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現(xiàn)代嬗變”而言,“‘集’奠其基”的要義有三。一是前述黃侃在現(xiàn)代大學設(shè)壇開講集部之《文心雕龍》,既宣告現(xiàn)代龍學之開啟,亦標志現(xiàn)代意義上的“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之肇始。二是“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現(xiàn)代學科的開創(chuàng)者們,從《總目》集部的詩文評(朱自清稱之為“集部的尾巴”)發(fā)現(xiàn)了“中國”的“文學批評”,具體而言是發(fā)現(xiàn)了中國文學批評的“最簡歷史”(從兩漢“文成法立”到明人“喜作高論”)、經(jīng)典文本(《典論》《文心》《詩品》《詩式》,等等)以及路徑(考證舊聞,觸發(fā)新意)、方法(討論瑕瑜,別裁真?zhèn)?和目的(博參廣考,有裨文章)。三是集部詩文評的類敘和140余條提要(含詩文評類存目),是典型的具體批評,從而為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提供了“具體批評”的學術(shù)范式。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對古典形態(tài)之兼性闡釋的通變,承續(xù)了集部具體批評的傳統(tǒng),在借鑒西學范式的同時,對失焦于“文學”、 以“理論”自身為目的的傾向保持了足夠的警惕,從而遠離“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之窠臼,遠離“理論生成理論”之陷阱。《總目》卷一八七《文章正宗》條引顧炎武《日知錄》稱真德秀選詩,病在“以理為宗,不得詩人之趣”:
故德秀號為名儒,其說亦卓然成理,而四、五百年以來,自講學家以外,未有尊而用之者,豈非不近人情之事,終不能強行于天下歟?(27)(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下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1699頁。
西方文論強制闡釋的“沒有文學的文學理論”和“理論生成理論”,均屬“不近人情之事”,故“終不能強行于天下”。
(二)“史”開其局
這里說的“‘史’開其局”有雙重內(nèi)涵:一是20世紀初葉的“初開其局”,二是20世紀末葉與21世紀初葉之交的“重開其局”。先說“初開其局”。20世紀初,中國文學批評史這門現(xiàn)代學科的開創(chuàng)者們,從經(jīng)史子集之“集”發(fā)現(xiàn)了文學批評,隨之通過“史”的書寫打開了研究局面。1927年,陳中凡《中國文學批評史》問世,這是與學科同名的第一部專著。1931年,朱東潤在武漢大學講授中國文學批評史,其講義數(shù)易其稿,1944年由開明書店出版;1935年之前,朱東潤在武漢大學的《文哲學刊》發(fā)表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系列論文。1934年,郭紹虞、方孝岳和羅根澤三位學者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同年問世:郭紹虞《中國文學批評史》上冊在商務印書館印行,方孝岳《中國文學批評史》在世界書局出版,羅根澤《周秦兩漢文學批評史》則由人文書店推出。幾位學術(shù)大師同時推出極有份量的中國文學批評史專著,不僅打開了這個學科的局面,而且為這個學科將來的發(fā)展構(gòu)筑了較高的起點,奠定了堅實的基礎(chǔ)。
20世紀下半葉,在經(jīng)歷了長達十多年的沉寂之后,中國文學批評史的重新繁榮,也是靠“史”重開其局。如果說20世紀的30年代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第一個春天,那么20世紀與21世紀之交則是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第二度春天,而“第二春”的顯著標志同樣是“‘史’開其局”:各種體量、體類、體式、路徑和風格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著作,重新打開中國文學批評史的研究局面并釀成一個不小的甚至是全局性的高潮。以復旦大學七卷本《中國文學批評通史》為代表的諸種批評史,自覺引入文化史、學術(shù)史、思想史和精神史的史識、史觀和史法,在民族文化、民族心靈和民族精神的層面揭示中國文論的歷史意義和當代價值。《總目》卷六五《廿一史識余》條:
所重乎正史者,在于敘興亡、明勸戒、核典章耳。(28)(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上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582頁。
文學批評史作為“史”之一類,亦有“敘興亡、明勸戒、核典章”之三大功能。“初開其局”的陳、朱、郭、方、羅五史,有根有據(jù)地敘述著三千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的崇替興衰;“重開其局”的后學諸史,有聲有色地敘述著近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波詭云譎:二者相續(xù)相承,既昭明前覆后鑒、經(jīng)驗教訓,又核準經(jīng)典辭章、義理考證,從而為中國文論的兼性闡釋提供史論、史觀、史識和史法。
(三)“子”拓其疆
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若套用現(xiàn)代學術(shù)分類,經(jīng)學屬于思想類,史學屬于歷史類,集部屬于廣義的文學藝術(shù)類,子學則屬于文化類。相比之下,子學的疆域最廣:不僅包括了先秦兩漢的諸子文化,還包括了整個儒釋道文化。《總目》卷九一《子部總敘》:
自六經(jīng)以外,立說者皆子書也。……夫?qū)W者研理于經(jīng),可以正天下之是非;征事于史,可以明古今之成敗,余皆雜學也。……然凡能自名一家者,必有一節(jié)之足以自立。(29)(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上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第769頁。
不僅“經(jīng)”外皆“子”,而且“經(jīng)”內(nèi)亦有“子”;子學不僅能以證經(jīng)史,而且能以廣見聞;子學不僅有思想之爭鳴,而且有資料之纂集……子學的博通與龐雜,在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之中尤其具有兼性闡釋的意味和特色。
兼性闡釋現(xiàn)代嬗變中的“‘子’拓其疆”,對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影響,突出表現(xiàn)在三個方面。一是文化視野;筆者的“中國文論詩性特征研究”,就是以子學之文化視野開拓出古代文論的詩性空間,揭示儒道釋文化的詩性精神如何孳乳出中國文論的詩性特征:儒家文化“比德”的人格訴求和“比興”的話語方式鑄成文論形態(tài)的人格化和理論范疇的經(jīng)驗歸納性質(zhì),道家文化的“道法自然”和“得意忘言”釀成文論言說的詩意性和審美性,印度佛教對世界的想象和中國禪宗對語言的超越助成中國文論詩徑與理路的融通。二是批判精神;子學緣起于先秦諸子的百家爭鳴,其間既有墨家對儒家的“非樂非命”,也有法家對道家的“解老喻老”,還有儒家內(nèi)部的“問孔刺孟”,既是見仁見智,也是立言立說,體現(xiàn)出子學“博明萬理,自成一家”的批判精神。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無論是摩羅詩力學與“為藝術(shù)而藝術(shù)”的對話,還是審美主義與歷史主義的對峙,抑或文化詩學與語言詩學的對談,思想與方法或許大相徑庭,但內(nèi)在的批判意識與子學精神則是一脈相承的。三是資料編纂;子學的思想爭鳴是需要文獻支撐的,故各類資料的匯編和纂集也是子學功夫之一。百年批評史研究的成果中,有大量的文論選注、文論辭典、文論資料匯編等。比如文論選注有郭紹虞、王文生主編《中國歷代文論選》;文論辭典有趙則誠、張連第、畢萬忱主編《中國古代文學理論辭典》;文論資料匯編有徐中玉《中國古代文藝理論資料叢刊》、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資料選注》以及王水照《歷代文話》、黃霖《歷代小說話》等。
(四)“經(jīng)”聚其力
經(jīng)史子集的知識學譜系,其四部之間并不是并列關(guān)系,經(jīng)史子集四部并不在同一個層面,借用《文心雕龍·宗經(jīng)篇》的話說:“經(jīng)”是“根柢槃深”,“史”“子”“集”則是“枝葉峻茂”。“經(jīng)”是根本,是綱紀;“史”“子”“集”是衍生,是羽翼。在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現(xiàn)代嬗變之中,“‘經(jīng)’聚其力”表現(xiàn)為“文以載道”式的本體闡釋和“詞以通道”式的范疇辨析。
《文心雕龍》開篇便講“文之為德也大矣,與天地并生者何哉”,與天地并生的“文德”之力從何而來?來自儒家經(jīng)典的“太山遍雨,河潤千里”和“鼓天下之動”,來自儒家詩學的思無邪、興觀群怨、知人論世、與民同樂、發(fā)憤著書、精誠由中,等等,這些先秦兩漢詩教的主流話語,構(gòu)成了一個經(jīng)世致用的理論系譜。《總目》卷首《凡例》:
圣賢之學,主于明體以達用。凡不可見諸實事者,皆屬卮言。(30)(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上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卷首第18頁。
近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無論是對古典文學理論批評的重新闡釋,還是古今通變、中西比較意義上的現(xiàn)代闡釋,均不約而同地帶有“明體達用”“見諸實事”的經(jīng)學本體論色彩。筆者從事中國文論及文化元典關(guān)鍵詞研究十多年,有兩點很深的感受:第一,那些生命力最旺盛、幅射力最遼闊、震憾力最強烈(我稱之為“命大、輻大和力大”)(31)李建中:《元典關(guān)鍵詞研究的中國范式》,《河北學刊》2020年第2期。的文論關(guān)鍵詞,大多是出自先秦兩漢的經(jīng)學元典,或者是出自對經(jīng)學元典的訓詁詮解之著;第二,這些出自經(jīng)學元典的關(guān)鍵詞,之所以命大、幅大和力大,之所以能鼓天下之動,是因為它們是對文學理論之根本問題的本體論回答。比如郭紹虞早期的批評史研究,《中國文學批評史》的書寫是圍繞“文學”這一根本觀念展開的,全書的框架是“文學觀念的演進期”與“文學觀念的復古期”。郭紹虞早期的批評史研究論文,也多圍繞核心觀念立論,如剖析“神氣”“文道”和“文法”,等等。
“經(jīng)”之影響中國文論范疇辨析,就是戴震所說的“由字以通詞,由詞以通道”,即從“小學”(文字學)經(jīng)由“經(jīng)學闡釋學”再到對文論關(guān)鍵詞的釋義與詮解。經(jīng)學范式的方法論意義,是關(guān)注“字”“詞”“道”之關(guān)系,由“我注六經(jīng)”與“六經(jīng)注我”兩條路徑,衍生出諸如文以載道、通經(jīng)致用、以意逆志、立象盡意、深究詁訓、精研義理等文學理論和文學批評的方法。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的諸多著述中,成功運用經(jīng)學闡釋法的,有劉師培《文章源始》、章太炎《文學總略》、姚永樸《文學研究法》和錢鐘書《管錐編》等。《管錐編》是雙重意義上的經(jīng)學闡釋:它的研究對象是經(jīng)學元典,如《周易正義》《毛詩正義》《左傳正義》等,此其一;它所使用的方法也是經(jīng)學的,如訓詁、傳注、考訂、詮解、正義、辨?zhèn)蔚取.斎唬豆苠F編》更是一個典型的兼性闡釋文本,其闡釋對象遍涉經(jīng)史子集四部,其闡釋方法既有經(jīng)學的“字以通詞,詞以通道”,也有史學的“辨章學術(shù),考鏡源流”,還有子學的“博明萬理,自成一家”和集部之學的“討論瑕瑜,別裁真?zhèn)巍薄摹豆苠F編》這部中國文論的現(xiàn)代經(jīng)典之中,我們又可以看出,古典形態(tài)的兼性闡釋,在百年中國文學研究的現(xiàn)代嬗變之中,仍然有著極強的生命力。
四、兼性闡釋的當代價值
中國文論的兼性闡釋,植根于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其學理依據(jù)內(nèi)置于兼性主體、兼性思維和兼性文本的邏輯互聯(lián),其古典形態(tài)積淀成典籍的互文性、學派的融通性和心態(tài)的平和度,其現(xiàn)代嬗變呈現(xiàn)為“集”奠其基、“史”開其局、“子”拓其疆和“經(jīng)”聚其力。中國文論的兼性闡釋,在理論和邏輯的層面整合成主體、思維和文本的有機統(tǒng)一,在歷史和實踐的層面,生生不息地繁衍成三千年古典形態(tài)的根柢槃深和枝葉峻茂,曲曲折折地流淌為近百年現(xiàn)代嬗變的參古定法和望今制奇。
兼性闡釋的知識學譜系或理論范式是經(jīng)史子集,經(jīng)史子集的根柢和綱紀是“經(jīng)”,是作為天下之公理的經(jīng)世致用。文學理論和批評的當下之“世”,一方面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大力倡導并推行復興傳統(tǒng)文化、構(gòu)建中國話語,另一方面卻是實際研究中對傳統(tǒng)文化(包括兼性思維、兼性闡釋)的淡漠和疏離,后者又突出地表現(xiàn)為兩點:一是西方話語對本土理論及實踐的“強制闡釋”,二是大學專業(yè)主義教育所導致的“端性思維”。當下之世,“強制闡釋”與“兼性闡釋”,“端性思維”與“兼性思維”,構(gòu)成深刻的沖突與對立,而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當代價值,正是建立在對“世”的清醒認識和對“用”準確體認之上。中國文論的兼性闡釋,在經(jīng)歷了三千年的“古典形態(tài)”和近百年的“現(xiàn)代嬗變”之后,如何完成當下的創(chuàng)造性轉(zhuǎn)換,如何實現(xiàn)其當代價值?本文擬從文論典籍之“新四部”、大學教育之“新文科”和學術(shù)話語之“中國性”三個方面略加陳述。
(一)文論典籍的“新四部”
作為傳統(tǒng)學術(shù)知識學譜系和理論范式的經(jīng)史子集,首先是一種文獻分類的方法,因而經(jīng)史子集對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影響,無論是“古典形態(tài)”還是“現(xiàn)代嬗變”,一個最為基本的層面還是文獻學的。三千年古典文學理論批評,從兼性主體、兼性思維到兼性文本,均與文獻學密切相關(guān)甚至就是文獻學本身。近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從“集”奠其基、“史”開其局,到“子”拓其疆、“經(jīng)”聚其力,每一個步驟或階段,若離開文獻學則為無根之談甚至是癡人說夢。就文獻學層面而論,中國文論的兼性闡釋,無論是主體、思維、文本,還是考據(jù)、義理、辭章,一個基本的功夫就是“學通四部”。前學科時代的古典時期,文論家的“學通四部”自不待言;分科治學的現(xiàn)代社會,真正的大學問家無一例外地“學通四部”。
不僅僅是“學通四部”。我們看到,百年中國文學批評史研究領(lǐng)域經(jīng)典著作的作者,除了“學通四部”,還是“學貫中西”,具有跨文化、跨語際、跨學科的知識構(gòu)成,有的原來學醫(yī)而后來從事文學創(chuàng)作和研究,有的是歷史學家而同時從事文學理論研究,有的更是精通多種語言或者在多個學科領(lǐng)域開課授徒、著書撰文:以跨學科經(jīng)典閱讀為基礎(chǔ)的學術(shù)研究和教書育人是他們的共同之處。在這個意義上或可將文獻學層面的“學通四部”作現(xiàn)代解讀:對中國文論的研究而言,“學通四部”在古代是兼通經(jīng)史子集,在當下則可引伸為兼通四大類文獻,后者又可稱之為“新四部”。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文獻,是主流意識形態(tài)的理論根基,是包括“中國文論”在內(nèi)的所有學術(shù)研究的綱紀和根本,因而是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經(jīng)”或新“經(jīng)部”。以《總目》集大成的經(jīng)史子集,它的總敘、類敘及萬余條提要,以及提要所評騭的海量典籍,構(gòu)成中國文論的全部史料性文獻,置身于當下時空或可將其統(tǒng)稱為“史”或新“史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文論,既打通了中與外,又突破了“文學”與其它領(lǐng)域的囿別區(qū)分,從而在后現(xiàn)代語境下返回到前現(xiàn)代,用《莊子·天下篇》的話說,從“方術(shù)”返回到“道術(shù)”。如同百年批評史研究的“‘子’拓其疆”,當下中國文論的“子”或新“子部”就是中外學術(shù)文獻及中外文學經(jīng)典。上述新經(jīng)學、新史學和新子學的各類文獻,在互聯(lián)網(wǎng)時代均能以數(shù)字化方式儲存、閱讀、檢索和引用。在這個意義上可以說,中國文論又稱之為e批評,而e批評所必需必備的海量電子文獻及各種數(shù)據(jù)庫則可稱之為中國文論的“集”或新“集部”。概言之,馬克思主義經(jīng)典文獻、傳統(tǒng)經(jīng)史子集四部文獻、中外學術(shù)及文學文獻和海量數(shù)字化文獻,共同構(gòu)成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新四部”。就學術(shù)研究的知識學譜系而論,“新四部”既與傳統(tǒng)四部有著內(nèi)在而深刻的文化關(guān)聯(lián),又是對傳統(tǒng)四部的合理性擴展或延伸,從而在文獻學領(lǐng)域突顯出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當代價值。
(二)大學教育的“新文科”
作為現(xiàn)代學科的“中國文學批評史”,肇始于黃侃先生1914年在北京大學向諸生講授《文心雕龍》。由此可知,中國文論兼性闡釋的“現(xiàn)代嬗變”是從“大學教育”開始的。百年之后,中國大學開始討論“新文科”,而“新文科”的重要內(nèi)涵是如何走出“專業(yè)主義”的狹窄遂道,走向“博雅通識”的新天地和新境界。從百年前黃侃在大學講壇創(chuàng)生“新龍學”,到百年后中國大學倡導“新文科”,這里面有一條內(nèi)在的脈絡(luò):中國文論的兼性主體、兼性思維和和兼性闡釋如何用之于人的教育和培養(yǎng)。《大學》有云:“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新民,在止于至善。”(32)(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頁。三“在”所指皆為“人”,人的德才兼?zhèn)洌说闹屑嫔疲说墓沤窦婷鳎说奈氖芳嫱āG懊嬲劦剑段男牡颀垺肥侵袊恼撝T多典籍中最為典型的兼性文本,這緣于劉勰學兼佛華、識通四部的兼性才能和彌綸群言、惟務折衷的兼性思維。作為“新龍學”的開創(chuàng)者,黃侃先生以古文字和古音韻學家的身份而涉獵文學理論,其“文學”觀又兼通章太炎之文字學、阮元之文選學和現(xiàn)代西方文論之純文學觀,其思維方式及闡釋理念有著鮮明的兼性特征。古典形態(tài)的《文心雕龍》和現(xiàn)代嬗變中的黃侃龍學,二者所共有的兼性闡釋成為當代大學“新文科”建設(shè)的寶貴思想資源和文化遺產(chǎn)。
以兼性思維和兼性闡釋以內(nèi)核的“新文科”,第一要義是跨學科經(jīng)典閱讀。就漢語人文經(jīng)典的閱讀而言,至少應包括《總目》卷首《凡例》所開列的“馬、班之史,李、杜之詩,韓、柳、歐、蘇之文章,濂、洛、關(guān)、閩之道學”(33)(清)永瑢等撰:《四庫全書總目》,上冊,中華書局1965年版,卷首第19頁。。傳統(tǒng)社會中無須出仕的大家閨秀(如《牡丹亭》中的杜麗娘和《紅樓夢》中的林黛玉)尚且學通四部,而將要成為國家棟梁甚至行業(yè)領(lǐng)袖的當代大學生,豈能滿足于只讀本專業(yè)的書籍?筆者在武漢大學主持通識教育,提出“博雅弘毅,文明以止,成人成才,四通六識”的十六字方針,其中“四通”指一通古今、二通中外、三通文理和四通知行,“六識”指淵博的學識、卓越的見識、經(jīng)典閱讀意識、獨立思考意識、文化批評意識和團隊合作意識。四通六識乃至十六字針作為當代大學“新文科”的范例之一,其教育理念和教學方法有著明顯的兼性思維和兼性闡釋之內(nèi)核:既包含了前述“新四部”意義上的跨學科經(jīng)典閱讀,又兼?zhèn)洹敖?jīng)”之立德樹人、“史”之以古鑒今、“子”之六通四辟和“集”之文備眾體。
(三)學術(shù)話語的“中國性”
從中西比較的層面看,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是中國學術(shù)所特有的,根源于古老華夏先民的文化基因、思維方式和話語傳統(tǒng)。中國的知識性和學術(shù)性活動及其成果,無論是傳統(tǒng)的儒道釋還是現(xiàn)代的文史哲,也無論是主體、思維和文本,還是原創(chuàng)、傳播和接受,無一不打上經(jīng)史子集的烙印,帶有經(jīng)史子集的色彩,秉有經(jīng)史子集的特質(zhì)。三千年的古典時期,中國文論的兼性闡釋與經(jīng)史子集知識譜系同步;近百年的現(xiàn)代進程,經(jīng)史子集依然潛行其間。而在 “強制闡釋”與“端性思維”的雙重困境之中,能否充分闡揚經(jīng)史子集知識譜系的兼性思維及兼性闡釋,關(guān)乎學術(shù)話語之“中國性”的重塑和重建能否真正實現(xiàn)。
經(jīng)史子集的兼性闡釋,自有其完整而系統(tǒng)的學術(shù)話語;而經(jīng)史子集四部,又各有一套自己的話語體系,包括認知路徑、理論面向、主要流派、核心命題、基本范疇、常用方法和典型案例,等等。經(jīng)學話語體系,其認知路徑是思想語境下的“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其理論面向是文學理論批評的“征圣宗經(jīng)”以及經(jīng)典闡釋的“敷理舉統(tǒng)”,其主要流派是漢學與宋學的對峙與互通,其核心命題是字以通詞、詞以通道,其基本范疇是是道、圣、經(jīng)、文,其常用方法是文以載道,通經(jīng)致用,以意逆志,立象盡意,等等。史學話語體系,其基本范疇是史才、史學、史識和史德,基本方法是舉本統(tǒng)末、知人論世、尚友古人和察古鑒今。子學話語體系,其基本范疇是立言、忘言、博物和游藝,其基本方法是見仁見智、非樂非命、解老喻老和寓言儲說;集部之學話語體系,其基本范疇是文章、文體、文脈和文事,基本方法是選文定篇、尋章摘句、敷理舉統(tǒng)和得意會心。經(jīng)史子集各自的話語行為及范式,在漫長而曲折的歷史流變中,在內(nèi)部的話語融通和外部的話語博弈中,整合成一個關(guān)于中國文化之思維方式及闡釋理論的宏大的話語體系。這一話語體系,既區(qū)別于現(xiàn)代學術(shù)“分科治學”的專業(yè)主義(方術(shù)式的端性思維)和“以西律中”的后殖民主義(單邊式的強制闡釋),又區(qū)別于西方理論的形而上學獨斷論和從理論到理論的形式化。
以經(jīng)史子集為知識學譜系的中國文論的兼性思維,是世界文明的“中國基因”,是知識考古學意義上的“本然之中國”;以兼性思維為方法或路徑的兼性闡釋理論是“中國智慧”,是中西文化比較意義上的“相對之中國”;以“兼”“通”“中”“和”等中華文化元關(guān)鍵詞為核心理念和意義世界的話語體系是“中國特色”,是話語重構(gòu)和范式重建意義上的“必要之中國”。在鏡鑒西方、通變傳統(tǒng)的基礎(chǔ)上標舉文學理論批評話語的“中國性”,正是本文討論經(jīng)史子集知識學譜系與中國文論兼性闡釋之內(nèi)在關(guān)聯(lián)與歷史演變的當代意義之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