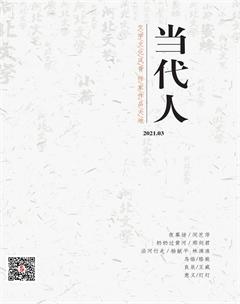雪一樣明凈
一
那個(gè)冬天的雪特別多,一次又一次的覆蓋,最底層的積雪都沒(méi)有機(jī)會(huì)化掉。我原來(lái)從沒(méi)有過(guò)要主動(dòng)去看父親墓地的想法,因?yàn)橐恢焙ε履欠N氛圍。最近幾年,家鄉(xiāng)因?yàn)樵?shī)歌變成了詩(shī)上莊,活動(dòng)非常多,我時(shí)常回來(lái)幫忙,而且也試著書寫文字,把對(duì)父親的思念一點(diǎn)點(diǎn)釋放出來(lái),心也開始像雪一樣純凈明朗。
弟弟沒(méi)在家,母親陪著我。
我們小心地往前走,走了很遠(yuǎn)還沒(méi)到。母親驚訝地說(shuō),哎呀,走錯(cuò)路了,多走了三四個(gè)壩臺(tái)。于是我們重新從上往下,踏著沒(méi)人走過(guò)的雪,繼續(xù)尋找父親的墓地。
我四歲時(shí),家里日子緊巴巴的。母親為省些糧食,不讓我們下床活動(dòng)。爺爺帶著奶奶還有沒(méi)成家的姑姑叔叔去了東北,把我們四口留在家里。爺爺對(duì)我父親說(shuō),孩子小,別折騰了,就讓我們?nèi)フ垓v吧。爺爺還做了一個(gè)決定,把屋子換成了吃的。他說(shuō)住得好賴無(wú)所謂,不能委屈孩子。爺爺走后,我們一家四口就住進(jìn)了臨時(shí)的房子。
這些都是我長(zhǎng)大后母親告訴我的。
一直住臨時(shí)的房子,咋能活人呢,孩子們逐漸大了。母親每天重復(fù)著這樣的話。
蓋,憋著不吭聲的父親終于發(fā)了話。
母親瞪大了眼睛,沒(méi)錢咋蓋呢,那一磚一瓦不是犟出來(lái)的。
第二天,父親就開始從山上往家里扛石頭。磨爛了肩膀,手臂。母親心疼地哭著不讓扛了,說(shuō)都是她的錯(cuò),不再打房子的主意了。那個(gè)時(shí)候,我正在與弟弟玩跳皮筋,捉迷藏。
后來(lái),我特意問(wèn)過(guò)大伯,他說(shuō): “曉娥啊,你爸要不是扛石頭,也不至于早早就沒(méi)了,都累得吐血啊,他的病純粹是那年頭兒又累又餓得上的。你爸爸走的時(shí)候,是在墳地里打的棺材,軟包抬到那兒的。”
二
我十歲那年,父親病了,在止痛藥再也止不住疼痛時(shí),三姑急得讓三姑父托人想方設(shè)法把父親送進(jìn)承德附屬醫(yī)院。住院期間,母親去陪床,我和弟弟留在家里。我和八歲的弟弟像兩只失去翅膀的小鳥,顫栗地在野地里覓食。那是我記憶里最黑暗的秋天,是家里最沒(méi)有歡笑的秋天。
板栗已經(jīng)熟了,自留地里的栗子樹長(zhǎng)得高大粗壯,給我們做伴的外公年紀(jì)大了,他也不能上樹打栗子。我們只能站在樹下,仰著頭,靜靜地等著板栗一顆顆落下。但是那些板栗好像刻意和我們作對(duì),從早晨等到下午,也沒(méi)落下幾顆。就這樣等了一個(gè)月,窗臺(tái)上的升也沒(méi)裝滿。
我學(xué)著母親的樣子喂豬。我把水和豬食面放進(jìn)鍋里,用火一點(diǎn)點(diǎn)熬熟,然后抬到豬圈邊兒上,一勺一勺倒進(jìn)豬槽里,我總是不小心倒到豬的腦袋上,而且無(wú)論喂給它多少食物,還是把它從肥胖喂養(yǎng)得瘦成皮包骨。
我和弟弟努力做著每一件事情,就想在父親回來(lái)時(shí)給他一個(gè)驚喜。
可是,在他回來(lái)不久,守候那么久的栗樹做成棺木,成了他的新家。我們緊緊看護(hù)著家,卻沒(méi)看護(hù)住我們的父親。那頭豬也成了給他送行人的飯食。
父親出院那天,下雨了,雨水打濕了他的衣服,順著臉頰往下流,分不清是雨水還是淚水。他是騎著三姑借的毛驢回來(lái)的,因?yàn)楦赣H已經(jīng)走不動(dòng)路。到家后,父親就感冒了,病情十分嚴(yán)重,他開始向我們囑咐每件事。
一天晚上,我在微弱的燈下寫作業(yè),屋里有些昏暗,父親倚在炕角,聲音孱弱地對(duì)我說(shuō),曉娥,好好寫字。我說(shuō),嗯。那時(shí)三年級(jí)的我字已經(jīng)寫得很好了,因?yàn)楦赣H經(jīng)常教我。現(xiàn)在三姑也說(shuō),我的字體像父親,好看。他繼續(xù)說(shuō),好好學(xué)習(xí),考上大學(xué),不要改姓,照顧好弟弟。我狠狠地點(diǎn)了點(diǎn)頭,答應(yīng)著,我們的眼睛對(duì)視著,他的眼神里滿是無(wú)助。
父親病危了,爺爺從東北趕過(guò)來(lái)陪著他,三姑含著淚后悔,每天念叨治晚了。
他們不時(shí)地把父親放在地上的一塊木板上,鋪上厚厚的褥子,可是他還是說(shuō)硌得慌,我眼里高大的父親已經(jīng)被疾病折磨得瘦骨嶙峋。他一說(shuō)疼,爺爺就去撫摸他的胃,然后像哄小孩兒一樣輕聲地問(wèn),是這兒疼嗎?父親皺著眉頭說(shuō),是,里面燒得難受。爺爺就用濕毛巾敷。我在旁邊,不停地把毛巾放進(jìn)水里,那水是溫的,放進(jìn)去擰干,放進(jìn)去再擰干。爺爺?shù)难蹨I有時(shí)和父親的融合在一起,我靜靜地看著。但我只能看著,因?yàn)槲也欢也攀畾q。
有一天,我在院子里玩,家里響起了喇叭聲,姥姥騎著小毛驢來(lái)我家。我記得清清楚楚,那毛驢是黑色的,耳朵上有點(diǎn)白。姥姥讓我扶著她,又瘦又小的姥姥,邊走邊哭。我還在想,姥姥怎么哭得這么傷心?后來(lái)才知道,白發(fā)人送黑發(fā)人,是世上最大的痛。可我還是沒(méi)有哭,因?yàn)槲也欢朗莻€(gè)什么概念。父親最終閉上了眼睛,他們把他抬走,我就跟在身邊,快到墓地時(shí),他們不讓我去了,說(shuō)親人只能送到這里。我沒(méi)有反駁,轉(zhuǎn)身回來(lái),我哪里知道,這是送父親的最后一程。
父親去世了,永遠(yuǎn)地離開了我們。按著他的遺愿,媽媽帶著我和弟弟嫁給了鄰村里父親生前的一位好友。后來(lái)聽繼父說(shuō),父親早就囑托他,一定要供我讀書。
而父親用生命建成的老屋就永久地閑置下來(lái),慢慢地變得破敗不堪。
從那以后,我有了每年秋天都會(huì)收藏一片栗葉的習(xí)慣。
三
這么多年來(lái),我是第一次近距離和父親的墓對(duì)視。雖然不知父親在這個(gè)新家里生活得怎么樣,但是那個(gè)我和父親生活了十年的老屋,老屋里發(fā)生的每一件事,卻歷歷在目。
老屋是三間黑瓦房,孤獨(dú)地立在西山腳下,顯得十分古老和沉寂。黑色瓦礫間已長(zhǎng)出茅草。由于年久失修,梁快要折了,用水泥抹的一塊塊石頭露在外面,老式的木格子窗戶也十分破舊。兩側(cè)墻根是嵌進(jìn)水泥里的五角星,還噴了白灰。由于長(zhǎng)期沒(méi)人居住,屋子成了別人寄存物品的地方。窗臺(tái)下面的石頭已坍塌,那是他們從窗子往外抬物品時(shí)碰撞造成的。上次,帶著東北回來(lái)的姑姑們?nèi)タ蠢衔荩磳⑻臉幼樱芟裎覀兊男那椋灰p輕碰一下,就會(huì)散落一地。
老屋的院子里有口菜窖,用石頭壘成的,蓋房子的事我不記得,幾年后挖井的場(chǎng)景歷歷在目。那是舅舅們幫忙挖的。記得挖井那天,天都黑了,地面上很多挖出來(lái)的土,在昏暗的燈光下,他們干活,我和弟弟在土堆邊玩。
我們搬走后,母親在老屋的四周栽了很多山楂樹,現(xiàn)在已有房檐那么高,那些山楂樹時(shí)常撕扯我的記憶。
老屋的門是兩塊普通的木板,藍(lán)色的,是父親為了防蟲蛀涂的藍(lán)漆,門上的漆痕已經(jīng)斑駁。在左門板上,父親曾寫過(guò)八個(gè)大字。
“曉娥,放學(xué)了別總是玩,做飯啊。”母親干活臨走時(shí)告訴我。父親怕我忘了,就用從學(xué)校找來(lái)的粉筆,專門在門板上寫上:“曉娥放學(xué)回家做飯。”
我每天都按照門板上父親寫的指示去做。記得第一次做棒米飯,燒的柴火是我和弟弟去山上撿的,父親說(shuō),誰(shuí)撿得多,給獎(jiǎng)勵(lì)。我們就拿著他割來(lái)的葛條,到山上把撿到的小柴火捆好,扛回來(lái)放在墻角,自己先比比高低,然后就等父親回來(lái)獎(jiǎng)勵(lì)。不過(guò)父親每次都是夸我,因?yàn)槲冶鹊艿艽髢蓺q,肯定比他撿得多。
灶膛里的火慢慢燒著,我不時(shí)地往里添些柴火,棒米飯是原湯的,母親告訴我,用小火一點(diǎn)點(diǎn)把水熬干。我做得非常成功,開心得像一只小鳥,圍著西屋的窗框來(lái)回地邊轉(zhuǎn)邊唱。
四
父親比母親大八歲,村里曾在海南工作的大叔說(shuō),父親比他聰明,因?yàn)樗?dāng)年一直讀書,后來(lái)留在海南工作。而我父親由于經(jīng)濟(jì)條件不允許,沒(méi)有完成學(xué)業(yè)。好不容易有個(gè)招考教師的政策,正在山上干活的父親,聽到爺爺?shù)暮艉埃瑲獯跤醯嘏苓M(jìn)考場(chǎng),手都沒(méi)來(lái)得及洗,就去考試,結(jié)果差一分落選了,最后只能在村里做了小隊(duì)長(zhǎng)。當(dāng)小隊(duì)長(zhǎng)時(shí),因?yàn)樗傁敕ㄔO(shè)法為村民的利益著想,所以,藏在大山褶皺里的十幾戶人家都很信服他,他也給自己樹立起威望。
那時(shí),晚上經(jīng)常開會(huì),商量村里的大事,而我就是曾經(jīng)的哨手。白天哨子躺在后窗臺(tái)的角落里,我像個(gè)戰(zhàn)士一樣守護(hù)著它,晚上召開全村會(huì)議時(shí),我就用它替父親發(fā)號(hào)施令。通常是在每家都吃完晚飯后,父親對(duì)我說(shuō),今晚開會(huì)。我拿起哨子,到院子里吹,當(dāng)“咻”的聲音滑過(guò)夜空,我就像個(gè)小英雄,隨后喊一句,“開會(huì)了”,每家的代表就聚集在我家,我?guī)兔δ玫首印5首雍苌伲嗟娜俗娇簧希械娜诉€坐進(jìn)炕里,我會(huì)像個(gè)大人一樣在父親身邊安靜地聽著。我從沒(méi)想過(guò)這樣的日子會(huì)改變。
我家曾養(yǎng)過(guò)牛。父親把棒秸稈扛回來(lái),我和弟弟就幫著喂牛,看它們咀嚼的樣子。父親說(shuō),牛會(huì)反芻,吃進(jìn)嘴里的食物,經(jīng)過(guò)一段時(shí)間以后,再將半消化的食物從胃里返回嘴里,再次咀嚼。從那時(shí)起,我們知道了什么是反芻。
有一頭牛生病了,實(shí)在不能醫(yī)治,父親不得不找人把它殺了。牛眼里含淚,父親眼里也含淚。殺牛時(shí),父親躲得遠(yuǎn)遠(yuǎn)的,牛叫最后一聲,他的眼淚還是流了下來(lái)。那是我們吃的最好的一頓飯,我和弟弟吃得開心、滿足。剩下的牛肉都被母親切成小塊,放到房頂上晾成了牛肉干。餓了時(shí),我和弟弟就去取著吃,取不到,就用木棍挑,實(shí)在取不到時(shí),就開始央求父親,父親的個(gè)子高,一下子能取下來(lái)很多。我現(xiàn)在依稀記得牛肉干的味道,以及多少孩子羨慕的眼神。
我第一次賺錢也是和父親學(xué)的。那時(shí),他有空就去山上割荊條。春天,漫山遍野都是淡紫色的荊條花,小小的花瓣。我和弟弟看到好大一片,我們就守候著,還用鼻子湊上去聞聞?dòng)袥](méi)有香味。一到秋天,山上的荊條密密匝匝的,小荊條隱藏在大荊條中間,我們力氣小,只能割小點(diǎn)兒的荊條。
可是,太小的荊條別人不愿意買。回家后我央求父親,用他割的大荊條把我的小荊條包在里面,那樣好看,還可以多賣錢。父親用不耐煩的聲音兇了我,他說(shuō)有時(shí)間他去賣。可是小孩子總有一種虛榮心,我站在父親身邊哭,他看我哭得委屈,就起來(lái)幫我捆好,然后,我扛著去賣。需要走五六里路,那捆荊條有五六斤,我走一會(huì)兒就得歇一會(huì)兒,到那兒后,收荊條的叔叔直夸我。回來(lái)的路上,我邊跑邊跳,心里盤算著,要買本子和橡皮,還要買兩塊糖,剩下的自己攢著。
今年春天回老家,看到崖壁上盛開的荊條花,它們立于荊條之上,審視著我的來(lái)歷。紫色小花,覆蓋了曾經(jīng)生活的拮據(jù)。
五
我把墓門旁邊的雪往邊上掃了掃,給父親倒了點(diǎn)酒,父親生平喜歡喝酒。
母親說(shuō),她真的不想失去老屋,那是她和父親之間唯一的念想了,說(shuō)著說(shuō)著就開始哭。她還說(shuō),現(xiàn)在日子這么好,家里蓋了樓房,如果你父親活著多好。我不會(huì)大聲哭,只在那里默默地流淚。我又給父親倒了點(diǎn)酒,用手摸了摸菜是不是涼了。父親不能吃涼的,他的胃不好。
(吳曉娥,河北興隆詩(shī)上莊人。有作品散見于《詩(shī)刊》《承德日?qǐng)?bào)》。)
特約編輯:劉亞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