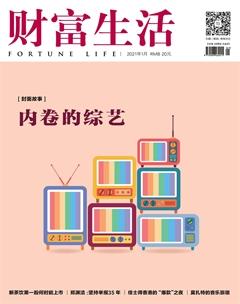閑談圍棋爛樵柯
游北君

《重屏會棋圖》卷,五代,周文矩繪。圖/故宮博物院網站

《荷亭對弈圖》頁,元。圖/故宮博物院網站
現代人說起才藝,總繞不開“琴棋書畫”四個字,可見圍棋在古代文化中占據著重要的地位,明代解縉有一首名為《觀弈棋》的詩,把大部分常見的圍棋別稱都嵌到了詩句里,讀起來別有趣味:“木野狐登玉楸枰,烏鷺黑白競輸贏。爛柯歲月刀兵見,方圓世界淚皆凝。河洛千條待整治,吳圖萬里需修容。何必手談國家事,忘憂坐隱到天明。”詩句中的木野狐、烏鷺、玉楸枰、爛柯、方圓、黑白、河洛、吳圖、手談、忘憂、坐隱都是圍棋的別號趣稱,之所以會有如此眾多的別號,這需要從圍棋的起源說開來。
圍棋在古代被稱為“弈”,相傳是帝堯或者帝舜發明的用來教化的游戲,當然這種傳說并不是太可信,但也能從側面反映出圍棋在我國起源之早。
《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中記述了衛獻公復國的一段歷史:衛獻公被孫文子驅逐逃到了齊國,而后孫文子和寧惠子共同擁立了衛殤公,寧喜(寧惠子之子)與孫文子產生了隔閡,衛獻公聽說之后派遣使者向寧喜許諾“茍返,政由寧氏”,寧喜同意了這個請求。大叔文子聽說之后表示:“今寧子視君不如弈棋,其何以免乎?弈者舉棋不定,不勝其耦,而況置君而弗定乎?必不免矣。”這段話的意思是寧喜在廢立這件事上的考慮不如下棋時周到,下棋時候舉棋不定都不能戰勝對手,更何況是廢立國君這樣的大事呢,這樣猶豫不決一定會大禍臨頭。而后寧喜殺掉了衛殤公,并迎接衛獻公復國,在第二年果如大叔文子所言,被衛獻公誅殺了。
這段文字的時代背景發生在公元前548到公元前547年的衛國,可以說是公認的關于圍棋最早的記載,大叔文子非常生動地用下圍棋來評論寧喜的所作所為,這說明圍棋在春秋戰國時期其規則已經發展得相對完善,甚至已經是當時貴族階層中普遍流行的一種游戲了。

木畫紫檀碁局。圖/日本正倉院
圍棋的棋盤,從春秋時期一直到近代,棋盤器具的縱橫數一直都在增加。最初的棋盤可能只有縱橫9道或者縱橫11道,但這種棋盤極大地限制了弈棋者們的發揮,因此從出土文物和文獻記載來看,從戰國時期開始17路棋盤就已經出現了,河北望都一號漢墓里出土過一件東漢時期的石棋盤,其形制就是縱橫各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藝經》),到了南北朝時期,縱橫19路的棋盤就已經出現,敦煌莫高窟中發現的《棋經》記載棋盤“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數”。北宋時期《忘憂清樂集》中也收錄了相傳是三國時期孫策和呂范的對局記錄,使用的也是19道棋盤,也就是說,自公元五世紀一直到現在,圍棋棋局的基本樣式幾乎沒有發生過變化,那么可以說自南北朝開始,圍棋的規則已經基本趨于完善了。
圍棋本身所蘊含的哲學,跟兩漢以來所尊崇的儒家思想格格不入,孔夫子嘲諷整天吃飽飯無所事事的人,認為哪怕是玩六博和圍棋都比毫無用心好(“飽食終日,無所用心,難矣哉。不有博弈者乎?為之尤賢乎己。”《論語·陽貨》)。孟子也認為:“博弈好飲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孟子·離婁下》)可以看出孔孟二人對于世人沉迷下棋的現象實際上都是頗有微詞的。而圍棋這種被儒家認為“以變詐為物,以劫殺為名”違背傳統儒家仁義思想的游戲,卻奇妙地在南北朝時期和道家結下了不解之緣。
圍棋之所以在南北朝時期得到了長足的發展,與當時社會氛圍崇尚談玄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而圍棋活動由于自身的特點,也受到了當時統治者和文人的喜愛,圍棋活動也逐漸成為清談活動的一部分,稱為“手談”,當時士人中還有“天下唯有文義棋書”的說法,將圍棋與詩詞歌賦、經義玄理以及書法相提并論,成為判斷一個文人是否能稱之為名士的標準。梁武帝還通過品定棋譜的方法來評定棋手優劣:“梁武帝好弈棋,使惲品定棋譜,登格者二百七十八人,第其優劣,為《棋品》三卷。惲為第二焉。”(《南史·柳惲傳》),甚至可以說,現在棋手評定所分成的九段,很可能最初的源頭就來自于此。

玉圍棋子,清。圖/故宮博物院網站
《世說新語》里記載了大量的關于圍棋的軼事,最著名的大約就是淝水之戰謝安的故事:“謝公與人圍棋,俄而謝玄淮上信至,看書竟,默然無言,徐向局。客問淮上利害,答曰:‘小兒輩大破賊。意色舉止,不異于常。謝安得驛書,知秦兵已敗,時方與客圍棋,攝書置床上,了無喜色,圍棋如故。客問之,徐答曰:‘小兒輩遂已破賊。”當時人們認為圍棋和兵法有著很大的關系,一個人在棋局上所顯示出的統觀全局胸有成竹和從容不迫的態度,被認為是作為成功的政治家和軍事家所必需的修養。
但謝安的經歷畢竟是當時少數的個例,魏晉之際由于政治風氣的高壓,廣大士大夫提出了崇尚老莊,“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思想風潮。有一大批為了逃避政治上的黑暗和迫害而隱逸山林的文人,圍棋在當時有“坐隱”和“忘憂”的名聲,和酣飲、清談等等活動一起成為了當時士大夫們逃避現實的放任之舉。以至于當時流行的神怪志異小說中,都不乏與圍棋有關的故事,其中最著名的,就是石室山觀棋爛柯的故事,其他的也多多少少都跟道家和神仙故事有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