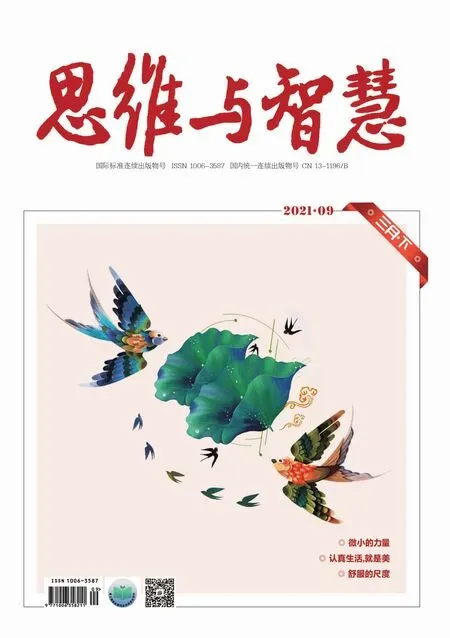蘆葦?shù)挠洃?/h1>
2021-03-23 03:11:40馬素欽
思維與智慧 2021年9期
● 馬素欽

我家珍藏著一張很大的蘆葦席,葦篾微微發(fā)黃、大小均勻,席花緊密、排列有序。每每夏天,我就拿它鋪在床上。燥熱的夏夜,躺在上面,渾身清爽。這席是我父親編織的,我們姊妹八個,一人一張。這張葦席,融入了我許多關于蘆葦?shù)挠洃洝?/p>
兒時的故鄉(xiāng)有綿延兩千多畝的蘆葦蕩,這里是孩子們的樂園。春天在蘆葦蕩里采摘野菜;夏天在蘆葦蕩里撿“水牛”,敲“氣肚蛤蟆”,捉“葦喳喳”;秋天剪蘆花;冬天吃葦芽。
那個年月,蘆葦是一個家庭里的主要經濟來源,它帶給孩子們無盡快樂的同時,帶給大人的卻是無窮無盡的辛勞。
春夏“薅葦子”。暮春,蘆葦已經長到兩米多高。蘆葦?shù)乩镉泻芏嘟g股藍,狗兒彎藤……這些藤蔓植物,順著葦稈往上爬,把附近的蘆葦緊緊纏繞在一起。如果不提前拔掉,它們會把蘆葦纏折,所以隔三岔五要去葦?shù)乩锇尾荩覀冞@里稱之為“薅葦子”。關于薅葦子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新媳婦,被公婆派到地里薅葦子,新媳婦到地里,看著一棵棵拇指粗的蘆葦,發(fā)起了愁,她用力地薅,手掌磨破,一棵也薅不下來,被難為得大哭起來……
秋天砍蘆葦。秋天里的第一次霜降,預示著該砍蘆葦了。四里八鄉(xiāng)砍蘆葦?shù)臅r間是統(tǒng)一的,提前一天各大隊部會下發(fā)通知。第二天,起五更,摸黑下葦?shù)兀瑹狒[極了!路上大車小車,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一家子都去,有的還提前通知了親戚。砍葦?shù)暮檬炙俣瓤欤畹娜敳绲停Φ奶J葦把子不容易散。成捆的蘆葦被運回家,然后靠到房檐下自然風干。人多力量大啊!兩千多畝的蘆葦蕩,一上午便蕩然無存。
冬天刨葦茬。刨的時候要躲開藏在泥土里的葦芽。每一個蘆葦芽,都是一個希望。葦茬上有時也會有葦芽,這種葦芽長大了也不成材,還影響其他蘆葦?shù)纳L,就成了我們口中的美味。
故鄉(xiāng)的大人沒有空閑的時候,地里沒有了農活,就開始在家里剝葦子、編葦席。我常常驚嘆于父親剝蘆葦?shù)乃俣龋J葦在父親的手里翻轉,葦葉唰唰落地。不論是擰還是揭,經他剝的蘆葦總是干干凈凈的。每次我剝葦子,總是很費力地把緊貼在葦子上的葦葉揭起、拽下,手指都被刺破了,葦節(jié)部分還會留下一部分葉子。我以為父親的手里有神器,曾數(shù)次翻開他的手掌,每次只能看到那厚厚的繭子。
父親的手很巧,他能用紅色高粱稈和金黃色的蘆葦稈編織成花色的席,席上四角編出大紅的喜字。農村的孩子結婚,喜床上,或舊或新,或買或借都要鋪上一張這樣的席。有錢的,會在喜床靠墻位置再釘一張大花席。我家老屋臥室里,有一張老式大床,靠床的墻上,釘著一張紅白相間的圈床席,席上“天下太平”四個字清晰依舊。這張席是父親親手編織的,是他和母親結婚時最奢侈的婚房裝飾。
因為父親手巧,左鄰右舍常常拿著葦篾到我家來編席,一是熱鬧,二是可以學些手藝。
編席的人先是蹲著,腳麻了就跪著,膝蓋疼了就坐在腳脖子上,實在太累了,就躺在自己尚未編好的席上伸伸腿。每次母親做好了飯,總是喊了又喊,父親的手指仍在葦篾間穿梭。我們常拿了饃坐在父親身旁,父親編幾下,抬頭咬一口。
編好的席子要帶出去賣。父親年輕時跟著爺爺挑著席去賣,為了在天明之前趕到賣席的地方,他們凌晨三四點就從家里出發(fā)了。細長的扁擔,一頭一捆席,扁擔壓彎了爺爺?shù)难V糁照鹊臓敔斕舨粍恿耍赣H就跟著鄉(xiāng)親,挑著家里的希望出門。
近幾年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種高檔涼席如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用葦席的越來越少,砍下來的蘆葦開始當柴燒。后來,蘆葦蕩被拖拉機統(tǒng)一耕掉,種上了莊稼。浩渺的蘆葦蕩,機器的轟鳴聲是它唯一的葬樂。
蘆葦蕩消失的那一年,父親為我們每人編了一張葦席,連同蘆葦?shù)挠洃浺徊⑺徒o了他的孩子們。
(郝巧鳳摘自《平頂山日報》2020年12月15日/圖 槿喑)
● 馬素欽

我家珍藏著一張很大的蘆葦席,葦篾微微發(fā)黃、大小均勻,席花緊密、排列有序。每每夏天,我就拿它鋪在床上。燥熱的夏夜,躺在上面,渾身清爽。這席是我父親編織的,我們姊妹八個,一人一張。這張葦席,融入了我許多關于蘆葦?shù)挠洃洝?/p>
兒時的故鄉(xiāng)有綿延兩千多畝的蘆葦蕩,這里是孩子們的樂園。春天在蘆葦蕩里采摘野菜;夏天在蘆葦蕩里撿“水牛”,敲“氣肚蛤蟆”,捉“葦喳喳”;秋天剪蘆花;冬天吃葦芽。
那個年月,蘆葦是一個家庭里的主要經濟來源,它帶給孩子們無盡快樂的同時,帶給大人的卻是無窮無盡的辛勞。
春夏“薅葦子”。暮春,蘆葦已經長到兩米多高。蘆葦?shù)乩镉泻芏嘟g股藍,狗兒彎藤……這些藤蔓植物,順著葦稈往上爬,把附近的蘆葦緊緊纏繞在一起。如果不提前拔掉,它們會把蘆葦纏折,所以隔三岔五要去葦?shù)乩锇尾荩覀冞@里稱之為“薅葦子”。關于薅葦子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新媳婦,被公婆派到地里薅葦子,新媳婦到地里,看著一棵棵拇指粗的蘆葦,發(fā)起了愁,她用力地薅,手掌磨破,一棵也薅不下來,被難為得大哭起來……
秋天砍蘆葦。秋天里的第一次霜降,預示著該砍蘆葦了。四里八鄉(xiāng)砍蘆葦?shù)臅r間是統(tǒng)一的,提前一天各大隊部會下發(fā)通知。第二天,起五更,摸黑下葦?shù)兀瑹狒[極了!路上大車小車,男男女女,老老小小,一家子都去,有的還提前通知了親戚。砍葦?shù)暮檬炙俣瓤欤畹娜敳绲停Φ奶J葦把子不容易散。成捆的蘆葦被運回家,然后靠到房檐下自然風干。人多力量大啊!兩千多畝的蘆葦蕩,一上午便蕩然無存。
冬天刨葦茬。刨的時候要躲開藏在泥土里的葦芽。每一個蘆葦芽,都是一個希望。葦茬上有時也會有葦芽,這種葦芽長大了也不成材,還影響其他蘆葦?shù)纳L,就成了我們口中的美味。
故鄉(xiāng)的大人沒有空閑的時候,地里沒有了農活,就開始在家里剝葦子、編葦席。我常常驚嘆于父親剝蘆葦?shù)乃俣龋J葦在父親的手里翻轉,葦葉唰唰落地。不論是擰還是揭,經他剝的蘆葦總是干干凈凈的。每次我剝葦子,總是很費力地把緊貼在葦子上的葦葉揭起、拽下,手指都被刺破了,葦節(jié)部分還會留下一部分葉子。我以為父親的手里有神器,曾數(shù)次翻開他的手掌,每次只能看到那厚厚的繭子。
父親的手很巧,他能用紅色高粱稈和金黃色的蘆葦稈編織成花色的席,席上四角編出大紅的喜字。農村的孩子結婚,喜床上,或舊或新,或買或借都要鋪上一張這樣的席。有錢的,會在喜床靠墻位置再釘一張大花席。我家老屋臥室里,有一張老式大床,靠床的墻上,釘著一張紅白相間的圈床席,席上“天下太平”四個字清晰依舊。這張席是父親親手編織的,是他和母親結婚時最奢侈的婚房裝飾。
因為父親手巧,左鄰右舍常常拿著葦篾到我家來編席,一是熱鬧,二是可以學些手藝。
編席的人先是蹲著,腳麻了就跪著,膝蓋疼了就坐在腳脖子上,實在太累了,就躺在自己尚未編好的席上伸伸腿。每次母親做好了飯,總是喊了又喊,父親的手指仍在葦篾間穿梭。我們常拿了饃坐在父親身旁,父親編幾下,抬頭咬一口。
編好的席子要帶出去賣。父親年輕時跟著爺爺挑著席去賣,為了在天明之前趕到賣席的地方,他們凌晨三四點就從家里出發(fā)了。細長的扁擔,一頭一捆席,扁擔壓彎了爺爺?shù)难V糁照鹊臓敔斕舨粍恿耍赣H就跟著鄉(xiāng)親,挑著家里的希望出門。
近幾年隨著人們生活水平的提高,各種高檔涼席如雨后春筍般出現(xiàn),用葦席的越來越少,砍下來的蘆葦開始當柴燒。后來,蘆葦蕩被拖拉機統(tǒng)一耕掉,種上了莊稼。浩渺的蘆葦蕩,機器的轟鳴聲是它唯一的葬樂。
蘆葦蕩消失的那一年,父親為我們每人編了一張葦席,連同蘆葦?shù)挠洃浺徊⑺徒o了他的孩子們。
(郝巧鳳摘自《平頂山日報》2020年12月15日/圖 槿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