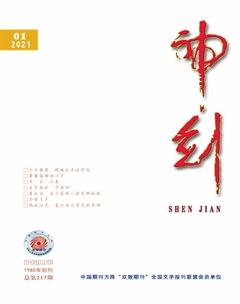無法清零的記憶(外一篇)
王秋燕
如果你問一個作家,是愿意寫報告文學還是愿意寫小說?你得到的回答幾乎不會有第二種:小說。因為小說可以讓作家去虛構,去想象,去天馬行空,去主宰你想寫的一切,但報告文學完全不同,它需要作家帶著“真實”這副鐐銬跳舞,就像畫家畫人物寫生,畫得越逼真越傳神,越像那個人,就越見畫家的功力。報告文學也是這樣,要把發生過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復原,不能憑空想象,更不能無中生有,它完全失去了寫小說的自由性。更要緊的是,你要花大量的時間去采訪,去收集原始素材,去面對一個又一個“陌生”的人物……所以,當上級要我去寫文昌發射場的報告文學時,第一感覺就是一個字:難。
文昌發射場,從立項到設計再到建設,光是工程指揮部的指揮長,就換過四任。有位負責技術工程設備的專家,他每天記工作“流水賬”,記了厚厚的十多本,摞在桌子上足有半人高,看一眼就讓人眼暈,更不要說,把它們全部消化完,濃縮成二十多萬字的書了。
有人勸我,人家都放棄了,你接手它干嗎?潛臺詞是,這么一個前后兩代人耗費十多年時間,動用千軍萬馬之力才完成的復雜又艱巨的工程,你用一支筆就能拿下嗎?意思是何必自討苦吃。這番好心人的提醒,讓我幾度萌生退意。
這時候,不知為啥,很多有關文昌發射場的相關細節,老在腦子里時隱時現,有時奔涌而來,有時悄無聲息,總之,讓你牽掛著,忘不了,又放不下。真正促使我下定決心,接受這個任務的,是兩件事:一個是2014年臺風“威馬遜”,把發射場掃蕩得慘不忍睹。有多慘,據說沒人能用文字描述,這對我無疑是個挑戰。第二件,是我聽人說起一個名字:周湘虎。這兩件事促使我拿起電話,打給了文昌發射場的指揮長張平,他一上來就聲調委婉但不留情面地向我開了一炮:你這個作家呀,老坐在家里,怎么可能寫得出真正接地氣的好東西來? 炮轟得我頓時斗志迸發。嘿,看來這活我還非干不可了。
這時,涌上我心頭的是一位同事的激勵:你去寫是最合適的,畢竟你和西昌衛星發射基地有很深的淵源。此話不假,我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工作了十四年,一直把西昌當成我的第二故鄉,而文昌航天發射場又隸屬西昌中心。為“娘家”做點事,你還糾結什么?再說,為航天人樹碑立傳,一直是你義不容辭的責任。這樣一想,心里真就被勇氣填充得滿滿,信心也足足的,它就是一塊再難啃的骨頭,你也必須去把它啃下來。當時的我,真有一股“風蕭蕭兮易水寒”“不破樓蘭終不還”的悲壯氣概。
就這樣,我登上了飛往文昌的飛機。
上了飛機后,看著舷窗外云海茫茫,心里卻又開始打鼓。因為我估算了一下,光是采訪的工作量,起碼小半年。可我手頭正在寫一部反映女兵生活的長篇小說,已經寫了十多萬字,如果不得不停下來去完成這個任務,那部長篇小說不知道要到猴年馬月才能完成了,因為寫過小說的人都明白,寫東西最怕中途停筆,一旦斷了氣,再撿回來就難了,事實也是,這部小說至今我都沒能完成它。此外,還讓我放心不下的是女兒當時懷孕在身,B超結果還是雙胞胎,這讓我怎么能放手遠行?女兒看我為難,故作輕松地對我說;放心去吧,我能對付得了。雖然我知道,我這個事事要強的女兒,打小就有很強的自理能力,但懷孕畢竟是女人的頭等大事,何況懷的還是雙胞胎,她一個人在家,即使有一個對她百般體貼的女婿在身邊,我作為母親終究還是會牽腸掛肚。
我就這樣揣著一肚子心思,來到海南文昌發射場。
這個發射場,跟西昌完全不同,沒有群山環抱,打眼望去,是無邊無際的碧海藍天和郁郁蔥蔥的椰子林。與西昌更不同的是,“三高”是這里的特色,不論你往哪里去,都會被高溫高濕高鹽所包裹,讓你躲都躲不開,在陽光下走幾步,全身透出一股咸濕的汗味,沒多久衣服上曬出斑斑鹽堿,那種感覺真像當地漁民說的那樣,這叫曬魚干。
在文昌發射場,所到之處,看見的都是創業者的艱辛和不易。特別是住房,天氣這么炎熱,四五個大小伙子,擠在十幾平方米民房改造的窄小空間,睡的是上下鋪。身子都轉不開,里面散發著一股汗臭味兒。若不是親眼所見,我是決不相信眼前這個事實的,你想,都什么年代,條件還這么艱苦,以當今國力,完全可以把他們的生活條件改善得好些。可為什么不呢?我帶著這個問題,向一位首長請教,他只淡淡地說了一句:創業哪有不艱苦的。當時,我覺得這話聽上去,是飽漢不知餓漢饑。但當我后來看到這些領導們也住在同樣的環境中時,我才對自己那一閃而過的念頭頓生羞愧。原來,建這個發射場,上面撥給的經費并不充裕,他們只好把每一分錢,都掰開揉碎,用在了發射場的主體建設上,而自己卻不得不把生活開銷壓到最低限度。即便這樣,有些項目在設計圖上還是砍了又砍。比如,大火箭矗立在發射架上時有個擋雨篷,因錢不夠,不得不舍棄。當臺風來襲,暴雨傾瀉時,只好讓人爬上塔架頂端去搭防雨布。類似這樣的事情,在這里還有很多。有位設計師,就因為自己的一項非常得意的設計被忍痛割愛而失聲痛哭。這種情況下,辦公設施和生活設施,當然就只能因陋就簡,能省則省了。
這后來,采訪的每一天,我都會被一些過去聞所未聞、從沒聽說的故事所打動,甚至感動得淚流不止。
我采訪的第一個人物,就是先進典型:周湘虎。心想,像他這樣的典型人物,早已被媒體打造得有了一口好口才,起碼讓我采訪不那么費勁。見了面后,我才明白自己多么自以為是。他竟然還是一個不懂得如何推銷自己的木訥之人,完全不像被各種媒體打磨過的角色。他帶著深度近視鏡,左眼已經永久失明,右眼裸視力為0.04,幾乎和盲人沒差別。你無法想象,當光明一點一點離他遠去的時候,這個人還能強忍病痛,一絲不茍地去完成他的監理工作,并且居然可以不出絲毫差錯。做到這一點,需要怎樣的堅強和毅力?我問他,在你視網膜脫落前,沒有一點征兆?他輕聲地說,有,眼睛脹痛,視力下降,以為是小毛病,想等著工程結束……后來,他是被強行送進醫院的。我想,只有把責任看得重于眼睛甚至生命的人,才會這么玩命!他為了國家崇高的事業,奉獻出人體最寶貴的器官:一雙看世界的眼睛。當他說到遺憾時,我的淚水再也止不住了。因為他并沒有說什么豪言壯語,而只是輕輕地說了一句:我再也看不清女兒長大的樣子了……
在這支發射場建設大軍中,這些人從未以英雄自居,而是有些自嘲地稱自己是“特殊民工”。說老實話,在我采訪的短短幾個月里,我發現他們的勞動強度比真正的民工還要大,而他們的生活境遇比民工還要苦。天天和鋼筋水泥打交道,哪天不是一身汗水一身泥漿?為了趕工期,他們幾乎每天出工比民工早,收工比民工晚,其中的艱苦程度,真的是難以用筆墨能描述的。兩個發射塔架一萬多噸鋼筋,三十個人去組裝;兩個導流槽七千噸鋼筋,七十個人去完成。許多人年紀輕輕,就因為這種超強負荷的工作,而過早地患上腰椎間盤突出了。有個戰士叫何睿,在五十多度的日照高溫下作業,突然眼前一黑,腳一滑,便從腳手架上跌落下去,系在他身上的保險帶沒能起作用,他的身體被一根鋼筋高高地舉在半空中,一條16毫米的螺旋鋼,從他的大腿根一直戳進他的肚子里,足有30厘米長,剛好頂在胃壁上。大家急忙把他送往海口醫院搶救。當他剛做完CT和B超,還沒清創傷口,見到他的領導楊曉明時,他的第一句話竟然是:楊總,對不起,我又給你們添亂了……把這個故事說給我聽時,身為總師的楊曉明,一個五十多歲的漢子,當著我的面哽咽了。他說:一個多懂事的孩子!這種時候,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的傷痛,而是替我們這些人著想……說到這里,楊曉明說不下去了。而我早已淚眼模糊,看不清楚這個鋼鐵漢子的面容。過了好一會兒,楊曉明又接著告訴我,他在當時所能做的,就是第一時間堵住小伙子的嘴,對他說:以后,你不要叫我楊總,叫我叔!你也不是給我們添亂,你是好樣的!以后不管你遇到什么,我都要管你一輩子!這時,那個被鋼筋戳進肚子里都沒有掉淚的小伙子,突然失聲痛哭起來。
這樣的故事,在以后的采訪中,我幾乎每天都會聽到。我第一次發現自己的眼窩是這么淺,它們總是存不住眼淚,讓我每天都控制不住地淚眼婆娑。
同樣讓我感動的,還有那些最先作出犧牲的農民兄弟們。整個發射場的建設,需要24個自然村搬遷,涉及1960戶,9000多人告別家鄉。你能想象祖祖輩輩生活在這塊肥沃土地上的人們,是怎樣在生息之地和國家大業間作出抉擇嗎?這種離棄家園的情感應該比割身上的肉還要痛吧?我采訪過所謂的“釘子戶”,說真的,這個說法并不準確,因為他們并不真“釘”,而只是在拆遷之際,流露出可以理解的故土難離之情。這種情感,有的人可能迅速就化解了,有的人則持續得久一些,甚至為這份情感與負責拆遷的人發生過些許沖突,但到了關鍵時刻,所有人都顯示出了以國家大局為重的情懷。有這樣一位中年婦女,丈夫病逝后,自己拖著三個年幼的孩子過日子,當她家七成新的房子被大型器械轟隆隆推倒時,她忽然跪倒在征地辦主任的面前不肯起來,讓在場的人大吃一驚,以為她要反悔,沒想到她只是提出一個十分卑微的請求,原來她擔心自己的兒子,搬離了這個地方后,會影響兒子的學習成績,而無法就讀本地的重點中學,這將影響孩子的前程,所以她希望政府能幫她解決這個問題。后來,她的兒子很爭氣,還是自己考上了……類似這樣善解人意又通情達理的故事,在采訪中我聽見了許多,可謂舉不勝舉。
在長五首飛的總結會上,有一位總部領導動情地說:我們真的要記住海南人民對我們航天事業作出的巨大貢獻,他們不計私利,不怕犧牲,舍小家為大家。假如有一天被我們遺忘,那就是我們的罪過。
現在,該來說一說臺風了。因為臺風也是文昌發射場的“常客”。為了感受一下臺風的威力,我特意選擇21號臺風“莎莉嘉”登陸海南島之前,又去了一趟文昌,親眼見證一線航天人戰臺風的壯舉。
與我想象的相反,臺風將臨的前一個夜晚,天氣晴好得讓人不可思議:大海上碧波萬頃,夜空中彩云飄飄,又圓又大的月亮套著一圈淡淡的光暈,像小姐姐臉頰抹了胭脂那樣好看,一點暴風驟雨將至的跡象都沒有。然而這只是一種溫柔的假象。睡到半夜,你會被突然而來的風聲所驚醒。側耳細聽,窗外仿佛有上萬頭公狼由遠而近地嘶聲低吼,這低吼漸漸變成數百萬臺摩托車在齊聲轟鳴。剎那間,天搖地動,狂風卷著暴雨死命拍打著所有的門窗,像一只只粗壯的手臂,要把每個房間里的人拽到屋外去抽打。那種恐怖,沒有親身經歷的人,很難想象。
接下來,整個發射場陷入一片昏暗。這個時候如果有人想摸索著出去,到戶外感受一下臺風的肆虐,肯定讓你站著出去,爬著回來,否則,狂風肯定會把你吹到找不著北的地方,也許一去無回。我也試著想推開門,看看外面的情況,好不容易擰開門鎖,還沒敢打開門縫,門外就像有一只巨掌,狂野又粗暴地想擠進來,嚇得我只能把門鎖彈了回去。這一下,我才明白,他們為什么給我送干糧、礦泉水、手電筒等一系列應急物資。另外,我終于明白為什么要把走道上的各扇門打開,并像防洪堤那樣壘上沙袋,把它們穩穩地固住。這也是為了讓臺風無遮無擋自由自在地抽風,不至于把整個大樓掀翻,把臺風的破壞力減至最低。我采訪時聽說很多細節,比如門打開后,屋子里的皮鞋像只大雁,倏地跟著臺風飛跑起來;汽車門一打開,就像墻上的紙一樣被撕扯下來,飄呀飄,在空中翻著跟斗……這些細節,你不來到臺風登陸現場,真的想象不出來。再說大暴雨吧。我看見過傾盆大雨,粗大的雨絲,連成一片,密不透風,將大地變成河流。大雨夠強勢了吧?可大雨在大風面前就弱小了許多,被風攆得直吐白沫,一會兒齊刷刷往東邊跑,一會兒又掉過頭往回撤,有時居然在風中扭來扭去,像條發瘋的巨蟒……再就是椰子林——我終于明白,椰子樹的樹葉為何要長得像梳子的模樣,原來它是用來和臺風斗智斗勇的,不然,它葉子上不長縫隙,不讓臺風從它密密的屏障鉆過去,不用幾下就可能被臺風連根拔起,何況它又長得這么高大茂盛。我住在六樓,每次看見大風把椰子樹一次次吹倒,幾乎整個伏倒地面上,又看見它頑強地站起來,感覺它身子還沒完全站直,又再次強行地被摁了下去……這個動作,來來回回不知要重復多少遍,看得人忍不住心驚肉跳。這場臺風過去之后,放眼一望,整個椰子林從綠色變成了褐色,仿佛被大火烤焦一樣。一見這顏色,就知它在這場臺風中,受到了多大的摧殘。當然,有些樹經不住這種折磨,早早四仰八叉躺在那里,場面十分慘烈。
大約刮了七個多小時之后,臺風自己也像是累過勁了,不那么張牙舞爪了。炊事班趕緊通知開飯。我把門鎖剛擰開,門一下撞開,感覺像一頭瘋牛沖了進來,讓我又驚出一身虛汗。沒想到,臺風的余威還這么足,以至于出了門,還讓我膽戰心驚,要不緊緊抓住欄桿,要不就是緊貼墻邊,防止狂風將我一把抓起,像抓小雞樣扔到樓下去。好不容易走到電梯口,發現門開著,但堵著沙袋:電梯停用了。我只能從樓梯下去,真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到一樓的,總之那個狼狽相,但愿沒有人看見。
更令人興奮的是,在文昌發射場,我跟蹤了長征五號首次發射的全過程。文昌發射場就是因它而建的,正好讓我多了一條線索:發射場的建設和“長五”首次發射,成了兩條平行線,過去時和正在發射時可以在這本書里齊頭并進。
經過這一段時間的采訪,我感覺眼前不斷有靈光閃爍。我知道,那是細節,是故事,是人物生動的語言,是每個人特有的個性;也許還是一株鮮活的植物,一根飄動的雨絲,一陣怒吼的狂風,抑或是一片涌動的海浪和一堆火紅的晚霞。總之,我內心完全接受去寫文昌發射場這個事實,并全身心地投入其中。也就是說,采訪這段時間,我的內心發生了變化,從被動走向了主動,心里那些硬生生的小結子,也一個個打開,一個個軟化,創作的信心也越來越足了。
尤其讓我無法忘懷的是“長五”首發的那天,發射程序因故障幾次暫停。為何暫停?每一次暫停,都讓你牽腸掛肚。特別是發射前的一分鐘,連環發生故障又被逆轉回來,那種緊張感,簡直無法用文字表述,我只感覺自己的呼吸一次次窒息,心一次次提到嗓子眼,神經一次次被拉抻得近乎要崩斷……這就是航天人,在每一次發射中,都必然要經歷的考驗。因為意外,總是會在你意想不到的節點和時刻發生,但又被沉著急智的航天人一次次排除,化險為夷。當我終于長松一口氣,看著大火箭呼嘯著從發射塔上冉冉升空時,我總是含著熱淚又一次體味到作為中國航天人的獨特自豪感。也就是在這種時候,能夠既成為他們中的一員,又用自己的筆記錄下中國航天人的輝煌行跡,難道不是一個寫作者的幸運和光榮嗎?!如今回身望去,在文昌發射場所見證的一切,都已隨著時間漸漸遠去,但所有那些閃光的人和事,都將成為我此生無法清零的記憶。
三天長于半生
三十多年前,第一次讀到艾特瑪托夫的長篇小說《一日長于百年》,就被他的書名深深吸引。一日長于百年是什么感覺,我沒體會,因為我的人生沒有那么漫長。但是,我的經歷中有三天時間,長于半生,卻是親身體會過的。
20世紀90年代前半期,是中國航天人郁悶憋氣的歲月。那時,離我們發射第一顆北斗衛星,還要等N年時間;離59星組網,還要有整整四分之一個世紀。
現在,那段記憶還沒在我們的記憶中淡漠,世界已然發生驚天巨變。北斗組網的最后一顆星,在讓人牽掛了多日之后,終于成功上天。作為伴隨了中國航天幾十年歷程的老兵,我的欣喜,比喜大普奔的國人,還要多一分。那就是,我終于吐出了憋在心頭26年的一口悶氣。
26年前,除了高懸的北斗七星,我們的“北斗”還沒掛上天。“北斗一號”計劃剛剛啟動。那時候,太空中屬于中國人的衛星,不超過10顆。通信衛星都還處在試驗階段,從轉播體育比賽,到艦船遠航通信,都需要租用他國的衛星。那真是一段讓中國既無奈又屈辱的日子。我親身經歷的這件事,就發生在這段時間。
1994年2月,我隨“遠望號”測量船去南太平洋預定海域執行衛星發射海測任務。一路上,如何的戰風斗浪,我有專門的文章另外記述。現在能想起來的就是暈船,暈得七葷八素,躺在船艙里一動也不能動,直到船過赤道,聽到艙外的歡呼聲,我才掙扎著爬起來。推開艙門一看,整個太平洋波平浪靜,我們的船,像一把劃玻璃刀,在鏡面似的太平洋上,留下一道白色的劃痕:預定海域——南太平洋到了。
再有四天,就是T0時間,也就是發射時刻。
當時的感覺,真是萬事俱備只欠東風。但就在這個時候,一件預料之外的事情發生了。
我記得非常清楚,那天的中午,船上的廣播突然響起來,先是呼叫相關人員去指揮所開會。最后又通知,下午四點鐘的全航區合練取消。
什么情況?
直覺告訴我,肯定有什么大事發生了。因為,全航區合練是從發射場首區,到海上末區,進行一次模擬發射演練,也是發射前最后一次對所有設備性能和全體工作人員備戰狀態的全方位檢測。這么重要的合練怎么能輕易取消?我的直覺是發射場那邊可能出了什么問題,心一下抽緊。從1992年澳星發射失利后,我就落下一塊心病,一旦臨近發射,任何突發的意外,都會讓我有一陣突然而至的心律失常,然后是一種近乎虛脫的感覺。
就在我為發射場那邊暗暗祈禱時,正式的消息來了,比我的感覺還要糟糕,原來是我們這邊遇到了大麻煩:船上的通信信號中斷了!
通信兵出身的我,哪能掂量不出“中斷”的分量。當年我頭戴耳機坐在機臺上值班,但凡遇見通信線路中斷,必須第一時間通知維修人員,讓他們火速去搶修,用最快的速度保障線路暢通。這海上的情況,跟陸地大不一樣,誰來保障船上的通信暢通無阻?
比中斷更可怕的是,故障的原因還沒查明。
記得那天下午我真是昏了頭,感覺太陽怪怪的,一會兒斜在船的右舷,一會兒又跑到船的左舷。后來才聽說,為了查明故障原因,遠望號顛顛地跑起來,一圈一圈地在大洋上畫圓。就是在這種跑動中,檢測所有的通信設備。
原來,通信設備沒問題,問題出在了“天上”。
為我們提供通信保障的外國衛星,信號沒有了。
我在西昌衛星發射中心工作了14年,非常熟悉331工程——也就是地球同步通信試驗衛星。331工程準備了三顆星,第一顆星發射是在1983年,因第二次點火失敗,未能到達預定軌道;1984年4月8日再次點火,發射成功!這兩次我都在發射場的附近半山腰上觀看點火,直線距離可能不超300米,火箭呼叫著轟隆隆起飛,感覺就像看別人放鞭炮一樣,沒有一點危險意識。有危險意識是在1992年澳星發射失利之后,那個半山腰上,再也沒人敢去了,也不允許去了。那時候,發射一顆衛星,至少準備一兩年,不像現在這樣“高密度”,十天半個月,一顆或(一箭)幾顆衛星就上天了。航天技術的飛速前進,從發射的速度便可見一斑。可我跟隨遠望號出海時,中國航天發展還處在起步階段,在天上,屬于我們自己的通信衛星,還覆蓋不到南太平洋。船上的正常通信,還要花大錢租用別國的通信衛星。當然,那時候的“北斗”,對大多數人來說,聽都沒聽說過,聽說過的,也只是個遙遠的夢。
眼下,要解決“天上”的問題,只有一個辦法:申請調換衛星。
遠望號用最原始的手段,向上級發出緊急電報。
可臨時調換或是租用別人的衛星,談何容易。
接下來,便是漫長的等待。
走道上聽不見腳步聲,也聽不見說話聲,好像大家都悶在船艙里,屏息等待。消息什么時候會來?這種時候,最好不問,因為沒人能回答你。那一整天,所有人和我一樣,一臉茫然又手足無措。
第一天,雖然心里慌慌,但還不是太煎熬,因為每個人都把希望寄托在明天。
明天,應該會有好消息。
頭一天晚上,有位室友提議明早一早起來去看日出。出海近二十天,還沒看過太陽咬開太平洋跳出海面的樣子呢!那是一種什么情形,一定轟轟烈烈!她是一家晚報資深記者,短發,聲調不急不緩,笑起來甜甜的,散發著小姐姐的魅力。看日出?行嗎?我勸她不要冒這個“險”。為什么?因為那時候,女人幾乎不能隨船出海。民間有句俗話:女人出海船要翻。這不,還真讓人說著了,這次出海,真就不順利。最先,剛到了舟山錨地時,首區發射場那邊出了故障,要我們在錨地待命。待命期間,船上在進行救生演習時,有位年輕的船員,因不小心,衣袖被纜繩卷了進去,手指受了傷,白花花的骨頭都露了出來。真是出師不利。當時,我們幾個女性,看到這場景,連魂兒都快嚇掉了,趕緊躲進艙室里,大氣不敢出,生怕那句魔咒式的俗話,是因我們而應驗的。
待命結束后,遠望號終于啟程,向預定海域出發。船才駛出公海,都沒來得及領略什么叫海闊天空,便聽見有人提醒說,趕緊早點休息吧。抬頭看天,天還是亮的,只是遠方的天像被誰砸了一拳,烏黑了一大片。后來才知道,它在醞釀一場臺風。遠望號努力想避開它,但繞了個大彎,還是沒能躲開它的尾巴!臺風的恐怖,我算徹底領教了。即使它的尾巴,也像虎豹一樣有力又兇猛,足以掃倒高于海平面的一切物體,連遠望號這樣的萬噸巨輪,在它的橫掃下,也一直來回搖擺。
出海經驗為零的我們,當時哪里聽得懂他的話,睡到半夜才被驚醒。至今,我仍是不想回憶那個可怕夜晚。這個記憶有多可怕?它讓我在整整四年的時間里,一想起這個夜晚,就一個字都寫不出來,因為一想那一晚的經歷,后腦勺就有一根筋會脹痛,它一痛,就會把全身的神經抽緊成一團,把你拋回那個驚魂之夜,使你只能像當時那樣緊閉雙眼,沒有勇氣想一個字眼,來形容它,描述它。十幾年后,有人再邀請我隨船出海,說是還可停靠外港,對于從沒出過國的我來說,這一點就足以讓我心動了,但一想到暈船的經歷,我馬上打退堂鼓。因為我再也不想重溫那種記憶。
據說,那個晚上,有一半多的人沒能頂住,全放倒了。原因都一樣:暈船。大海是公平的,它的慷慨與暴烈也是公平的。暈船更是公平。不會因為你是女人就對你格外憐憫,也不會因為你是什么特殊人物而對你網開一面。聽說凡是哺乳動物都會暈船,連老鼠也不會放過。
事后,我常常想,究竟是船只出海,遭遇臺風是常事,還是我們這幾個女人上了船才帶來的霉運?這個問題,把我這個無神論者困擾了很久。盡管我明知道這是迷信,但船上無論哪位男性投來哪怕極友好的目光,都會讓你感到一種心照不宣的壓力,好像這一系列事情都跟我們有關。一種很強的負罪感壓得人抬不起頭。因此,我希望室友們不要亂跑,待在狹小空間里靜候消息。
當我們熱切期盼的明天變成今天又變成昨天,好消息始終沒有如期而至。
等待,就像一根鐵絲,越拉越長,越拉越細,不知什么時候會“咯嘣”一下拉斷。
其實,比我們更難挨的,應該是肩上挑著擔子的人們。他們中有人嘴唇撩起了一層水泡,有人幾年不犯的胃炎復發了,尤其是船長臉上那抹彌勒佛般的笑容不見了,好像一下蒼老了十歲……他們在等待中受到怎樣的煎熬和焦慮,是我們這些不用擔當什么責任的外人體會不到的。
第二天終于在希望和失望的交替中熬過去了。
第三天才是最難過的。人,在海上關閉導航和通信設備,與外界完全切斷聯系,哪怕只有三天,就足以達到人所承受的極限。真不敢回想,當時真的只有三天嗎?我的感覺比我當時全部的人生還要漫長。
這之前,我也思考過人生,以及生死問題。確切地說,剛剛從人生的低谷中掙扎出來,重生的喜悅正如花盛開,怎么又倒逼回去了?恐懼是有傳染性的。那位記者小姐姐,她的膽子居然比我還小。她是第一次登船出海。這三天里,她差不多每天都瞪著一雙大眼,反復問我同樣的問題:船上抽煙的人,會不會把火柴棍掉下去,把底下的油箱點著?這次如果我們回不去了怎么辦?如果回不去,我們是不是應該寫一份遺囑?遺囑怎么寫?她的聲音一直在我耳邊叨叨個沒完。我終于不耐煩了,對她說,如果這次真回不去,就是被你這些不吉利的話念叨壞的。她的眼睛瞪得更大了,張著嘴,好半天才囁嚅著說了一句:你別嚇我,我膽子小。
我看她一下子臉色慘白沒了血色,就又趕緊安慰她:我騙你呢。但不管怎么安慰,她的臉色很久都沒紅過來。
第三天的感覺,明顯比前兩天加在一起還長。在陸地上,24小時一眨眼就過去了。別說三天,就是三年,也是倏忽間的事。可這會兒怎么會這么長?難道這就是愛因斯坦的相對論嗎?盡管臺風后的大洋,一望無際,海風親和,海平面像被一只柔軟的小手抹得絲光水滑,與藍得像鳶尾花一樣的天空海天相映,應該讓人迷醉才是。可這一切現在在你眼里,完全沒有任何詩意,甚至視若無睹。因為此刻的你,像關在一個完全密封的黑罐子里,見不著光,聽不到聲音,完全與世隔絕。這就是失去了導航、失去了通信,失去了與陸地的一切聯絡后給你的真實感受。
記得在第三天,還發生了一件令人尷尬的事。現在回想起來,記憶仍是模糊的,我是說當時自己都不知是怎么跑進駕駛艙的。我上船有半月之久,狀態一直不是太佳,先在舟山錨地得了重感冒,差點下船返回陸地;后又暈船暈得死去活來,耗去一星期時間。剩下的,也就沒幾天好日子可以回憶了。我到駕駛艙,是自己上來的嗎?我想走遍船上的每個角落,是一直都有的想法。跟船出海,不就是體驗生活嗎?你連駕駛艙都沒去過,怎么叫體驗?當然要上去看看,不僅要看,還要和人家聊上兩句。那會兒,完全忘記自己是誰了。剛跟舵手聊了沒兩句,突然,有個威嚴的聲音在我身后響起:你怎么能站這里,趕緊下去!這聲音,雖不嚴厲,但很嚴肅。船上的人,對這個聲音都很敬畏,因為他是這船上最老的船長,也是這次任務的指揮長。他的話,像在我臉上熱辣辣地扇了一巴掌,但我不知道自己當時是如何做到的,明明心里嚇得要死,卻裝作毫不慌張,淡定離開。出來后,站在甲板上看著傍晚的光線,和艷麗的晚霞纏綿在一起,很久很久。而我一直在問自己:你做錯了什么?
那天晚霞燃燒的時間似乎很長。夜幕,也像忘記了自己的職責,久久不肯落下。使本來準備在甲板上放映電影的時間,一再延遲。
為了打發凝固不動的時間,宣傳部門組織大家在甲板上看電影。我也拿把椅子,坐在人群的邊角上,準備讓銀幕把不安的思緒帶走,好讓擰成紙團一樣的心,松散開來,喘一口氣。我實在是太緊張了。看電影的人們都一聲不響,我也一樣。電影開始了,片名跳出來時,有人輕“哦”一聲,似乎被片名驚到了。直到現在,電影內容我一點沒記住,倒是《血濺天涯》這四個字沒有忘記。大概也是因為這四個字,和我們當時的心境有某種相似之處吧。我們千里迢迢趕到這里,和祖國失去聯系,變成真正的游子,遠離家鄉千萬里,不是也有人在天涯之感嗎?想到這,我眼睛突然潮濕,又怕哭出聲,趕緊悄悄離開人群,一人倚在船欄上。
舉頭望星空。真是滿天的繁星啊。星星們就在頭頂上一眨一眨地搖晃著,毛茸茸肥嘟嘟的,可愛極了,真想伸手摘一顆下來。可定睛一瞅,怎么感覺星空這么陌生,全然一副不認識的樣子,我熟悉的北斗七星在哪里?原來,月亮還是那個月亮,星星已不是那顆星星。南半球的星星,也在用它的陌生,提醒你是遠離故土的游子……在這一霎間,我終于繃不住,眼淚嘩嘩地流下來,披蓋了一臉。暈船暈得死去活來,我沒哭,卻在這一刻忍不住了……
人在無依無靠,失去航向的時候,很容易脆弱,甚至是絕望。
不知又過了多久,那個嚴肅的聲音又響了起來,老船長站在離我一丈遠的地方,問:害怕了?
我說:沒……沒有。
放心吧,都會好起來的。他寬慰人的時候,倒挺和藹。
我大起膽子問:沒有通信,我們的任務怎么完成?要是完不成任務,我們還有臉回去嗎?這是我心里最最擔心的。當然,后面這句話,我沒說出來。
他哈哈笑了,說放心,任務一定能完成的。因為我們的背后有堅強的靠山。
靠山?我下意識地朝他身后空曠的海面望去,好像要去找什么靠山。三天了,每天發出的求助電報,都沒有回應,我們現在就像一群沒娘的孩子,誰是我們的靠山?昨天、前天熬過去了,今天也快熬過去了,明天要來了,可明天就有希望嗎?我真想把積攢在心里無名的火氣發泄出去,可我能嗎?面對一位長者,我敬重的人。我忍著,硬把它憋回肚子里。這時候,海面波光蕩漾,像無數的金子在發光,又像星星們從天上跳下來,在水里無憂無慮地嬉戲。太平洋的夜晚,美麗又靜好,只是我沒有心情享受這份靜美。我倒希望,太平洋再來一次驚濤駭浪,讓船再度搖擺,把煎熬、焦慮和不安統統晃出去,不再折磨人,然后,暈暈乎乎期待好消息來敲門。
好像看出了我的心思,老船長還告訴說,租用別人的衛星,需要多方協調,沒那么快的。不過,也應該快有消息了。他說完這些話,電影散場了,甲板上零零散散剩下幾個像我一樣睡不著覺的人,氣氛仍是沉悶的,窒息的。他沒再說什么,而是轉身離去了。他可能是船上最年長的人員了,嘴唇上撩起一層水泡說的就是他。看見他微駝的背影,盡管顯得有些蒼老,但步子卻邁得堅定而自信。
這背影,讓我突然在心里崩出一粒火星,把心里的燈倏地點亮。人,在看不到光亮時,不應該熄滅心中的那一盞燈,世界可以黑暗,你的心不能黑暗啊……像老船長那樣振作起來,從容自信,相信身后的堅強靠山:祖國!
后來,當我可以平靜地回想這段往事時,我忽然從中悟出了某種人生的道理:人是社會動物,所以他需要與其他人溝通和聯絡,也需要有人給你指點迷津。這也意味著,我們每個人,都離不開導航與通信這些人際交流工具,一旦失去,就會讓你陷入深深的孤寂。由此,我又想到,人生不也如此,一個人的信仰,就是你自己的導航系統與別人溝通的工具,一旦失去了這些,你就會因孤身一人而失去信念,進而失去堅守下去的信心。這也反過來告訴我,任何時候,都不要失去人生的導航設備和人際聯絡工具,不要讓自己變成一個孤立又封閉的人,要善于與人溝通,更要堅守自己的信仰,因為有了信仰,你才會有信念和信心,你才能到達彼岸。當然,這些馬后炮式的感悟,全是二十年后的事,而在當時,我已深陷在那三天似乎一生都走不出來的困境里。
老船長說得真準,一大早,傳來喜訊:上海人民作出犧牲,把國外體育賽事直播取消,把頻道讓給了遠望號。不加倍努力工作,把這次長征三號運載火箭首飛試驗的海測任務完成好,是當時全船人的共同信念。那次遠望人不負眾望,任務完成得非常圓滿。
因為圓滿,所有的折騰好像都是值得的。但它終將凝固成一段歷史。
歷史不可以復制,但可以回味。
現在,天上布滿屬于中國的“北斗星”。你從每一顆星,都可以感受到祖國在漸漸強大,也可以好好享受她給我們帶來的便利。真好!而那次不平凡的海上經歷,盡管只有三天,但在我有限的人生記憶中,卻長過了我的大半生,因為這三天,我把前半生沒想透的事情都想透了,它也成了我人生彌足珍貴的財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