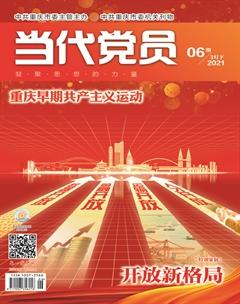巨波狂瀾下的重慶留法勤工儉學運動
黎余
尋路
五四運動前后,一大批胸懷救國夢的中國青年遠渡重洋到法國“勤于做工、儉以求學”,史稱“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四川是留法勤工儉學運動赴法人數最多的省份,重慶則是四川開展留法勤工儉學運動最活躍的地區之一。據統計,四川參加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人數達511人,而重慶僅巴縣和江津兩地就有93人。重慶輸送了以鄧小平、聶榮臻等為代表的一大批杰出人才,同時以趙世炎為代表的渝籍青年也從全國各地匯入留法勤工儉學大軍的洪流中。他們當中的許多人在法國一邊做工,一邊學習新知識、新思想,并從這里起步,走上革命道路,開始了振興中華的偉大歷程。
五四時期,相對落后和閉塞的重慶地區,為何能興起如此大規模的留法勤工儉學運動呢?
一個重要而特殊的原因,得益于吳玉章的積極推動。吳玉章是全國留法勤工儉學運動的主要發起人之一,1917年2月,他回到家鄉四川發起組織留法勤工儉學四川分會,還親自發電報或寫信給上海華法教育會,聯系四川勤工儉學出國事宜,盡可能動員一切力量推動運動的開展。在吳玉章的積極奔走下,四川當政者和各界名流給予了積極支持。
另一個重要的原因是,面對四川軍閥年年混戰,廣大人民陷于水深火熱之中,受到新文化運動和五四運動洗禮的重慶先進青年有了新的覺醒,他們選擇到缺少勞動力的法國做工,走勤工儉學的道路,從而尋求國家、民族和個人的前途。對此,聶榮臻在回憶自己勤工儉學的動機時曾說:“所有這些發生在我中學時期的兵連禍結的事情,都使我感到苦惱……出路何在?我當時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出國去學點本事,回來辦好工業,使國家富強起來,也許能改變這種局面。軍閥混戰造成國家貧窮落后,更增強了我對‘工業救國論的信念。這是我決心去法國勤工儉學的另一方面的原因,也可以說是最重要的原因。”
赴法
1919年8月28日,為培養救國人才,振興地方實業,重慶總商會會長汪云松、巴縣教育局局長溫少鶴等人發起成立了留法勤工儉學會重慶分會。重慶留法勤工儉學會成立后,便積極籌備重慶留法預備學校。9月中旬,位于夫子池的重慶留法預備學校正式開學,汪云松出任董事長。
重慶留法預備學校招收中學畢業生和具有同等文化程度的青年,他們主要來自重慶所轄各縣,亦有少數川北、川南、川西的學生。如來自廣安的鄧希賢(鄧小平),年僅15歲。他的同學,來自江津的江克明回憶說:“他那時就是顯得非常精神,總是精力十分充沛,他的話不多,學習總是非常刻苦認真。”
重慶留法預備學校共有學生110人,其中計劃招收公費生60名。學校學制為一年,校內既無宿舍,也無體育活動場所,食宿由學生自行解決,學習條件十分艱苦。學校開設法語、中文、數學、工業知識四門課程,目的是使學生掌握一定的工業基礎知識和法語知識。因文化程度不一,學生被分成初級班和高級班,分別授課。在準備赴法的過程中,學生們在刻苦學習的同時,還積極參加重慶學生抵制日貨的斗爭。愛國斗爭的實踐,激發了他們的愛國主義熱情,使他們尋求真理的信念更加堅定。
重慶留法預備學校的創辦,為重慶地區的有志青年赴法勤工儉學提供了條件。但由于學校經費和規模所限,不少青年只得在學校的幫助下選擇自費留法的途徑。
1920年7月,重慶留法預備學校首批學生畢業,經過考試和體檢,共有83名學生獲準赴法。其中,冉鈞、代坤忠、謝陳常、鄧紹圣和鄧希賢、周貢植、胡大智等人分別獲得貸費生和自費生資格。在法國駐中國公使館向法國外交部提交的注明重慶留法勤工儉學生抵法后選擇工種的名單中,“鄧希賢”一欄中注明的工種是鑄鐵。8月27日,鄧希賢等84名學生從重慶太平門登上法商“吉慶”號客輪,告別山城順江東下,經上海踏上了留法勤工儉學的征途。
當時,赴法勤工儉學的還有一批在外地求學的重慶青年學生,譬如酉陽的趙世炎、巴縣的周欽岳等人。值得一提的是,在留法勤工儉學的潮流中,張雅南、潘惠春、朱一恂等不少接受新思潮影響、追求婦女解放的重慶女學生,沖破封建倫理束縛,遠渡重洋,成為重慶女性留法勤工儉學的先行者。
錘煉
1919年春至1920年秋,法國正處于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后的經濟恢復期,勤工儉學生赴法,正是工廠需要大量勞動力的時候。學生們到法后,經華法教育會聯系,他們很快被分到工廠工作和進學校補習。來自四川的不少人進入鋼鐵廠、汽車廠、化工廠、煤礦、農場等地做散工、雜工,大多干的是體力活或很臟的粗活,做技術工的人很少。如在四川學生比較集中的克魯梭工廠里,趙世炎、鄧小平、周欽岳等100多人相繼在此工作,多數在高溫下進行重體力勞動。
他們的住地離工廠較遠,要坐火車上下班,凌晨3點左右就得起床,遲到了進不了工廠,次數多了就有被開除的危險。由于極度疲勞,不少人下班后在火車車廂就睡著了。
他們的生活極其艱苦,住的是木板工棚,睡的是雙層床,幾個人共用一個汽油爐,飯大家做,大家吃,吃得極省。周欽岳回憶說:“我們既是雜工、臨時工,工資可以說是最低,大致每日10法郎左右…… 每人每日工資所入,除了全部必須費用外,所余無多了。”盡管如此,趙世炎等許多人仍堅持每天學習,有的進補習學校,有的自學,有的參加法國工人或華工活動。
但好景不長。1921年初,正是留法勤工儉學生大量來法的時候,法國卻陷入了經濟危機:大批工廠倒閉,工人失業,貨幣貶值,生活費暴漲幾十倍。當時,不僅新來者找不到工作,就連已經在法國做工的陳毅等人也被工廠遣散。而中國赴法學生仍不斷抵法,大批學生無工可做,更談不上進校讀書。無工無錢的學生只得去華僑協社,過著每天領5法郎維持費的艱苦生活,狀況十分凄慘。
艱苦的工作及失工、失學的磨煉,使中國學生看到了法國社會的真實情況,感受到了資本主義的不合理,在一定程度上認識到資本主義的殘酷和虛偽。陳毅當時就寫道:“法國的工廠生活,是寄在資本制度的下面,不容工學者有發展余地,嘗(常)感著一種迫我同化的壓力……資本家完全為自己的利益起見,實毫無人性,我才知歐洲資本界是罪惡的淵藪。”
面對困境,作為組織者和發起者的華法教育會和駐法公使館,非但不采取措施,反而推卸責任,采取拖延態度,甚至要取消勤工儉學生賴以生存的維持費。因此,廣大學生不得不向中、法當局就生存權、求學權展開大規模的斗爭,主要是1921年間的“二二八運動”、“拒款運動”和進占里昂中法大學的斗爭。進占里昂中法大學的斗爭發生后,法國當局以“過激黨”和“宣傳共產主義”的罪名強行囚禁了蔡和森、趙世炎等勤工儉學生,并于10月13日將蔡和森等104人強制遣返回國,其中包括陳毅、周欽岳等34名四川(含重慶)學生。趙世炎則在聶榮臻等人的幫助下,從監獄逃脫而幸免。
擇路
三大運動斗爭失敗的經驗教訓促使留法勤工儉學生群體中的先進分子意識到,無論是勤工還是儉學都難以達到改造社會的目的。此后,在勤工儉學生中接受馬克思主義,要求進行社會革命來改造中國的人越來越多。其中,趙世炎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
趙世炎通過在法國實際工作的磨煉,感到自己以前對社會改造問題的看法空想太多。他給“少年學會”的朋友寫信說:“盼望我們朋友務要從冷靜處窺探人生,于千辛萬苦中殺出一條血路。”他和李立三等人組織了華工組合書記部和“勞動學會”,辦起《華工周報》,開展華工教育,并從中選擇、培育革命積極分子。
1921年,趙世炎接到陳獨秀的來信。之后,他與周恩來、張申府、劉清揚(不久又增加了陳公培)組成巴黎共產主義小組(中共成立前的八個共產主義小組之一)。趙世炎利用工余時間捧讀《資本論》和法共中央出版的《人道報》,向勤工儉學生宣傳馬克思主義,并立志:“我認定的主義一定是不變了,并且很堅決地為它宣傳奔走。”傅鐘等人回憶說:“如果沒有世炎同志經常向大家講解,我們對馬克思主義還不可能懂得那么快。”
1922年四五月間,趙世炎為了籌組青年團,奔走各地,積極聯絡各方面的優秀人才。
6月3日至5日,趙世炎、周恩來、王若飛、李維漢、劉伯堅等18人在巴黎西部布倫森的露天咖啡館召開旅歐中國少年共產黨第一次代表大會,選舉趙世炎為書記,周恩來任宣傳委員,李維漢任組織委員。為加強對黨員、團員的馬克思主義教育,“少共”創辦了由趙世炎負責編輯的油印月刊《少年》(后改為《赤光》)。后來,鄧小平成為《赤光》編輯部的一員,主要負責刻寫和印刷,他以出色的工作和才干贏得周恩來等人的信任和好評,獲得了“油印博士”的美譽。
1922年秋,中共旅歐總支部成立,趙世炎被選為總支部委員和中共法國組書記。1923年2月17日至20日,旅歐少年共產黨在巴黎召開臨時代表大會,趙世炎主持討論改組問題。會議決定按照中共中央的要求,將“旅歐少年共產黨”改名為“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并要求入團的團員必須“對于共產主義已有信仰”,明確“中國社會主義青年團中央執行委員會為本團上級機關”。會議選舉周恩來為書記。
旅歐黨團組織的建立,使得一大批追求新思想、謀求改造中國的留法勤工儉學生先后加入中國共產黨和青年團。在四川留法勤工儉學生中,有106人加入了旅歐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聶榮臻回憶說:“這一段的生活,在我的頭腦里的烙印很深,因為這在我一生經歷中,是完成世界觀的根本轉變,真正走上革命道路的起步時期。革命的起點是永遠難忘的。”
在國家危難、民族命運堪慮的時刻,重慶留法勤工儉學生中的絕大多數人和全國其他省份的留學生一道,把個人理想與國家前途凝結在一起,為尋求強國富民的真理之路,披荊斬棘,篳路藍縷。他們學成歸國后,或投身革命,或以自己的專長為振興中華而不懈奮斗,譜寫出中國近代革命史、教育史和留學史上的光輝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