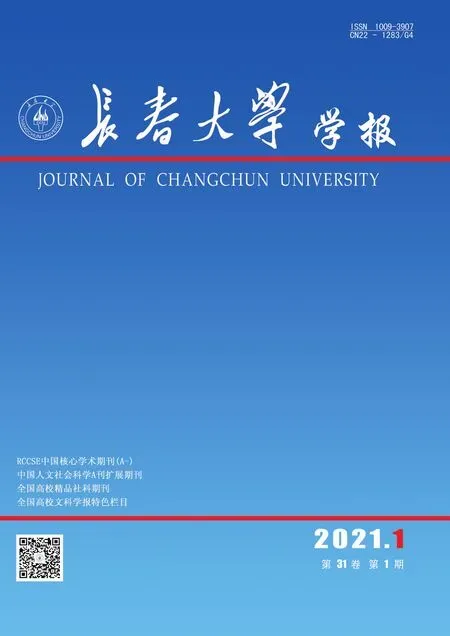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實質與時空方位
王 建
(合肥工業大學 馬克思主義學院,合肥 230000)
黨的十八大報告中提出的“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越來越得到世界的認同。作為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重要方略,也是對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情懷”的彰顯,從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理論基石、現實境遇、思想理念等幾個方面展現出來。
一、“自由人的聯合體”理想的創造性踐行: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精神實質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馬克思主義的當代形態。馬克思主義與中國革命,建設與改革實踐相結合,實現了兩次飛躍,產生毛澤東思想與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體系兩大理論成果,推動中國革命與建設不斷走向勝利和繁榮。無論理論如何發展,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一根本問題沒有改變,在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這一根本問題上,我們必須堅定不移,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都不能動搖。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標志著基于我國社會主要矛盾新變化而進入新階段,但不變的是中國仍然處于并將長期處于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發展中國家,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理論的重要組成部分,是馬克思主義在中國建設與改革實踐過程中與時俱進的產物。習近平總書記指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而不是其他什么主義,科學社會主義基本原則不能丟,丟了就不是社會主義。”
“自由人的聯合體”是馬克思主義“全人類解放”的目標設計。馬克思、恩格斯將“自由人的聯合體”稱為“真正的共同體”,而在此之前還存在著“天然的共同體”和“虛幻的共同體”。“天然的共同體”以血緣、地緣為紐帶,體現為“人的相互依賴”。血緣共同體是人類群體的最初形態,在人剛剛脫離動物界而實現自然界中的偉大進步時,需要群體力量集體自衛和維護生存,以共同勞動、共同生活為基本特征,形成原始群共同體。在經濟往來和相互通婚基礎上又發展成為氏族共同體,兩個氏族在通婚關系基礎上形成部落共同體。在這種共同體中,“共同體是實體”[1]458,個體依附于共同體而生存,個性被淹沒,因此,不是理想的共同體。商品經濟的發展使“人的相互依賴”轉變為“人對物的依賴”,人的自由與獨立在對“物”的依賴中呈現出抽象性和虛幻性,為了生存而不得不接受資本的奴役,個體與共同體日趨獨立,共同利益日益退化為統治階級的“特殊利益”,共同體日益成為“虛幻的共同體”,成為新的桎梏。而“自由人的聯合體”中個人自由的實現是與生產力高度發展、私有制被消滅三者互動的結果,實現了人的全面自由發展,在這個聯合體中,“每個人的自由發展是一切人的自由發展的條件”[2],是個體自由與整體自由的結合。
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實現馬克思主義“自由人的聯合體”思想的創造性踐行,兩者有機地統一于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實踐之中。一是兩者在服務對象上是一致的。“自由人的聯合體”理想致力于“全人類解放”,以“全人類”為對象;“人類命運共同體”也是以“全人類”為對象,從中國共產黨誕生起,“全人類”的共同利益就是黨的價值目標的重要組成部分,“中國應當對于人類有較大的貢獻”[3]45,“中國共產黨是為中國人民謀幸福的政黨,也是為人類進步事業而奮斗的政黨。”[4]二是兩者在價值旨歸上相同。“自由人的聯合體”以人的自由全面發展為目標,而“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在不完全具備自由全面發展的現實條件下,依據世情、國情提出的新理念,在價值指向上與“真正共同體”相一致,都是為實現人的自由全面發展,實現共同富裕。三是兩者在實現路徑上相契合。“自由人的聯合體”是以“生產力的普遍發展和與此相聯系的世界交往為前提的”, 而這恰好與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要求高度契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需要以世界各國的快速發展為基礎,需要以世界一體化為前提。總之,實現“全人類共同利益”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價值目標的重要內容,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就是將“自由人的聯合體”思想貫徹到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建設與改革之中,推動人類社會生產力的提高,維護國際社會的公正平義,創造世界人民的美好生活,努力“建設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榮、開放包容、清潔美麗的世界”[3]46。
人類命運共同體以馬克思主義“自由人的聯合體”實現人的全面自由發展為宗旨,致力于人類生產力的提高和國際社會和平、安全、平等、公正價值觀的培育,努力建立一個開放、包容、和諧、美麗的共同體,與馬克思主義的價值目標是根本一致的,從而豐富和發展了當代中國的馬克思主義。
二、歷史新方位的時代性選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時間定位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根據世界總體發展趨勢和現實矛盾,倡導個體利益與全人類整體利益的統一,“在追求本國利益時兼顧他國合理關切,在謀求本國發展中促進各國共同發展”[5]。強調“中國夢是奉獻世界的夢”[6],“中國人民的夢想同各國人民的夢想息息相通”[3]20。中國特色社會主義進入新時代,國內社會主要矛盾已經轉化為人民日益增長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發展之間的矛盾,國際社會存在著世界人民對和平發展的時代訴求與“人類面臨許多共同挑戰”的矛盾。如何在矛盾叢生的國內國際形勢下把握國家發展的正確方向? 就是要使個別國家利益與人類共同利益相統一。2017年1月19日,習近平在聯合國日內瓦總部的演講時對人類的未來提出了深切的思考:“從哪里來、現在在哪里、將到哪里去?”中國的解決方案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實現共贏共享”[7],這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作出的時代性選擇。
“共贏”的前提是共同利益的實現。共同利益是人類利益的最大公約數,“共贏”即一個成員利益的實現也是其他成員或整個群體利益的實現,利益各方“正比相關”,他者與自我利益重合[8]。實現“共贏”的基本條件是合作,“治理作為一種機制,本質上是一種國際合作”[9]。競爭不是造福人類的唯一價值,競爭無極限的結果是國際社會的失衡和失控,構建共同目標的全球協調合作體系才能避免“全球自我爆炸的危險”[10]。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共同利益”為基礎,而自由主義以“相同利益”為訴求,利益最大化的沖動使個體與個體、群體分離甚至對立,個體利益的損失非但不被認為是后者的損失,反倒可能是后者產生的結果。共同利益能夠帶來合作,相同利益則可能帶來紛爭。共同利益、共同危機的存在和不斷擴大增強了人類對命運共同體的依賴和歸屬,也為國際合作奠定了物質和認同的基礎。
十九大報告提出“中國秉持共商共建共享的全球治理觀”,“共商共建共享”形成了一個完整系統的全球治理價值架構。馬克思所設想的“自由人的聯合體”就是一個人人共享發展的社會組織,人民創造了物質和精神財富,推動歷史前行,擁有分享發展成果的權利。一個國家內部的人民共享國家發展,世界各國人民共享全人類的共同發展。在全球治理中,由于個人與全人類之間存在著民族—國家這一層次,全人類共享發展的實現需要國家發展與全人類發展關系的協調,而這一過程需要在“共建”中完成,因為在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中,主權國家扮演著雙重角色——建設者與享受者,兩者辯證統一于偉大實踐之中。
“共建”是全球治理中主權國家所需要承擔的基本責任。“共建”是積極主動的行為,要求責任共擔。事實已經證明,沒有任何一個單一的國家能夠承擔起全球治理的重任,共迎挑戰,共冒風險,共擔責任是全球治理的基本要求。“義務是一切責任的主要內容”[11],共擔責任就要共盡義務。中國提出要樹立正確的義利觀,其中有兩層含義,一是利益與道義的統一,二是權利與義務的統一。前者指以義取利,以利弘義;后者指權責利相連,只享受權利而不承擔責任、履行義務是強權剝削者的作為,而盡義務、擔責任的同時,享受權利的權利不容削奪。“共建”“共享”實現了利益與道義、責任與權利的統一。
全球治理是一種協商和合作行動的過程,“共建”必須以“共商”為基礎。“共商”是國際社會民主化的表現,排除“單邊”“強權”“剝削”的可能性,保障國際合作的平等公正和國際秩序的持久和諧。
“合作共贏”“共商共建共享”以實現共同利益和權責統一奠定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構建基礎和發展秩序,凝結著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原則理念和行動準則,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在人類面臨諸多矛盾和全球治理面臨困境中的現實選擇,為推動中國與世界的共同發展提供了中國方案。
三、中華5000年文明的民族性表達: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空間定位
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世界情懷”還體現為中華民族對人類整體意識的繼承和發展,將5000年中華文明孕育的“天下”意識、“和諧”思維和“共同”理念運用到治國理政過程之中,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通過對中華民族優秀文化精髓“天下”“和諧”“共同”等思想理念的繼承與發展,表達了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文化自信,彰顯出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世界理想的民族特性和風格。
首先,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天下”意識的當代回應。“‘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這是中華民族始終崇尚的品德和胸懷”[6]。“天下”本身即有“世界”“全球”“人類”之意, “普天之下”表明古代中國從整體觀世界,與西方從民族和個體觀世界不同,從而產生不同的思考世界方式。“天下”觀念以世界為單位,以共同幸福為目標,將一切外部性轉化為內部性,所有他者都以某種共在方式被納入天下體系之中,因此在邏輯上“天下”觀念是沒有敵人的世界觀。在這里,斗爭政治因既不尊重人類也不尊重世界而遭遇顛覆,天下體系希望構建一個和平與安全的保證體系,這個關鍵就在于使任何試圖摧毀他者的行為都無利可圖[12]。可以看出,“天下”是一種整體性觀念,內化無外,各國處于共在狀態,沒有敵對因而無需戰爭。在歷史的長河中,中國人的“天下”視野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意識形成“和衷共濟”“協和萬邦”“兼濟天下”“親仁善鄰”“和而不同”等價值理念。新時代,超越民族主義和傳統天下主義,擺脫中心化和等級化趨勢,構建共有、共建、共享、共治的新的天下秩序成為時代需要,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是天下主義在新時代的必然延伸。
其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以“和諧”思維化解分歧與矛盾。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主張國家之間相互尊重、平等協商,對話而不對抗、結伴而不結盟;談判解決爭端,協商化解分歧,是和諧思維的現實運用。“和”是中華文明的源頭,《史記·五帝本紀》就有“合和萬國”的理想,倡導天人合一、協和萬邦、和平和睦,主張“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等和諧思想。中國的和諧思維與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對世界產生不同的影響。西方的二元對立思維主導了國際政治領域中尋找異己和敵人的基本特征,“零和”與擴張成為交往的常態。中國自古形成的思維模式有著尚中貴和(合)的特征,主張矛盾以“和”“合”而解,使“華夏中心主義”沒有滑向純粹的“中心—邊緣”的不平等國際結構體系,而是形成一種強弱各安其位、強強包容共存的多中心共生體系。“和合”而解的基本思維方式,使亞洲正在生成一種“協和安全秩序”,各國共享領導權,而非強國主導而弱國邊緣化;強國自我克制和約束而形成分享性領導體系,并賦予弱國在共同決策中的話語權[13]。這一和諧共生秩序的形成就是厚重的中國傳統智慧的時代展現,也是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現實需要。
再次,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秉持“共同”理念,就是以共同命運為紐帶,以實現全人類的共同利益為目標,以和諧方式化解矛盾,以共同行動應對共同挑戰,形成休戚相關、命運與共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共同”與古代的“和同”“大同”之論有聯系也有區別。西周末周太史史伯、春秋末齊國晏嬰先后對“和同”之論有形象闡釋,發展出“和而不同、同則不繼”等思想。在此,“和”即多元事物的共存,強調多樣性和多元性;同就是單一性,強調同質性、一元性,有“相同”之意。“和同”將“和”與“同”對立起來,以“和”抑“同”,而“共同”則是以“同”求“和”,“同”為“共同”而非“相同”。“大同”理想是儒家世界主義的目標,懷有對“大道之行”的美好憧憬,描繪了一幅公有、公共的社會畫卷,這里有“天下為公”的思想境界,有“選賢與能”的政治清明,有“講信修睦”的社會秩序,有不獨“親其親,子其子”的人間溫情,有“皆有所養”的共享機制等,其倡導的“仁、義、禮、智、信”核心價值超越族群而成為人類普遍價值,從中可以看到“人類命運共同體”的思想萌芽。“共同”不僅包含著“和同”中的“融合”“統一”思想和“大同”中的“公共”“共有”思想,也內含著“彼此皆有”“同等”“一起、一齊”“合力”之意。“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汲取了中國傳統文化的精髓并于世界發展融合中加以改造,為中華文明的當代復興注入了動力和活力。
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是推動中國發展中更基本、更深沉、更持久的力量,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的源頭,而構建人類命運共同體在繼承民族傳統優秀文化精髓的基礎上,主張促進和而不同、兼收并蓄的文明交流,以文明交流、互鑒、共存超越文明隔閡、沖突與優越,表現出對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內涵與價值、文化特質與生命力的肯定與自信,是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文化自信的民族性表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