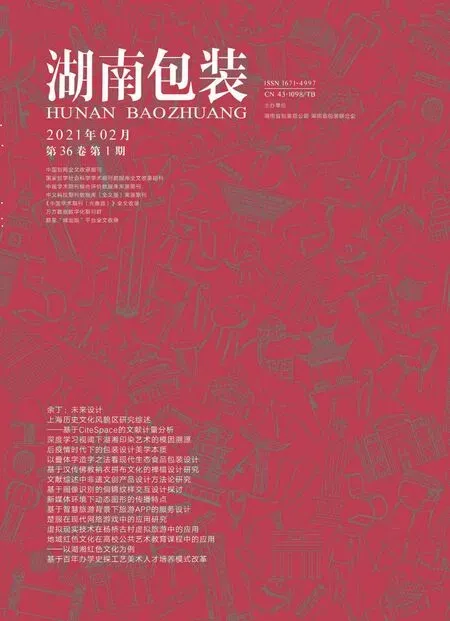淺析宗祠文化數字化保護價值和成果應用
——以湖南宗祠建筑為例
祝佳銘 范迎春
(湖南第一師范學院美術與設計學院,湖南 長沙 410205)
藝術化、非物質化、生態化是未來設計發展的普遍趨勢,也是近些年在開展文物和文化遺產全面永久保護過程中提出的應對新方法。同時,非物質手段是實現這些物質遺產保護的重要手段,也是目前永久保護的唯一途徑。通過非物質設計等有效手段可以實現對文化遺產客觀、全面的數字化保存和多維互動的展示。這種保護方法是運用信息設計以數字化應用信息系統建設為紐帶,對歷史文脈加以測繪、數字化建模、虛擬修復、數字展示的一種文化遺產保護方式[1]。借此,宗祠能夠以實體建筑和數字建模兩種方式同時保存,其還能為數字化宗祠的本體保護規劃制定工作提供有效參考借鑒。
2019年初,財政部聯合國家文物局等部門發布了《國家文物保護專項資金管理辦法》,在全國各地展開了文物數字化保護工作,也大大提高了文物工作者的積極性。同時,湖南宗祠數據測繪經過湖南第一師范學院范迎春教授團隊多年耕耘初具成效,但如何有效將其與實際應用結合,這是有待討論和商榷的。因此,本文對湖南宗祠建筑文化數字化成果應用領域和后期發展展開分析和討論。
1 湖南宗祠的歷史價值
祠堂是祭祀、族人集會、族尊施政的場所,其經歷了奴隸社會的啟蒙、封建社會的發展和近百年民族動蕩和變革,其本身承載的文化價值和意義也越來越廣泛。元朝的理學家吳澄把祭祖分為朝廷特建的家廟和 “俗人之家” 兩種類別的祠堂,也可以看出宗祠由最開始的達官貴人獨有變為全民共享,是中華民族禮制文化和世俗風氣的集大成者[2]。由于近代以來的戰亂以及20世紀60年代期間 “破四舊” “評法批儒” 等運動,許多宗祠受到了嚴重影響和打擊。到如今,隨著40多年的改革開放和海外中華兒女認祖歸宗的期盼,大量古宗祠被復興,族譜被續寫,海外華僑華裔則不斷翻新舊宗祠,團結家門。可以說,宗祠建筑是文化空間的重要類型,凸顯了中國古典建筑的形式美,集中展示了中國傳統裝飾的藝術美,祠堂楹聯、匾額等蘊含中國傳統祭祀禮俗與道德倫理的社會美,具有物質文化遺產和非物質文化遺產雙重屬性[3]。當下的宗祠早已沒有了過去宗法制度的負面影響,更多是尋根問祖、祭拜祖先、勉勵后人、互幫互助等積極效應[4]。
當下,我們很難再看到保存完好的宗祠建筑群,而湖南省由于多山地、丘陵等,湖南的宗祠保存完好,散落在群山之間,保存完好的宗祠多達300余座,被湖南省列為重點文物保護單位的明清古宗祠就有70多座。古宗祠建筑深受湖南傳統文化的渲染,是湖南地域文化的物質和精神載體,代表了湖南傳統民居建筑中公共禮制建筑的最高成就,具有非常重要的保護和傳承價值。這些古建筑,座座博采藝術精華,廣納八面來風,體現了湖湘文化 “吃得苦、霸得蠻、耐得煩” 的精髓和特點;發揚了三湘兒女愛國主義和艱苦創業的精神;起到了各民族團結,發揚民族核心凝聚力的作用;增進了宗親鄰里情誼,聯絡感情的效果。湖南宗祠建筑歷史美學價值和建筑本身價值的重要性不言而喻。
保護湖南的祠堂并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已經留存幾百年甚至更久的文化遺產,無時無刻都面臨著天災人禍的威脅,很多文物最終可能還會在歷史的長河中消失。我們一方面要保護宗祠建筑,另一方面也要對它們進行數字化存檔。例如:運用CAD、3Dmax等軟件對宗祠建筑整體建模(見圖1),運用Photoshop、Illustrator軟件對實地拍攝收集的圖像進行加工處理,運用Unity3D軟件實現三維場景漫游制作……用非物質設計的手段對宗祠進行數字化修復和保護,這也是發展和傳承中華民族優秀歷史瑰寶的一種有效途徑和方法。
2 數字化成果的應用
當地時間2019年4月15日下午6時50分左右,法國巴黎圣母院的一場大火,讓世界為之心碎。反觀當下,如何讓湖南古宗祠建筑保持當下的姿態繼續在歷史長河中前行,使將來的人們仍然能與今天的我們一樣,追思先祖創造的燦爛文明?宗祠的數字化保護成果是實現宗祠作為中國傳統文化、特別是鄉土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有效保存手段的途徑之一。數字化處理方式再造與建構的傳播也為提高公眾審美、全民通識教育、基層社區和諧關系提供了智慧和啟迪。從非物質設計及與其相關的可持續設計、體驗設計、全設計、虛擬再現技術、體感技術等迅速發展來看,從持續深入的湖南古宗祠建筑保護需求來看,湖南古宗祠建筑數字化保護將呈現以下趨勢:

圖1 朱氏宗祠照片及CAD正立面圖[5]
第一,湖南古宗祠建筑從被動的、靜態的、旁觀的、局部的展示到互動的、動態的、體驗的、沉浸式的全面展示轉變,從面向族人的展示到兼顧游客的展示,從單純族群文化、審美性展示向導覽性、傳承性展示轉變。
第二,湖南古宗祠建筑從借鑒的、一維的、部分的傳承到主動的、交互的、立體的、多方面的繼承發展。
第三,湖南古宗祠建筑從單一的、局部的分析,到整體的、研究性的分析變化[6]。
2020年國務院政府工作報告指出, “十四五” 期間將繼續出臺推進 “互聯網+” 的支持政策,打造數字經濟新優勢。湖南省古宗祠建筑文化抓住政策宏利,對前期勘測整體進行數據整理錄入,對實體建筑進行紋理拍照、多維度建模復原,最后形成高清數字文物搭建數據庫,并租賃服務器利用融媒體技術,如:PC網頁、手機小程序、公眾號或手機應用軟件等數字平臺進行展示推廣。通過大數據的采集、分析,與受眾有效互動,形成了一套互聯有效的良性循環(見圖2)。
通過湖南古宗祠APP等媒介,能夠為專家學者或文物保護單位提供古宗祠保護與修繕的一手詳細數據資料,提升宗祠保護的質量。其次,可以為本宗族人群提供本宗族祭祀活動的影像資料或是宗祠全景圖片展示,甚至可以對特定的宗祠活動進行現場直播,方便本宗族人群了解宗族活動。此外,數字化成果的應用開發也為大眾零距離接觸文化遺產提供了方便,讓千年文脈綿延傳承。能夠對學生或是普通群眾進行宗祠文化科普,了解宗祠文化魅力。這不僅填補了國內利用數字化技術和新媒體技術系統研究湖南古宗祠建筑文化的空白,而且在傳承湖南傳統文化,逐步利用、開發優質傳統文化資源等諸多方面有較大現實意義,而且將研究成果轉化為具有較大的社會紅利和經濟收入。

圖2 基于數字化研究邏輯框圖

圖3 湖南古宗祠應用UI圖
3 數字化成果后期發展
歷史文物走出單一展示媒介不僅帶來了更多的社會效益,同時也增添了經濟效益。在我國,與中華民族優秀傳統文化相結合的產品在系列化開發、周邊授權、商品包裝、體驗設計、商品品類、營銷推廣等6個方面都取得了可喜的發展成績,但還存在著不少問題,如同質化現象嚴重、地域發展差異明顯、商品化程度不高等。隨著 “優質精神消費” 和 “內容為王” 時代的到來和中產階層的日益壯大,需要獨特且附有設計感,有審美導向,能產生共鳴,能夠傳承文化的優質消費品缺口越來越大,我國擁有該品類消費訴求的人群已達1.09億人次[7]。
國家統計局2018年數據顯示,2018年上半年我國居民人均文化教育娛樂消費支出達到932元,同比增長7.2%。同樣也反映出我國消費升級態勢仍在持續,文教衍生品消費市場十分龐大。
3.1 興趣驅動的社交平臺
2020年初的疫情,也讓全國各地的藝術館、博物館等科普重鎮被迫閉館,甚至各大高校畢業展也轉向了線上開展。相比線下科普場所的慘淡,線上2 000余項展覽卻欣欣向榮,百花齊放。360度全息影像、AI、5G+VR等多媒介技術通過互聯網架起觀眾與主辦方的橋梁,也推動著傳統陳列展示向多元互動展示的轉變。 “湖南古宗祠” 數字化應用的開發,也可以抓住這波發展的機遇,讓用戶在手機應用中結識同宗同好,品味各類宗祠趣事,搜羅各式宗祠建筑傳統審美指南。新媒體在 “湖南古宗祠” 數字化中的應用可分為建立網絡博物館、虛擬現實博物館、掌上APP博物館、設置數字展廳與互動裝置等幾方面。 “湖南古宗祠” 數字化應用不僅內含宗祠三維模型、測繪資料和專業資訊,也將開發結合中國宗祠文化定制的宗祠趣味知識游戲,線上祭祀H5和設計潮流的文創產品,用年輕的視角讓宗祠建筑活起來,重塑生機,為用戶構建一個符合新中式審美的生活場景。
3.2 創新發展的科普天地
宣傳媒介鋪天蓋地之勢出現在人們的生活中,高度碎片、通俗娛樂、方便易用、快速傳播、淺顯海量、互動傳播、傳播效果如暴風驟雨又轉瞬即逝……這是當下人們閱讀和傳播的突出特點,正是因為這些特點使得新型傳播媒介迅速被社會大眾所接受[8]。 “湖南古宗祠” 數字化應用以互聯網 “工匠精神” 開始重建,一度變得小眾化的文博內容讓更多人通過 “湖南古宗祠” 數字化應用了解文化文脈,參與到傳承中華文化的隊伍中[9]。在國家大力發展 “文化自信” 的維度下將互聯網產生的小眾文化與中國主流文化相結合,孵化不同的文化元素,使文化輸出一改以往居高臨下的面貌,以知己、朋友的面目出現,給人以親切感,寓教于樂的同時緩解快節奏生活的壓力。

圖4 湖南古宗祠品牌logo及吉祥物
3.3 強大IP的交互網絡
通過挖掘——塑造——轉化——賦能IP層層遞進,構建出以IP為核心的全新的文化生產方式,文物的知識傳播模式從閉環走向全新的動態傳播形態(見圖3)。第三產業的發展是建立在可持續的版權保護和研發上的,授權是文化產業發展中的重要一環。如手機端游戲 “王者榮耀” 與敦煌研究院聯名推出的敦煌定制皮膚即是IP賦能的新模式。九色鹿是出自敦煌壁畫鹿王本生圖,一定程度上代表著敦煌壁畫,而飛天也是敦煌壁畫的一大特色,所以飛天與九色鹿基本上就是這款皮膚的核心元素。這次聯名上線一小時內有超4 000萬人次競相使用,在娛樂游戲的同時,敦煌文化也走出洞窟,轉變為更生動的姿態映入數千萬玩家的眼簾[10]。
近些年來國貨不斷推陳出新,茶顏悅色、百雀羚、中國李寧等,通過品牌商與文化產業的聯名轉化為富有藝術氣質的電影電視、數字媒體、日用文具、大型建筑以及其他娛樂事業,開拓了品牌方和銷售方雙贏的局面,成為市場上無法企及的黑馬IP。湖南古宗祠建筑的授權可以是藝術和品牌授權的結合(見圖4)。其內容主要包括古宗祠建筑的數字圖像資源、日用品、工藝品等。將湖南宗祠文化和背后的中華優秀民族文化進行創造性轉化和創新性發展,通過實現文化價值和產業賦能,為湖南古宗祠新文創的建設提供創新辦法。
湖南古宗祠建筑擁有得天獨厚的文化資源,而社會上也不乏專業的制作包裝團隊。如果將這些資源有效地結合在一個完整的文化產業鏈上,文化價值則能大幅度被開發,湖南古宗祠建筑藝術授權正是合適的商業模式。湖南古宗祠建筑藝術授權的產業鏈大致是這樣的:湖南古宗祠建筑作為授權內容的提供者,將內容授權給市場運營者,市場運營者使其成為具有藝術、文化價值及附加值的文化渠道,再由湖南古宗祠建筑的授權開發商將其推向文化市場。就我國文物目前文創產業發展現狀來看,湖南古宗祠建筑通過藝術授權的模式,在保障知識產權的前提下,同樣也擴大了湖南古宗祠建筑資源的使用率。下一步,再將其升級為大IP,為優秀的文化資源匹配鏈接入口,更大程度地推廣湖南古宗祠,借助平臺觸達海量用戶,形成流量和變現閉環,傳統的藝術賦能現代消費品,引領新的時尚潮流。實現社會效益的最大化,滿足人們日益增長的文化需求。
4 結論
本文在前期研究湖南古宗祠建筑內容、傳承現狀以及文化遺產數字化保護設計相關理論的基礎上,探索湖南古宗祠數字化保護未來發展的可行性;從歷史實物的數字化、傳播方式的多樣化、開發保護的多元化等角度,闡明了以湖南宗祠建筑為例的宗祠文化進行數字化開發的應用價值。
數字技術在宗祠建筑或其他文物保護領域的運用,拓寬了文化傳播的空間,縮短了傳播的時間,同時也會產生不俗的社會和經濟效益。未來,湖南古宗祠將打造自己的品牌,聯系更多專業領域專家學者和宗祠愛好者,與更多市場運營者攜手合作,共建一個公開透明、團結互助、全新的宗祠文化圈[11]。關注科技落地與學術創新,通過 “非物質化+AI化” ,在數字化采集與文化研究等領域貫徹湖南古宗祠數字化的建設。重點打造針對青少年的 “第二課堂” ,以更多的全息投影、VR等形式,將文物數字化,吸引更多的未成年人走入宗祠博物館里,讓宗祠文化元素重新融入日常生活,用非物質化設計的力量活化和保護更多優秀的歷史文化,開辟宣傳文化遺產的新陣地,打造更多耕織于老百姓內心的中國文化名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