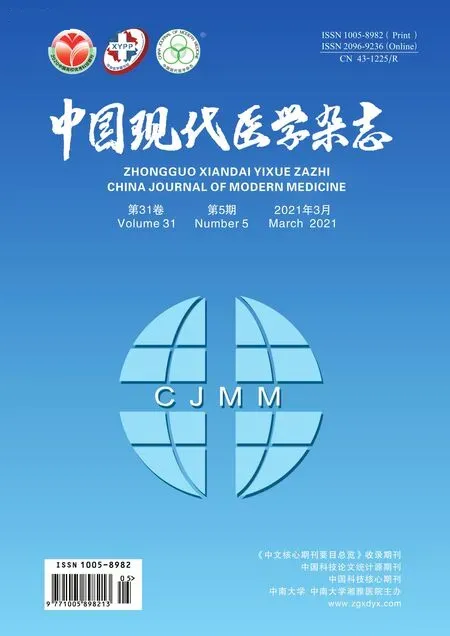常規超聲、超微血管成像和超聲造影診斷頸動脈狹窄的對比研究*
王華,李天天
(1.鄭州大學附屬洛陽中心醫院 超聲科,河南 洛陽471000;2.新鄉醫學院,河南 新鄉453303)
近年來,腦血管疾病的發病率隨著全球老齡化程度的增加不斷上升,對醫療保健造成極大負擔[1]。有研究認為,缺血性腦血管病的發生風險與血管狹窄或閉塞存在一定的相關性[2]。頸動脈狹窄是誘發心腦血管疾病的主要因素之一,約占7%缺血性腦卒中[3]。對無癥狀患者實施臨床干預措施能夠有效減少腦卒中的風險,具有重要的臨床意義。在頸動脈狹窄率為50%~99%的患者中,8%~15%患者會在標志性癥狀出現的72 h 內出現腦梗死[4]。盡早評估無癥狀患者管腔狹窄程度,可篩查識別有心血管疾病和中風風險的患者,從而進行早期干預治療。
快速發展的現代醫學影像學在頸動脈狹窄的診斷中獲得突破性進展。包括二維超聲、計算機體層攝影血管造影(computed tomography angiography, CTA) 和磁共振血管成像(magnetic resonance angiography, MRA)在內的無創診療技術不僅為血管病變診斷提供可靠的依據,而且能夠指導臨床用藥及療效評估[5]。傳統的數字減影血管造影(digital subtraction angiography, DSA)是診斷頸動脈狹窄的金標準[6],然而這種有創的診斷方法存在0.1%~0.5%的腦卒中風險。二維超聲由于其低輻射、無創等特點得到了廣泛應用,但該方法對頸動脈狹窄的敏感性和特異性并不高,往往需要第2 次檢測來證實。CTA 能夠提供頸動脈病變的詳細信息,但也存在輻射暴露和使用碘化對比劑的風險。MRA 對重度頸動脈狹窄的治療效果優于二維超聲技術,但是MRA 增強對狹窄程度評估的特異性不足[7]。因此,臨床上需要尋求一種無創、經濟、安全可靠、操作簡便、準確率高的檢測方法,為腦血管疾病風險的評估提供參考依據。
隨著醫學影像學的發展,超微血管成像(superb microvascular imaging, SMI)和超聲造影(contrast-enhanced ultrasound, CEUS)技術廣泛用于頸動脈斑塊篩查及評估頸動脈斑塊的穩定性[8]。SMI 是基于彩色多普勒原理基礎上發展起來的一種超聲血流顯像技術,采用自適應計算方法,能夠有效去除組織運動偽像,較傳統彩色血流顯像技術有更高敏感性及分辨率,能更敏感地捕捉真實低速血流[9]。CEUS 技術廣泛用于動脈粥樣硬化斑塊新生血管的診療,通過造影劑來檢測患者斑塊內新生血管的分布及走行,能夠定量評估診斷效果,具有很高的敏感性,對腦血管病變評估具有較好的臨床診斷價值[10]。
目前,國內外尚未見SMI 和CEUS 診斷頸動脈狹窄程度的對比研究。本研究通過對比分析常規超聲、SMI 和CEUS 對頸動脈狹窄程度的診斷價值,旨在尋求一種更具有臨床推廣意義的腦血管相關疾病的診斷方法。
1 資料與方法
1.1 研究對象
選取2018年1月—2018年12月因頸動脈、鎖骨下動脈、椎動脈重度狹窄或閉塞在鄭州大學附屬洛陽中心醫院住院的患者100 例。所有患者行頸動脈DSA 檢測,再進行常規超聲、SMI 及CEUS 檢查。其中,男性56 例,女性44 例;年齡39~77 歲,平均(56.2±10.6)歲。研究經醫院的醫學倫理委員會批準(審批號:2020-07-13),家屬均簽署知情同意書。
1.2 納入和排除標準
1.2.1 納入標準①常規超聲診斷頸動脈、鎖骨下動脈、椎動脈重度狹窄或閉塞患者。②年齡>18歲。③簽署頸動脈超聲造影檢查知情同意書。
1.2.2 排除標準①嚴重心、肝及腎功能不全者。②意識不清不能配合檢查者。③有超聲造影劑使用禁忌證患者,包括已知對六氟化硫或造影劑其他組份有過敏史;近期急性冠脈綜合征或臨床不穩定性缺血性心臟病;正漸變或進行性心肌梗死;過去7 d 內心臟癥狀出現明顯惡化;剛接受冠狀動脈介入手術或其他提示臨床不穩定的因素;急性心力衰竭,心功能Ⅲ級、Ⅳ級及嚴重心律紊亂;伴有右向左分流的心臟病、重度肺動脈高壓(肺動脈壓>90 mmHg)、未控制的系統高血壓及成人呼吸窘迫綜合征;孕婦及哺乳期婦女。
1.3 儀器設備
采用日本東芝Aplio500 彩色超聲診斷儀,線陣探頭,頻率4~11 MHz;SMI 檢查的參數設置:1.50,深度3~5 cm;超聲造影機械指數為0.07,動態范圍為65 dB,幀頻為10 fps。
1.4 方法
常規超聲檢查篩選頸動脈、鎖骨下動脈、椎動脈重度狹窄或閉塞患者,并同時行SMI 檢查及CEUS 檢查。以DSA 為金標準,將常規超聲檢查、SMI 及CEUS 檢查結果與DSA 結果進行對比分析。所有檢測圖像均由2 位神經科主任醫師在不知任何臨床信息的前提下,獨立完成閱片,有不同意見時相互討論并得出結論,計算研究對象的頸動脈狹窄程度。
1.4.1 DSA 檢測采用德國西門子公司Artist.zee數字血管造影機,通過Sedinger 穿刺技術行右側股動脈穿刺,插5 F 造影導管,在影像示蹤圖及超滑導絲引導下,導入雙側鎖骨下動脈,行常規雙側頸總動脈、頸內動脈及雙側椎動脈血管造影。多角度顯示狹窄處頸動脈血管,采集并重建圖像。
1.4.2 常規超聲檢測選用日本東芝Aplio 500 超聲診斷儀,探頭頻率為4~9 MHz,具備SMI 及CEUS 功能。患者取低仰臥位,先采用常規超聲長軸和短軸掃查雙側頸總動脈及頸內動脈,雙側鎖骨下動脈、雙側椎動脈的起始段,記錄超聲圖像上血管狹窄部分的形態、內徑及遠端正常血管直徑,計算狹窄率。
1.4.3 SMI 檢測進行常規超聲檢查后,啟動對狹窄部位內新生血管形成更為敏感的mSMI 模式。將探頭固定在動脈斑塊最厚處,在此切面檢測斑塊內的增強情況即低速血流顯像,設置參數,持續觀察并記錄血管狹窄部位的低速血流信號。記錄狹窄血管的位置、形態、內徑及遠端正常血管直徑,并計算狹窄率。
1.4.4 CEUS 檢測在各血管狹窄處固定探頭,啟動CEUS模式,設置參數:MI 0.15,深度3~5 cm,頻率2~3.7 MHz。采用六氟化硫微泡作為造影劑,按比例配制Sono Vue 混懸液,混勻后,通過管針將2~3 ml 造影劑經肘正中靜脈推注,隨后注入3 ml生理鹽水沖洗,觀察并記錄察頸動脈腔內造影劑顯影效果。采用定量分析軟件分析斑塊內造影感興趣區域,準確測量狹窄血管內徑及遠端正常血管直徑,并計算狹窄程度。
1.5 血管狹窄程度的評價標準
根據北美癥狀性頸動脈內膜切除術試驗協作組的NASCET 法來計算狹窄率[11],狹窄率(%)=(1-最狹窄處管腔直徑/狹窄遠端正常血管直徑)×100%。依據狹窄率將頸動脈狹窄分為輕度狹窄(<30%)、中度狹窄(30%~<70%)、重度狹窄(70%~<100%)和閉塞(100%)。
1.6 統計學方法
數據分析采用SPSS 17.0 統計軟件。以DSA 為金標準,用Cohen's Kappa 系數進行檢查方法的一致性檢驗;狹窄程度的一致性采用Kappa 檢驗:κ ≥0.75 表明一致性好;κ 0.40~<0.75 表明一致性良好;κ <0.40 表明一致性差;3 種檢查方法的敏感性、特異性及準確性比較,用χ2檢驗,P<0.05 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果
2.1 二維超聲與DSA診斷頸動脈狹窄程度
常規超聲與DSA 診斷頸動脈狹窄情況見表1,經Kappa 檢驗,2 種檢查方法診斷頸動脈不同程度狹窄的一致性較好(κ=0.862,P=0.042)。常規超聲診斷頸動脈重度狹窄及閉塞(以>70%為切點)的敏感性為90.0% (95% CI:0.86,0.94),特異性為94.0%(95%CI:0.91,0.97),準確性為90.0%。

表1 常規超聲與DSA診斷頸動脈狹窄的一致性比較 例
2.2 SMI與DSA診斷頸動脈狹窄程度
以DSA 診斷為金標準,對頸動脈狹窄程度的診斷進行組間比較,2 種檢查方法診斷頸動脈不同程度狹窄的一致性較好(κ =0.958,P=0.024)。以重度狹窄率為70%作為切分點,頸動脈狹窄SMI 診斷的敏感性為96.0%(95% CI:0.93,0.99),特異性為97.0%(95%CI:0.95,1.00),準確性97.0%。見表2。

表2 SMI與DSA診斷頸動脈狹窄的一致性比較 例
2.3 CEUS與DSA診斷頸動脈狹窄程度
CEUS 與DSA 診斷頸動脈狹窄情況見表3,經Kappa 檢驗,兩種檢查方法診斷頸動脈不同程度狹窄的一致性較好(κ=0.903,P=0.035)。CEUS 診斷斑塊內新生血管的敏感性為96.0%(95% CI:0.93,0.98),特異性為94.0%(95%CI:0.90,0.98),準確性為94.0%。

表3 CEUS與DSA診斷頸動脈狹窄的一致性比較 例
2.4 3 種檢查方法診斷頸動脈重度狹窄及閉塞的一致性比較
3 種影像學檢查方法診斷頸動脈重度狹窄及閉塞的敏感性、特異性及準確性比較,經χ2檢驗,差異均無統計學意義(χ2=1.183、1.238 和1.824,P=0.071、0.083 和0.093)。見表4。

表4 3種檢查方法對頸動脈重度狹窄及閉塞的診斷價值比較 (%)
3 討論
腦卒中是重大的全球健康問題,目前已成為世界人口的第2 大死因,僅次于缺血性心臟病。非致命性中風患者的恢復期較長,花費較高,且存在潛在的獨立性喪失等風險,顯著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鑒于面臨醫療預算的巨大壓力,在出現臨床癥狀之前進行低成本、高效益的預防已成為醫療實踐的重要組成部分。頸動脈狹窄是動脈粥樣硬化早期階段的表現之一,對腦血管疾病的預測起到重要作用[12]。非對稱性頸動脈狹窄會在非腦卒中或局灶性神經功能缺損的前6 個月出現頸動脈狹窄。研究表明,每年中度狹窄(狹窄率>50%)的中風風險<1%,而>80%狹窄率的中風風險高達5%[13]。
頸動脈成像和狹窄程度的測量具有重要的臨床價值。影像學成像技術的篩查可早期判斷頸動脈血管的狹窄率,便于盡早采取臨床治療措施,降低缺血性腦卒中的發病率[14]。動脈DSA 是一項昂貴且有潛在高風險的技術,因此不能作為頸動脈狹窄的篩查工具。目前針對頸動脈狹窄的影像學檢測方法有很多,無創超聲技術可用于判斷影響頸動脈分叉的狹窄程度,是目前應用最廣泛的成像技術。然而,無創超聲技術不能準確地評估顱內血管的狹窄程度,尤其在血管嚴重鈣化的情況下評估更為困難[15]。CTA 和MRA 能夠觀察顱內外血管情況,從而直接測量頸動脈狹窄率[16-17]。CTA是一種非常快速的動脈觀察方法,可以識別頸動脈疾病的并發癥,如夾層和假性動脈瘤。MRA 與CTA 具有相似的敏感性和特異性,且受周圍骨骼或鈣化的影響較小,可以顯示斑塊特征及穩定性。然而,這些篩查方法的適用性受其成本、靜脈造影劑和電離輻射相關風險的限制。
近年來,SMI 和CEUS 可有效檢測血管狹窄處的超微血管,顯示斑塊內新生血管形成,判斷狹窄率,具有更高的敏感性和準確性,可更好地用于腦血管疾病的篩查[18-19]。其中SMI 無需使用造影劑,且與頸動脈超聲造影在顯示斑塊內新生血管部位方面有良好的一致性,可以初步評估斑塊內新生血管情況,進而評價斑塊的穩定性。SMI 具有2 種檢測模式,可以實現高幀率、高分辨率的可視化,但SMI 對頸動脈斑塊內新生血管的敏感性和檢出率并不高。盡管CEUS 可以清晰地顯示頸動脈內的血流情況,提高斑塊的檢出率,但是不能對動脈粥樣硬化性及血栓性疾病進行量化評估,并且少部分患者在使用造影劑后會出現頭痛、惡心等不良反應,且費用相對較高。此外,CEUS 在操作上至少需要2 名放射科技術人員共同完成,臨床應用價值有限。
血管狹窄程度可分為輕度、中度、重度及閉塞。本研究應用常規超聲、SMI 和CEUS 對100 例頸動脈、鎖骨下動脈、椎動脈重度狹窄及閉塞患者進行檢查,并以DSA 技術為金標準對比評估常規超聲、SMI 及CEUS 在診斷頸動脈、鎖骨下動脈、椎動脈重度狹窄及閉塞中的價值,發現3 種檢查方法與DSA 診斷頸動脈狹窄程度具有較高的一致性。進一步評估3 種檢查方法診斷頸動脈重度狹窄及閉塞的準確性、敏感性及特異性,SMI 的準確性為97.0%,敏感性為96.0%,特異性為97.0%,有助于評估患者頸動脈狹窄的嚴重程度。因此,無創、經濟、簡便的SMI 評價斑塊內新生血管的準確性較高,可為臨床提供更可靠的影像學信息。
超聲可動態反映動脈管壁的形態學變化,CEUS 量化分析可準確檢測病變不同階段血管新生情況。CEUS 能夠通過顯示動脈粥樣斑塊內新生血管的分布情況,用于評估斑塊的穩定性[2],CEUS定量分析方法較半定量分級方法對造影后斑塊增強程度的評估更客觀、精確。雖然使用SMI 也可能無法檢測超慢的血流,并且在沒有SMI 檢測到血流信號的情況下,還需要CEUS 輔助確認檢查,但是而隨著技術的進一步發展,SMI 的敏感性有望得到提高[20]。本研究結果表明,3 種檢查方法診斷頸動脈狹窄程度具有較高的一致性,其中SMI 作為一種更簡單、經濟、無創的方法,有助于進一步可視化頸動脈狹窄部位,提高頸動脈斑塊臨床評價的穩定性。SMI 未來的發展包括結合三維成像能力和增加量化功能,這將有助于消除其當前診斷的局限性及提高整體臨床診斷水平,有望最終取代CEUS 在動脈粥樣硬化、血脂異常、高血壓等疾病干預治療中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