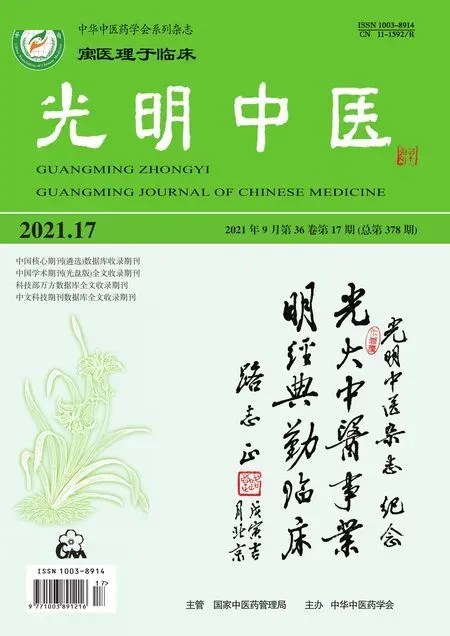李慧臻主任異病同治治療血壓異常2則*
扈麗萍
補中益氣湯是李東垣治療內傷脾胃病的代表方之一,《內外傷辨惑論·辨陰證陽證》言:“舉世醫者,皆以飲食失節,勞役所傷,中氣不足,當補之證,認作外感風寒”,在此背景之下,李東垣創立了補中益氣湯[1]。補中益氣湯原為治療脾胃受傷、中氣不足之證,為治療消化系統常用的方劑,后世醫家不斷發揮,用于治療各種慢性疾病,本文試將李慧臻主任用之治療高血壓和低血壓驗案進行報道。
李慧臻主任系天津中醫藥大學第二附屬醫院脾胃病科主任,主任醫師、博士生導師。全國第三批名老中醫繼承人、第三批優秀中醫人才、天津市第二批中醫藥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天津中醫藥大學131工程青年學術帶頭人、天津市教委綜合創新人才,多次獲科技成果獎。她從事臨床、教學、科研工作20余年,融古貫今,積累了豐富的臨床經驗,對消化系統疾病的治療有著極高的造詣,且對于其他系統疾病應用“從脾胃論治”的方法治療每獲良效。余有幸侍診于側,滋將李主任治療血壓異常驗案2則報道如下。
1 低血壓病案
患者,女,63歲,退休,2020年9月就診。主訴:頭暈、失眠2周。患者平素血壓偏低,常于勞累或睡眠不足后易感頭暈耳鳴,2周前因勞累即出現頭暈,自服“眩暈停”“甲鈷胺”等藥不能緩解,遂就診,刻癥:頭暈耳鳴,倦怠乏力,氣短心悸,不寐,便秘,舌淡暗,胖大,苔白,脈沉細。BP:80/50 mm Hg(1 mm Hg≈0.133 kPa)。診為眩暈,證屬脾虛氣陷、痰濕阻竅。治以健脾祛痰、益氣舉陷。處方:黨參15 g,柴胡6 g,升麻6 g,生白術10 g,黃芪30 g,陳皮6 g,炙甘草10 g,當歸15 g,海浮石9 g,桃仁10 g,肉蓯蓉15 g,苦杏仁6 g,枸杞子10 g,川芎6 g,火麻仁10 g,五味子10 g,麥冬10 g,枳殼6 g,生地黃15 g。7劑,水煎服,每日1劑,分2次溫服。二診:1周后患者復診,諸癥皆明顯好轉,唯睡眠不安、多夢,原方去枳殼,加遠志10 g,夜交藤15 g。再服7劑后,患者幾乎無不適感,囑其適當運動、增強體質、避免勞累。
按:本例為低血壓病患者,根據其臨床表現,可歸屬于中醫“眩暈”“虛勞”等疾病范疇。稟賦不足、飲食不節、煩勞過度是其最常見的病因。患者病程較長,五臟皆受損,脾則首當其沖,蓋脾為后天之本,脾虛則生化無權,氣血化生乏源,氣血不能充養四肢肌肉則倦怠乏力、不能濡養心脈則心悸不寐,氣虛日久、下陷不固,不能循經上行充達腦絡,且脾腎虧虛水濕溫化無力,聚而成痰,上泛腦絡,故見頭暈耳鳴,氣血虧虛、腸腑失潤則大便秘結。治療以補益為要,以補中益氣湯合生脈散加減化裁,方中黨參、黃芪、炙甘草、白術、柴胡、升麻益氣升提,麥冬、五味子養血益脈,陳皮、海浮石化痰開竅,火麻仁、桃仁、苦杏仁合當歸、肉蓯蓉、生地黃養血扶正、潤腸通便,枸杞子益腎,取以先天扶助后天之意,川芎、枳殼行氣血,防補益而留滯,本方以先天滋后天、以后天養五臟,實為標本施治之方,故效果顯著。
2 高血壓病案
患者,男,58歲,業務員,2020年8月就診,主因頭暈頭疼求治,既往高血壓病史,長期服用纈沙坦、硝苯地平緩釋片等藥物治療,近日因勞累血壓波動,自測臥位血壓常在160~170/90~100 mm Hg,而立位血壓120/70 mm Hg左右,立位時頭暈則加重,伴有周身乏力,因妨礙正常工作遂來就診,刻癥:頭暈、頭脹痛、頭昏沉、立位加重,伴有倦怠乏力、少氣懶言,腰酸腿軟,納差,食后即脘悶不舒,便溏,2~3日一行,失眠。舌暗紅,齒痕,苔白膩,脈沉弦。診斷為眩暈,證屬脾腎虧虛,治以補脾益腎。處方:黨參15 g,黃芪30 g,柴胡10 g,葛根15 g,生地黃15 g,枸杞子10 g,山萸肉10 g,牛膝10 g,桑寄生15 g,當歸10 g,白芍15 g,白術10 g,茯苓15 g,遠志6 g,炒山藥10 g,澤瀉15 g,甘草6 g。7劑,水煎服,每日1劑,分早晚2次溫服。二診:患者訴上癥均有不同程度的減輕,血壓漸穩,大便干,略感口干,原方去澤瀉,加夏枯草15 g,黃芩10 g。水煎服。三診:患者諸癥不顯,血壓平穩,維持在130/80 mm Hg左右,囑患者可長期服用補中益氣丸。
按:本案患者立位血壓正常,臥位則血壓升高,高血壓發病與體位相關,而血壓正常時癥狀卻加重,這是本患者的病情特點。《素問·上古天真論》:男子“七八,肝氣衰,筋不能動,天癸竭,精少,腎臟衰,形體皆極”,隨著年齡增長,精氣漸衰,平臥時因人體消耗相對較少,血脈尚能充盈,通過血壓增高的代償尚能維持正常的生理需求,而當直立時,氣血不能上達于腦,故癥狀加重,其病機根本在于脾腎虧虛,氣虛下陷,治療應以補益脾腎、益氣升提為主,方中以黃芪、黨參、山藥、白術、茯苓健脾益氣;遠志安神定志;當歸、白芍、山萸肉、生地黃、枸杞子補腎增血;桑寄生、牛膝補益腎氣、平穩血壓;柴胡、葛根升提清氣;澤瀉補中有瀉,一則防補藥滋膩、一則有降壓作用。二診患者病情好轉,血壓尚不穩,且見熱象,故用黃芩、夏枯草以清火散結降濁。因患者虛損明顯,故可長期服用補中益氣丸。
3 體會
3.1 關于異病同治辨證論治是中醫學的一大特色,異病同治則是中醫辨證論治思想最精華的體現[2]。我們可以從《黃帝內經》的論述中發現有關異病同治思想的端倪:如《素問·至真要大論》病機十九條言“因火而致病者有五,可為熱瞀瘛,可為禁鼓慄,可為逆沖上,可為躁狂越,可為病胕腫、疼酸驚駭,皆可用清熱瀉火法治之”。在仲景的《傷寒論》中則直接體現了關于異病同治思想在臨床中的靈活運用,他在太陽病和太陰病的治療中均使用了桂枝湯[3,4]。清代程文囿則首次提出了“異病同治”的名稱:“臨床疾病變化多端,病機復雜,證候多樣,病勢的輕重緩急各不相同,故治法須變化萬千……有時異病須同治”。歷代醫家也不乏對異病同治的應用[5],李老師在臨床中,無論治療何種疾病,都先要明確立法,而立法的基礎便是“證”,主張以證統方,方隨法變,“證”即是病機根本。我們可以把病看成是相對獨立的、靜態的;其通過一系列癥狀表現出來,故癥是病的外在呈現形式,是動態的,可以千變萬化;證則是病癥產生的根本,或者可以認為是病癥的本源,源于是證,有是病,表現為是癥。正如此,在不同的疾病或者是同一疾病的不同階段,只要表現出一致的證,便可以使用一致的治療方法,中醫看待疾病并不是只看疾病本身,而是透過疾病的癥狀表象挖掘其背后的發病機制,有是證便用是藥,所以對于高血壓和低血壓這2個看起來表現相反、本應治療相反的疾病卻采用了相同的治療方法并且效果都頗為明顯。
3.2 關于補中益氣湯補中益氣湯出自《脾胃論》,是李東垣所創,具有補中益氣、升陽舉陷的功效,是治療脾胃病補益類的代表方劑[6],脾胃為后天之本,對人體臟腑正常生理機能的發揮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東垣認為“內傷脾胃,百病由生”,所以百病皆可從脾胃論治;脾胃衰的核心機制皆可歸于中氣虛損、中陽不生,故補益中氣、生發陽氣是治療的重要環節。李主任認為,補中益氣湯治療的主旨是調理人體之氣機、充養人體之元氣,其病位涉及中焦及上焦,一方面,脾胃為氣機升降之樞,氣機升降正常,陽氣才能得以升展,元氣才能得以流轉,元氣主一身之正氣,正氣即中氣,亦是后天脾胃之氣,補中益氣湯正是通過加強脾的升清陽氣之能而降濁陰之氣、使中焦升降有序而達到協調脾胃功能、充實元氣。另一方面,從補中益氣湯的組成看,方中以黃芪、人參、甘草、白術為主藥,在補脾升陽的同時重用黃芪意在培土生金、開啟上焦,以柴胡、升麻、陳皮為輔藥,性既升也散,是引陽氣上升、補上焦之元氣,所以統觀全方是提中焦并開上焦。故而在此基礎上,老師認為此治法必須有個前提,即下焦充盛、下元穩固。腎為人之先天,藏精納氣,脾為人之后天,化生氣血,精血互化,腎與脾互資互生,脾為氣之樞,腎為氣之根,腎乃真陰真陽所聚之地、元氣納藏之所,是氣化之根本,下元陰陽之氣充盛,方可開闔中焦脾胃之氣,使中焦升降有度、中陽振作、中氣充實;若中焦虛損又下元不足,只補脾胃則會空拔其氣,不但影響療效,而且還會消耗元氣,故在用藥前要注意患者有無腎虛之表現,一是有腎虛之癥狀,一是無腎虛之癥但尺脈浮大,如果二者有其一,一定要配以補腎固元之品;如果患者無腎虛之表現,也可少佐補腎益氣之品,可達到事半功倍的治療效果。在臨床中李老師用補中益氣湯時常常聯合地黃湯系列、枸杞子、桑寄生、鹿角膠、淫羊藿等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