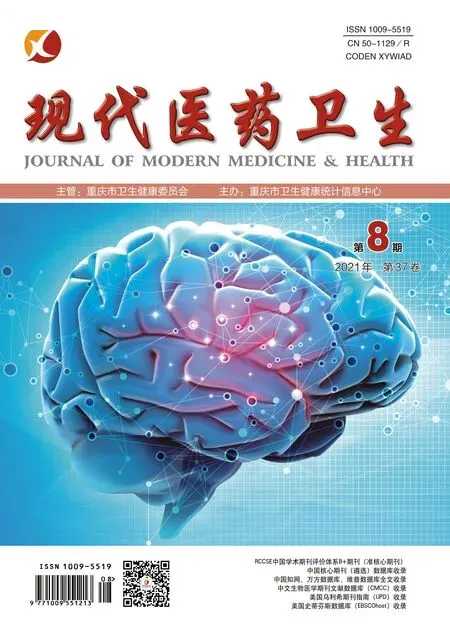兒童朗格漢斯細胞組織細胞增生癥發病機制及靶向治療研究進展
周 嬋 綜述,于 潔 審校
(重慶醫科大學附屬兒童醫院血液腫瘤中心/國家兒童健康與疾病臨床醫學研究中心/兒科學重慶市重點實驗室/兒童發育疾病研究教育部重點實驗室/兒童發育重大疾病國家國際科技合作基地,重慶 400014)
朗格漢斯細胞組織細胞增生癥(LCH)是一種罕見的以CD1a/CD207陽性的未成熟樹突狀細胞增殖為特征的炎性髓系腫瘤。LCH可發生于任何年齡段,但以兒童多發,發病高峰年齡為1~4歲,發病率為為2/100萬~9/100萬,男∶女比例為1.2 ∶1~1.4 ∶1[1]。LCH患者臨床表現多種多樣,全身各器官系統均可受累,輕者累及骨骼、皮膚、垂體和肺,重者累及肝、脾和造血系統等危險器官,肺已被證實不是危險器官。病理檢查是診斷LCH的“金標準”,典型組織形態學病理表現為特征性朗格漢斯細胞組織細胞增生。由于LCH的罕見性及異質性,其發病機制尚未完全闡明,LCH是炎癥性疾病還是腫瘤性疾病一直存在爭議。BRAF-V600E基因突變及絲裂原活化蛋白激酶(MAPK)通路的發現使LCH更傾向于是一種腫瘤性疾病。LCH治療方案的選擇主要基于患者臨床表現和治療反應,類固醇聯合長春花堿系統治療12個月(LCH-Ⅲ方案)是國際標準一線治療方案,但腫瘤再激活風險高(27.0%)[2];針對MAPK通路的靶向治療是目前積極研究的領域,對高危LCH患者可能具有重大意義。現將LCH發病機制及靶向治療最新研究綜述如下。
1 LCH起源
1973年NEZELOF首次通過電鏡發現LCH 病變組織存在特異的Birbeck顆粒[一種與郎格素(CD207)相關的細胞器],當時認為Birbeck顆粒是皮膚朗格漢斯細胞所獨有的,從而有了LCH起源于皮膚朗格漢斯細胞的假設,并導致了目前“朗格漢斯細胞組織細胞增生癥”的命名[3]。但后續研究發現,LCH細胞高表達CD2、CD11b、CD11c、CD13、CD33、CD66c、CD300LF等與髓系前體細胞有關的標志物,而低表達上皮細胞黏附分子、E-鈣黏著蛋白和CD36等與皮膚朗格漢斯細胞有關的標志物,發現LCH細胞與CD14+單核細胞分子表達一致,從而證明LCH起源于髓系前體細胞[4]。
2 LCH發病機制
2.1白細胞介素-17(IL-17)/IL-17A受體通路 LCH病理活檢發現,LCH病變組織不僅含LCH細胞,還含有各種炎癥細胞,包括T淋巴細胞、巨噬細胞、漿細胞、嗜酸粒細胞、破骨細胞樣多核巨細胞、中性粒細胞、自然殺傷細胞等,這些細胞產生大量的細胞因子,如粒細胞-巨噬細胞集落刺激因子、干擾素-γ、腫瘤壞死因子-α、IL-1α、IL-2、IL-3、IL-4、IL-5、IL-7、IL-10、IL-17等,與LCH細胞表達產生的趨化因子及其配體相互作用,形成細胞因子風暴,在LCH細胞的擴散遷移及炎癥細胞的募集中具有重要作用[5]。IL-17/IL-17A受體不僅可通過誘導成骨細胞的核因子-JB受體激活劑導致LCH溶骨性骨損害,還與其他細胞因子協同作用,通過誘導促炎性細胞因子和趨化因子的釋放加重組織炎癥,并上調生長因子、抗菌肽和基質金屬蛋白酶,促進肉芽腫形成和神經進行性退變[6]。有研究表明,IL-17A表達水平與進行性神經變性LCH(ND-LCH)的發生有關[7-8],IL-17A有望作為ND-LCH的生物標志物,為檢測和監測ND-LCH提供新方法,為ND-LCH患者的精準治療提供新靶點。
2.2MAPK通路 隨著近十年二代基因測序技術的快速發展,MAPK通路的激活在幾乎所有的LCH病例中被發現,表明MAPK通路的激活可能是LCH的關鍵致癌驅動因素。MAPK通路中最常見的突變基因為BRAF-V600E(50.0%~60.0%),其次為 MAP2K1(20.0%~30.0%)[9]。此外,其他RAF家族成員(如ARAF)、MAP3K1等基因突變也逐漸被報道。
2.2.1BRAF-V600E基因突變 有學者報道了57.0%的LCH患者病變中存在BRAF-V600E基因突變,隨后在幾個獨立的隊列研究中證實了LCH病變中BRAF-V600E基因突變的高發生率[10]。BRAF-V600E基因突變的發現為LCH是克隆性腫瘤性疾病提供了強有力的證據。BRAF基因位于染色體7q34上,是一種致癌基因,編碼RAF家族絲氨酸-蘇氨酸激酶,在MAPK信號通路的3個RAF亞型(ARAF、BRAF、CRAF)中具有最高活性。BRAF基因的突變譜廣泛,最常見的是位于外顯子15上600位的纈氨酸密碼子突變(V600E突變),其參與調控細胞的增殖、存活、分化和凋亡。小鼠動物實驗模型表明,BRAF-V600E基因突變通過促進樹突狀細胞有絲分裂驅動小鼠LCH樣疾病的發生[11]。隨后有研究表明,BRAF-V600E基因突變可抑制趨化因子受體7和增加B細胞淋巴瘤/白血病-2樣蛋白的表達,抑制樹突狀細胞的遷移和凋亡[12-13]。關于BRAF-V600E基因突變對LCH臨床特征的影響,多項研究表明,BRAF-V600E基因突變與LCH患者年齡(<2歲)、皮膚和危險器官(肝、脾、血液系統)受累、中樞神經系統相關后遺癥(尿崩癥、神經退行性疾病)、一線長春花堿-類固醇化療耐藥性、再激活風險增加等顯著相關[13-16]。但這一發現并未在所有研究中得到證實,一項日本學者進行的研究表明,BRAF-V600E基因突變與LCH患者危險器官受累有關,但與性別、年齡、一線治療耐藥性等臨床特征無關[9]。研究結果的差異考慮與遺傳背景不同有關。有研究還表明,外周血循環中的無細胞BRAF-V600E(cf BRAF-V600E)水平與LCH疾病嚴重程度有關,且在化療期間cf BRAF-V600E仍為陽性的LCH患者更有可能再激活[17-18]。北京市兒童醫院的一項研究表明,在LCH確診時、6周(首次誘導治療后)、12周(第2次誘導治療后)、52周(一線治療維持治療結束)、8個療程(二線治療強化治療結束)4個時間點的cf BRAF-V600E水平存在差異,cf BRAF-V600E水平與LCH的無進展生存率有關[19]。cf BRAF-V600E可作為判斷LCH疾病程度和治療反應的指標,有望成為LCH的一個有前途的非侵入性的生物標志物(液體活檢),有益于LCH患者管理和疾病評估。因此,應密切關注確診及治療過程中cf BRAF-V600E水平的動態變化。
2.2.2MAP2K1基因突變 除BRAF-V600E基因突變外,MAPK通路中的其他基因突變也相繼被發現,且不同突變之間是互相排斥的,其中最常見的是MAP2K1基因突變。MAP2K1通路與BRAF是相同的,但其在BRAF的下游,功能上有助于激活細胞外調節蛋白激酶,MAP2K1基因突變與危險器官受累、一線治療耐藥性有關[9,20]。
2.3LCH其他可能的驅動因素 除上述發病機制外,TP53、U2AF1、KIT基因突變及磷酸肌醇-3激酶/蛋白激酶B/哺乳動物雷帕霉素蛋白(PI3K)通路激活可能也是LCH的驅動因素。有研究表明,TP53突變的LCH患者均同時存在BRAF突變,考慮到TP53基因突變可能與癌癥患者不良預后或治療反應差有關,TP53突變和BRAF突變的共同出現可能有助于解釋已報道的與BRAF突變LCH相關的高危特征和對化療的短期反應較差[21]。U2AF1是一個3′-剪接位點識別因子,與骨髓單核細胞惡性腫瘤的發生有關,但U2AF1在LCH致病中的具體作用尚不清楚,尚需進一步研究[21]。皮膚受累LCH患者KIT突變率與MAP2K1相當,但KIT抑制劑——甲磺酸伊馬替尼治療皮膚LCH患者的療效性和安全性尚不確定[22]。PI3K通路是調節細胞周期的細胞內信號通路,參與了細胞增殖、分化、凋亡及葡萄糖轉運等多種細胞功能的調節,是腫瘤發生的關鍵驅動因素,已被證明與MAPK信號通路相互作用[23]。到目前為止已報道了3種PI3K途徑的改變,PICK1、PIK3R2和PIK3CA,其中PIK3CA突變在10.0%~20.0%的Erdheim-Chester病(ECD)患者中被報道,但在LCH中只有個案報道[23-24]。
3 LCH靶向治療
3.1治療現狀 LCH治療方案的選擇主要基于患者臨床表現和治療反應。孤立的皮膚病變可自發消退,只有在患者有癥狀的時候給予治療。局部類固醇是局部皮膚和骨骼疾病的一線治療方法。對多灶單系統或多系統疾病,國際組織細胞協會先后進行了LCH Ⅰ~Ⅲ方案的臨床研究,LCH-Ⅳ方案研究將持續至2025年。目前,LCH-Ⅲ方案是多灶單系統或多系統LCH標準的一線治療方案。LCH-Ⅲ方案患者的總體5年生存率為84.0%,5年再激活率為27.0%,明顯好于LCH-Ⅰ方案(分別為62.0%、55.0%)和LCH-Ⅱ方案(分別為69.0%、44.0%)[2]。LCH-Ⅲ方案包括1~2個療程的初始治療(每天口服類固醇和每周注射長春花堿連續6~12周)和后續的維持治療(每3周沖擊1次類固醇/長春花堿),總治療期為12個月;對有危險器官(肝、脾、血液系統)受累的患者在維持治療期間加入6-巰基嘌呤。阿糖胞苷、克拉屈濱、氯法拉濱等抗腫瘤藥物及造血干細胞移植也逐漸成為LCH二線或挽救性治療方案,尤其對一線治療無效的難治性多系統受累LCH和危險器官受累LCH取得了較好的療效,但治療相關毒性、高再激活率(30.0%~50.0%)及后遺癥遺留問題仍是一大難題[2]。
3.2MAPK 通路抑制劑 考慮到MAPK信號通路在所有LCH患者中均被激活,且BRAF-V600E基因突變與危險器官受累、中樞神經系統相關后遺癥、一線化療耐藥性、再激活風險等有關,針對MAPK通路突變(特別是BRAF-V600E)的個體化靶向治療似乎是一個合乎邏輯的選擇,特別是對高危LCH患者(累及危險器官、對一線治療無反應)而言可能具有重大意義,也是一個目前積極研究的領域。BRAF抑制劑——威羅菲尼、達拉菲尼和絲裂原細胞外信號調節激酶(MEK)抑制劑——曲美替尼已用于難治性復發性LCH患者的臨床治療。
威羅菲尼是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準的第一種用于惡性黑色素瘤的選擇性BRAF抑制劑,并于2017被批準用于治療ECD。HAROCHE等[25]首次將威羅菲尼用于3例攜帶BRAF-V600E突變的多系統難治性ECD患者,其中2例患者同時合并皮膚或淋巴結受累LCH,3例患者治療后臨床癥狀明顯改善,LCH皮損迅速消失,初步顯示了威羅菲尼的療效。隨后出現更多的威羅菲尼治療LCH的文獻報道,所有患者的臨床癥狀和疾病活動均迅速減輕或停止,并經代謝檢查、組織病理學或影像學檢查證實。1例多系統LCH嬰兒在3 d后皮損減輕,60 d后完全緩解;90 d皮膚再激活,再服用威羅菲尼2個月后完全緩解[26]。1例顱骨、垂體受累LCH嬰兒在1周后癥狀改善,1年后完全緩解;1年6個月顴骨及垂體再激活,再服用威羅菲尼6個月后完全緩解[27]。同時,威羅菲尼的藥物安全性問題也得到了關注。一項對美國成人的研究表明,威羅菲尼治療LCH常見的不良反應包括關節痛、斑丘疹、疲勞、脫發、QT間期延長、皮膚乳頭狀瘤和角化過度等,還發現所有患者至少有1次不良事件導致減量和(或)停止治療,包括1例患者被認為與治療相關的KRAS突變乳頭狀甲狀腺癌[28]。DONADIEU等[29]最近進行的一項關于威羅菲尼在BRAF-V600E陽性、難治性兒童LCH中的治療反應和安全性研究表明,54例LCH患者服用威羅菲尼20 mg/(kg·d),70.4%完全緩解,29.6%部分緩解;血清威羅菲尼水平為10~20 mg/L,安全、有效;最常見的不良反應是皮疹(74.0%),未發現繼發性皮膚癌;停止威羅菲尼治療后LCH再激活率高達80.0%(24/30),復發時間較短(中位0.9個月)。表明威羅菲尼具有良好的臨床療效,但并不能根除腫瘤克隆,多數LCH患者停止威羅菲尼治療后存在較高的再激活風險。
除威羅菲尼外,另一種BRAF抑制劑——達拉菲尼也用于LCH的靶向治療,且有研究表明,服用達拉菲尼不良事件發生率較威羅菲尼低[30-31]。有學者報道了1例皮膚胃腸道受累LCH患者服用達拉菲尼后皮損減輕、胃腸道癥狀緩解[32];1例神經系統受累LCH合并ECD兒童數天后臨床癥狀緩解,2個月后影像學檢查顯示顱內病變范圍縮小[33];4例LCH合并繼發性嗜血細胞性淋巴組織細胞增生癥的嬰兒8周后臨床癥狀完全緩解,影像學/活檢顯示病灶改善,其中1例嬰兒達拉菲尼停藥后臨床持續緩解,1例嬰兒達拉菲尼停藥10個月后中樞神經系統再激活,轉用曲美替尼治療[31]。KIERAN等[34]進行的一項達拉菲尼治療BRAF-V600E陽性兒童惡性腫瘤的臨床試驗結果顯示,27例兒童(低級別膠質瘤15例、高級別膠質瘤 8例、LCH 2例、神經母細胞瘤1例、甲狀腺乳頭狀癌1例)口服達拉非尼3.00~5.25 mg/(kg·d)均耐受性良好,最常見的藥物不良反應為斑丘疹和關節痛(均為7.4%),沒有患者因藥物不良反應而停止治療,也沒有成人報道的繼發性皮膚鱗狀細胞癌的發生。
此外,MEK抑制劑——曲美替尼治療LCH也有部分病例報道。1例攜帶MEK1突變的多系統LCH患者服用曲美替尼1個月后皮疹完全緩解,尿崩癥顯著改善,但停止治療后再次出現皮疹,需重新治療[35];1例攜帶MAP2K1突變的肺LCH患者服用曲美替尼1個月后呼吸困難改善,6個月后呼吸困難消失,影像學檢查改善[36];6例攜帶BRAF-V600E或MAP2K1突變的LCH患者使用曲美替尼(0.0125~0.018 mg/kg)聯合BRAF抑制劑或單用曲美替尼治療可達到完全或部分緩解[37]。
4 小 結
LCH發病機制目前尚不明確,基于LCH細胞的克隆性、BRAF-V600E基因突變及MAPK通路的發現,LCH更傾向于是一種腫瘤性疾病,目前認為LCH是一種炎性髓系腫瘤。目前,LCH治療方案的研究重點是降低再激活率、優化早期搶救方案和預防晚期后遺癥。針對BRAF-V600E/MAPK通路的個體化靶向治療是一個活躍的研究領域,高危LCH患者可能是理想的靶向治療對象。目前,臨床證據仍然有限,且主要來自對成人患者的研究,需對兒童進行更多的研究,以解決最相關的問題(不良反應的范圍和嚴重程度、適宜的劑量、適宜的治療時間、單藥治療的效果、再激活后治療方案等),然后再進行更廣泛的臨床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