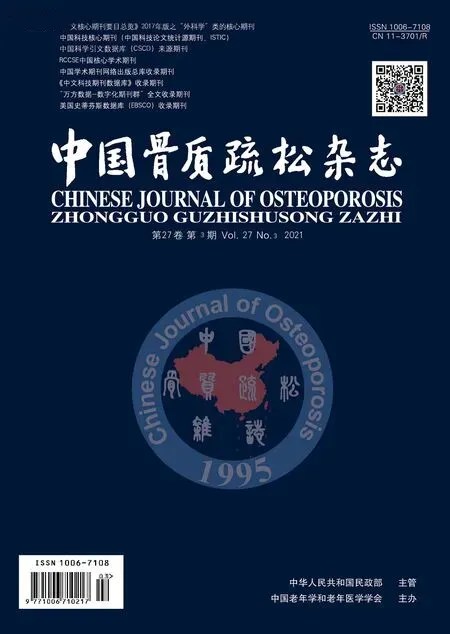系統性紅斑狼瘡相關骨質疏松危險因素的研究進展
金迪 王玉偉 安穎 劉建忠 王小磊
1.濰坊醫學院附屬益都中心醫院風濕免疫科,山東 青州 262500 2.濰坊醫學院附屬益都中心醫院心內科,山東 青州 262500 3.濰坊護理職業學院,山東 青州 262500
近年來,研究發現SLE患者骨質疏松發病率升高[1],SLE繼發骨質疏松的傳統危險因素有高齡、女性、絕經及低體重等[2]。1999年至2012年,英國Rees等[3]開展了一項大規模研究,研究發現SLE患者骨質疏松的發病率較普通人群增加2.53倍。近期一項Meta分析發現SLE的骨質疏松患病率為16 %[4],SLE患者骨質疏松性骨折發生率是非SLE患者的1.78倍[5]。Tedeschi等[6]最近報道,在47 709例SLE中發現骨折風險增加3倍,除外糖皮質激素的影響后只降低部分患者骨折風險。
SLE患者容易合并骨質疏松,除傳統危險因素的作用外,還有多個因素共同參與,本文將從SLE疾病相關炎癥反應、代謝、內分泌、自身抗體、遺傳因素以及藥物影響來探討SLE相關骨質疏松危險因素的研究進展。
1 疾病相關炎癥反應
SLE的系統性炎癥會增加骨吸收和減少骨形成,主要由IL-1、IL-6、IL-17和腫瘤壞死因子(TNF)-α介導的炎癥反應可促進破骨細胞分化并抑制成骨細胞活性,從而導致骨量丟失[7-8]。于1999年,Teichmann等[9]開展了一項關于絕經前期女性SLE患者的研究,納入研究對象均為近期診斷且未經治療的患者,研究發現患者體內骨形成的指標——血清骨鈣素水平減低,尿液中檢測到骨吸收的代謝產物增多,提示SLE疾病本身會影響骨代謝。Petri[10]研究發現低C4水平能預測脊椎的骨量丟失,而低C4水平作為狼瘡活動的一個重要指標,這提示系統性炎癥在SLE患者骨質病變中的作用。Zhu等[11]開展一項研究,對125名中國女性SLE患者隨訪5年,研究發現隨訪期間患者髖部出現明顯的骨量丟失,SLE的疾病活動度(SLEDAI評分)與SLE骨量丟失明顯相關,也支持系統性炎癥促進SLE骨量丟失的假說。
免疫系統異常激活改變成骨細胞和破骨細胞之間的平衡從而影響骨重建,導致骨質疏松。在骨質疏松發病中起主要作用的是骨代謝的信號傳導途徑護骨素(OPG)、核因子-κβ受體活化因子(RANK)、核因子-κβ 受體活化因子配體(RANKL) 分子及相關的信號傳導通路組成的 OPG/RANKL /RANK系統,此信號傳導通路參與調節破骨細胞的分化成熟,是成骨細胞與破骨細胞相互作用的重要途徑。免疫調節功能紊亂以及T、B 細胞功能異常是SLE的重要特征,T、B 細胞功能異常導致OPG 和RANKL基因的表達異常可能是引起SLE患者骨量減少的原因之一[8]。
SLE血清中炎性因子能誘導并促進RANKL表達,RANK與受體RANKL結合后,促進破骨細胞前體細胞分化為成熟的破骨細胞,刺激破骨細胞活性,進而促進骨吸收。同時,TNF-α能夠促進骨吸收及骨基質膠原合成,減弱成骨細胞對維生素D的轉錄反應性,抑制細胞外基質沉積并刺激基質金屬蛋白酶的合成,從而降解有機骨質。另外,SLE患者體內氧化型低密度脂蛋白 (oxidized low-densitylipoprotein,Ox-LDL) 水平升高,Ox-LDL能夠活化T細胞,誘導RANKL和TNF-α的升高,促進骨質疏松的發生。近年來研究發現,在SLE病情活動時,TNF、ox-LDL水平明顯升高,激活T細胞可誘導RANKL和TNF-α升高,RANKL和TNF進一步促進破骨細胞分化和活性[12]。RANKL和OPG比值異常與低骨密度有關,最近一項關于SLE兒童的研究發現血清RANKL/OPG比值升高是導致骨量減少的危險因素[13]。
2 代謝因素
動脈粥樣硬化和骨質疏松是SLE患者常見的合并癥,盡管動脈粥樣硬化和骨質疏松病理機制不同,但它們存在雙向相關性:一方面,骨量減少的患者發生心血管事件危險增加,SLE患者骨密度減少是早期冠狀動脈鈣化的獨立危險因素;另一方面,有心血管疾病的女性患者發生骨質疏松及骨折的風險也升高。
研究發現男性、絕經前和絕經后女性患者中均發現血清LDL和三酰甘油水平與腰椎和髖部的骨密度呈顯著負相關[14]。血清LDL是動脈粥樣硬化性疾病的傳統危險因素,在動脈粥樣硬化發生和發展的病程中發揮重要作用。動脈粥樣硬化和骨質疏松具有潛在聯系,血清LDL水平可能作為兩者共同的危險因素。健康女性患者減少脂肪攝入、控制血清LDL水平可維持較高的骨密度[15]。之后,于2015年我國發表一項研究納入119名未經治療的女性SLE患者,并測定脊柱和髖部的骨密度,該研究也發現患者骨密度與血清LDL水平呈負相關[16]。此項研究認為未經治療的女性SLE患者血清LDL水平越高,其脊柱和髖部的骨密度越低。
此外,SLE患者普遍存在維生素D缺乏,是引起SLE骨量丟失的重要代謝因素[17]。荷蘭SLE患者的一項橫斷面研究發現血清25-羥基維生素D水平減低與脊柱骨密度低明顯相關[18]。荷蘭開展一項6年的前瞻性研究,納入126例SLE患者,發現血清25-羥基維生素D水平減低是脊柱和髖關節的骨質疏松的獨立危險因素[19]。SLE患者對紫外線不耐受,避免陽光照射并使用防曬霜[20],進而會減少皮膚中維生素D的合成。深膚色的SLE患者黑色素較多,更大程度上阻礙紫外線吸收導致維生素D產生進一步減少。SLE患者中,非洲裔美國人比白種人血清維生素D水平低[21]。另外,SLE患者發生腎衰竭后會導致1,25-二羥基維生素D水平減低,有研究發現血清肌酐水平高與1,25-二羥基維生素D水平減低相關[22]。有高達60 %的SLE患者在病程中可能合并狼瘡腎炎,甚至發生腎功能不全。嚴重的腎衰竭患者會出現繼發性甲狀旁腺功能亢進,進而促進破骨細胞增多、骨質溶解,也會出現血清1,25-二羥維生素D水平下降,影響腸道鈣吸收,最終引起骨量丟失。此外,長期糖皮質激素治療可以影響維生素D的代謝。近期一項研究納入43名維生素D缺乏的SLE患者并隨訪12周,研究發現與安慰劑組相比,每天補充2 000~4 000 IU維生素D的患者骨轉換指標無明顯變化,此研究提示SLE患者額外補充維生素D對骨代謝的短期影響可能并不顯著[23]。
3 內分泌因素
絕經是骨質疏松和脆性骨折的危險因素,性激素對骨質代謝有保護作用,絕經后SLE患者發生骨質疏松和相關骨折的風險增加[24]。與同性別、同年齡段健康人群相比,SLE患者雌激素水平較高,雄激素水平減低,脫氫表雄酮(DHEA)的水平也減低。而且,在SLE疾病活動時,DHEA較緩解期更低。隨著年齡增加,大多數人DHEA水平逐漸減低會引起骨量丟失,這也是老年人發生骨質疏松的原因之一。SLE患者雄激素水平減低要比雌激素升高對骨代謝的作用更加明顯,所以會出現骨量丟失甚至骨質疏松。絕經后SLE患者比絕經前更容易發生椎體壓縮性骨折。Formiga 等[25]研究發現絕經前女性SLE患者骨量丟失與DHEA水平減低相關,這也為應用DHEA治療SLE相關骨質疏松提供依據[26]。選擇性雌激素受體激動劑如雷洛昔芬常用于絕經后SLE患者維持骨密度治療。
4 自身抗體
Mok等[27]開展了一項關于中國絕經后女性SLE患者的橫斷面研究,發現抗Ro抗體陽性患者髖部骨量減低,抗Sm抗體陽性的患者髖部骨量相對較高,考慮其原因可能是抗Ro抗體陽性患者往往被建議在日常生活中避免日曬,從而導致骨量減少,該研究還發現抗dsDNA抗體與SLE骨質改變關系不大。另外,4 %的SLE患者體內檢測到抗維生素D的自身抗體,但是它們的臨床意義尚不清楚[28]。目前有關SLE患者自身抗體對骨代謝的研究較少,SLE骨質疏松與其他自身抗體之間的相關性仍需要深入研究。
5 遺傳因素
研究已發現攜帶FOK-1 維生素D受體(VDR)ff基因型的SLE患者血清維生素D水平要高于攜帶FF基因型的患者[29]。2015年,荷蘭Jacobs等[30]發現FOK-1 VDR ff基因型SLE患者脊椎骨密度要高于攜帶FF和Ff基因型。此外,我國也開展一項研究測量74例女性SLE患者腰椎、股骨上端的骨密度,并檢測61例女性SLE患者的維生素D受體基因型,研究發現SLE患者骨質疏松的發病率較正常人群明顯增高,但其骨質疏松的發生與維生素D受體基因型關系不明顯[31]。
6 藥物影響
糖皮質激素在SLE及其并發癥的治療中應用較普遍,對骨質的影響具有雙面性:一方面,長期或大量使用糖皮質激素會促進骨質疏松發生或發展;另一方面,糖皮質激素又能抑制全身炎癥反應對骨質的破壞作用。糖皮質激素治療與骨量變化的縱向隨訪研究相對較少,有兩項大型前瞻性研究發現SLE合并骨質疏松多見于潑尼松服用劑量達7.5 mg/d以上的患者,但是使用低劑量潑尼松治療的患者與骨質減少相關性不大[19,32]。為探討小劑量潑尼松與骨密度之間的關系,于2017年我國發表一項研究,為盡可能排除疾病活動對骨密度的影響,研究納入長期服用小劑量激素的緩解期SLE患者。其結果發現與健康對照組相比,潑尼松≤7.5 mg/d者、潑尼松7.5~10 mg/d者骨密度均減低,研究認為即使潑尼松≤7.5 mg/d長期服用也會導致骨密度明顯減低,提示長期服用激素對骨密度可能并無安全劑量[33]。
疾病活動會促進SLE患者骨量丟失,免疫抑制藥物治療尤為重要。一方面,免疫抑制藥物能夠減少疾病活動;另一方面,對于反復發作、慢性活動期需頻繁或長期應用糖皮質激素的患者來說,免疫抑制藥物的應用有助于減少糖皮質激素治療的劑量和使用時間[2]。免疫抑制劑的對骨質疏松的影響存在爭議,免疫抑制劑的使用通常表明患者存在病情活動或病情較嚴重,很難清楚地確定其對骨骼的作用。此外,Cramarossa等[1]開展的一項大規模橫斷面研究未能發現免疫抑制劑的使用與骨密度之間的相關性。
羥氯喹治療SLE對骨質的影響尚不統一。有研究認為羥氯喹通過抑制25-羥基維生素D向1,25-雙羥維生素D轉化,從而干擾骨代謝[34],另有研究卻認為羥氯喹是保護因素[2]。研究報道環孢素可能通過多個途徑影響骨代謝,環孢素和他克莫司等鈣調酶抑制劑可能導致維生素D抵抗而影響維生素D的正常生理代謝[35]。環磷酰胺導致骨質疏松的機制可能與細胞DNA的變性與破壞,蛋白質的合成代謝減少,導致骨細胞形成減少,部分骨基質合成異常有關;另外,環磷酰胺與卵巢功能不全有關,可引起絕經時間提前,間接影響骨代謝[36]。服用嗎替麥考酚酯的SLE患者與未服用此藥患者比較,兩組血清RANKL水平相近,但服用嗎替麥考酚酯組破骨細胞數量下降[37],其臨床意義尚不清楚。
7 總結
SLE治療主要是抑制疾病活動、防治器官損害。但是,隨著SLE患者骨質疏松及骨折風險增加,我們應將骨健康也作為SLE治療的一個目標。治療的主要方面是控制病情活動,抑制免疫炎癥反應。骨骼和免疫系統由共同的細胞因子及受體、信號分子和轉錄因子等調節,免疫功能紊亂影響骨重建進而導致骨質疏松。另外,動脈粥樣硬化和骨質疏松存在雙向相關性,血脂代謝對骨代謝的影響機制需深入研究。SLE患者疾病活動度對血清維生素D水平的影響以及抗維生素D的自身抗體對代謝的抑制作用仍需進一步研究。絕經與SLE多種合并癥有關,包括動脈粥樣硬化和骨質疏松,提示性激素在其中發揮作用,選擇性雌激素受體激動劑可能成為潛在的防治SLE絕經女性骨質疏松的重要藥物。FOK-1維生素D受體基因多態性可能與SLE患者合并骨質疏松有關,進一步研究有較高的臨床價值,如通過檢測基因分型可對特定人群進行針對性預防和定期評估。各種免疫抑制劑對SLE患者骨代謝的作用仍需進一步明確,制定治療方案需兼顧SLE病情活動及骨代謝情況,防治SLE骨質疏松的藥物也將成為今后的研究熱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