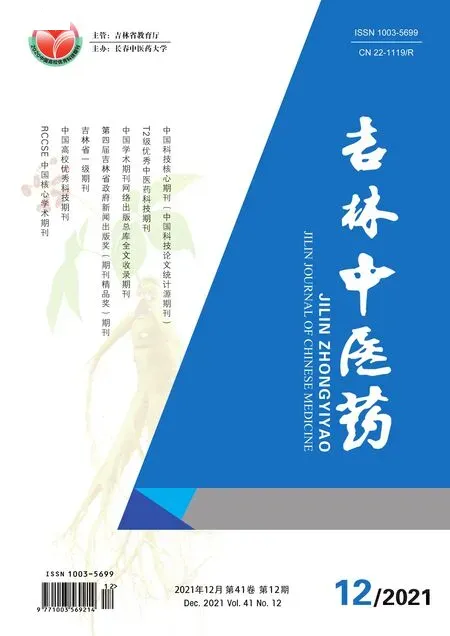灶心土的臨床應用及其用量探究
王 歡,衛若楠,朱向東
(甘肅中醫藥大學,蘭州 730000)
灶心土為燒木柴或雜草的土灶內底部中心的焦黃土塊。本品主要含硅酸(H2SiO3)、氧化鋁(Al2O3)、三氧化二鐵(Fe2O3),還含有氧化鈉(Na2O),氧化鉀(K2O),氧化鎂(MgO),氧化鈣(CaO),磷酸鈣Ca3(PO4)2等[1]。灶心土辛,溫;歸脾、胃經。具有溫中止血,止嘔、止瀉等功效。本文通過對運用灶心土的經典名方以及古今醫家臨證經驗進行整理分析,總結灶心土臨床常用劑量、配伍以及量效關系,以期對灶心土的臨床運用提供一些借鑒。
1 經典名方用量與配伍
古代醫家常用灶心土配伍不同中藥治療吐血、衄血、鮮血淋等疾病。如東漢《金匱要略》黃土湯,灶心土(半斤約110.4 g)溫中攝血,配伍白術、附子健脾溫陽止血,主治遠血,先便后血,亦主吐血,衄血。宋《十便良方》伏龍肝飲,灶心土(一兩約41.4 g,每服灶心土約1 錢,折合成現代用量約4.14 g)溫中止血,赤芍清熱祛瘀,二者配伍溫中活血止血,治療鮮血淋。唐《備急千金要方》伏龍肝湯,灶心土(五合約22 g)溫經止血,干地黃滋陰補血,二者配伍共奏溫中補血止血之功,治療崩中下血赤白相間,或如豆汁。宋《太平惠民和劑局方》伏龍肝散,灶心土(一兩約41.4 g,每服灶心土約0.35 錢,折合成現代用量約1.44 g)溫經止血,赤石脂收斂止血,二者配伍共奏溫中止血之功,治療婦女氣血勞傷、沖任脈虛所致的經血非時而下。宋《圣濟總錄》伏龍肝丸,灶心土(半兩約20.7 g,每服灶心土約0.6 錢,折合成現代用量約2.5 g)溫中降逆止咳,豆豉化痰止咳,二者配伍加強止咳之功,主治暴嗽。
2 名老中醫灶心土用量及配伍經驗
2.1 于己百 于己百提出肝氣犯胃型妊娠呃逆治法以疏肝解郁,降氣止呃為主的觀點,認為女子生理以肝為先天,易發生肝失條達、情志失調,孕期肝藏血功能不足,則更易發生肝郁氣滯、肝氣強盛、陰虛陽亢的病理變化,而肝失條達、疏泄失職,肝氣犯胃,胃氣亦會逆上,運用灶心土煎液煎煮逍遙散可治療各種類型的妊娠呃逆,其中灶心土溫中散寒止血,止嘔止呃,能“妊娠護胎”,配伍柴胡溫中疏肝降逆,灶心土用量為30 g[2]。
2.2 陳昭定 陳昭定提出小兒泄瀉臨床宜辨寒熱虛實,謹守病機的觀點,認為小兒泄瀉病因病機是脾胃虛弱為本,外邪、藥物、飲食、情志等誘發因素為標,病位在脾胃、大腸,久及傷腎,寒熱虛實,小兒病情易發生演變。常采用灶心土配伍赤石脂、肉豆蔻治療小兒虛寒型泄瀉,其中灶心土收斂止瀉,赤石脂收斂固澀止瀉,肉豆蔻溫中健脾止瀉,合而用之,共奏運脾止瀉,溫中澀腸之功,灶心土用量多為10 g[3]。陳老認為小兒潰瘍的病機是脾胃虛弱,氣血失調,氣滯血瘀,雖常以腹痛就診,但多有出血,“離經之血必為瘀血”,而出血之源頭多為蘊熱,故當務之急是清蘊熱以止血,散瘀滯以暢瘀血,常用灶心土收斂止血,燥濕生肌,配伍青黛、紫草清熱燥濕,活血止血,灶心土用量多為10 g[4]。
2.3 王應麟 王應麟提出治療小兒泄瀉要以扶正固本,固護脾胃為主,認為小兒胃腸非常脆弱,泄瀉最容易傷害胃腸,對于虛寒性泄瀉應扶脾助胃,溫中固腸,常用灶心土溫補而不燥,專入脾及肝,澀腸止瀉通便,配伍赤石脂溫中健脾,固腸和胃,灶心土用量多為10 g;王應麟提出小兒肝病主要病機為肝膽郁滯、濕熱,認為該病起病急,多兼表邪,小兒精氣未充,臟腑嬌嫩,易虛易實,病變傳變迅速,邪正交爭,虛實夾雜,故在解表之后,多采用清熱解毒、活血行瘀、調和肝胃、行氣解郁、消食建中、運濕退黃治之,常用灶心土調理中氣,升降氣機,配伍木香理氣止痛,健脾和胃,灶心土用量多為10 g[5]。王應麟提出小兒便秘病機雖以脾虛胃熱腸燥為主,但仍需考慮肝熱、肺火等因素,認為治療該病應以調理脾胃、平肝抑火、潤腸通便為法,而不以瀉下為安,用藥從草、木、藤、果、土等各類平和藥物入手,不傷胃、不瀉下,恢復腸道蠕動,促進排便,常用灶心土促進腸蠕動,起通便之功,甘草護胃和營,二者合用起潤腸通便之效治療小兒習慣性便秘,灶心土用量多為10 g;王應麟提出小兒嘔吐病機為胃失和降,胃氣上逆,認為嘔吐時發時止是由于小兒體質素虛,尤其是脾胃虛弱,脾陽不振,水谷熟腐運化不及,稍有飲食不慎或感受外邪即吐導致的,故常用灶心土溫中澀腸,藿香健脾止瀉,兩藥配伍加強澀腸止瀉之功,灶心土用量多為10 g[6]。
2.4 陸長清 陸長清提出糖尿病性腹瀉的病機以脾氣虛弱為本,腹瀉為標,認為治病必求于本,當從脾胃著手,而不側重止瀉,常用灶心土溫中收澀、益火散寒,配伍黨參、附子暖腎扶脾,溫陽止瀉,灶心土用量為20 g[7]。
3 方藥量效研究委員會專家用量與配伍
仝小林院士提出中滿內熱是糖尿病病人脾胃運化功能失職的直接因素,認為熱蘊中焦,阻滯氣機,升降失常,故而水谷膏濁停滯,清濁不分,混雜而下,變生泄瀉,針對此病機,治之當以健脾和胃,平調寒熱為主。常用灶心土燥濕止瀉,生姜溫中和胃降逆,訶子澀腸止瀉,諸藥合用,健脾和胃、平調寒熱以治療脾虛胃弱、寒熱錯雜導致的糖尿病胃腸功能紊亂,灶心土用量為60~120 g(未說明服用時長及配伍注意事項)[8];治療水濕內停、氣化不利導致的肺間質纖維化失代償期伴腹水,多用灶心土溫中燥濕,黨參益氣健脾,茯苓利水滲濕,三藥為伍,共奏益氣健脾燥濕之功,灶心土用量為120 g(未說明服用時長及配伍注意事項)[9]。
4 現代醫家用量與配伍
4.1 配伍大黃 沈仲賢治療中焦虛弱、胃氣上逆型十二指腸雍積癥,用灶心土降逆止嘔以散結氣,配伍大黃通利腸腑,二者合用補中運脾,下氣降逆,其中灶心土300 g(未說明服用時長及配伍注意事項),大黃10 g[10]。杜順福治療膽汁反流性胃炎,用灶心土疏肝理氣,厚土健運,配伍大黃清熱降逆通腑,二者合用疏肝清熱,健脾和胃,其中灶心土30 g,大黃10 g[11]。牛忻群治療鼻衄、便血、十二指腸球部潰瘍出血、帶下色白清冷,用灶心土燥濕止血,配伍大黃清熱解毒,二者合用清熱止血,灶心土用量多為300 g(水煎取澄清液,未說明服用時長及配伍注意事項),大黃用量多為10 g[12]。
4.2 配伍附子 于世樓治療血小板減少性紫癜和過敏性紫癜,用灶心土溫中止血,配伍炮附子溫里祛寒,二者合用散寒止血,其中灶心土60~68 g,附子3 g[13]。印會河治療心腎陽虛、水氣不化型風濕性心臟病,用灶心土溫中散寒,配伍熟附片補火助陽,二者合用溫陽散寒,其中灶心土用量多為120 g(煎湯代水,未說明服用時長及配伍注意事項),熟附片用量多為30 g(未說明服用時長及配伍注意事項)[14]。
4.3 配伍血余炭 王濤治療脾陽虛、血失統攝型鼻衄、婦女月經過多及胃腸道出血,用灶心土溫脾養血,配伍血余炭止血化瘀,二者合用健脾攝血,灶心土用量多為15 g,血余炭用量多為15 g[15]。
4.4 配伍蓮子肉 宋祚民等治療脾虛胃敗,肝氣橫逆型小兒慢脾風,用灶心土溫中止瀉,配伍蓮子肉補脾止瀉、益腎固精,二者合用燥濕健脾和胃,灶心土用量多為10 g,蓮子肉用量多為10 g[16]。
4.5 配伍仙鶴草 邵昕昕治療功能性子宮出血,用灶心土溫中止血,配伍仙鶴草收斂止血,二者合用加強止血功效,灶心土用量多為30 g,仙鶴草用量多為30 g[17]。
4.6 單用 黃立中治療氣血虧虛型宮頸癌并發尿血,認為大劑量灶心土單用能溫陽固攝止血,灶心土用量為500 g(用約2 L 水單藥煎煮1 h,靜置沉淀后取清液,如茶而飲,頻頻續服,同時服用益氣養血止血中藥,血止2 天后停服);治療肺癌并發咳血,認為大劑量灶心土能平肝降氣,降火止血,灶心土用量為800 g(將灶心土火燒約1 h 后,用約2 L 開水澆漬,取漬水微溫,頻頻而服,每天按此法服用,期間停服其他中西藥)[18]。李干民等治療神經性失眠癥,單用灶心土調和中焦,強力鎮靜,灶心土水煎劑為20 mL[19]。謝作鋼治療中焦虛寒、血失統攝型經期皮疹,灶心土溫中止血,于月經來潮前1 周早晚各50 g 搗碎,開水沖服,連服2周為1 個療程,3 個療程即愈[20]。
5 小結
綜合歷代經典方劑和現代名家經驗,總結出湯劑中灶心土臨床用量范圍為4.14~800 g,常用劑量為10~30 g,煎湯代水劑量為60~120 g,丸、散劑中灶心土的臨床用量范圍為1.44~2.5 g。根據疾病、證型、癥狀,選擇灶心土最佳用量與配伍,如灶心土行氣通便常配伍甘草,用量為10 g;調理中氣、降逆止咳、升降氣機常配伍木香、大黃等,湯劑常用量為10~30 g,丸劑為2.5 g;溫中燥濕止瀉常配伍肉豆蔻、訶子、肉桂等,用量為10~300 g。溫胃止嘔常配伍柴胡、藿香等,用量為 10~300 g。溫中攝血常單配伍肉桂、白術、大黃等,用量為110~300 g。溫經止血常單用或配伍赤石脂、肉桂、干地黃等,湯劑常用量為4.14~500 g,散劑為1.44 g。平肝降火,降氣止血常單用,用量為800 g。
現代藥理研究證實灶心土具有止嘔、吸附血氨、凝血等藥理作用[21-23]。臨床運用灶心土雖安全劑量范圍較廣,常用湯劑用量下(10~300 g)未見明顯毒副作用,但本品在使用過程中仍應注意其不適用人群(陰虛失血及熱證嘔吐反胃忌服。陰虛吐血者不宜用,癰腫毒盛難消者,不得獨用;無濕勿用)。臨床運用本品時應當綜合多方面考慮,根據患者疾病的具體證型、癥狀,選取最佳劑量及配伍藥物,以提高臨床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