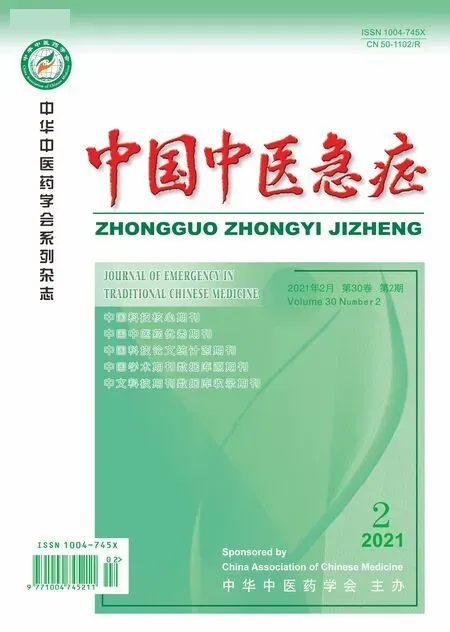“風毒”立論治療吉蘭-巴雷綜合征?
王 達 劉涌濤 張 洋 石鑒泉 石志超
(1.遼寧省大連市金州區中醫醫院,遼寧 大連 116100;2.大連醫科大學附屬第二醫院,遼寧大連 116000;3.石志超全國名老中醫藥專家傳承工作室,遼寧 大連 116000;4.遼寧省大連市中醫醫院,遼寧 大連116013)
吉蘭-巴雷綜合征(GBS)又稱急性炎癥性脫髓鞘性多發性神經病,表現為急性對稱性弛緩性肢體癱瘓,嚴重可累及肋間肌和膈肌導致呼吸麻痹死亡,少數患者遺留持久的神經功能障礙,是神經內科常見的臨床危重急癥。可以歸屬于中醫學“痿證”范疇。本章主要討論中醫以“風毒”論治痿證,對其病因病機的認識和臨床體會,主張病證結合,衷中參西,標本兼顧,可以拓展臨床痿證辨證的新思路。
1 中西醫治療方式及其缺點
GBS又稱急性炎癥性脫髓鞘性多發性神經病,一組急性起病的自身免疫性周圍神經病,主要累及神經根、周圍神經甚至顱神經,以四肢對稱性無力,反射減退或消失為主要臨床表現。病理改變是由于病原體的某些組分與周圍神經髓鞘的某些組分相似,機體免疫系統發生了錯誤識別,產生自身免疫性T細胞和自身抗體,針對周圍神經組分發生免疫應答,引起周圍神經髓鞘脫失。并且周圍神經組織中小血管周圍淋巴細胞侵潤與巨噬細胞浸潤,神經纖維出現節段性脫髓鞘和軸突變性,主要損害多數脊神經根和周圍神經,也常累及腦神經。GBS主要特點:腦脊液檢查見蛋白-細胞分離特征;神經電生理則表現為周圍神經傳導速度減慢,傳導阻滯和波形離散。金標準為病理診斷,包括有髓鞘纖維多灶性脫髓鞘炎性細胞浸潤等。臨床主要表現為:急性四肢遠端對稱性無力,很快加重并向近端發展,顱神經可受累,甚至為首發癥狀,可合并心動過速、自汗、血壓異常等自主神經功能障礙,嚴重可累及肋間肌和膈肌導致呼吸麻痹,死因主要為呼吸功能不全、肺部感染、自主神經功能障礙和心臟驟停,死亡率在3%~7%。發病后6個月仍有20%GBS患者在無輔助下仍不能走動,成人患者常遺留持久的神經功能障礙,嚴重影響日常活動和生活質量。
臨床常見的西醫治療包含多學科的醫療照顧和免疫治療(免疫球蛋白、血漿置換及糖皮質激素治療等),雖然能夠有效抑制免疫反應,同時清除致病因子,預防疾病持續發展,但部分患者長時間治療后可能產生一定局限性,甚至增加并發癥發生率,提升對患者的傷害,同時延長康復時長。隨后中醫技術快速發展,中醫學認為本病歸于“痿證”范疇,《素問玄機原病式·五運主病》云“痿,謂手足痿弱,無力以運行也”[1]。痿證指肢體筋脈弛緩、軟弱無力,不能隨意運動或伴有肌肉萎縮的一種病證,臨床以下肢痿弱常見,亦稱痿躄。中醫學認為痿證總以虛為本,以起病急、發展快歸屬于感受燥熱毒邪或濕熱浸淫;起病與發展較慢歸屬于脾胃肝腎虧虛,久病入絡。另寒邪也可致萎,魏荔彤云“有冷之萎,如霜殺之則干矣”。《素問·痿論篇》提出“治痿獨取陽明”成為臨床治療痿證的重要原則,即補益后天方法。“陽明虛則宗筋縱,帶脈不利,故足痿不用也”[2]。人體全身的肌肉、筋脈都需要脾胃所運化的水谷精微來營養,肺熱傷津,耗灼胃液,胃火清則肺金肅,也是獨取陽明的臨床體現,故有“五痿皆由肺熱生,陽明無病不能成”之說[3]。此外《素問·生氣通天論》又有“因于濕,首如裹;濕熱不攘,大筋軟短,小筋弛長,軟短為拘,弛長為痿”。朱丹溪亦提出“瀉南方、補北方”[2],清熱利濕和清熱滋腎也為治痿常用大法。但相關報道中曾指出,GBS除少數患者發病前1~3周有發熱、呼吸道、胃腸道等前驅感染史,或勞累、受涼、創傷、外科手術等非特異誘因,大多僅有上感病史且無發熱又無藥物接觸史,甚至僅僅有一過性尿、便障礙為主要癥狀,亦無他癥。因此中醫臨床以肺熱、濕熱、脾虛、肝腎不足等辨證論治,難免牽強附會,削足適履,療效大都不盡人意。
2 “風毒”立論治療
2.1 “風毒”病機與用藥原則
筆者認為此類疾病的直接致病因素為風邪挾毒外襲、風邪內蘊郁滯成毒。風毒瘀濁膠結于肺更能反映其病理實質,更能反映其病性。“蓋六氣之中惟風能全兼五氣”,風寒、風火、風濕、風溫、風燥之邪挾毒侵襲于肺,多為本病發生的誘因,是為外因[4]。葉天士在《臨證指南醫案·卷四》指出“肺位居最高,受臟腑上朝之清氣,秉清肅之體,性主乎降。又為嬌臟,不耐邪侵,六淫之氣一有所著,即能致病。其性惡寒、惡熱、惡燥、惡濕,最畏風火。邪著則失其清肅,降令遂痹塞不通爽矣”。且“肺主百脈,為病最多,肺與大腸相表里,又與膀胱通氣化,故二便之通閉,肺實有關系焉”,臨證可見尿便障礙,亦是臨床提壺揭蓋治法機理[4]。“邪之所湊,其氣必虛”,正氣不足風邪易襲,不能驅邪外出,是為內因。
《素問·太陰陽明論》曰“傷于風者,上先受之”,風為陽邪善行而數變為百病之長,易襲陽位[2]。邪毒多依附于風而侵襲肺表,或內蘊久滯成風毒,郁而發熱。《靈樞·經脈篇》云“肺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胃腸道感冒亦可責之肺受風毒所致[5]。方星巖說“肺為清虛之臟,喜通利,惡壅塞,毫發不可干之”。肺葉嬌嫩,易被邪侵[6]。程國彭《醫學心悟》曰“且肺為嬌臟,攻擊之劑,既不任受,而外主皮毛,最易受邪,不行表散則邪氣留連而不解”。肺為華蓋,主皮毛,主宣發肅降,朝百脈,與他臟關系密切。肺傷則肝木無制約,木無制就會反侮土,脾土不足則后天之精無以化源,腎氣不能充盈[7]。腎水無土承制,水無制就會泛濫克火,心火不能下交腎水,腎水則不能獨化;心火無腎水制約,又火旺灼金,肺傷亦甚。可見風毒傷肺在本病的發生舉足輕重。風毒侵襲人體,損傷正氣,宣發失職,不能將脾所輸津液和水谷精微布散全身,外達于皮毛;肅降失常,不能將肺吸入清氣和水谷精微向下布散。肺為水上之源,腎為主水之臟。金水相生,經絡上密切相關,肺通調水道失職水液代謝失常,腎精不能蒸騰氣化致津液代謝障礙。肺主降而肝主升,肺降不及則肝升太過,相火上亢下劫腎陰,水不涵木筋失所養;兼肝失條達疏泄,氣機郁滯導致津液輸布障礙。肺主氣心主血,肺氣不足不能助心行血致津血運行失常。致此五臟不能潤澤,四肢筋脈、肌肉失養而弛縱,不能束骨而利關節,發為痿證。
中醫上關于痿病辨證要點包含以下幾點,其中辨虛實中起病較急,且病情發展較為迅速,患者通常肢體力弱,拘急麻木,肌肉萎縮現象不明顯,可判定成實證;而起病較為緩慢,且呈現不斷加重現象,通常患者病程較長,肢體弛緩,肌肉萎縮顯著,可判定成虛癥。另外辨臟腑發生是在熱病過程中,或者熱病后,患者伴有咳嗽咽干現象,其病變則在肺部;而患者面色萎黃不華,食少便溏,其病變在于脾胃;而起病緩慢,月經不調,腰脊酸軟,遺精耳鳴,其病變則處于肝腎。但既往治療中不論選方用藥,而利用針灸選穴,增加對脾胃調理的重視程度,但隨著醫療技術的改進,臨床應給予辨證論治,其中實邪突出者,應提供祛瘀、清熱及化濕方式達到以祛邪實目的;而正虛突出者,可提供滋補肝腎、健脾襤氣方式來恢復止氣;虛實夾雜者則扶正與祛邪兼顧。另外在邪實祛除后,應進行補虛養臟,調和氣血,濡養筋脈的治療。近年來隨著中醫水平的不斷提升,臨床經過分證論治后發現,針對肺熱津傷證,其身熱退凈、食欲衰退、口燥咽干較為嚴重者,可判定為肺胃陰傷,應選擇益胃湯加薏苡仁、山藥、谷芽等,達到益胃生津的功效,切不可使用苦寒燥濕辛溫之品。針對濕熱浸淫證,主要是由兇濕熱浸淫引起,不可急于填補,預防助濕。除濕之外還應兼施清養,不可使用辛溫苦燥之品,一旦發現患者濕熱傷陰后,可轉清滋善后。針對脾胃虛弱證,實發在中焦,若出現食滯后,可給予谷麥芽、山楂、神曲等。針對肝腎虧損證,應以補腎清熱為治療原則。針對瘀阻絡脈證,尤其是瘀血較重者,可在常規治療基礎上加入地龍、水蛭、蜈蚣、全蝎等蟲類,已達到搜剔經絡、痛經活絡的作用。隨后在臨床辨治過程中,考慮GBS發病及病機衍化皆以風邪挾毒侵襲肺表,或正氣虛弱不能逐風邪于外,內蘊成風毒最為得當,故以“風毒”立論,而其治療原則應以搜風剔毒,滋補肝腎,活血通絡為主,例如桑寄生、黃芪、柴胡、牛膝、桑枝、地龍等中藥均可運用其中,達到發散邪熱、通經活絡、益氣固表、疏肝解郁的作用。
2.2 臨床用藥對中醫辨證和治療的影響
2.2.1 激素類藥物對本病的影響 激素類藥物按中醫理論分析為補陽藥物的范疇,此類藥物久用必有助火升陽、耗竭肺腎陰液之弊。故在補陽的同時必須考慮到陽損及陰的一面,治療必用養陰之品。石師認為病患久用激素,陰陽失調,應補陰配陽,既減少激素之燥熱不良反應,又為激素替代療法,緩撤激素,應時時以顧護陰精為念。
2.2.2 β受體阻滯劑對本病脈證的影響 β受體阻滯劑主要治療高血壓、心絞痛及心律失常。抗心律失常基本藥理是阻滯β受體可以使心肌收縮力下降,收縮速度以及傳導速度減慢,并且通過阻止兒茶酚對竇房結、心房起搏點及浦肯野纖維4期自發除極,減慢房室結及浦肯纖維傳導速度糾正快速室上性、室性心律失常。此類藥物按中醫理論分析可歸為收斂藥物的范疇,此類藥物有收斂氣機作用,減弱心臟鼓動氣血力量,必見有沉遲、沉緩等表現為虛寒脈象。故在辨證尤其脈證方面可以舍脈從證。
2.2.3 宣肺搜風剔毒之品的藥理作用及臨床應用注意 從中西醫結合的角度上講,本病發病機理主要是感染后自身免疫性疾病,與機體的免疫反應、淋巴細胞浸潤、炎癥反應、髓鞘脫失等密切有關。中藥宣肺疏風剔毒之品大都具有調節免疫、抗變態反應、抗過敏之功。從“風毒”立論治療,“風毒”辨治亦當貫徹始終。故選用宣肺搜風剔毒的藥物如:桑寄生、地龍、蟬蛻、僵蠶、烏梢蛇、蛇蛻、桑枝、牛蒡子等之品,一者取其走竄之性搜風剔毒,二者又有取蟲藥之以毒攻毒之意,每獲良效。痿證多虛實夾雜互見,兼夾之證不可等閑視之,“至于活血化瘀通絡之法,近代醫家每以久病入絡立論,而實質是風毒膠結,新病即夾瘀,不單純久病而入絡”,必輔以活血化瘀通絡等法及時救治免成痼疾。然搜風剔毒、化瘀通絡之法,終屬正治八法中之“消”法范疇,正治當以“補”法為主,搜風剔毒、化瘀通絡之藥可用,只宜當作必不可少的治標之品貫穿病程始終。祛邪而不犯無過之地,刻刻以顧護正氣為念[8]。
3 病案舉隅
患某,男性,80歲。2019年5月20日初診。患者既往高血壓病、冠心病、心律失常房顫、心衰病史。于1個月前因突發排尿困難予導尿后現雙手麻木,左上肢疼痛,逐漸出現四肢麻木無力疼痛劇烈,于某醫院住院治療,確診為“GBS,急性炎癥性脫髓鞘性周圍神經病”。予糖皮質激素、免疫球蛋白、營養神經、抗凝,擴冠、利尿、β受體阻滯劑穩定心室率治療后,能自行排尿,四診無力癥狀略改善,麻木疼痛癥狀略減輕,出院后仍臥床不能翻身活動。入院前3 d患者又復感風寒后出現四肢麻木無力疼痛加重,呼吸困難,為求中醫系統治療遂來我院。入院神經系統查體:神清,言語流利,顱神級未見異常。左側上肢肌力2級,右側上肢肌力3-級,雙側下肢肌力2級。四肢痛覺減退,腱反射未引出。西醫予抗凝、降壓、降糖、減輕心臟負荷穩定心室率(酒石酸美托洛爾50 mg/片,每次50 mg,每日2次口服)、糖皮質激素(強的松5 mg/片,每周減5 mg)、營養神經(維生素B1100 mg/支、維生素B12500 mg/支,每日1次,各1支肌注)對癥治療。刻下:精神亢奮,顏面潮紅,偶有發熱(37.4℃),口干不欲飲,胸窒如塞,四肢麻木無力,左肩背疼痛,稍動即疼痛劇烈難忍,納寐可,大便干。舌紅苔薄白少津,舌下絡脈瘀紫,脈結代沉遲無力。診斷:痿證(GBS急性期)。辨證:風毒瘀滯,肝腎陰虛,瘀血阻絡。治法:搜風剔毒,滋補肝腎,活血通絡。方藥:桑寄生30 g,桑枝6 g,地龍15 g,丹參20 g,柴胡6 g,牛膝 15 g,桃仁15 g,炒白術30 g,黃芪 20 g,黃柏 15 g,當歸 15 g,白芍 15 g,生地黃 15 g,熟地黃15 g,龜板10 g,川芎6 g,生杜仲15 g,雞血藤30 g,炙甘草15 g。7劑,每日1劑,水煎早晚溫服。二診2019年5月27日:麻木無力癥狀改善,口和,疼痛緩解,納少,時有發作性胸悶氣短,五心煩熱,二便調。舌淡紅苔薄白,脈結代遲緩。去黃芪加知母10 g,黨參15 g。7劑,日1劑,水煎早晚溫服。湯藥未盡,患者能自行站立,可緩步慢走,限于體力不能步遠。三診2019年6月3日:患者疼痛癥狀基本消失,四肢麻木無力癥狀明顯改善。去黨參、黃柏,加生山藥30 g,桃仁6 g。14劑,出院帶藥繼服。2月余后,患者可以杖助步獨自行動。
按語:治病必求其本,治療危重疑難,更當辨證求因求其本。診治之時,“審查病機,勿失病機”,以法立方。“從毒立論,頑疾皆由毒作祟”治療本病[8]。方中桑寄生、桑枝、地龍宣肺搜風剔毒,調節免疫、抗過敏、抗變態反應,地龍性寒解諸熱疾,下行能利小便兼通經絡。所謂補其肺者益其氣,予黃芪益氣固表,從太陰托里之邪毒外出,增強機體免疫功能;四物補血活血止痛;風之為患,肝木主之,兩相感召,同氣相求,歸、芍、芎和肝血,柔肝降逆,先安未受邪之地;補其腎者益其精,二地、龜板、杜仲、黃柏補腎填精,滋陰潛陽,引浮陽龍火歸宅,金水相生,肺金得潤,其令可行,能固其衛氣,陽氣外達;柴胡者,氣質輕清,苦味最薄,可和解表里,發散邪熱,亦能疏肝解郁,調暢情志,從少陽領邪外出;《甲乙經》曰“夫膽者,中精之腑,五臟取決于膽”[9],正邪相爭必取少陽,少陽為樞機,斡旋上下,攘外安內,能恢復中軸升降之職,使清陽自升,濁陰能降,陰陽調和,液道運行;柴胡、牛膝法血府逐瘀湯之義,升降氣機,活血通絡,丹參活血養血涼血,安神止痛,一味丹參功同四物;《日華子》云“通利關節”[10],現代藥理表明能抗動脈粥樣硬化,降低心肌耗氧量,增加冠脈流量[11],改善泵血功能;藤類入絡,雞血藤行血補血,舒筋活絡止痛;桃仁流通凝滯氣血止痛;使瘀祛新生;另桑枝、牛膝引藥入四肢。最后入山藥者,補益肺脾腎三臟,概因其不寒不熱,不燥不滑,有補虛祛風之長,意徐徐緩圖之,謂必得正氣至后風氣可去也;“土常不足,最無有余”[12],術、草和胃氣而健脾,補益后天,助精氣化源,培土生金,調和諸藥;先后兩天同補,諸藥相輔相成而建功。方中理法方藥直中病機,面面俱到,藥證和拍,故能獲效,體現了中醫治病謹守病機和辨證論治奧義。故依此法辨證論治,多可獲效良佳,不獨此例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