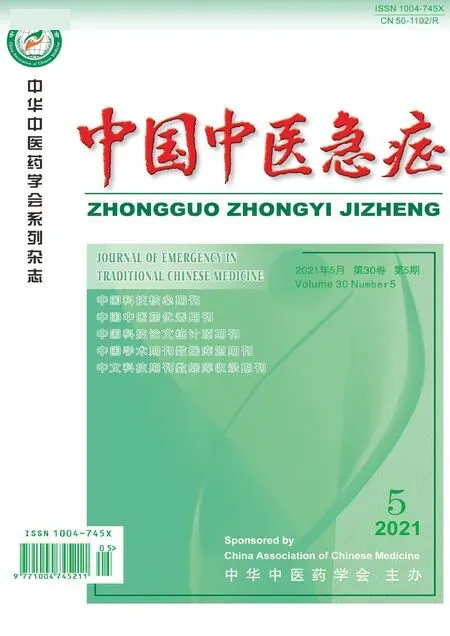中醫藥修復腸黏膜屏障治療潰瘍性結腸炎的研究進展
趙 穎 張小琴
(1.南京中醫藥大學,江蘇 南京 210023;2.南京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江蘇 南京 210029)
潰瘍性結腸炎(UC)是以腹瀉、腹痛、黏液膿血便為主要表現的慢性非特異性結腸炎,臨床上存在治愈難度大,復發率高等問題,被WHO列為現代難治病之一。雖然UC的病因和發病機制尚不明確,但腸黏膜屏障與UC發病的密切聯系已被普遍認同,修復腸黏膜屏障成為治療UC的新途徑。目前西藥治療價格較昂貴,患者經濟負擔重,且長期使用還可能產生嚴重的副作用和不良反應,近年來中醫藥治療UC已取得較大進展,在修復腸黏膜屏障、緩解臨床癥狀、減少復發等多方面具有一定優勢,受到越來越廣泛的關注。
1 腸黏膜屏障受損與UC的發病
腸黏膜屏障是腸道重要的防御體系,它通過有效隔離腸道內的有害物質以維持屏障功能的完整和腸道穩態。腸黏膜屏障目前被大致分為機械、免疫、生物、化學屏障4大類。腸黏膜機械屏障是抵抗腸道有害物質入侵和維持細胞選擇通透性的結構基礎,主要由腸上皮細胞(IECs)和細胞間緊密連接構成。腸淋巴和分泌型免疫蛋白(SIgA)構成的免疫屏障可以識別自身或者外界抗原引發機體免疫反應,是腸免疫穩態的重要保障。生物屏障是腸道內常駐菌群組成的微生態系統,不僅可以分泌保護腸道的生物菌膜,還可以酸化腸道抑制致病菌生長,產出細菌素、短鏈脂肪酸等殺滅外來菌。化學屏障由腸上皮細胞分泌的黏液糖蛋白和消化液等組成,具有潤滑、殺菌、隔離等多種作用。
許多研究證明腸黏膜屏障功能異常是UC重要的發病因素和分子基礎,甚至有學者將其形容為一種“屏障器官性疾病”[1]。機械屏障、免疫屏障、生物屏障和化學屏障都被證實參與了UC的發病。首先腸黏膜屏障受損時產生大量炎性因子,不僅誘導上皮細胞凋亡,還可通過激活某些信號通路如MLCK、PI3K/Akt、PKC等影響緊密連接蛋白的表達和分布,破壞腸黏膜機械屏障的結構,使黏膜通透性增高,導致腸腔內細菌、抗原物質向黏膜固有層移位并激活固有層免疫細胞,誘導黏膜異常免疫反應的發生。各種細胞因子的異常表達在UC的病程中也起到重要的推動作用,其中核因子NF-κB的活化是中心環節,可與IL-1、TNF-α等相互反饋產生級聯反應,使炎癥反應不斷持續和放大,是造成炎癥性腸病反復發作、難以治愈的原因之一。UC患者生物屏障的受損主要體現在腸道菌群的改變上,腸黏膜免疫系統對改變的菌群失去免疫耐受,對腸黏膜產生損傷,使細菌相關產物如短鏈脂肪酸和丁鹽酸在體內的含量減少,不僅影響了腸道的pH和腸上皮細胞的能量代謝,也可導致腸上皮細胞的凋亡。黏液層是化學屏障的重要組成之一,炎性因子、致病菌等還可以通過抑制杯狀細胞和黏蛋白影響發病,UC患者腸黏膜中的杯狀細胞減少,黏蛋白的表達降低,黏液層厚度變薄,不能有效清除腸黏膜表面細菌,不僅使細菌更容易穿過黏液層侵襲腸上皮細胞加重細胞的凋亡,還會破壞腸道微生態的平衡,容易誘導和加劇腸道炎癥的反應。綜上可見,機械屏障、免疫屏障、生物屏障和化學屏障雖然通過不同的作用機制參與了UC的發病,但腸黏膜各屏障之間相互依賴、相互協調、相互影響、共同作用,形成了統一的腸黏膜屏障保護系統,這也是中醫藥多靶點、多層面作用的優勢所在。
2 中醫藥修復腸黏膜屏障治療UC
2.1 中醫藥修復腸黏膜機械屏障 單味中藥、中藥提取物和中藥復方已在多項實驗中被證實有不錯治療效果,可以從調節腸上皮細胞、增加緊密連接蛋白和黏膜修復因子的表達等方面修復腸黏膜機械屏障。朱磊等[2]觀察了黃芩苷對UC大鼠結腸免疫炎性反應的影響,實驗結果顯示黃芩苷顯著降低了大鼠PI3K和Akt蛋白磷酸化水平,PI3K/Akt信號通路是抑制IECs凋亡的關鍵信號,故黃芩苷抑制UC腸道免疫反應可能是通過PI3K/Akt信號通路減少腸上皮細胞的凋亡達成的。張振芳等[3]使用白花蛇舌草的乙醇提取物對DSS誘導的UC小鼠進行治療,發現小鼠血清和腸組織中的核抗原ki67陽性率降低,腸黏膜炎性細胞浸潤和損傷得到明顯改善,核抗原ki67可抑制腸上皮細胞的異常增殖,說明白花蛇舌草乙醇提取物對腸上皮細胞有一定的保護作用。黃芪組成的復方在臨床中被發現對UC的療效甚佳,臧凱宏等[4]就此對黃芪提取物黃芪多糖進行研究,發現黃芪多糖可劑量依賴性升高黏膜表皮修復調節因子EGF和緊密連接蛋白Occludin和ZO-1的表達,促進腸黏膜機械屏障的修復。鹽酸小檗堿(BBR)是從中藥黃連中提取的有效成分,價格低廉,臨床應用廣泛,BBR治療后小鼠腸道干細胞標志物LGR-5、TERT和緊密連接蛋白Claudin-1、Occludin、ZO-1的的表達明顯升高,證明其減輕腸道炎癥的機制與維護腸黏膜機械屏結構的完整性有關[5]。潘燕等[6]觀察了錫類散治療活動期輕中度左半結腸UC的療效,錫類散組患者的癥狀改善和結腸黏膜愈合度明顯高于氫化可的松組,且安全性佳,后續動物實驗還證實錫類散通過上調緊密連接蛋白Occludin的表達改善黏膜愈合。韓玉娜[7]發現中藥復方改良愈瘍湯也可提高腸黏膜多種緊密連接蛋白及mRNA的表達以維持黏膜機械屏障結構的完整性,減輕結腸黏膜的炎癥損傷,抵御致病菌的入侵。
促炎因子TNF-α、IFN-γ、IL-1β等和抗炎因子IL-4、IL-10等通過影響緊密連接調控腸黏膜屏障,中醫藥治療UC的機制或許與調節細胞因子改善腸黏膜機械屏障有關。祁燕等[8]發現中藥成方潰結康對UC小鼠腸黏膜的炎癥因子和腸黏膜屏障均有影響,表現在調節促炎因子和抑炎因子的平衡減輕炎性因子對腸黏膜的損傷,還可以上調黏膜修復因子ITF和緊密連接蛋白Occuludin、Claudin的表達。馬鐵明等[9]選取大腸經募穴天樞穴、脾經大橫穴對TNBS/DSS聯合造模的UC大鼠進行艾炷灸治療,結果顯示艾炷灸可以降低UC疾病活動度,修復受損的腸黏膜上皮結構,且治療效果與灸量呈正相關,其作用機制可能與降低促炎因子IL-8提高抗炎因子IL-10,抑制NF-κBp65的轉錄下調TLR-9有關。
2.2 中醫藥修復腸黏膜免疫屏障 作為腸道的重要防御線,腸黏膜免疫屏障具有維持腸道菌群穩態、抵抗外界和自身抗原等重要作用,免疫異常引起的免疫屏障功能障礙影響了UC的發生發展。西藥免疫抑制劑如氨甲蝶呤、硫唑嘌呤、環孢素等起效較慢并且具有細胞毒性,尋找有效治療且副作用小的藥物已成為當前的治療目標。中醫藥被證實對腸淋巴和免疫球蛋白有免疫調節作用,現已成為UC治療的重要手段之一。李相玲等[10]發現中藥枸杞、苦瓜、茯苓的水提物可改善腸系膜淋巴結T、B淋巴細胞比例和促進腸系膜淋巴細胞整合素a2β7表達,整合素a2β7的表達決定淋巴細胞經腸道和淋巴組織的能力,提示上述中藥水提物可增強腸黏膜的免疫屏障功能。雷公藤的有效成分雷公藤多苷、雷公藤甲素均有免疫抑制作用,對UC有明顯療效,但由于藥物毒性限制了臨床的應用,但經過甘草炮制的雷公藤未見明顯肝毒性,治療后小鼠T細胞浸潤顯著減少,FoxP3+Treg增加,說明雷公藤通過誘導抑制性T細胞浸潤發揮腸道免疫調節的作用[11]。劉思邈等[12]觀察了以白頭翁湯加減化裁的清熱利濕方對大腸濕熱型的UC小鼠核轉錄因子和腸免疫功能的影響,結果顯示清熱利濕方不僅可以降低核轉錄因子和TNF-α以減少促炎因子對腸黏膜的損傷,還可以下調腸黏膜IgA和SIgA水平維護腸黏膜局部免疫功能,且療效與療程呈正相關。吳東升等[13]研究了芍藥湯對UC大鼠腸黏膜屏障的作用機制,芍藥湯組大鼠腸黏膜的CD4+T淋巴細胞和SIgA較美沙拉嗪組升高,芍藥湯通過改善腸黏膜淋巴細胞比率和調節免疫球蛋白水平修復腸黏膜免疫屏障,減輕腸黏膜的損傷。
2.3 中醫藥修復腸黏膜生物屏障 正常人腸道中各菌群共同生長并互相制約,若腸道菌群的動態平衡被打破,會導致機體免疫功能紊亂,是炎癥性腸病的重要發病因素。UC作為炎癥性腸病的一種,也與腸道菌群失調有密切聯系,多項研究發現UC患者存在不同程度的菌群失調,致病菌和優勢菌的比例改變,菌群的多樣性減少。中醫藥被證實對腸道菌群有較好的調節作用,能促進腸道有益菌(雙歧桿菌、乳酸桿菌等)生長,抑制有害菌(腸球菌、腸桿菌等)增殖,幫助腸道菌群恢復動態平衡,以達到減輕炎癥水平,促進黏膜修復,改善機體免疫等功效。侯天舒等[14]發現UC大鼠的糞便細菌豐度較健康大鼠降低,主要體現在雙酶梭菌增加,乳酸菌、毛螺科菌減少,而選取足三里、上巨虛、天樞穴進行針刺治療后大鼠的乳酸菌和毛螺科菌含量增加,雙酶梭菌含量減少,糞便細菌豐度得以改善,提示中醫電針治療能夠增加菌群的多樣性和豐度,促進腸道菌群恢復動態平衡。王曉梅等[15]選取雙側天樞穴、氣海穴對UC大鼠進行隔藥餅灸治療,發現灸法治療后的大鼠糞便中的有益菌(乳酸菌素、雙歧桿菌)含量明顯增加,有害菌(脆弱擬桿菌、腸桿菌)含量明顯降低,且大鼠炎癥因子TNF-α、IL-12的表達顯著降低,說明隔藥灸可改善UC大鼠的腸道菌群紊亂且具有恢復腸道微生態系統、減輕腸黏膜炎癥反應的作用,從而保護腸黏膜。
2.4 中醫藥修復腸黏膜化學屏障 杯狀細胞特異產生的黏蛋白(MUC2)三葉因子(TFF3)在化學屏障中發揮了主要的防衛作用,黏蛋白相關基因MUC13敲除小鼠經DSS誘導后出現更嚴重的結腸炎癥,上皮細胞凋亡也更加明顯,體現了黏膜化學屏障在UC中的重要性。惠毅等[16]觀察到烏梅丸能有效提高UC大鼠腸上皮組織中MUC2、TFF3的含量,推測烏梅丸可能通過促進杯狀細胞增殖分泌修復腸黏膜化學屏障。杯狀細胞近年來被發現不僅是純分泌細胞,它的數量和分泌物對維持腸道穩態具有重要作用,還參與了免疫調節[17]。臧凱宏等[18]使用當歸補血湯對 TNBS造模的UC大鼠灌胃,發現當歸補血湯可以減少未成熟杯狀細胞數量,使成熟的分泌態杯狀細胞接近正常。目前腸黏膜化學屏障在UC的研究中相對較少,仍具有較大的研究空間。
2.5 中醫藥多靶點、多層面修復腸黏膜屏障 實際上,中醫藥對腸黏膜屏障的保護作用往往不是單一、孤立的,而是對腸黏膜各屏障有多靶點、多層次的作用。中醫藥從修復腸黏膜結構、降低腸黏膜通透性、調節腸道免疫功能及腸道菌群等多方面發揮作用,最終達到修復黏膜、緩解癥狀、縮短病程、減少復發的良好治療效果。木瓜總三萜在消化道潰瘍中已被證明有較好的損傷修復作用,可能與其抑制炎癥、促進上皮細胞增加、修復黏膜屏障有關。熊興軍等[19]在此基礎上研究了木瓜的重要活性成分木瓜總三萜對UC小鼠的作用機制,發現木瓜總三萜可以上調腸黏膜屏障保護因子E-cadherin,緊密連接蛋白Occludin,黏蛋白MUC2,TFF3 mRNA的表達,對腸黏膜機械屏障、化學屏障均有作用。馬齒莧是臨床上治療UC常用的清熱解毒藥,它的有效活性成分馬齒莧多糖不僅能增加小鼠雙歧桿菌和乳桿菌數量,還能促進抗炎因子的生成,降低炎癥因子水平,提高免疫球蛋白含量,對生物屏障和免疫屏障具有雙重調節作用[20-22]。張博[23]認為腸黏膜屏障與中醫“脾為之衛”有異曲同工之妙,而經典方劑四君子湯不僅可以提高黏蛋白和三葉肽因子的表達修復大鼠化學屏障,還可增加腸黏膜sIgA的含量、CD3陽性T細胞百分比,以提高腸黏膜免疫屏障功能。
參苓白術散是止瀉常用方,首載于《太平惠民和劑局方》,具有健脾益氣、滲濕止瀉的功效,臨床常用于癥見腹痛腹瀉的脾虛濕盛患者,由于UC的主要癥狀之一就是腹瀉,所以參苓白術散對UC也有不錯的治療效果。研究表明參苓白術散可維持腸黏膜屏障結構完整、改善腸道免疫調節、促進黏膜愈合。劉玉暉等[24]發現參苓白術散可升高UC小鼠Claudin、Oc?cluding蛋白,JAM和ZO-1 mRNA,調節腸上皮細胞間的緊密連接。劉翠英等[25]認為參苓白術散調節緊密連接的機制是通過抑制NF-κB水平,減少MLCK/MLC通路的過度激活達成的,MLCK/MLC通路通過影響腸黏膜的緊密連接參與UC的發病,高表達于腸上皮細胞的長鏈MLCK激活后使MLC磷酸化作用于腸上皮細胞的肌球蛋白和肌動蛋白,使緊密連接受牽拉后開放,而核因子NF-κB的持續激活引起MLCK的轉錄,引起以上步驟的進行。在免疫調節方面,參苓白術散下調UC大鼠細胞凋亡相關基因Caspase-8和蛋白的表達,進而調節細胞因子IL-1β、IL-4含量,改善結腸黏膜免疫功能,延緩組織凋亡,促進腸黏膜組織細胞的修復[26]。李曉冰等[27]用TNBS對小鼠造模,發現參苓白術散直接影響腸系膜Treg細胞,提高了腸道CD4+CD25+Foxp3+調節性T細胞的數量,以發揮腸黏膜免疫調節的功能。黏液結合肽TFF3是近年發現的新型生長因子,與MUC2形成膠狀復合物保護腸黏膜,還能驅動上皮細胞遷移快速修復損傷腸黏膜,對上皮細胞的重組、修復有重要作用,參苓白術散還可通過上調MUC2、TFF3 mRNA表達,促進腸黏膜化學屏障損傷的修復[28]。
清腸化濕方是沈洪教授在經典方芍藥湯的基礎上化裁而來的,以清腸化濕、斂瘡生肌、調氣和血為主要功效的中藥成方,在臨床上取得良好療效,它的作用機制被證實與腸黏膜屏障有關。吳昊等[29]發現清腸化濕方可增加緊密連接蛋白ZO-1的表達,還抑制腸上皮細胞半胱天冬氨酸酶-3蛋白的表達,從而抑制腸上皮細胞凋亡,修復腸黏膜機械屏障功能。翟金海等[30]使用清腸化濕方灌腸治療TNBS造模UC大鼠,結果顯示清腸化濕方明顯降低大鼠腸組織TNF-α水平,減輕了對Claudin-1蛋白損傷,保護了腸黏膜緊密連接。顧培青等[31]探討了清腸化濕方以過氧化物酶體增殖物激活受體-γ和NF-κB為中心的作用機制,實驗結果顯示清腸化濕方不僅可以通過PPAR-γ信號通路促進MUC2和TFF3的分泌達到修復腸黏膜化學屏障的功能,還可以降低NF-κB的激活減輕腸黏膜炎性反應,有效改善UC大鼠的病變程度。
中醫特色外治療法治療UC的作用機制也可以從腸黏膜屏障進行解釋。馬喆等[32]使用隔藥灸和溫和灸大鼠“天樞”穴觀察艾灸預處理UC大鼠的作用機制,發現艾灸預處理后大鼠的Occludin蛋白、MUC2、JAN1、ZO-1蛋白明顯升高,說明艾灸對大鼠腸黏膜機械屏障和化學屏障均有保護作用,可能是艾灸有效預防減輕UC的作用機制之一。還有相關動物實驗顯示,隔藥餅灸天樞穴能抑制腸上皮細胞凋亡,調節炎癥細胞因子和腸黏膜免疫,幫助恢復腸道菌群的動態平衡,從多個屏障作用以減輕大鼠腸道炎癥反應,修復腸黏膜[33-34]。
3 總結與展望
腸黏膜屏障一直是近年UC研究的熱點之一,長期的腸道炎癥可增加結直腸癌的風險,與黏膜炎癥程度、持續時間、嚴重程度呈正相關,故促進黏膜組織愈合是UC重要的治療目標[35]。現代醫學單靶點、單通路、局部作用有一定局限性,中醫藥強調整體觀念,從多靶點、多層面修復腸黏膜屏障,具有獨特的優勢,在臨床上也取得了不錯的治療效果,為修復腸黏膜屏障提供了新的治療思路。但由于中醫藥的作用機制不明確,目前的研究集中于中藥單體和復方,且中藥提取物成分較為復雜,尚不能判定各成分是否會互相影響。相信隨著研究的深入,中醫藥對腸黏膜屏障的作用機制會越來越明確,現代醫學對腸黏膜屏障的理解可以和中醫藥進行有機整合,為臨床提供更多科學可靠的依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