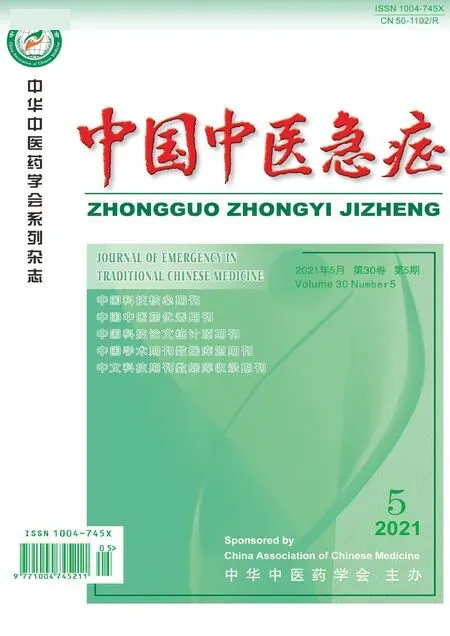經筋恢刺法治療髕股疼痛綜合征的臨床觀察
胡克萍 邢基斯 詹彩銀 李曉純 陳惠雅
(廣東省佛山市中醫院,廣東 佛山 528000)
髕股疼痛綜合征(PFPS)多是由于髕股關節軟骨的表層下出現變異,引發局部炎癥,多表現為髕前及髕周疼痛、膝關節活動受限、膝關節不穩[1],長時間屈膝久坐、跑步、久蹲等動作常易引發其急性發作。PFPS多見于運動員、士兵、登山愛好者等運動量較大人群,占運動相關膝關節損傷的25%~40.5%,女性多于男性[2]。目前認為其發病與髕周肌力失衡導致膝關節屈伸時髕骨運動軌跡不良密切相關[3]。PFPS屬中醫學“膝痹”“筋痹”范疇,中醫經筋理論認為其發病與筋骨失衡相關,既往循證醫學證實經筋針刺有利于改善膝關節周圍肌肉張力,提高肌群協調性,恢復筋骨平衡[4]。《靈樞·官針篇》記載“恢刺者,直刺傍之,舉之前后,恢筋急,以筋痹也”。本研究旨在觀察經筋恢刺法治療PFPS的臨床療效。現報告如下。
1 資料與方法
1.1 病例選擇 診斷標準:診斷標準參考《骨及骨關節疾病診斷學》[5]有關內容擬定。納入標準:符合上述診斷標準;年齡18~40歲;患者同意知情并簽署同意書。排除標準:由膝關節外傷、膝骨關節炎、痛風性關節炎、風濕性疾病、類風濕性疾病、感染性關節炎等引起的膝關節疼痛者;既往有膝關節手術、結核、腫瘤等病史者;伴心血管系統、消化系統等嚴重內科疾病者;妊娠期或哺乳期婦女;認知障礙或精神障礙者;局部皮膚病變者。
1.2 臨床資料 選擇2019年10月至2020年2月于本院就診的PFPS者80例按隨機數字表法分為治療組與對照組各40例。治療組男性14例,女性26例;年齡18~40歲,平均(27.38±5.22)歲;病程1~16個月,平均(6.85±2.20)個月;患側為左側14例,右側16例,雙側10例。對照組男性16例,女性24例;年齡20~40歲,平均(25.84±4.95)歲;病程 1~15個月,平均(6.15±2.18)個月;患側為左側13例,右側16例,雙側11例。兩組患者在性別、年齡、病程、患側等方面差異無統計學意義(P>0.05)。
1.3 治療方法 對照組予以常規治療,囑患者適當休息,避免負重和劇烈運動,遵醫囑予以口服雙氯芬酸鈉緩釋片(北京諾華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0980297,75 mg/片),每次75 mg,每天1次;奧美拉唑腸溶片(湖南方盛制藥股份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20103295,20 mg/片),每次20 mg,每天1次;若有關節積液,皮膚張力大,浮髕試驗陽性者,行關節腔穿刺,注射玻璃酸鈉注射液(山東博士倫福瑞達制藥有限公司,國藥準字H10960136,20 mg/支),每次20 mg,每周1次;由康復師評估,選擇性指導患者股四頭肌、臀中肌力量訓練、柔韌性訓練、平衡和本體感覺訓練[6],每次20 min,每日1次。連續治療2周。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予以經筋恢刺治療,采用經筋結點觸診法尋找膝關節周圍經筋結點,目前主要分4條經筋,足太陽經筋結點主要包含委中次、委陽次、合谷次、合陽次、陰故次等,足少陽經筋結點主要包含陽陵次、成骨次、腓骨小頭、成腓間等,足陽明經結筋點主要包含髕周、脛骨內髁、脛骨外髁,足三陰經筋結點主要包含陰陵上、血海次、膝關次等[7-8]。選取6~10處筋結點,確定每處筋結點位置、深淺、疼痛范圍,常規消毒后,采用華佗牌0.3 mm×40 mm針灸針,針刺手法采用恢刺法[9],在筋結點旁常規直刺,深至骨面或痙攣肌腹,將針退直皮下,沿著疼痛范圍前后左右透刺,配合提插捻轉手法,以出現強烈酸脹感或四周放射感為度。留針20 min,每天1次,連續治療2周。
1.4 觀察指標 1)疼痛評分:采用視覺模擬量表(VAS),評定兩組治療前后關節疼痛情況。2)關節活動:采取膝關節主動屈膝活動度(AROM),測定患膝主動活動度,測量時量角器中心對準股骨股外側髁,固定臂與股骨縱軸平行,移動臂與脛骨縱軸平行,測量主動屈膝時最大活動角度。3)關節功能:選用Lysholm評分[10]評估兩組治療前后膝關節功能,從跛行、支撐、上下樓梯、下蹲等方面評估。
1.5 統計學處理 應用SPSS22.0統計軟件。計量資料若符合正態分布且方差齊,以(±s)表示,采用t檢驗,方差不齊時采用t'檢驗。計數資料采用頻數或構成比表示,采用χ2檢驗。P<0.05為差異有統計學意義。
2 結 果
2.1 兩組治療前后VAS評分比較 見表1。治療后,兩組VAS評分均明顯降低,且治療組較對照組降低更明顯(P<0.05)。
表1 兩組治療前后VAS評分比較(分,±s)

表1 兩組治療前后VAS評分比較(分,±s)
注:與本組治療前比較,?P<0.05;與對照組治療后比較,△P<0.05。下同。
治療后2.36±0.72*△4.57±1.43*組別治療組對照組n 40 40治療前6.58±1.40 6.74±1.28
2.2 兩組治療前后AROM水平比較 見表2。治療后,兩組AROM均明顯升高,且治療組較對照組升高更明顯(P<0.05)。
表2 兩組治療前后AROM水平比較(°,±s)

表2 兩組治療前后AROM水平比較(°,±s)
組別治療組對照組n 40 40治療前125.08±1.68 124.26±1.70治療后142.02±1.30*△134.60±1.28*
2.3 兩組治療前后Lysholm評分比較 見表3。治療后,兩組Lysholm評分均明顯升高,且治療組較對照組升高更明顯(P<0.05)。
表3 兩組治療前后Lysholm評分比較(分,±s)

表3 兩組治療前后Lysholm評分比較(分,±s)
組別治療組對照組n 40 40治療前43.64±5.28 42.55±5.42治療后75.27±4.68*△61.88±4.05*
3 討 論
PFPS是運動醫學科常見疾病之一,好發于青少年和運動愛好者,多表現為膝關節前側彌漫性疼痛,癥狀與日常活動相關(上下樓梯、下蹲、跑步等),且隨著活動加重。早期不及時治療,極易發展成不可逆的髕股關節炎,嚴重影響日常工作和生活。髕股關節是膝關節重要組成部分,對下肢穩定起著重要作用,主要由髕骨、股骨內外側髁、髁間窩以及髕周支持帶組成。在膝關節屈伸過程中髕股關節起杠桿作用,膝關節屈伸過程,髕骨在內外側髁關節溝中滑動,髕骨作為人體最大的籽骨,具有重要生物力意義,可通過增加股四頭肌力臂從而增加膝關節伸肌力距[11]。但由于各種內外因素,導致髕骨運動軌跡異常,常引起髕骨外側面與股骨外側髁產生應力性摩擦,引起無菌性炎癥。目前對于其發病機制尚無定論,目前多認為與解剖結構異常、肌力不平衡、膝關節周圍軟組織張力異常、超負荷、創傷等因素有關[12]。其中,髕周肌力失衡是髕骨運動軌跡異常的重要因素,肌肉力量不足,增加髕骨與股骨關節滑車接觸,使膝關節負荷增加,減震能力下降,增加髕股關節損傷;周圍軟組織緊張,引起髕骨側移、傾斜,增加髕股關節局部應力,導致髕股關節損傷[13]。以往,現代醫學對于其治療主要包括運動療法、髕骨扎貼、髕骨支具、足踝矯形等保守治療和外側髕股韌帶松解術、脛骨結節截骨術等手術治療。治療取得一定療效,但存在一定的局限性。中醫學應用歷史悠久,對于該病的治療,具有獨特療效。
PFPS屬于中醫學“膝痹”“筋痹”范疇。中醫學認為,“膝者,筋之府”,膝關節與經筋具有密切的聯系,所謂“宗筋主束骨而利機關也”,筋主約束骨骼,活動關節的作用。經筋理論是中醫學重要組成部分,正常膝關節處于“筋骨平衡”狀態,當外邪侵犯或勞損筋傷等因素,引起氣血運行失暢,經絡不通,導致膝關節經筋牽掣、攣縮、拘急、強直、轉筋,引發經筋循行產生條索狀、結節狀的“結、聚”點,形成“橫絡”,即所謂“橫絡盛加于大經之上,令之不通”,此為經筋病的發病機理,經筋對骨骼約束能力下降,局部力學環境改變,影響膝關節穩定性,局部應力異常,增加膝關節負荷增加,增加髕股關節損傷。“解結”為經筋病治療原則,通過“病在筋,調之筋”,通過松解筋結點,膝關節周圍軟組織張力,恢復關節力學平衡,從而恢復筋骨平衡[14]。針刺是中醫重要組成部分,具有行氣活血、通經活絡、協調陰陽的作用,常用于經筋病的治療[15],其應用于膝關節疾病治療,有效性已得到循證醫學證實[16]。針刺的鎮痛作用已得到廣泛認可。鎮痛機制是一個綜合的、復雜的過程,涉及多通絡、多水平,主要包含神經機制、體液機制、循環機制[17]。基礎研究表明,針刺能夠調節骨關節炎軟骨細胞、細胞外基質、軟骨下骨、滑膜組織、炎癥反應,保護關節軟骨,改善和延緩關節退變過程[18]。此外,隨著醫學研究的不斷發展,機械換能學說逐漸深入研究,針刺刺激產生的機械性刺激,啟動細胞一系列反應,調動內環境反應,促進細胞激動素、血管活性物質、降解酵素等物質釋放,發揮自我調節功能,恢復針體周圍軟組織損傷[19]。嵇征鴻等[20]采用經筋針刺治療膝骨關節炎,利于恢復膝關節經筋系統的平衡狀態,提高膝關節功能。恢刺是古法針刺手法之一,《靈樞·官針》“恢刺者,直刺傍之,舉之前后,恢筋急,以治筋痹也”。《靈樞·懸解·官針》記載“恢,擴也,前后恢筋急者,恢擴其筋,以舒其急也”。可見恢刺主要用于治療經筋病,通過針刺攣縮拘急的筋結點,直刺、深刺得氣后再朝各個方向針刺,以發揮通經活絡,舒緩拘急的作用。既往有學者通過總結發現,恢刺屬于撬拔刺法的范疇,具有松解軟組織和行氣催氣的作用[21]。韓振翔等[22]采用經筋結點恢刺法應用于腦卒中偏癱肩痛患者,利于調暢氣血,舒緩筋結,可改善肩部運動功能。劉軍等[23]采用經筋恢刺法治療頸肌筋膜疼痛綜合征,可疏通經氣,舒筋緩急、緩解肌肉痙攣、改善微循環、促進炎癥消退。
本研究提示,在常規治療基礎上,經筋恢刺法治療急性PFPS,不僅能降低VAS評分,同時能提高AROM和Lysholm評分。說明在常規治療基礎上,經筋恢刺法治療髕股疼痛綜合征,能有效緩解疼痛,提高膝關節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