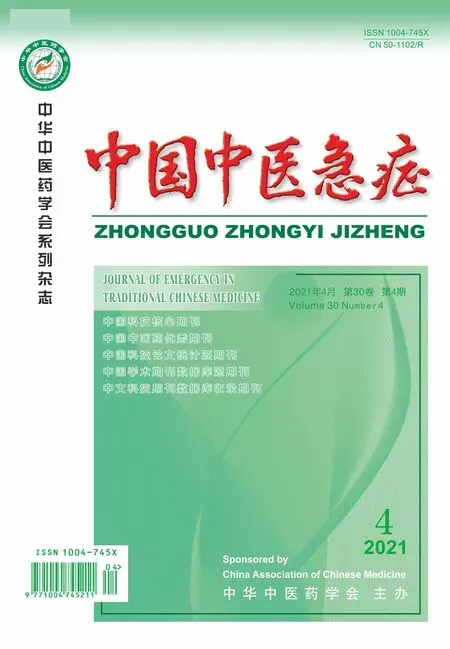熊大經教授以“氣血雙向調節”理論防治過敏性鼻炎經驗介紹*
謝 艷 劉小剛 劉 洋 蔣路云 張 鍇
(1.成都中醫藥大學附屬醫院,四川 成都 610072;2.四川省成都市新津區中醫醫院,四川 成都 611430)
熊大經教授是全國第3批中醫藥臨床優秀人才,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第5、6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指導老師。熊老在從事耳鼻喉科臨床工作的50多年間,提出了諸多耳鼻喉科中醫理論、取得了頗高的成就。熊老在臨床工作形成了一套獨具特色的“氣血雙向調節”理論,在過敏性鼻炎(AR)治療方面臨床療效顯著。筆者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第6批全國老中醫藥專家學術經驗繼承工作繼承人,師從熊大經教授。隨恩師跟診以來,所學所思所悟良多,獲益匪淺。特將吾師“氣血雙向調節”理論在AR防治中的應用與大家分享。
AR是一種由于變態反應而出現的疾病,臨床上常表現為打噴嚏、流清涕,同時也可見鼻塞、鼻部瘙癢等癥狀。隨著社會環境的變化,當今AR發病率居高不下,人群中發病率約為20%~30%,其中在國內每年患病人數更是高達2 000萬,除了痛苦的臨床癥狀,該病還同時因為其病程之長給患者帶來了不小的經濟負擔,對患者的生活質量造成了嚴重的影響,也給整個社會造成了較大的影響[1]。AR除了上述幾個典型癥狀之外,還可以伴見眼癢、流淚等其他癥狀,是耳鼻喉科的一個常見疾病[2],中醫病名為鼻鼽。《靈樞·口問》說“陽氣和利,滿于心,出于鼻,則為嚏”[3]。《素問玄機原病式》云“鼽者,鼻出清涕也”[4]。《說文解字》釋“鼽,病寒鼻窒也”[4],指出了鼻鼽多為寒邪致病,流涕多伴鼻塞,通氣不利。
1 明確氣血與臟腑的雙向辨證關系
中醫理論認為,氣是促進人體健康的動力,血液是滋養人體的源泉。人體之中有元氣、衛氣、營氣、宗氣等多種氣分布循行,各司其職。具體而言,在人體中,我們所說的“氣”遍布在各個臟腑之中,而臟腑的功能和氣機正常與否密切相關。熊老認為在“氣、陰陽、五行”的學說中,首重氣。《素問·寶命全形論》云“人以天地之氣生,四時之法成”[5]。關于血的認識,《靈樞·決氣》曰“中焦受氣取汁,變化而赤,是謂血”[5]。然《素問·調經論》亦有“人之所有者,血與氣耳”[5]。營衛不行,五臟不通,血與氣一陰一陽,相輔相成,血為氣之母,氣為血之帥。人體內的氣和血都在不斷地變化、轉換中實現了機體的代償。若機體氣血充足,得以濡養臟腑,則臟腑功能正常;反之,若人體氣血虧損,臟腑失于濡養,則臟腑功能異常。
熊老認為AR雖然有先天因素所致,亦離不開后天氣血生化的影響。肺氣虛寒,衛氣虛弱,衛外不固,則外感風寒邪氣乘虛而入,循經上犯鼻竅,肺失通調,氣機不利發為鼻鼽。若僅從肺進行辨證治療,療效不佳。脾胃是后天的基礎,氣血生化源弱,血生化被動,陽氣不升。如果肺失氣血,鼻亦失于濡養,外邪從口鼻侵入人體,并將其送至鼻子。《靈樞·營氣》“谷入于胃,乃傳之肺,流溢于中,布散于外”。《靈樞·經脈》言“肺手太陰之脈,起于中焦,下絡大腸,還循胃口,上膈屬肺”[5]。肺與胃經脈相連,與中焦氣機宣降相承,故脾胃的健運與否,直接關系到肺衛氣的功能發揮。脾氣虛則是肺溫虧損、水濕運化失調、濕邪侵犯鼻孔而發為鼻漏。同時,腎陽虛,氣血失于溫潤的鼻腔,鼻孔容易被外界病原體侵入。因此,對疾病的病因病機,主要責任為肺、脾、腎三臟功能障礙。肺、脾、腎三臟運輸水分流失,體液壓縮異常,鼻水濕潤,可明顯反復流水。盡管虛證和實證皆可導致鼻鼽,但更以虛證多見[6]。熊老建議,要從鼻鼽的基本病機入手,將本病與肺、脾、腎緊密結合起來,通過扶正益氣提高機體自身免疫力。
氣血的盈虧密切關系著臟腑的邪正盛衰,熊老提出的鼻部“五度辨證”提及氣血兩度,下鼻甲、下鼻道應肺,肺主氣,故曰氣度。肺氣同于鼻,肺氣充沛,則肺鼻互相協調,完成其生理功能。如《靈樞·脈度》說“肺氣通于鼻,肺和則鼻能知香臭矣”。肺的功能失調,容易導致鼻病的發生。如《靈樞·本神》曰“肺氣虛則鼻塞不利,少氣”。《諸病源候論·卷二十九》說“肺臟為風冷所乘,則鼻氣不和,津液壅塞為鼻齆”。鼻中隔前下部的網狀動脈叢為鼻出血的好發部位,小兒及青少年的鼻出血多發生在利特爾區。此處血管豐富,表淺,吻合支多,易受外傷或干燥空氣刺激,黏膜受傷時易發生血管破裂。鼻中隔特別是利特爾區與心的密切關系,心主血,故曰血度。心主嗅,與心主神明和心主血脈的功能有關。《難經·四十難》說“心主臭,故令鼻知香臭”。心肺有病可致鼻病,而鼻部作為局部官竅,可以反映臟腑的氣血盛衰變化。如《諸病源候論·卷十》說“心主血,肺主氣而開竅于鼻,邪熱傷于心,故衄”。《杏苑生春·卷六》認為“鼻之為病,盡由心肺二經受邪,有寒有熱”。因此熊老在AR中的診斷中強調在善辨臟腑的同時也要細辨氣血的榮虧。全身氣血的榮衰可影響一個或多個臟腑的功能,換句話說,整體狀態可影響局部功能;另一方面,局部臟腑和單個系統的過度虧損也會影響全身氣血的運行、轉化。因此,在AR治療的過程中必須要實現整體與局部的結合,不可因過度強調攻補局部而弱化甚至忽略人體整體氣血的調節,要做到“補而不滯,攻而不過”[7]。
2 強調氣血對疾病發展的雙向影響
人體內部生克制化的規律以及氣血狀態對疾病的雙向調節規律在《黃帝內經》中就已經明確闡明,即“亢則害,承乃制,制則生化”。在臨床工作中,熊老強調,人體存在著內在的雙重調節,即相互作用的雙方相互調節、相互制約,這與中醫理論所強調的陰陽極為相似。這兩個方面相輔相成,通過維持動態平衡的狀態以保證機體健康,即陰平陽秘。當發生疾病時,動態平衡就被打破了,人體自身的調節失衡了,自然也就無法談論陰陽平衡了。在先天稟賦、內生五邪、外感邪氣等多種病因病機的多重調節作用下,即使是同一個疾病,在不同的機體所出現的部位、所處的層次、所屬的性質、所發展的趨勢也會大相徑庭,甚至可能會完全相反,即虛虧易弱與榮盛易亢兩種狀態。
基于這一點,雖然同為AR,不同機體由于不盡相同的氣血狀態產生了各自的病機,即寒熱虛實。在AR的辨證中,雖多為寒證,但基于氣血對疾病發展的雙向影響,臨床必不得忽視熱證,這也要求我們做到辨證論治。《證治準繩·七竅門下·鼻鼽》中完整地闡述了人體氣血狀態對鼻鼽的發病影響,即“若素有痰火積熱,則平素上升之氣,皆氳而為濁。痰氣內結,郁而化火,內生痰火,蘊結于體內,清陽不能向上,成為體內濁氣。濁氣向上,熏蒸于肺,肺氣失宣發肅降,停留于上焦,故成涎涕。
3 通過對氣血的雙向調節提高臨床療效
陰陽之間的關系存在多樣性,然而許多人只看到陰陽存在對立制約、此消彼長的矛盾關系,殊不知陰陽也有著互根互用的關系,統一于矛盾之中。這一點在陰陽證病機演變中得到了充分體現。在臨床治療四肢發冷、陽衰等癥狀時,可在溫陽的同時補充適量的滋陰藥,即“陰中求陽”;同樣,在治療潮熱盜汗等陰偏衰的癥狀時,可于滋陰劑中佐以適當補陽藥,即“補陰當于陽中求陰”,這兩種治療思路都是基于陰陽互濟進行調補陰陽。熊老強調陰陽氣血的雙向調節,并且著眼于如何通過調整氣血的雙向調節實現臨床療效的提高,通過數十載的臨床積累形成了一套系統的組方用藥體系,在龐大的體系里面我們可以看到諸如寒熱并用、攻補兼施等核心思維。同時,熊老根據不同患者各自的陰陽盛衰和氣血盈虧,在臨床上立方遣藥時注重平衡,宣發而不過辛散,酸收而不過閉斂,溫補而不過燥熱,補益而不過呆滯。
同時,熊老還指出在進行方劑配伍時要注意不同藥物間的“動靜結合”,其中“動藥”即一大類能夠發揮行氣活血消導功效的藥物,否則氣機易郁而生痰瘀等病理產物;“靜藥”即能夠發揮補氣養血滋陰功效的藥物,為機體運行提供充足的物質補充[8-12]。“動靜結合”是指在方劑配伍中主要使用“動藥”同時佐以少量“靜藥”,或者主要使用“靜藥”同時佐以少量“動藥”從而對氣血進行雙向調節。如在AR治療中,氣血虛弱的患者靜藥用量較動藥量宜大,熊老強調“補養之藥”須適量佐以“疏調行動”之藥,其效堪靈。對于氣血亢進的患者,應多給些“動藥”,如行氣、散熱、清熱等。鼻鼽雖多為寒證但仍存熱象,若在方中過度使用一大類具有補氣斂血功效的藥物而不注重加入少許行氣藥,極易產生氣滯血瘀的病理狀態。在治療氣血偏亢的患者時,臨床用藥上需要以“動藥”為主,以行氣活血、清滌腑熱,同時應該適當補以滋陰養血之品,使攻而不過。如龍膽瀉肝湯中,在使用龍膽草、梔子、黃芩等一大隊清肝涼血的藥物同時配伍當歸、生地黃等滋陰養血藥,通過雙向調節陰陽氣血提高了臨床療效。對于表虛不固,氣血虛弱者,熊老多用黃芪桂枝五物湯進行治療,以達到調和營衛、益氣補肺之效。
在其具體用藥方面,針對氣血兩虛的患者熊老善用益氣滋陰養血收澀的藥物,如五味子、陳皮、烏梅、沙參等。五味子、烏梅在補肺氣的同時收斂肺氣,防止過量食用損傷;沙參滋養津液,加入陳皮具有健脾理氣之效,充分體現了滋而不膩、補而不滯的原則。針對氣血偏亢的患者,熊老善用知母、玄參、牡丹皮等藥物,同時熊老指出黃芩、黃連等藥物雖有清熱之效,但苦寒之性太過,易傷脾胃,若調和氣血不宜純用寒涼,如知母、玄參既可清虛、實兩熱,又可滋陰涼血,甘寒而不損陽氣,正所謂攻而不傷正。
4 針藥并用
熊老指出針刺副作用小,在臨床工作中應該充分加以利用[13-15]。針刺的主要作用在于能將全身的氣血調動起來,從而達到平衡陰陽的目的。在病變區域實施針灸治療可將局部氣血疏通,又可實現引經的功能,引藥直達病所。在臨床實踐中,熊老通過數十載的經驗積累總結了一些合谷穴[16-17]的使用心得。陽明充滿氣血,合谷穴是其原點,可以調節全身氣血。在臨床實踐中,針刺合谷穴配合各種刺激手法針對氣血虧虛可補氣血,治療氣血偏亢可降其亢,從而做到陰平陽秘。值得一提的是,這樣的治療方法不僅可以提高臨床療效,還可以促進患者提升免疫功能,這一點也詮釋了中醫“治未病”的治療理念。
5 病案舉隅
患某,男性,30歲,反復鼻塞、流清涕、打噴嚏6+年,遇冷、感冒加重。2020年7月19日初診。3 d前因外出受涼感冒,患者復發加重,出現鼻塞、流清涕量多、噴嚏,伴鼻癢、眼癢、咳嗽、惡風寒,納眠可,二便調,舌淡苔薄白,脈浮。鼻內鏡檢查見:鼻腔黏膜色淡紅,鼻中隔基本居中,雙側下鼻甲腫脹、色紅,各鼻道未見明顯分泌物。中醫診斷:鼻鼽,屬風寒外束證。治則:疏風散寒、益氣養陰。處方:黃芪30 g,南沙參30 g,柴胡10 g,桔梗20 g,白芍15 g,山藥30 g,茯苓20 g,麻黃10 g,干姜10 g。6劑,水煎服。二診(2020年7月28日):服上方后稍好轉,仍鼻塞、噴嚏、清涕,惡風寒,手足冰冷,納可,夜寐欠佳,失眠多夢,二便調,舌淡苔白膩,脈弱。檢查:鼻腔黏膜色淡,鼻中隔基本居中,雙側下鼻甲稍腫脹、色淡白,各鼻道未見明顯分泌物。其證候為肺脾兩虛,陽氣虛證。治則:養陰健脾、益氣養血。處方:柴胡10 g,桂枝10 g,白芍30 g,黃芪30 g,北沙參10 g,地龍20 g,干姜15 g,附子20 g,山藥30 g,大棗10 g,雞內金20 g。6劑。三診(2020年8月4日):服上方后稍好轉明顯,鼻塞、噴嚏、清涕明顯減輕,手足冰冷較前好轉,納眠可,二便調,舌淡苔薄白,脈弱。雙側下鼻甲未見腫脹,呈淡紅色。
按:初診,肺開竅于鼻,肺氣虛則衛外不固,平素易感,鼻塞不利少氣。舌脈、經色、二便、飲食、惡風寒等均風寒外束之象。方中柴胡升舉陽氣、和解表里,麻黃解表宣肺,黃芪益氣固表,山藥補脾益氣,茯苓利水滲、濕健脾消腫,桔梗宣肺止咳,白芍、南沙參益氣養陰以防發散太過,加之以干姜溫中散寒,溫肺化飲。二診,鼻塞、噴嚏、清涕,惡風寒,手足冰冷,納可,夜寐欠佳,失眠多夢,二便調,舌淡苔白膩,脈弱辨證屬肺脾同病,陽氣失于溫宣,采用肺脾同治的方法,培土生金,重在治脾,健脾益氣,培補中土,予以驗方“五龍顆粒”加減,方中以黃芪、山藥、大棗等補中益氣,加桂枝溫陽祛風,附子、干姜溫陽通脈,白芍、北沙參收斂養陰,防燥熱傷陰,配合地龍等通竅通絡止癢、雞內金運脾消食開胃。
6 結 語
綜上所述,本文通過對熊大經教授在氣血雙向調節防治過敏性鼻炎的三個理論層次進行分析,即“氣血與臟腑的雙向辨證關系”“氣血對疾病發展的雙向影響”以及“通過氣血雙向調節增加臨床療效”;同時,結合熊老臨床用方用藥,發現熊老在進行中醫辨證論治開具方藥的同時不拘泥于古法,強調在進行局部治療的同時重視全身氣血的調節,并進行了理論創新。熊老根據患者的不同情況,做到三因制宜,一人一方,值得中醫臨床工作者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