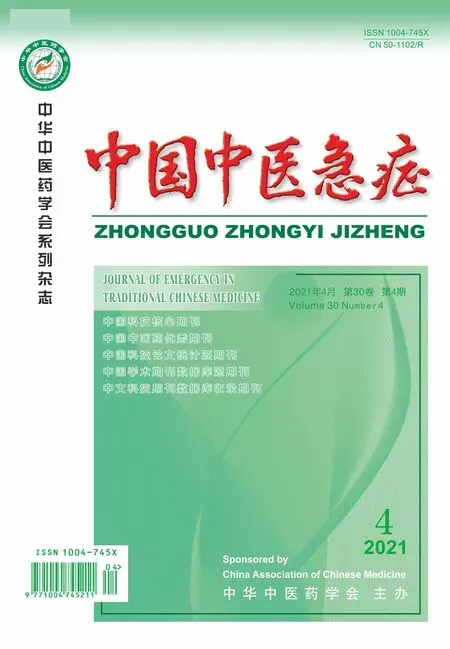癌性疼痛的中醫外治法研究進展*
趙傳琳 任秦有 鄭 瑾 吳 昊 劉克舜
(1.陜西中醫藥大學,陜西 咸陽 712046;2.空軍軍醫大學唐都醫院,陜西 西安 710038)
癌性疼痛主要是指腫瘤細胞直接或間接浸潤、轉移、擴散及壓迫有關組織或抗腫瘤治療引起的慢性疼痛,主要以持續或間斷的燒灼、針扎、撕裂、刀割樣疼痛為臨床表現,為腫瘤患者常見的癥狀。2018年WHO發布《世界癌癥報告》,全球目前有1 810萬癌癥新發病例和960萬癌癥死亡病例,而至2025年全球癌癥新增病例將會增加至3 000萬人,死亡人數由960萬上升到達1 700萬,其中中國新增癌癥患者將達到510萬人,死亡人數到達280萬,中國新增癌癥患者居全球第一[1]。據2018年CA Cancer J Clin雜志統計的中國癌癥數據統計,2018年國有429萬新發癌癥病例,以及280萬人死亡;其中大約35%~79%癌癥患者忍受中度到重度疼痛并嚴重影響他們生存質量及心理狀態(焦慮與抑郁),現代研究調查[4]發現76.4%的癌痛患者對止痛效果不滿意[2-3]。因此,研究應用有效、簡便的止痛方法緩解患者疼痛癥狀,提高患者生存質量顯得尤其必要,現代醫學對癌痛主要采用口服阿片類藥物為主,但是其消化道及中樞性反應對其應用有一定限制,因此研究中醫外治法成為現代癌痛治療的熱點。中醫學在緩解癌痛患者疼痛,延長生存期限,提高生活質量方面發揮了重要的治療作用,現就近10年國內公開發表的文獻為依據,概括總結癌性疼痛的中醫外治法治療進展,以期為臨床工作者提供更好地治療思路及方法。
1 治療原則
1.1 辨證論治 現代醫學根據癌性疼痛發作特點分為急性與慢性疼痛,其中急性疼痛主要由化療、放療、免疫治療、感染等引起,其臨床特點為近期發作,病史短暫,有明確的發生時間,并能確認原因;慢性疼痛主要為疼痛超過1個月或更長時間,主要分為神經病性、神經病理性、骨轉移性、內臟性疼痛等。根據其病理生理學機制主要分為傷害感受性及神經病理性兩種。中醫學認為其病因無外乎氣滯、血瘀、痰濁、濕熱等,但其總體病機屬“不通”與“不榮”兩方面,因此不同醫家根據其不同病因,主要將不同病因分為“不通”與“不榮”兩主要病機,采用不同的治法取得良好的療效。
郭玉玉分析王文萍教授治療癌痛的經驗,認為癌痛屬于心主血脈,血榮諸臟,若氣血運行障礙,則諸癥生,因此認為癌痛的治療應從“心”論治,在辨證論治的基礎上,以癌痛一心(生理病理)一臟腑經絡為主線與切入點,以“通心脈,疏經絡,寧心神,調氣血”為綱領,糾正和消除使氣血瘀滯、運行障礙的因素,通過調理心功能與疏通經絡,以改善氣血運行障礙的狀態,可采用蟾酥、冰片、白花蛇舌草等歸屬心經藥物外用治療達到止痛的目的[5]。吳勉華認為癌痛的病因為六淫邪毒、七情內傷、飲食失調、正氣虧虛、氣機不暢五方面,其病機為癌毒內郁、痰瘀互結、經絡壅塞導致疼痛,其中癌毒內蘊為病機根本,痰濁與正氣內虛為重要因素,病理性質為本虛標實,其中尤其以氣機不暢、經絡阻塞為主,采用解毒祛瘀、化痰行氣通絡是為治療大法,抗癌解毒活絡為治療關鍵,行氣祛瘀貫穿始終,采用通絡活血威靈仙、蜈蚣、全蝎等取得良好的療效[6]。程堯根據臨床用藥特點及現代醫學分析癌痛由氣滯、瘀血、痰濕、熱毒4方面的病理產物侵犯組織形成,根據用藥特點分氣機不暢,肝氣郁結、瘀血內停,脈絡阻塞、痰邪凝聚,濕濁內阻、熱毒雍盛,傷及臟腑、氣血不足,形神失養5種病機類型,并認為臨床中癌性疼痛的病因病理往往是復雜多方面的,辨證施治關鍵在于認清病理性質及病機所在,進行綜合治療[7]。總之,諸位醫家認為癌痛的病因病機大致相似,因此根據其病因病機以“辨證論治”為核心,結合疼痛特點,以“通”“榮”為主要治療原則,根據證型選擇合適的中藥,以理氣、活血、祛瘀、解毒為具體治法必將取得良好的療效。
1.2“通”“榮”原則 中醫各位醫家普遍認為癌痛的病機為“不榮”與“不通”兩大基本病機,吳喜慶[8]根據七情與腫瘤的發生關系,自身臨床經驗、中醫通路系統及“三不”病機學說(內外通路系統由水谷通路、水液通路和外氣通路3部分組成,體內通路由經絡系統、血脈系統、三焦系統和腦神經系統4部分組成)將癌痛分為“不通”即氣滯、血瘀、痰濁等;“不榮”即氣虛、血虛、陰虛、陽虛等;“不平”即陰陽失衡、臟腑失衡、氣血運行失衡等,根據其病機采用不榮補之,不平調之,不通泄之3種治法原則,分別采取不同的藥物治療取得相應的效果。著名中醫腫瘤學家[9]周岱翰將癌痛分為氣血虧虛、氣滯血瘀2型,認為癌毒內郁、痰瘀互結、氣滯血瘀是癌痛的基本病機,臨癥中氣血陰陽虧損者,采用當歸四逆湯補益氣血、溫經止痛之法;氣滯血瘀證則用失笑散活血祛瘀、通絡止痛,“通”“榮”原則取得良好的療效。北京中醫藥大學胡凱文教授依據30余年治療腫瘤經驗分析癌痛為癌毒引起,其病機主要為“毒損絡脈、不通則痛、不榮則痛”,采用“通、榮”原則治療癌痛可以取得良好的療效[10]。總之,大部分醫家在臨癥中根據不通與不榮的基本病機,采用“通”“榮”的基本治療大法,療效顯著。
2 治 法
2.1 針刺療法 白偉杰[11]基于“火以暢達,通則不痛”理論,認為腫瘤的發生與寒邪相關,癌痛由陽虛痰凝瘀滯形成,即《素問·舉痛論篇》曰“寒氣客于五臟,厥逆上泄,陰氣竭,陽氣未入,故卒然痛死不知人,氣復反則生矣”,因此采用毫火針焠刺治療癌性疼痛100例,即在對照組三階梯止痛法的基礎上給予火針針刺足三里、三陰交扶陽養陰,結果治療組總有效率為96%,對照組總有效率為74%,兩組療效差異有顯著性意義,因此認為火針療法具有溫經通絡、行氣活血止痛的作用,其機理在于《醫學正傳》云“夫通者不痛,理也,但通之法各有不同,調氣以活血,調血以和氣,通也”。劉洋[12]采用經皮穴位電刺激聯合三階梯止痛抗中重度癌痛168例,認為癌痛主要由于經絡閉阻、氣血瘀滯所致,而針刺治療疾病的作用機制為疏通經絡、調和氣血,而足三里、三陰交內關、合谷四穴具有促進疏通周身之絡脈、調和氣血、通經活絡止痛的作用。張琰[13]采用秦氏頭八針治療癌性疼痛30例,其中治療組給予百會、印堂、雙側風池、雙側率谷、雙側頭臨泣針刺5 d,結果顯示治療組明顯優于對照組,其治療機理在于《黃帝內經》“主取督脈,以治雜病”和“主取督脈,以治四肢病”的理論,認為針刺治療癌痛不針對腫瘤本身(病因)進行治療,而是通過其他的某些機制和路徑,在繞過“腫瘤”這個“本”的基礎上,直接對“疼痛”這個“標”進行了干預、緩解,即“本虛標實”,治療標實當以“通”為用。鮑關愛[14]分析閆教授采用調神活血止痛針刺法治療癌痛,根據《景岳全書》“凡人之氣血猶源泉也,盛則流暢,少則壅滯,故氣血不虛則不滯,虛則無有不滯者”與《黃帝內經》“心寂則痛微”選取水溝、雙側內關、都門、陰都、血海、照海穴位,認為癌痛的病機屬于“不通”“不榮”兩方面,但多以“不通”為主,“瘀血阻滯,心神被擾”為其中一個重要病機,確立了“活血止痛、清心調神”的治療原則,創立了“調神止痛針法”取得良好的療效。王劍鋒[15]采用Meta統計分析阿是穴以痛為腧穴位敷貼治療癌性2 170例,其中治療組多采用辨病取穴選取相應的疼痛點進行穴位敷貼,對照組給予相應的三階梯止痛法,結果治療組明顯優于對照組,認為癌痛與局部正虛邪盛的病理機制有關,主要為局部疼痛因正氣虛于內,邪氣亢盛于外,邪氣積聚于某一局部導致經絡不通而發為疼痛,所以針刺局部的壓痛點,可以起到直接疏通局部經氣的作用,從而達到通則不痛的治療目的。馬浩然[16]分析目前針刺癌痛治療的現狀,認為針刺治療癌痛主要為溫通經脈、行氣活血,現代醫學機理為針刺能夠有效減少組織胺及神經末梢前列腺素的水平,增加外周血中的β-內啡肽水平,降低外周感覺神經沖動的傳入從而來干預痛覺的傳導達到止痛作用。
現代癌痛動物[17-18]實驗表明不同的頻率治療可促進體內不同阿片類物質的釋放,具有不同的治療效果,如低頻電針刺激促進大腦水平β-內啡肽、腦啡肽釋放,進而激活MOR和DOR起到鎮痛作用,高頻電針刺激促進脊髓水平強啡肽釋放,進而激活KOR產生鎮痛效應。總之,針刺治療癌痛機理各不相同,正如《素問·舉痛論》“脈澀則血虛,血虛則痛,不榮則痛”與邪毒壅塞,瘀阻脈絡,閉塞凝聚所致“不通則痛”,但是各位醫家根據基本病機“不通”“不榮”確立不同的治療方法與法則,以辨證辨病為核心,根據不同的治法如溫經活血通絡、活血行氣止痛等,選取不同的穴位都取得良好的療效。
2.2 艾灸治療 艾灸為通過艾葉熏灼與局部穴位,通過艾灸與穴位同時作用而達到止痛的目的。陳軍[19]通過艾灸聯合三階梯鎮痛治療癌痛60例,其中治療組給予艾灸背俞穴(厥陰俞、肝俞、膽俞、腎俞、三焦俞)聯合三階梯止痛,對照組給予三階梯鎮痛,兩組對比治療組在疼痛緩解率方面優于對照組,其機制可能與艾灸抑制體內前列腺素,相關腫瘤壞死因子相關。歐劍標等[20]將120例癌癥患者隨機分為兩組,對照組60例予以三階梯止痛法,治療組60例在對照組基礎上加用溫陽艾灸中脘、神闕、關元,并給予對癥辨病選穴,結果顯示艾灸可明顯緩解癌痛患者的疼痛程度。《黃帝內經》中“陰成形”理論認為癌痛病因為寒邪凝滯,經絡閉阻,陽氣不達導致疼痛加重,而艾灸法通過艾葉溫熱作用溫熱肌膚,活血通絡,調理氣機使氣血調和達到止痛的目的。
2.3 穴位敷貼療法 穴位敷貼法主要是以一定的中藥在相應的穴位上進行敷貼、離子導入、注射、藥物搽涂、埋植等,以達到控制癌痛目的的一系列外治方法。李瑛[21]采用蟾烏凝膠膏穴位貼敷治療癌癥疼痛50例,其中對照組給予三階梯鎮痛,治療組給予蟾烏凝膠膏(蟾酥、川烏、重樓、兩面針、關白附、三棱、細辛、丁香、肉桂、乳香、沒藥、冰片、薄荷腦等)敷于腫瘤背俞穴,結果治療組疼痛緩解明顯優于對照組,李瑛認為癌痛病因病機主要為氣滯、血瘀、熱毒、痰濕等導致經絡阻滯,不通則痛,故應采取“以通止痛”的治療原則,并且分析蟾烏凝膠膏藥物多為活血化瘀、行氣通絡止痛之品。吳文通[22]采用中藥外敷聯合電生理刺激對改善中重度癌痛84例,治療組在電生理刺激基礎上給予中藥外敷(川芎、桃仁、紅花、乳香、沒藥、冰片)外敷局部疼痛部位,結果治療組明顯優于對照組,吳文通認為癌痛多為臟腑經絡功能的失調,阻滯人體正常氣血運行,影響體內津液的正常輸布,進一步可導致瘀血的產生,瘀血阻絡,不通則痛,藥理研究表明全方具有活血化瘀止痛作用,能明顯抑制相關炎性因子分泌從而抑制痛覺神經通絡,拮抗傷害感受器從而起到止痛作用。王方圓[23]采用動物實驗分析通絡散結凝膠外用對骨癌痛大鼠痛覺行為的影響,發現外用通絡散結凝膠小鼠骨癌痛模型相比對照組大鼠可明顯減輕自發性疼痛評分,增加骨癌痛大鼠機械痛覺縮足閾值,其機制可能為通絡散結凝膠(川烏、制草烏、細辛、丁香、冰片等)具有溫經通絡、行氣活血通絡止痛之功,認為癌毒痰瘀為骨癌痛基本病理因素,治法當以活血化瘀、軟堅散結,拔癌止痛,以“通”為用,正如《醫學衷中參西錄》“開通經絡,透達關節之力”。李贊[24]采用蟲類藥止痛散穴位敷貼治療癌性疼痛,認為癌痛由氣滯血瘀,經絡痹阻,日久正氣不足,氣血虧虛所致,采用蟲類藥(全蝎、娛蚣、地鱉蟲、天龍、生南星、馬錢子)具有疏通經脈、調和氣血、平衡陰陽、通絡止痛之功效,直接作用于體表穴位,使藥物從皮膚筋膜滲入其腠理從而達到止痛的目的。
總之,穴位敷貼[25]治療癌痛多認為癌痛由“不通則痛”與“不榮則痛”引起,其取穴原則多為遠近配穴法、俞募配穴法、表里配穴法、左右配穴法,但多數以局部阿是穴通絡止痛,選藥原則根據辨證論治,分清疾病的寒熱虛實、藥物的寒熱溫涼、四氣五味,以及藥物的特性選取活血化瘀通絡蟲類藥物,行氣補虛補益藥物等,穴位敷貼中醫藥外治法治療癌痛體現了中醫整體觀及辨證施治精神,其療效確切、迅速,副作用小,使用方便,容易控制,療效顯著,值的應用,正如《醫學源流論》云“外治法,用膏貼之,閉塞其氣,使藥性從毛孔而入其腠理,通經貫絡在皮膚筋骨之間,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較服藥尤有力。
2.4 耳穴治療 耳穴治法是通過耳穴穴位按壓刺激刺激全身精氣、調節經絡氣血達到止痛作用。姜義明[26]采用耳穴壓豆療法(皮質下、神門、肝、三焦、交感)對癌痛患者的疼痛緩解情況,其中對照組給予三階梯止痛治療,治療組給予耳穴壓豆法,結果發現治療組可明顯減輕癌痛癥狀及心理,其機制可能為通過耳穴促進體內腦啡肽與內啡肽等陣痛物質生成與釋放從而達到鎮痛目的。白濤[27]采用丹參注射液耳穴穴位注射(臟器對應穴位、交感、耳中、神門、三焦、皮質下)0.2 mL通過治療48例癌痛患者,發現治療組可明顯緩解疼痛,其機制可能為激動中樞神經系統內的阿片受體,從而發揮鎮痛作用。王敬等[28]采取耳穴埋豆法(神門、皮質下交感及臟腑所侵犯主穴)治療骨轉移痛60例,其中試驗組在對照組氨酚羥考酮鎮痛基礎上給予耳穴壓豆,結果試驗組不良反應(惡心、嘔吐、便秘)發生率低于對照組,疼痛緩解程度高于對照組。耳穴治療疾病[29],首先見于《黃帝內經》“耳者,宗脈所聚也”,認為臟腑通過經脈、絡脈、奇經八脈等將氣血匯聚于耳,因此在耳穴可尋找臟腑疾病反應點,通過刺激反應點可以治療相應疾病。總之,耳穴治療癌性疼痛效果明確,不僅能夠緩解疼痛,并且可以有效降低爆發痛、延長鎮痛時間,操作簡便,值得臨床應用推廣。
3 綜合療法
綜合療法是指針刺、艾灸、穴位敷貼、穴位埋線等兩種或兩種以上聯合治療癌痛的方法。胡陵靜[30]采用止痛酊配外敷疼痛部位同步微波并配合針灸及電針綜合治療癌性疼痛53例,其中治療組在對照組基礎上給予中醫外治綜合治療,結果治療組有效率明顯高于對照組,胡陵靜認為癌痛的病因多由于氣滯、血瘀、痰濕、熱毒或寒邪閉阻經脈,氣血運行不暢所致,導致不通則痛,正如《黃帝內經》云“大骨枯槁、大肉陷下、胸中氣滿、喘息不便、內痛引肩頸”,因此止痛酊采用乳香、莪術、川芍、腫節風、冰片舒經活絡、活血化瘀之品組成,取其“通則不痛”的止痛原則。程堯[31]分析中醫外治治療癌痛方藥及辨證分型,發現現代醫家多認為癌痛病機氣機不暢、瘀血內停、痰邪凝聚、熱毒壅盛四類,外用藥物分析多為活血祛瘀、行氣、溫經散寒、清熱解毒為其常用治法,主要原則為補虛瀉實。張雙雙[32]采用丁香骨痛方外敷治療骨轉移癌痛陰證的80例,其中治療組給予外敷、艾灸,中藥選取溫經通絡、解毒散結中藥(丁香、細辛、肉桂、炮姜、全蝎、半夏等),結果治療組有效率優于對照組,并根據“通則不痛、痛則不通”的原則,認為寒凝、氣滯、血瘀等均可導致局部經絡阻滯,局部經絡不通、氣血不榮則痛,治療“不通”癌痛應選用應采取溫陽散寒、解毒散結、通絡止痛的方法,使經絡得以溫通,陽氣經絡中推動氣血運行,榮養局部肌膚經絡,從而使疼痛局部的寒凝得以化解,再通過化痰、軟堅、解毒藥物使局部結節得以軟、散,使毒邪化解,從而達到止痛的功效。沈麗賢[33]采用止痛散外敷、針刺和復方丹參注射液穴位注射液治療晚期肝癌癌痛40例,對照組給予嗎啡緩釋片治療,聯合組在此基礎上采用止痛散外敷肝區疼痛部位,針刺肝、心俞和穴位肝俞、心俞、曲泉注射復方丹參注射液,其治療理論根據“不通則痛”“通則不痛”,通過針灸特定的穴位舒通經絡、調節氣血止痛的原則,正如《靈樞·行氣》云“氣行則神行,神行則氣行,神氣之相隨也,夫行針者,貴在得神取氣”,止痛散外敷、針刺及穴位注射三法并用,共奏益氣活血、通絡止痛之功。沈麗賢認為穴位注射的機理為藥物通過刺激局部皮膚毛細血管、淋巴管循環,組織液與血液局部流速,增加熱量從而具有止痛的作用,于中醫“通則不痛”原則相似。吳昭利[34]采用冰硼散外用聯合穴位注射治療肝癌痛81例,治療組給予冰硼散外用聯合苦參注射液穴位注射,對照組給予癌痛三階梯治療,結果治療組有效率為93.5%;對照組有效率為83.3%,吳昭利認為肝癌痛病機為癌瘤,阻滯肝臟氣血阻滯,經絡不通導致疼痛,經絡不通,進一步加重氣血不暢使疼痛加重,因此應采用活血通絡止痛為治療大法,選取冰片、延胡索等破氣活血散瘀的藥物治療,正如《黃帝內經》“內病內治,外病外治”的治療原則。總之目前各位醫家采用綜合治療多以“不通則痛”的病機,辨證選取不同的中藥外敷,以活血化瘀、行氣止痛、散結祛瘀、清熱解毒等治療方法取得良好的療效。
4 結 論
綜上所述,中藥外治通過施藥于外而作用于內,可避免口服經消化道吸收所遇到的多環節滅活作用及藥物內服帶來的某些毒副作用,療效明確,且沒有西藥的成癮性、依賴性及戒斷性等缺點。中醫外治目前已成為中醫治療癌痛成為特色廣泛開展,具有鎮痛時間快、反復操作、辨證選穴簡短等優點。
中醫外治各種方法都有其機理,其中針刺治療癌性疼痛機理自古有之,唐·孫思邈《千金要方》“凡病皆由血氣壅滯不得宣通,針以開啟之”,認為針刺治療疼痛的機理在于通過針刺刺激相應穴位,使得機體正氣得以激發,臟腑經絡疏通,氣血流暢,臟腑機體濡養從而達到止痛的目的。艾灸治療痛癥機理在于艾葉具有補氣溫通散寒的作用,通過灸熱刺激經絡保持氣血通暢從而達到止痛的目的,正如清代吳儀洛《本草從新》“艾為陽火,諸經除百病”。國醫大師賀普仁認為艾灸通過溫熱刺激達到疏通氣血而止痛。穴位敷貼阿是穴是通過藥物敷貼于疼痛部位,通過腧穴及經絡刺激長久的作用治療疾病的一種治療方法,具有功效持續時間長、操作簡便、不良反應小等優點,穴位敷貼、注射、埋線是將腧穴功效與藥物治療作用相結合治療疾病的方式,現代研究發現中藥通過穴位等局部刺激產生激發經氣、通理陰陽的作用而止痛。
現代諸多醫家認為癌痛的病機總體屬于“不通則痛”“不榮則痛”兩方面,但外治多屬于本虛標實,外用多使用活血化瘀、行氣止痛、通絡散結等治法,如藥物從皮膚黏膜滲入腠理,通經活絡,直達病所,針對病邪或提而出之,或攻而散之,從而止痛;針刺通過穴位刺激疏通經絡、調和氣血、平衡陰陽來緩解和消除因寒邪、熱毒、痰邪、瘀血阻滯經絡和氣血不榮而導致的疼痛;綜合中醫外治療法在于聚集針刺、穴位、藥物等諸多優點;總的來說,中醫外治治療癌性疼痛應該以“不通則痛”“不榮則痛”為基本病機,以辨證論治為核心,以“通則不痛”“榮則不痛”為治療原則,以活血化瘀、行氣止痛、散結祛瘀、清熱解毒、通絡止痛、行氣活血等為治療方法,才能達到療效。
目前中醫外治治療癌痛的臨床研究實驗較少,數據較少,沒有多中心、大樣本的臨床研究試驗,并且在中醫外治中針刺、艾灸、穴位貼敷、綜合外治中其中治療方法多以辨證、辨病取穴與治療為主,方式多沒有創新,并且目前中醫外治治療癌痛多以疼痛緩解率、生活質量、焦慮抑郁評分為主觀評價標準,缺少相關客觀指標的評價標準,因此希望在之后的臨床研究中,多加入客觀評價指標。癌痛嚴重影響患者的生活質量,現代醫學對其治療手段有限,因此應該發揮中醫治病求本的優勢以局部治療與整體治療相結合,提高患者的生存質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