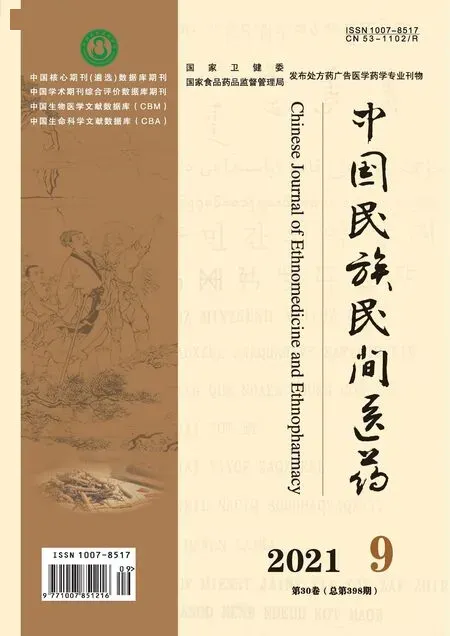童安榮治療過敏性紫癜性腎炎臨證經驗
楊小雙 童安榮* 謝彧軒 岳婷婷
1.寧夏醫科大學,寧夏 銀川 750004;2.寧夏回族自治區中醫醫院暨中醫研究院,寧夏 銀川 750021
過敏性紫癜性腎炎(Henoch-schonlein purpura nephntis,HSPN),簡稱紫癜性腎炎,是指由過敏性紫癜累及腎臟導致的一種疾病,臨床主要表現為血尿、蛋白尿。本病大多呈良性、自限性過程,于數周內座愈,但也有反復發作或遷延數月、數年,約25%患者可有GRF下降[1]。該病多發生于秋冬季節,且任何年齡段的人群均可發病,最常見于見于兒童。國內近年來對HSPN 患兒行腎活檢發現幾乎 100%的患兒有不同程度的腎損害[2]。目前西醫多采用免疫抑制劑、抗組胺藥物、糖皮質激素等藥物改善血管通透性等治療,雖然近期治療效果顯著,但是停藥后易反復,且副作用較大,缺乏長遠的預防調護。中醫藥在治療皮膚紫癜、蛋白尿、血尿,保護腎臟功能及改善患者過敏體質等方面療效可靠,具有獨特的優勢。
童安榮主任曾師從全國著名腎病專家時振聲教授、沈慶法教授學習,為國家中醫藥管理局慢性腎衰中醫升降理論及應用重點研究室創作者,致力于升清降濁治療慢性腎衰升降失常的理論、臨床與實驗研究,從事臨床工作30多年,擅長腎臟病及其它內科病的治療。
1 病因病機
中醫文獻中無“紫癜腎”的病名,根據其臨床癥狀類屬于祖國醫學“紫癜”“紫癜風”“血證”“尿血”“肌衄”“斑疹”“斑毒”“葡萄疫”“水腫”“腰痛”等病證范疇,2010年國家中醫藥管理局重點專科優勢病種協作組根據本病臨床特點將之命名為“紫癜腎”[4]。各代醫家對其認識也不盡相同,王肯堂《證治準繩·瘍醫》云“夫紫癜風者,由皮膚生紫點,搔之皮起而不癢痛者是也。此皆風濕邪氣客于腠理,與氣血相搏,致榮衛否澀,風冷在肌肉之間,故令色紫也。”宋代嚴用和《濟生方·失血論治》認為血證的病因病機有“大虛損,或飲酒過度,或強食過飽,或飲啖辛熱,或憂思恚怒”等病機強調“血之妄行也,未有不因熱之所發”。清代唐容川,乃血證之集大成者,其著作《血證論》更是做出“血證,氣盛火旺者十居八九”的論述。
童安榮主任認為過敏性紫癜性腎炎病機總屬本虛標實,病理因素為“風、濕、熱、瘀、虛”。病因不外內外二因,內因多由于先天稟賦不足,脾腎虧虛,或血熱內蘊,或素體陰虛;腎為先天之本,若先天不足,腎氣孱弱,則不堪邪擾,邪易入里,表現為易被外邪侵襲或體質敏感,接觸過敏原或進食某些食物容易比常人表現出亢進狀態[5]。脾為后天之本,脾主運化水液,脾氣不足,水液不能運化,生成水濕,日久濕蘊化熱,熱迫血行,脾氣虛弱不能統攝血液而引起的血不循經而外溢,形成紫癜。素體陰虛,日久耗傷氣陰,陰虛火旺,灼傷脈絡,致血溢脈外,溢于皮膚可見皮膚瘀點、瘀斑,血液溢出滯于關節,不通則痛,則見關節腫痛,血溢胃腸,則見腹痛,熱擾膀胱腎絡,則見蛋白尿、血尿。外因多由于食辛辣、海鮮等腥膩之品或外感風濕熱邪毒,風濕熱邪毒侵襲人體,致血絡受損,迫血妄行,發為紫癜。內外因共同作用于人體,氣血失調,氣不攝血,血溢脈外,發為本病。童安榮主任認為瘀血貫穿于紫癜腎病程始終,治療上注重活血化瘀。
2 辯治思想
2.1 注重清熱涼血,祛風除濕 本病初期多由于風邪挾濕熱邪毒侵襲人體,風為百病之長,常兼它邪合而傷人,紫癜腎初起可見發病急,變化快,符合風性善行而數變的致病特點,多伴皮膚瘙癢,及咽痛,發熱等外感風熱癥狀。風熱之邪,從口鼻而入,侵入肌膚,氣血相博,灼傷血絡,發為紫癜,在疾病初期側重祛風解毒,臨證常配以麻黃、荊芥、防風、蟬蛻等祛風之品。因疾病初期以皮疹為主要癥狀,治療上童安榮主任善用皮類藥物,取以皮治皮之意。
《景岳全書》云: “血本陰精,不宜動也,而動則為病;血主營氣,不宜損也,而損則為病。蓋動者多由于火,火盛則逼血妄行;損者多由于氣,氣傷則血無以存”。熱邪為紫癜腎的啟動原因,素體血熱內蘊,陰虛火旺,外感風熱,熱迫血行,血溢脈外,童安榮主任在治療上注重配伍牡丹皮、赤芍等清熱涼血之品;過敏性紫癜患者初起皮疹多出現于雙下肢,伴關節疼痛,且顏色深紅,符合濕邪致病特點。濕為陰邪,其性趨下,易襲陰位,故皮疹部位多見于雙下肢;濕性重濁粘膩,易阻滯氣機,妨礙氣血運行,血行不暢,瘀血阻絡,不通則痛,臨床可見患者出現關節腫痛,故在組方中加入四妙散加減以清熱祛濕。
2.2 健脾補腎為基本 本病常病程長,遷延難愈,紫癜腎病至后期皮疹多半顏色變淡或消退,但往往出現血尿、蛋白尿癥狀,病程日久,濕熱蘊生,有礙脾之健運,脾氣虧虛,濕熱下絡腎臟,腎失封藏,脾失固攝,故臨床表現血尿、蛋白尿遷延不愈。童安榮主任在臨證時多用黃芪、黨參健脾補腎,取其一脾健則水濕得化,濕濁不生以治其本,二者脾健則統攝有權,腎固則氣化得利,固攝有權,精微不外泄[6]。
2.3 活血化瘀貫穿病程始終 瘀血既是病理產物又是致病因素,紫癜腎患者均有不同部位的出血,中醫上講“離經之血為瘀血”,離經之血排出體外就是出血,蓄于體內就是瘀血,瘀血阻滯,防礙氣血運行,新血不生,致病情反復不愈,遷延日久。《血證論》則有“經隧之中,既有瘀血踞住,則新血不能安行無恙,終必妄走而吐溢矣,故以去瘀為活血要法”,出血和瘀血共存,相互影響,唐容川的《血證論》提出通治血證之大綱有四,其中消瘀為第二法,即“以祛瘀為治血之要法”,故在本病治療上童安榮主任注重活血化瘀,在方中常加入丹參、桃仁、紅花等藥物以活血化瘀。
3 醫案舉隅
李某,女,12歲,2020年3月18日初診,2020年3月1號因感冒后出雙下肢瘀點、瘀斑,色鮮紅,遂就診于寧夏醫科大學總院,診斷為過敏性紫癜,予以雙嘧達莫,蘆丁等藥物治療后,皮疹消退,但皮疹仍反復發作,患者家屬為求進一步中西醫系統治療,遂就診于我院門診,刻下癥見:患者神清,精神一般,雙下肢散在瘀點、瘀斑,色暗紅,壓之不褪色,乏力,咽痛,咽部紅腫,咳嗽,無咳痰,無雙下肢浮腫,二便調,納食可,夜寐可,舌紅,苔薄白,脈浮細。查體:心、肺、腹未見異常。輔助檢查:尿常規示:潛血2+,腎功能正常。西醫診斷:紫癜性腎炎;中醫診斷:紫癜(風熱夾瘀證);治以祛風清熱,涼血活血。方藥:北柴胡6 g,黃芩10 g,荊芥10 g,金銀花10 g,桔梗10 g,甘草10 g,浙貝母10 g,牛膝10 g,牡丹皮10 g,黨參10 g,黃芪10 g,川芎6 g,當歸10 g,赤芍10 g,桃仁10 g,紅花 10 g,防風10 g,炒神曲10 g。共7劑,日1劑,分早晚溫服,同時口服雙嘧達莫25 mg,3次/日;維生素C片,100 mg/次/日。囑患者服藥期間避風寒、暢情志、慎勞累、勿食辛辣刺激、海鮮等腥膩之品。
二診:2020年4月03日,患者散在雙下肢瘀點,顏色淡暗,無咳嗽、咳痰,乏力較前緩解,納食可,夜寐可,二便調,舌紅,苔薄黃,脈細。查體:心、肺、腹未見異常。輔助檢查:復查尿常規示:潛血(+);腎功能未見異常。患者癥狀較前緩解,無咳嗽,故在原方中去桔梗、甘草、浙貝母,加黃柏繼續服用7劑。
三診:2020年4月20日,患者雙下肢皮疹消退,仍感乏力,納食可,夜寐可,二便調,舌質紅,苔薄膩,脈細滑,復查復查尿常規示:潛血1+;腎功能未見異常。考慮患者目前皮疹消退,仍感乏力,因病情日久,處于病程后期,正虛邪戀,故調整處方,治以健脾補腎,益氣活血化瘀。方藥:北柴胡6 g,黨參10 g,黃芪10 g,麩炒蒼術10 g,黃柏6 g,薏苡仁10 g,牛膝10 g,地黃10 g,酒萸肉10 g,麩炒山藥10 g,當歸10 g,川芎6 g,桃仁10 g,紅花10 g,防風10 g,炒神曲10 g。患者服藥三月后,復查尿常規:潛血(-)、尿蛋白(-),腎功能未見異常,后隨訪患者未再復發,囑患者慎勞累,避風寒,勿食辛辣刺激、海鮮等腥膩之品,注意飲食調攝。
4 小結
目前紫癜性腎炎的發病率逐年上升,占成人繼發性腎臟病第2位,西醫的治療手段雖多,但整體療效難以令人滿意,且停藥后病情易反復。童安榮主任經過多年的臨床實踐,在治療上獨具經驗,臨床辨證論治,將活血化瘀法貫穿疾病始終,中西醫結合治療,注重醫患之間的配合,以期獲得最佳療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