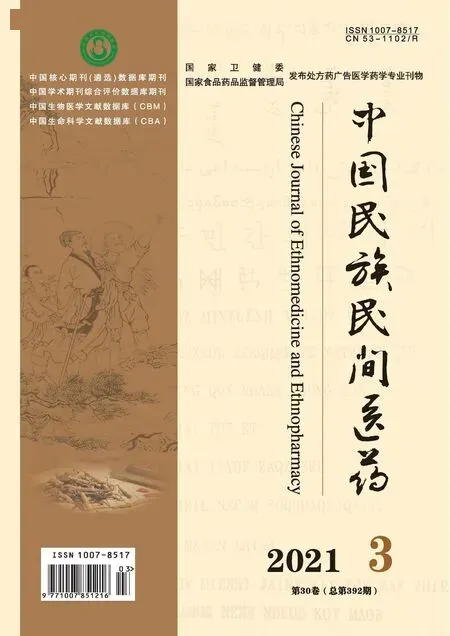陳煒主任辨治隱源性機化性肺炎臨證經驗
陶春芳 陳 煒
1.安徽中醫藥大學,安徽 合肥 230038;2.安徽中醫藥大學第一附屬醫院,安徽 合肥 230031
隱源性機化性肺炎(Cryptogenic Organizing Pneumonia,COP),按照其臨床-放射-病理學特征,屬于特發性間質性肺炎類型中的一種[1]。病因不明確[2],肺部CT的典型表現為雙側或單側多發斑片狀支氣管肺泡實變影、磨玻璃或結節影,以及多發或單發胸膜下實變影[3],癥狀一般見咳嗽、咳痰、氣短,有的伴有發熱、胸痛及乏力等,缺乏特異性。目前西醫主要以激素治療為主,激素起效的同時伴隨諸多不良反應及并發癥,更有甚者遺留難以治愈的后遺癥[4]。陳煒主任認為COP可歸屬于中醫學“咳嗽”“上氣”“喘證”“肺痿”“肺痹”范疇。
陳煒主任從事中醫肺病的臨床、教學、科研工作多年,對隱源性機化性肺炎的診療頗有心得,師從國家級名中醫韓明向教授,為國家第五批名老中醫學術經驗繼承人。筆者在跟師學習中獲益匪淺,現將陳煒主任辨治COP經驗介紹如下。
1 病因病機
陳煒主任根據隱源性機化性肺炎的臨床表現及中醫證候學特點,認為本病的發生乃內外因合而發病,為本虛標實之證。本虛乃肺氣不足,《內經》云:“正氣存內,邪不可干,邪之所湊,其氣必虛”。《素問·通評虛實論》:“氣虛者肺虛也”。肺虛則衛外功能減退,乃發病的內因,日久可延及脾腎,肺脾乃母子相依,肺腎乃金水相生。外因乃外邪襲肺,宣發肅降失職,首先痰濁內生。《丹溪心法》曰:“凡痰之為患,為喘為咳,為嘔為利,為眩為暈,心嘈雜,怔忡驚悸……皆痰飲所致”。痰為病理性產物,形成后又成為新一輪的致病因素。然病程遷延,而肺朝百脈而主治節,邪郁于肺,痰飲停滯于肺,阻塞肺絡,致血滯成瘀。痰瘀互結,加重肺臟負擔,肺絡瘀堵更甚、肺氣愈虛,喘促亦甚。標實乃痰瘀為患。
總之,隱源性機化性肺炎的發生發展一則責之于肺氣虛,衛外不固,外邪入侵;另則責之于痰瘀為患,本虛標實之證。故治療從痰、虛、瘀論治,顧其標本,觀其主次,分而治之。
2 辨治經驗
2.1 從痰論治 痰在隱源性機化性肺炎的發病中占有重要的地位[4],既是病理產物,又是致病因素,更是纏綿難愈的宿根所在。陳煒主任從痰論治指出須辨風痰、寒痰、燥痰、熱痰之不同,靈活運用清法、溫法、潤法等。風痰為病即風痰壅盛于肺所致咳嗽,其病因或風因痰起,或因風生痰。風因痰起可見于素有痰濁,溫化不及,上壅于肺;因風生痰包括外風生痰和內風生痰,內風生痰以臟腑功能失調為主,外風生痰,多由風邪外襲,肺氣失宣,治節通調失利,津液不能布散,痰濁內生所致。風為百病之長,常兼寒、熱、燥邪兩兩并發。寒痰可見色白清稀,咯之易出;熱痰為痰黃粘稠,咯之難出;燥痰則痰少色白,澀而難出。但臨床可見寒熱錯雜,真假寒熱,需結合舌苔、脈象等綜合辨別。隨證治之,每多效驗。
隱源性機化性肺炎,陳煒主任認為痰熱證居多,或因痰熱為患,或因痰濁郁久化熱。以清化痰熱為主,以清金化痰湯、桑白皮湯、溫膽湯、二陳湯、半夏厚樸湯等化裁運用。陳煒主任認為治痰當先理氣,氣順則痰自消,正如“善治痰者,不治痰而治氣,氣順則一身之津液亦隨氣而行”。陳煒主任喜用半夏燥濕降氣化痰,枳實下氣化痰,竹茹清熱化痰,茯苓健脾化痰,地龍祛風清熱化痰,辨證用之,則氣降,濕性驅下,亦絕生痰之源,藥順其性,化痰濕之功尤甚,痰氣兼顧,從而化之。
2.2 從虛論治 《理虛元鑒》云:“治虛有三本,肺、脾、腎是也,肺為五臟之天,脾為百骸之母,腎為性命之根,治脾、治肺、治腎,治虛之道畢矣。”陳煒主任對于COP的治療非常重視補虛之法,常從肺脾腎入手,標本兼顧。肺臟乃COP病位,肺氣不足是其發病的重要內因。然脾主運化,脾虛水液代謝失調,從濕成飲化痰,痰壅氣道,而見咳喘;腎主納氣,腎虛致氣不歸根,喘促息涌,此三臟虛損,虛之本質也。因此COP的病機與肺、脾、腎密切相關,三臟病機上相互影響。陳煒主任認為對于肺氣虛根據臨床分度分而治之,輕度為肺之衛外或主氣之功稍減弱;中度時肺之衛外、主氣功能進一步降低,其癥狀可見輕度時的臨床表現但發生頻率增快、持續時間加長及程度的加重,并必表現出氣短喘促,動則尤甚之癥;重度即肺的衛外、主氣和治節功能整體減退或紊亂,表現在中度肺氣虛的基礎上出現上不能助心行血、下不能通調水道,氣機逆亂,升降失常。故補肺即衛外、納氣、行血、利水。常用黃芪、黃精、補骨脂、黨參以及山藥之類。肺氣已虛,邪氣入內,郁而化熱,痰熱互結,在肺中積聚,消耗肺陰,而成氣陰兩虛之證,滋肺陰陳煒主任常用沙參、玉竹、麥冬、百合等。
2.3 從瘀論治 病久多虛,虛久必瘀,陳煒主任認為COP患者久治不愈的根本原因,往往與血瘀入絡相關。心肺密切相關,兩者相互配合,保證氣血的正常運行,維持機體各臟腑組織的新陳代謝。陳煒主任認為臨床COP病情反復者,多因痰瘀阻塞日久,肺之氣陰耗傷較重,正氣不歸,邪易往復。臟腑功能失調是痰瘀生成的本質。痰瘀既可化熱耗傷陰津,又可阻遏胸陽,閉塞腦竅,故COP患者常見心悸、胸悶、眩暈諸癥。心主血,肺主氣,心與肺的關系即氣與血的關系,氣行則血行,氣滯則血瘀,COP患者肺氣失于宣降,氣滯血瘀則見胸悶胸痛等癥。陳煒主任在臨證治療中善用化瘀、通絡之品,事半功倍,常選用丹參、當歸、桃仁、紅花、敗醬草等,現代醫學[6]證明活血化瘀藥能夠改善微循環及血流動力學,促進炎癥吸收。陳煒主任認為痰瘀當同治,痰瘀互結治宜化瘀祛痰,乃標本兼顧之法。臨證時,當以整體觀分清痰、瘀的主次輕重,若痰、瘀并重,膠結不分,則痰瘀并治;若痰瘀有所側重則隨證加減。
3 典型病例
患者,男,29歲,2019年6月1日我院初診。主訴:反復咳嗽、咳痰伴胸悶1年,加重1周。現病史:2018年7月患者受涼后出現咳嗽,咳黃痰,伴有胸悶,就診于當地醫院,行胸部CT檢查示右下肺內基底段可見不規則軟組織腫塊影,范圍約4.7 cm×3.5 cm,邊緣呈淺分葉狀,內密度尚均勻,灶周見少許斑點狀高密度影。2018年8月1日胸部增強CT示:右肺下葉占位性病變,惡性病變可能,右肺上葉類結節灶,轉移待排。住院治療,2018年8月10日肺穿刺病理示:鏡下見支氣管粘膜及少量肺泡,粘膜下間質內可見大量淋巴細胞、漿細胞及中性粒細胞浸潤伴少量炭末沉著,呈慢性炎改變,抗酸染色(-)。2018年8月15日胸部CT平掃示:右肺下葉占位性病變,與前次CT比較,大致相仿,考慮機化性肺炎;右肺上葉類結節灶,建議隨訪。予以抗感染治療好轉后出院。2018年9月復查右下肺病灶無明顯變化,10月口服強的松治療,11月復查病灶較前明顯減小,12月激素減量,但2019年1月復查病灶較前明顯增大。西醫治療仍予激素口服至2019年4月,后停藥。2019年5月復查病灶未見吸收,建議手術治療,患者拒絕,就診前一周感咳嗽、胸悶加重,2019年6月1日至我科門診尋求中醫中藥治療。患者既往體健,無基礎疾病,刻下癥:咳嗽,咳痰,痰色黃,神疲乏力,胸悶氣喘,胸部脹痛,活動后加重,口干,納差,便干,夜寐尚可,舌紅苔黃,脈細滑。西醫診斷:隱源性機化性肺炎;中醫診斷:喘證之肺脾氣虛,痰熱郁肺證。治法:清熱化痰、降氣平喘。處方:桑白皮20 g,魚腥草后入20 g,黃芩15 g,蘆根20 g,枇杷葉20 g,竹茹10 g,梔子10 g,杏仁9 g,知母10 g,半夏9 g,茯神10 g,浙貝母10 g,前胡10 g,桔梗10 g,黃精10 g,地龍10 g,當歸10 g,炙甘草6 g。共7劑,每日1劑,水煎服,分2次服用。
二診(2019年6月8日):7劑藥后患者咳嗽、咳痰頻次較前減少,胸悶好轉,二便尚調,胃口漸漸恢復,睡眠稍差,但覺口干,乏力,舌紅,苔薄黃,脈細滑。守前方去蘆根、桔梗、枇杷葉,加郁金10 g,遠志10 g,百合10 g。繼服7劑。
三診(2019年6月15日):患者訴服藥后,胸悶氣喘明顯好轉,睡眠改善,納食可,二便正常,感乏力。舌紅苔白,脈細滑。上方去魚腥草、杏仁、知母、遠志、茯神,加黨參10 g,山藥 20 g。繼服7劑。
四診(2019年6月23日):服藥后患者訴癥狀明顯改善,偶有咳嗽,納寐可,二便正常,偶感口干,舌紅,苔白,脈濡。上方去黃芩、前胡,加南北沙參各30 g。繼服7劑。
患者一直服用中藥治療3個月,癥狀消失,無不適主訴,2019年8月28日復查胸部CT示:右下肺內基底段軟組織腫塊影較前明顯縮小。后繼續服用中藥鞏固治療,2020年2月25日復查胸部CT示:右肺下葉慢性炎癥及陳舊灶。病灶吸收,治療有效。
按語:患者咳嗽,咳痰,痰色黃,神疲乏力,胸悶氣喘,胸部脹痛,活動后加重,口干,納差,便干,夜寐尚可,舌紅苔黃,脈細滑,四診合參可辨為喘證之肺脾氣虛,痰熱郁肺證。肺氣虛,衛外不固,外邪襲肺,痰熱內郁,肺宣降失常,而見咳嗽,咳黃痰。肺脾乃母子相依,肺病日久,影響于脾,故見神疲乏力,胸悶氣喘等癥。治療上從痰治重用桑白皮、魚腥草、枇杷葉、黃芩、竹茹、蘆根、梔子清熱化痰,桑白皮且降氣以平喘,熱退則無以煉津生痰,咳喘自除;以桔梗載藥上行,引藥入肺經,與前胡合用,一升一降調節氣機,杏仁、半夏降氣且止咳平喘,氣順則痰消,從痰從氣而治。慮病久,耗傷氣陰,從虛而治,黃精味甘,性平,入肺脾腎精,以補氣養陰,健脾,潤肺,益腎;貝母、知母皆入肺經,共同發揮滋陰潤肺之功效。病久多虛,虛久必瘀,從瘀而治,以當歸、地龍活血化瘀通絡;夜寐較差故加茯神寧心安神,炙甘草調和諸藥。此患者治療,緊扣病機特點,從痰、虛、瘀論治,標本兼顧。二診咳嗽咳痰癥狀緩解,仍乏力,夜寐稍差,故原方去少許止咳化痰藥,加郁金、百合配遠志清心安神。三診癥狀均已減輕,故減清熱化痰藥之用量,加黨參、山藥補肺脾腎以衛外,以健脾,以納氣,亦有培土生金之意。四診諸癥悉輕,清熱化痰之藥減量,以養陰潤肺為主以固其本,鞏固療效。
4 結語
陳煒主任認為COP的發生乃內外合因,本虛標實。根據其病機特點,辨治以痰、虛、瘀為要,顧其標本,觀其主次,分而治之。從痰治,理氣為要兼清、溫、潤之;從虛治,肺脾腎兼顧,分度治之;從瘀治,瘀血去則新血生,臟腑功能恢復,諸癥自除。中醫藥關于肺系疾病的辨治經驗傳承了五千年,臨床療效經得起時間和實踐的檢驗。本文意在將陳煒主任關于COP的辨治經驗和學術思想薪火相傳,傳承精華,守正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