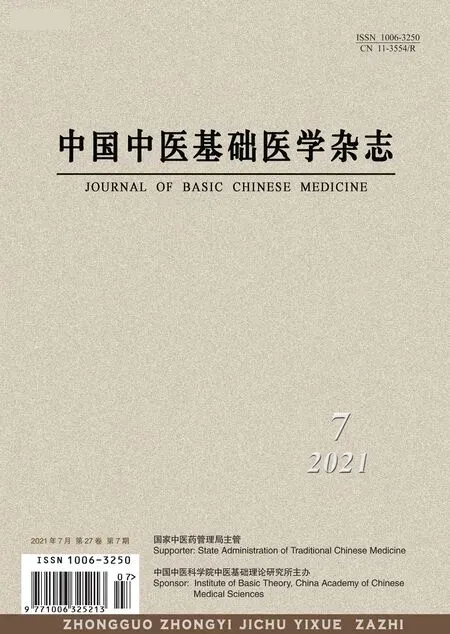從食治文獻管窺唐宋食治發展特點?
孟 璽, 季 強, 楊金萍
(山東中醫藥大學中醫文獻與文化研究院, 濟南 250355)
食治,即在中醫理論指導下,運用食物來治療疾病。食治歷史悠久,早在《周禮·天官》中便將醫生分為“食醫”“疾醫”“瘍醫”與“獸醫”,并將食醫列于各類醫生之首。《黃帝內經》有眾多關于食物的認識,如《素問·臟氣法時論篇》指出:“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素問·五常政大論篇》指出:“谷肉果菜, 食養盡之”,為食治的發展提供了理論基礎。《金匱要略》設專篇論述眾多食物的食用禁忌與中毒治療,并載當歸生姜羊肉湯治療寒疝腹中痛并沿用至今。《本草經集注》記載有果、菜、米谷等類眾多食物的藥用價值。至唐宋時期,孫思邈重視食治并列專篇論述,指出治療疾病時應將食治列于藥治之前。隨著中醫理論的發展,醫家逐漸認識到性味平和食物的藥用作用與優勢,使食治得到迅速發展。此時,出現了《食療本草》《食醫心鑒》《食性本草》等眾多有關食治的專著,《千金要方》《太平圣惠方》《圣濟總錄》《養老奉親書》等綜合性醫書也設專篇論述食治理論與治療。此外《外臺秘要方》《經史證類備急本草》《幼幼新書》雖不設專篇,但其中也記載眾多方劑由食物組成,至此食治發展日趨成熟。現對唐宋時期食治文獻有關內容進行分析,以期總結唐宋時期食治發展特點。
1 食治理論完備化
在唐宋有關食治的專篇專著中,大都包含有論說性內容。《千金要方·食治·序論第一》提出:“安身之本,必資于食”的觀點,闡述食物的重要作用為“能排邪而安臟腑,悅神爽志以資血氣”[1],并指出“食療不愈,然后命藥”,將食治列于藥治之前。隨后孫思邈引用《靈樞·五味論》內容指出五味與五臟的關系,引用《素問·五臟生成篇》指出五味多食的壞處,并根據食物性味提出五臟適宜的食物,結合《素問·臟氣法時論篇》指出:“五臟病五味對治法”。成書于唐代大中年間(847~860)的《食醫心鑒》雖已亡佚,但《醫方類聚》記載了其中11篇論述各類疾病病因病機的文字,其中包括中風、心腹痛、淋病、妊娠病等以闡釋食治之優勢。如《食醫心鑒·論婦人妊娠諸病及產后》云:“飲食失節,冷熱乖衷,血氣虛損,因此成疾,藥餌不知,更增諸疾,且以飲食調理,庶為良工耳。[2]”此外,《食醫心鑒》亦以《黃帝內經》理論為基礎,引經據典。如《食醫心鑒·論脾胃氣弱不多下食》以《黃帝內經》脾胃為土臟展開論述,并佐以《左傳》《莊子》等內容,指出本病應以飲食補益胃氣,最后借用《千金要方·食治》的內容:“凡欲治病,食療不愈,然后命藥”[2],升華提出食治之重要。至宋初《太平圣惠方·食治》理論內容更加豐富,包含《食治論》1篇,論述各種疾病病因病機及食療優勢的醫論28篇,部分內容引自《食醫心鑒》。如同樣對于產后病,《太平圣惠方·食治產后諸方》云:“若飲食失節,冷熱乖理,血氣虛損,因此成疾。藥餌不和,更增諸病,令宜以飲食調治,庶為良矣。[3]”此外,《太平圣惠方·食治》亦增加了《食醫心鑒》所不載的內容,如食治“虛損羸瘦”的優勢:“虛損之人,精液萎竭,氣血虛弱,不能充盛肌膚,故令羸瘦,宜以飲食補益也”[3]。《圣濟總錄·食治門》也在首篇設置“食治統論”,論說食治之重要,其內容多引自《黃帝內經》《千金要方·食治》《食醫心鑒》《太平圣惠方·食治》等文獻[4],亦對相關內容進行闡發并提出新的觀點,如引用《素問·臟氣法時論篇》“五谷為養,五果為助,五畜為益,五菜為充”,解釋五谷之重要,升華提出“辨為益、為助、為充,必先之為養”[5]的觀點。
2 食物、劑型多樣化
從唐初開始,食治所包含的食物種類不斷增加。《千金要方·食治》將食物分為果實、蔬菜、米谷、鳥獸4類總計154條,至《食療本草》增加了鱸魚、綠豆、蕎麥等種類,掌禹錫《補注所引書傳》記載共計227條[6],短短幾十年間《食療本草》便較《千金要方·食治》增加了眾多食物的記載,且內容更加詳實。《千金要方·食治》以記載四氣五味、有毒無毒、主治功效、飲食禁忌為主,《食療本草》的內容則更加豐富。如對于藕的功效,《千金要方·食治》云:“食之令人心歡,止渴去熱,補中養神,益氣力,除百病,久服輕身,耐老,不饑延年。[1]”而《食療本草》還載有:“蒸食甚補益下焦,令腸胃肥厚,益氣力”“與蜜食相宜,令腹中不生諸蟲”[7]等內容。此外,《食療本草》增加了部分飲食禁忌:“凡男子食,須蒸熟服之,生吃損血。[7]”可以看出,與《千金要方·食治》相比,《食療本草》不僅對功效主治與飲食宜忌的記載更加詳實,還增加了食用方法及簡單配伍。隨后《食醫心鑒》《太平圣惠方·食治》《圣濟總錄·食治門》雖以方劑記載為主,但也增加了《千金要方·食治》《食療本草》不曾記載的烏豆、蒔蘿、杏酪等食物的使用方法。此時本草著作記載的食治食物種類也在增加,如北宋《證類本草》雖未單列食治,卻增添了諸如醍醐、絲瓜等食物的功效主治及復方。
除了食物種類,食治方劑劑型也在不斷增加。《千金要方·食治》只是簡單記載食物功效,對服用方法并沒有過多闡述。后《食療本草》出現了“蒸食”“作粉食之”“和米食之”“煮羹”等零散記錄,甚至有《食療本草·芋》:“又,和魚煮為羹,甚下氣,補中焦,令人虛,無氣力。[7]”至《食醫心鑒》出現了粥、鲙、索餅等劑型,且大多方劑記載有固定劑型。到了宋代食治劑型更加多樣,如《圣濟總錄·食治門》就有粥、羹、飲、索餅、臛、汁、撥刀、鲙、飯、棋子、馎饦、葅、糜、漿、乳、醍醐、饸子、餛飩、饆饠、糝等20余種,且多為北宋常見的食物類型。此外,《圣濟總錄》將前代方劑劑型進行改進,如取商陸治風水,《千金要方》為酒劑,《圣濟總錄·食治門》改為粥劑[5];再如牛蒡葉治療中風,《食醫心鑒》載:“細切牛蒡葉,煮三五沸,漉出于五味汁中重蒸,點酥食之。[2]”而至《圣濟總錄》明確記載其劑型為菹。通過以上分析可知,唐宋時期食治不僅以食物治病,且食療方劑型與普通飯食大多無異。以飯食的形制作食療,不僅口感較藥物湯劑、丸劑好,而且有利于疾病的治療。如對于粥,《素問·玉機真臟論篇》即指出:“漿粥入胃,泄注止,則虛者活”,如前文提及的商陸粥,將酒劑改進為粥劑,能減輕商陸峻猛之性對人體的傷害,可見飯食形制較傳統湯、丸等劑更具優勢,這使食治與藥治方劑出現了劑型的區別。
3 組方、制作復雜化
《千金要方·食治》以單味食物為綱,僅記載食物藥用功效與飲食宜忌等內容,應用食物或食物佐以少量藥物組成治療疾病的方劑即食療方,與其他方劑一同記載于《千金要方》其他卷次之中,此時并未重視食物組方應用。《食療本草》亦是以單味藥的記載為綱,部分食物附有簡單配伍,如雞頭實與蓮實同食可“駐年”[7];此外還有少量組方記載,如蓮子“著蠟及蜜,等分為丸服”[7],但此類記載甚少且比較簡單。至于《食醫心鑒》由于今已亡佚,無法判斷其體例,《證類本草》引《食醫心鑒》內容多為單方驗方,《醫方類聚》引用內容亦以食療方為主,可知此時已開始重視食療方的應用。至宋代出現了大量食療方,且食療方食物味數也有所增加,如《圣濟總錄·食治門》食羊肉方與鯉魚羹的藥食種類均達到9味。隨著醫家對于食物功效認識的不斷深入,食治應用經歷了從單味藥到簡單配伍再到食療方的過程,且食療方不斷復雜化,反映出食治向臨床應用不斷發展。
通過對《食醫心鑒》《太平圣惠方·食治》《圣濟總錄·食治門》分析發現,除了配伍、組方愈發復雜外,食療方的制作工藝也在不斷進步。如《食醫心鑒·小兒諸病食治諸方》記載治小兒血痢方:“取馬齒菜生搗絞取汁一合,和蜜一匙攪調,空心食之。[2]”而至《太平圣惠方》應用此方時記載更加詳細,明確了馬齒菜用量為兩大握,并加入粳米三合改為粥劑,且在方后注中詳細記錄制作及服用方法“上以水和馬齒莧煮粥,不著鹽醋,空腹淡食”[3]。此外,對面食工藝的改進亦十分普遍,如今存《食醫心鑒》209首食療方中僅有6首為面食形制,至《圣濟總錄·食治門》面食食療方達到40余首,且制作更加復雜。究其原因,一方面受到飲食文化的影響,如《圣濟總錄·食治門》載有“胡椒餛飩方”,而餛飩是宋代常見食物形制,《東京夢華錄》就記載北宋開封城內食店里就有餛飩店[8];另一方面,劑型的改進可促進疾病的治療,如《食療本草》載“小麥面”能“補中益氣,和五臟,調經絡”[7]。《圣濟總錄·食治門》有羊肉索餅方,用羊肉、白面、雞子黃與生姜汁作索餅,“治脾胃氣弱,見食嘔逆,瘦劣”[5]。方中羊肉、雞子黃補益脾胃,生姜汁止嘔,加入白面制成索餅能加強補益功效。可見,唐宋時期食療方制作在不斷優化,更加接近于普通飯食,食治的特點更加鮮明。
4 治病范圍全面化
隨著食治理論的發展,食治所能治療疾病的范圍也在擴大。今存《食醫心鑒》食療方按病證分為15類,包括內、外、婦、兒各科。至北宋初期,《太平圣惠方·食治》將食療方分為28類,增加了霍亂、耳聾耳鳴等病證的食療方。至北宋末期《圣濟總錄·食治門》又增加了治療吐血、婦人血氣病、蛔蟲病等內容,此時所治療疾病的種類逐漸增加并發展變化。如《太平圣惠方·食治》尚有記載服石的《補益虛損于諸肉中蒸煮石英及取汁作食治法》,記載服石食療方,至《圣濟總錄·食治門》不僅不見服石方,反而有《食治乳石發動》用以記錄治療服石后發動的食療方。因唐代服石之風盛行,北宋時期醫家對服石的危害有了比較清醒深刻的認識,多數追求長生者轉而進行內丹的修習[9],故此種趨勢也對食治產生影響,糾正了宋初《太平圣惠方·食治》的不足。此外,單個食療方治療疾病的范圍也有所拓展,如《太平圣惠方·食治》記載用檳榔粥“治腳氣,心腹妨悶”[3],至《圣濟總錄·食治門》除有以上記載外,還用以治療大便壅澀之證[5]。從以上內容可以看出,隨著中醫理論與食治理論的不斷發展,唐宋時期對于食治認識不斷深入,對于食物組方應用更加靈活,食療方治療疾病的范圍也在不斷擴大。
5 食治受眾普及化
除了以上提及的文獻外,部分非食治著作也開始重視食療方的應用。如老年養生專著《養老奉親書》就設專篇記載治療老年人17種疾病的食療方。陳直在《養老奉親書·食治養老序》中云:“今以《食醫心鏡》(即《食醫心鑒》)《食療本草》《詮食要法》《諸家法饌》,洎是注《太平圣惠方》食治諸法,類成養老食治方。[10]”再如《幼幼新書》中收錄《食醫心鑒》食療方治療小兒夜啼、驚癇等[11],此外普通民眾也開始接受食治。如南宋烹飪著作《山家清供》就有青精飯“久服,益顏延年”、酥瓊葉可“止痰化食”的記載[12]。食治的運用也進入宋人飲食生活中,如《東京夢華錄》記載酒肆有決明兜子、決明湯齏,夜市有藥木瓜等食物售賣[8];蘇軾有“一枕清風直萬錢,無人肯買北窗眠。開心暖胃門冬飲,知是東坡手自煎”[13]的詩句,記載蘇東坡清晨早起為米芾煮門冬飲的故事。以上可以看出,至北宋食治已被普遍接受,不僅得到各科醫生的重視,還進入了尋常百姓家。
綜上可知,食治在唐宋時期呈現出各方面迅速發展的特點,正是此時的發展使食治日趨成熟,成為中醫一門獨立的學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