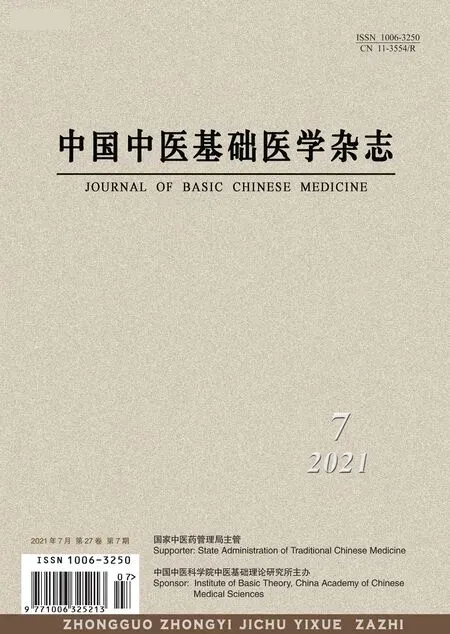近代上海疫病的中醫(yī)藥防治特色探究?
徐超瓊, 李 贛, 楊奕望△
(1.上海市徐匯區(qū)衛(wèi)生健康委員會, 上海 200030;2.上海中醫(yī)藥博物館, 上海 201203)
近代(1840~1949年)上海自1843年開埠以來,人口大規(guī)模流動,工業(yè)快速發(fā)展。在多重因素作用下,滬上霍亂、鼠疫、白喉、疫痙等疫病叢生,其中危害最大的當(dāng)屬霍亂[1]。故筆者主要以霍亂為探究對象,并涉及其他類型的疫病,如喉痧、疫痙等,挖掘相關(guān)史料,梳理當(dāng)時滬上中醫(yī)對疫病的防治特色。需要說明的是文章所指滬上中醫(yī),包含該時期在申城行醫(yī)的全國各地中醫(yī),并非特指籍貫上海的醫(yī)者。
1 師承古方,自定療法
1.1 王孟英創(chuàng)制霍亂方
上海開埠后人口密集、河水惡濁。1862年,霍亂流行,此病發(fā)于腸,常伴隨劇烈腹瀉導(dǎo)致患者嚴重脫水。避亂定居滬上的王孟英修改著述,名曰《隨息居重訂霍亂論》,總結(jié)歷代治療霍亂的理法方藥并根據(jù)病情改良藥方。霍亂初定時,對于余熱未清、神清而脈至模糊者,王孟英根據(jù)陳平伯《游宦紀(jì)聞》所載方藥,調(diào)雄黃、牙硝比率為一比六,研細熔化,取三厘與藥汁調(diào)勻以內(nèi)服[2]。王孟英還師法《金匱要略》治療霍亂轉(zhuǎn)筋的雞矢白散,創(chuàng)制名方蠶矢湯[2]。
1.2 徐相任擬定霍亂方
l908年夏秋間,滬上霍亂肆虐,徐相任主張師承各家之說,需取其長而糾其偏也。他斷定霍亂為陰寒證,應(yīng)以溫?zé)崴幹沃⒏鶕?jù)不同時期的發(fā)病特征自擬脫疫方。霍亂初起,形氣未變、冷汗未甚、四肢微冷者,自訂理中定亂湯,該方由張仲景附子湯、《衛(wèi)生寶鑒》附子溫中湯衍化而來,有溫中祛寒化濕、順氣辟穢之效;霍亂吐泄稍后,形氣不支、冷汗愈多、四肢如冰者,取《太平惠民和劑局方》處方,又據(jù)《婦人良方》四神丸加減,得經(jīng)驗方回陽來復(fù)丹回陽救逆、溫中導(dǎo)濁;危篤霍亂后,據(jù)王孟英蠶矢湯化裁擬定三矢定亂湯,供霍亂善后調(diào)理或預(yù)防服用,以晚蠶矢、豭鼠矢、干雞矢白為主藥,溫中燥濕、理氣辟穢,臨床療效顯著[3]。
1.3 丁甘仁自制疫喉方
時疫喉痧由來久矣,傳染迅速,流行滬上之際,孟河名醫(yī)丁甘仁頗有心得。他指出此癥發(fā)于夏秋者少,冬春者多,且與白喉的治療有所差異。白喉固宜忌表,而時疫喉痧初起時須速表,故將其分為初中末三個階段,治以汗、清、下,又細分在氣在營,或氣分多,或營分多,遵循葉天士的衛(wèi)氣營血辨證綱領(lǐng),列有自制經(jīng)驗方,如解肌透痧湯、加減麻杏甘羔(膏)湯等。
1.4 嚴蒼山化裁疫痙方
嚴蒼山師承丁甘仁,對疫痙的診斷有著獨到的見解。1929年春上海疫痙流行,患者多有頭痛如劈、項強等癥狀。西醫(yī)稱之為流行性腦脊髓膜炎,較為常見的治法是注射球菌血清,但效驗不佳。當(dāng)時中醫(yī)界對疫痙的認識各持己見,有認為肝風(fēng)或瘟毒引起,也有認為中風(fēng)或驚風(fēng)導(dǎo)致,意見紛紜,治法各異。嚴蒼山指出該年滬上疫痙流行與冬春易令、陰陽乖逆有關(guān),冬應(yīng)寒而反溫,春應(yīng)回暖而酷冷,天時不正影響身體,使奇疫乃發(fā)。他認為治療疫痙需疏通表里、祛除外寒透郁熱、增津液養(yǎng)營血以解疫氣。《傷寒論》中的葛根湯即為此疫特效方[4]。嚴蒼山遂根據(jù)病情實際變化增減化裁,創(chuàng)葛根梔豉湯、羚羊舒痙湯等方[5]。
可見,傷寒學(xué)說、溫病學(xué)說與疫病學(xué)說在發(fā)展過程中內(nèi)在緊密相連。中醫(yī)治療疫病承歷代經(jīng)典,博采眾長,不拘一家之言,可結(jié)合實際病證、癥狀創(chuàng)新改良古方,從而更好地發(fā)揮臨床療效。
2 中西并行,巧用西學(xué)
2.1 改良藥劑,延長存儲時間
1919年6月上海再度霍亂流行,南市一帶患者罹難眾多。醫(yī)藥界人士為此深感擔(dān)憂,倡議設(shè)立中醫(yī)診察所,聘請神州醫(yī)藥總會諸醫(yī)士擔(dān)任醫(yī)務(wù),經(jīng)費則由藥業(yè)籌募,在咸瓜街沙布弄湯府空余的房屋內(nèi)成立了臨時疫癥救濟社。歐風(fēng)東漸,西藥以其便利逐漸盛行,而中藥不可避免“撥爐分炭、裹絹去毛”的繁瑣煎制過程才可被患者服用,不足以救時疫之急,于是藥界人士打算改良藥劑。起初醫(yī)家預(yù)煎各種藥汁,待病人診斷結(jié)束后便給以服用。服之即有溫脈止吐泄之良效,中醫(yī)確能治疫、中藥確能救疫的事實廣為人知,即便未有廣告宣傳,滬西、閘北等地的患者紛至沓來。由于天氣炎熱,煎成的湯藥經(jīng)宿即壞,或隔數(shù)小時就不能再用,耗費藥資頗巨。
疫情暫緩時,中醫(yī)藥界聯(lián)合各慈善家打算擴充原址,將其改為滬南神州醫(yī)院,并向藥劑師、化學(xué)家請教研究,得知飲片提精可以讓藥劑延長保存時間,并就藥物計重、配方等問題反復(fù)試驗,效果顯著。1920年夏疫病又一次爆發(fā),醫(yī)院在中華路分設(shè)臨時治疫所,并用制成的藥水治療患者,奏效迅速,治愈千人。在中醫(yī)藥團體的支持下,醫(yī)界人士籌劃建造制藥廠以樹立改良藥材之基礎(chǔ)。1920年9月,李平書、丁甘仁等醫(yī)家聯(lián)合上海總商會創(chuàng)辦制藥廠,聘請理化學(xué)專家、藥劑師及醫(yī)藥界人士化驗分析如何保存中藥性能的科學(xué)方法,提選出藥水、藥粉、藥精等精華,并用于次年夏季的疫病救療[6,7]。粹華制藥廠的藥水取用原料道地,經(jīng)過生炒炙制的分別,服用時不存在渣滓且無須煎煉,奏效尤靈,深得醫(yī)界好評。故粹華制藥廠在南京路設(shè)立營業(yè)部開幕以來,改良藥品十分暢銷[8,9]。正如時人所言,此舉“在醫(yī)生仍可照舊開方,在病人可免煎之勞,實我國醫(yī)藥界之大進步云”[10]。
2.2 融會新知,匯通中西醫(yī)理
不少中醫(yī)人士逐步了解西醫(yī)知識,對中西醫(yī)理進行學(xué)習(xí)與比較。1926年的上海霍亂席卷重來。章太炎認為霍亂為寒證,宜用四逆湯、通脈四逆湯二方主治,有強心臟、止吐利之效。西人用鹽水注射脈中,能保住水分,令不泄出,鹽能凝血亦能調(diào)血,霍亂血結(jié)如塊,用鹽水者是謂取其柔也,故認為鹽水與四逆茱萸二湯有異曲同工之妙,醫(yī)理相通,對此持肯定態(tài)度。在此基礎(chǔ)上,章太炎又提出可以用明礬或石榴皮或銅青殺菌[11,12]。1927年,名醫(yī)祝味菊由成都避亂來到上海,提及霍亂當(dāng)以鹽水補充水分、激發(fā)心力,并指出霍亂邪毒入侵血分時,血液會產(chǎn)生特異物質(zhì)中和并削弱毒素[13]。祝味菊臨床亦多用附子、干姜等溫?zé)崴帲〉幂^好的療效。
陸淵雷主張治療霍亂的中西學(xué)理方法根本相同,認為姜附可留住人體液汁避免吐泄,而鹽水則起到補充液汁的效果。前者是保全未喪失的水分,后者是補充已喪失的水分。中西療法皆從水分上施治,但臨床仍需依據(jù)實際情況選擇合適的療法,若遇到病人吐泄不止,體內(nèi)液汁喪失已多,存亡呼吸之頃,考慮到服用姜附發(fā)揮效力需要相當(dāng)時間,則強調(diào)用西醫(yī)灌注鹽水的療法較佳。中醫(yī)若熟知鹽水灌注的學(xué)理方法,如鹽水的濃度也可自行操作。陸淵雷又指出,服用姜附除有保全水分的功效,還有興奮機體產(chǎn)生抗毒素的機能。因此他認為霍亂初病時,服用姜附與鹽水注射相比能使患者恢復(fù)更快,建議患者即便病重在灌注鹽水后也應(yīng)兼服姜附,雙管齊下提高療效[14]。
西醫(yī)注射鹽水的療法得到中醫(yī)學(xué)界的普遍認可,但對于霍亂的寒熱屬性,中醫(yī)界則各持己見,頗有爭議。王一仁認為雖見霍亂患者有吐泄肢冷、脈伏、冷汗如漿之癥,未可如章太炎所論直接投以四逆等溫?zé)釀O喾矗?dāng)結(jié)合歲運而定,他認為天時亢旱過久,導(dǎo)致心臟亢熱過盛,霍亂癥多為熱者,故其療法與之相悖,以五苓散治之或用萸連解毒湯清心臟之熱,外加碧玉散銀花連翹丹皮山梔等味佐助清暑。章太炎與王一仁商榷再論霍亂之治法,提及即便天時亢旱、熱癥之多,然若深夜當(dāng)風(fēng)、裸袒露臥、多飲寒漿亦能致寒,又言暑候脈緩流遲,多見心弱虛寒之癥。因此,章太炎道四逆為急救之方,而五苓為善后之藥。見此王一仁又言,以熱劑治愈者為感暑熱之輕者,而受暑熱之深重者不適此法,當(dāng)究致病之源,辨其可別之癥,故與章太炎相約,觀熱霍亂癥者以證其言[15,16]。張聿青在滬行醫(yī)10余年,對于霍亂病的療法則另有見解。據(jù)記載,張聿青指出霍亂熱證未必于未病之前先顯火象,反之霍亂寒證亦未必先露寒證。認為霍亂初起之時可不問寒熱,概用芳開之品,之后再根據(jù)所見之象治之。若為熱象,則使火熱之氣透于濕外;若為寒象,則使陰凝之氣宣暢運行[17]。上海中醫(yī)界展開的激烈學(xué)術(shù)探討,進一步推動了疫病的預(yù)防治療水平。
3 改善環(huán)境,衛(wèi)生防疫
3.1 水源衛(wèi)生
早期開埠的上海人煙稠密,城市居住環(huán)境不斷惡化,疫癘時行。王孟英提倡保持飲水衛(wèi)生以防感染霍亂,認為水道應(yīng)避免污穢沉積,可積極開鑿井泉,避免飲用污濁水源。此外,還提出在特定時節(jié)利用藥物對飲用水源進行消毒,杜絕外邪滋生之源。尤其夏季,提議在井中放入白礬、雄精之整塊者,或在水缸內(nèi)浸泡石菖蒲根和降香。
3.2 飲食習(xí)慣
在飲食習(xí)慣方面,王孟英認為夏季可少服參藥或膩滯之補益品如龍眼、蓮子等,避免加重脾胃運行負擔(dān),使邪氣得補而無從宣泄。而瓜果冰涼等物過食亦遏伏熱邪,宜有所忌,其他如鰻鱔等性熱助陽者,若食之而得霍亂更難救治,故宜杜絕。反之,一些夏令蔬菜如芹、筍、蘿卜、絲瓜等,多食亦可防霍亂浸染[2]。一些中醫(yī)開始關(guān)注疫病傳播途徑。陸淵雷認為霍亂菌的傳染在于飲食衛(wèi)生。蒼蠅業(yè)集霍亂病人的吐瀉物,再次接觸食物,人食此物即被傳染。所以當(dāng)避免食物顯露在外,食畢即罩起減少蒼蠅接觸的機會,切斷疫病傳播途徑[14]。
3.3 生活起居
由張贊臣、楊志一、朱振聲等發(fā)起創(chuàng)辦的醫(yī)界春秋社,作為民國時期極具影響的中醫(yī)社團,在疫病流行期間進行了夏令防疫個人衛(wèi)生的知識宣傳。除了主張市民勿食蒼蠅扒過之物,妥善處理霍亂吐瀉物,在飲食方面吃熟食、飲沸水、忌食冷物、禁食葷物和隔宿之物等外,還強調(diào)應(yīng)當(dāng)重視起居,勿露宿貪涼、勿汗流當(dāng)風(fēng)、勤沐浴以及多休息養(yǎng)足精神等,這些措施說明滬上中醫(yī)已經(jīng)懂得利用團體組織的力量,宣傳帶有中醫(yī)特色的防疫方法。
3.4 空氣衛(wèi)生
民國初年的上海與開埠初期大相徑庭,現(xiàn)代化工業(yè)已具雛形。李平書指出喉痧多在北省流行,后來在南方蔓延,上海較為嚴重,與當(dāng)時上海廠房劇增、嚴重的大氣污染有關(guān)[18]。可見疫病的流行與環(huán)境污染有著緊密的聯(lián)系,保持空氣潔凈對喉痧的防治有著重要意義。
3.5 消毒、隔離與藥物預(yù)防
嚴蒼山向大眾推薦了可預(yù)防夏令霍亂的國產(chǎn)藥物,如鮮蘆根、青蒿、鮮荷葉等簡便藥餌,紅靈丹、辟瘟丹等常備藥[19]。有中醫(yī)強調(diào)須在廢棄病人吐泄物之前,用極濃臭藥水處理殺菌,避免出現(xiàn)蒼蠅接觸吐泄物進而傳播病菌的情況[14],同時還建議將既病之人進行隔離[20]。以上舉措清晰可見西方醫(yī)學(xué)之防疫方法,如化學(xué)法處理穢物、隔離病人等,說明當(dāng)時中醫(yī)逐步接受并開始實施西式衛(wèi)生方法預(yù)防疾病。
正因為上海開放較早,更先一步受到西方文化熏染,城市環(huán)境不斷變化。隨著疫病發(fā)生頻率的顯著提高,王孟英、李平書、陸淵雷等中醫(yī)大家逐漸意識到自然環(huán)境、飲食衛(wèi)生、生活起居等因素與疫病流行的相關(guān)性,將防治重點轉(zhuǎn)移到隔離病患、消毒殺菌等先進防治措施上,表明中醫(yī)已將治未病的優(yōu)良傳統(tǒng)落實到防疫的具體實踐中。
4 結(jié)語
中醫(yī)藥對近代上海防治疫病起到至關(guān)重要的作用。清末時期,西醫(yī)尚未在上海廣泛傳播,中醫(yī)作為防治疫病的主要力量,在大疫之年不避疫氣,施醫(yī)送藥,治愈了無數(shù)疫病患者。為了讓更多的患者免于疫病疾苦,滬上中醫(yī)常通過大眾傳播媒體,如報刊專欄刊布醫(yī)案及良方,主要針對疫喉痧、霍亂等疫病[21,22]。民國時期,西醫(yī)白喉抗毒素、天花疫苗等臨床藥物的研制足以對此類疫病進行有效干預(yù)。然而因存在社會階層經(jīng)濟條件的巨大差異,滬上多數(shù)居民如南市城郊一帶貧民無力負擔(dān)昂貴的西藥費用,故疫病時期尋求中醫(yī)診治依舊是多數(shù)市民的選擇。更有貧瘠者無力購買中藥,而此時懸壺于鄉(xiāng)間的中醫(yī)則不收其診金。如1902年秋松江瘟疫流行,名醫(yī)姚水一擅長治療時疫,面對貧病患者經(jīng)常施診給藥。因醫(yī)務(wù)繁忙,有時難卻病家之請遠道出診,往往黃昏始得返家。同樣,世醫(yī)張友萇亦以民命為重,時常下午出診至次日凌晨才返回,中途有人邀請也不忍拒絕,對貧病者往往免費出診,自己則忍饑耐勞遂得胃病[24]。盡管個人醫(yī)療作用相對有限,但治愈的患者卻不在少數(shù),從中不僅看到滬上中醫(yī)同情病患的仁愛之心,也反映出當(dāng)時民間豐富的中醫(yī)醫(yī)療資源。
近代滬上疫疾盛行的環(huán)境客觀上推進了中醫(yī)診療方式的創(chuàng)新。一方面,對于疫病不同時期的病情變化,中醫(yī)在師承歷代傷寒、溫病大家經(jīng)典的基礎(chǔ)上博采眾長,自擬方藥。如霍亂流行時期,有王孟英的蠶矢湯、徐相任的理中定亂湯等;疫痙爆發(fā)期,有嚴蒼山的葛根梔豉湯、羚羊舒痙湯等。另一方面,疫疾流行時期,患者劇增,而中醫(yī)治病擬方煎藥不可避免,此時藥液準(zhǔn)備耗時較長、過程繁瑣的弊端逐漸顯現(xiàn),使得中醫(yī)界人士萌發(fā)了改良藥劑的想法,并在社會各界支持下,提精飲片制得藥水,提高了中藥性能的保存時間,使大眾免于病況危急且用藥供遲之隱患。
近代上海中醫(yī)防治疫病更有一定階段性,大致以“中華民國”成立(1912年)為界,前后分2個階段。清末時期在疫病治療方面,上海中醫(yī)普遍使用中醫(yī)治法辨證論治,因地制宜。如青浦19代世醫(yī)陳蓮舫,在江南兵災(zāi)橫行、瘟疫肆虐之時,精醫(yī)理、諳運氣、詳審時疫,憑借高超醫(yī)術(shù)使民眾免受疾患之苦[24]。至民國時期,如陸淵雷等學(xué)習(xí)西醫(yī)藥知識精深的醫(yī)家,肯定西醫(yī)鹽水注射治療霍亂法。此外,滬上這2個時期的中醫(yī)對疫病預(yù)防的觀念也明顯不一。清末上海中醫(yī)的防疫思想相對傳統(tǒng),除王孟英提到需注意飲水衛(wèi)生外,多數(shù)醫(yī)家強調(diào)保持健康的飲食習(xí)慣,以增強自身抵抗力,抵御外邪入侵。比較而言,民國時期隨著西方新式衛(wèi)生防疫機制的引入,部分中醫(yī)逐漸接受了清潔衛(wèi)生、殺菌消毒、病患隔離等防疫方法,并提倡實施,起到了較好的防疫效果。時光荏苒,彈指百年。2019年末的新冠疫情以來,預(yù)防和治療疫病成為全球關(guān)注的焦點,上海再一次交出了令世人滿意的答卷。新的時代背景下,回顧一百多年前的史料,梳理近代上海疫病的中醫(yī)藥防治特色,可以為當(dāng)今疫病的防治提供有益的借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