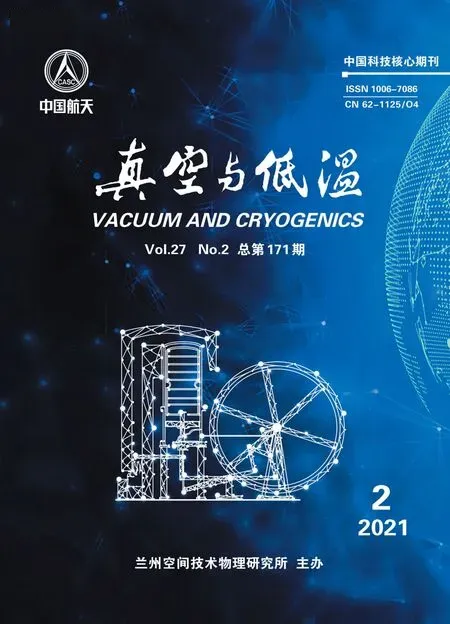物理氣相沉積銅膜本征應力形成機制及影響因素研究進展
王蘭喜,張凱鋒,王 虎,王 藝,熊玉卿,吳春華,李 坤,周 暉
(蘭州空間技術物理研究所 真空技術與物理重點實驗室,蘭州 730000)
0 引言
隨著薄膜航天器、大型空間電池陣、柔性展開天線、柔性電纜、柔性電子學等技術的快速發展,對物理氣相沉積(PVD)高質量銅(Cu)膜材料提出了迫切的需求[1-4]。然而,在沉積過程中,Cu膜會形成本征應力,導致Cu膜彎曲變形,這不利于后期對Cu膜的高精度加工和高可靠應用,在本征應力非常高的情況下,甚至會導致Cu膜開裂和脫落[5-8]。用PVD制備Cu膜的本征應力類型和高低隨膜厚呈現出一定規律的變化[9-11],本征應力會受到鍍膜方法[12]、基底狀態[13-14]、鍍膜工藝參數[15-17]等的顯著影響。科研人員研究了Cu膜本征應力的形成機制、演變規律和影響因素,為降低或消除Cu膜本征應力提供了理論依據和技術途徑。
本文根據近幾年用PVD制備Cu膜的研究工作,總結并歸納Cu膜本征應力的形成機制、演變規律、影響因素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為開展真空鍍制低本征應力Cu膜的研究提供參考。
1 物理氣相沉積Cu膜本征應力形成機制及變化規律
對于大多數非外延的用PVD制備薄膜材料而言,薄膜主要有兩種生長模式:一是對于高熔點(或沉積原子的遷移率低)材料,薄膜以柱狀晶生長為特點,連續成膜后保持本征張應力狀態;二是對于低熔點(或沉積原子的遷移率高)材料,薄膜按照Volmer-Weber的島狀方式生長,連續成膜后本征應力出現張應力向壓應力轉變的變化過程,如圖1所示。Cu屬于高遷移率材料,Cu膜生長過程包括島的生長、島與島接觸、島合并成連續的薄膜、連續薄膜繼續生長增厚,薄膜具有多晶體結構的特點。研究人員對Cu膜這類高遷移率薄膜中不同本征應力狀態的形成機制給出了一定的解釋。

圖1 薄膜本征應力隨膜厚的變化關系示意圖Fig.1 Schematic diagrams of the intrinsic stress evolution with film thickness
關于薄膜島狀生長階段壓應力的來源,Camma?rata等[9]認為島的表面原子和內部原子間的成鍵狀態存在本質區別,這種區別形成的Laplace壓力[18]將導致產生表面應力。他們將島簡化為圓柱體模型,如圖2所示,理論上,島的本征應力由圓柱體上下表面和側面的表面應力決定,如式(1):


圖2 薄膜生長初期島的圓柱體模型圖Fig.2 The cylindrical model of the island in the beginning of film growth
式中:f、g、h分別為圓柱體模型上表面、膜基界面和側面的表面應力;t和d分別為圓柱體的厚度和底面直徑;t0和d0是零本征應力所對應的值;β的表達式為β=1+2S13′(/S11′+S12′),S11′、S12′、S13′分別是圖2笛卡兒坐標系下的彈性柔度,各向異性材料的β值與晶體取向有關,如Cu的β100=-0.448,β111=0.26。
該理論解釋了薄膜在島狀生長階段產生壓應力的原因,并認為該壓應力始終存在于薄膜后續的生長階段。他們借鑒了Nix等[19]關于島合并時表面能變化(島的自由表面變成晶粒界面)會產生較高張應力的理論,該張應力抵消了島狀生長階段產生的壓應力,因此對外表現出張應力的快速上升。
除了島狀生長階段產生壓應力及島合并形成晶界使表面能變化引起張應力快速上升外,薄膜連續生長后的本征應力隨著沉積條件的不同而存在差異。為了更詳細地從理論上研究島合并成連續薄膜后本征應力的變化過程及特點,Chason等[10]采用了一種模擬晶界生長的模型,如圖3所示,假設相鄰兩個晶粒分別以外延方式生長,當兩個晶粒中第i原子層相遇時晶界長大。薄膜的本征應力可用式(2)表示:


圖3 多晶薄膜晶界生長過程示意圖Fig.3 The schematic of grain boundary growthin polycrystalline film
式中:σC為本征壓應力;σT為本征張應力;D為吸附原子向晶界的擴散率;R為沉積速率;L為晶粒尺寸;γ為一個與表面原子濃度和薄膜機械性能有關的系數。在單一因素影響下,沉積原子向晶界的擴散率越大、薄膜沉積速率越低、晶粒尺寸越小,對張應力的弛豫作用越強。γD/RL作為整體代表吸附原子擴散進入晶界的時間,γD/RL?1時,吸附原子沒有足夠的時間擴散進入晶界,本征應力向張應力發展;γD/RL?1時,吸附原子具有足夠的時間擴散進入晶界,本征應力向壓應力發展。另外,雖然晶粒尺寸小能夠增強對張應力的弛豫作用,但小晶粒薄膜中具有更多的晶界并能形成更高的張應力,晶界增多產生的張應力增強要遠高于原子擴散進入晶界對張應力的弛豫,因此實驗結果更多地體現出晶粒越小,張應力越高的趨勢。
薄膜自身生長過程中本征應力的形成過程,也可稱為生長應力,比較成功地解釋了蒸發鍍膜本征應力的產生和變化過程:在薄膜成核階段,分立的島緊附于基底之上,由于島的表面應力作用,使島中的晶格常數不能保持平衡條件而產生壓應力;隨后,在島合并過程中,島與島相互接觸形成晶界,島的表面能降低,導致薄膜產生張應力并快速增加;島合并完成后形成連續薄膜并持續生長,根據沉積原子遷移率或是沉積速率的高低,薄膜最終的本征應力狀態可為張應力或是壓應力。
Kaub等[11]認為用式(2)描述用濺射這種載能沉積方法所鍍薄膜的本征應力存在局限,模型中應該引入由載能粒子碰撞、錘擊效應引起的應力變化。因此,對式(2)進行了優化,加入了粒子碰撞或錘擊效應在薄膜晶界和晶體結構中引入缺陷所導致的本征應力變化,如式(3)所示,較好地解釋了磁控濺射鍍Cu膜和鍍Mo膜本征應力隨沉積氣壓和沉積速率的變化過程。

式中:A0和B0為模型為帖近實驗數據而設立的可調參數;l為一個假設的相對長度值,l與粒子能量有關,在l范圍內的載能粒子轟擊薄膜表面將會引入壓應力;τs為一個缺陷擴散至表面并消失這一過程的特征時間。
總之,薄膜最終本征應力狀態主要由材料特性和微觀結構決定。Cu膜本征應力對沉積過程比較敏感,易受沉積方法和沉積條件的影響,呈現出豐富的本征應力狀態。以下對PVD中常見鍍Cu膜的蒸發法和濺射法所制備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因素的重要研究進展進行總結。
2 真空蒸發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因素
2.1 沉積速率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
科研人員在原位測量Cu膜本征應力隨沉積時間的變化過程中發現,沉積結束后Cu膜本征應力經常出現向張應力轉變的趨勢,可以理解為Cu膜沉積速率的變化導致Cu膜本征應力的改變。因此,科研人員開展了沉積速率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研究。
Vecchio等[15]研究了沉積速率對蒸發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Cu膜是沉積在(100)取向的Si片上,樣品溫度被全程記錄以去除熱應力的影響。作者設計了兩類實驗方案:一是Cu膜沉積過程中沉積速率恒定不變,分別制備不同沉積速率下的Cu膜。二是不中斷Cu膜沉積過程,通過沉積速率的交替變化來原位監測Cu膜本征應力的動態變化。研究結果表明,Cu膜的平均張應力極大值與沉積速率無明顯依賴關系,具有隨機分布的特征,即使在同一沉積速率下也可能出現完全不同的平均張應力極大值,如圖4(a)所示。因此,沉積速率不是影響Cu膜張應力極大值的因素。Cu膜的島合并后,平均壓應力增量隨著沉積速率的增加而下降,如圖4(b)所示,在沉積速率高低交替變化的情況下同樣出現了平均壓應力增量隨沉積速率增加而減小的結果,如圖4(c)所示。

圖4 沉積速率對蒸發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曲線Fig.4 The influence of deposition rate on the intrinsic stress of evaporated copper film
Friesen等[20]研究了熱蒸發鍍Cu膜過程中斷和沉積速率變化對本征應力的影響。發現在沉積中斷期間,Cu膜的單位寬度應力(Stress-thickness)隨時間增加向張應力方向變化,生長重新開始后單位寬度應力的恢復時間顯著比沉積中斷后的弛豫時間短,呈現出明顯的不對稱性,如圖5(a)中的D和E階段。繼續深入研究后發現,Cu膜的這種變化特征實際上與沉積速率的變化有關。在Cu膜生長的各個階段,沉積中斷時平均本征應力的逆向變化量隨中斷前沉積速率的增加而增加,如圖5(c)所示,與中斷時的膜厚無關,如圖5(b)所示。連續沉積條件下改變沉積速率,如果改變后沉積速率高于改變前沉積速率,則沉積速率改變后單位寬度應力存在瞬時壓應力增量,如圖5(d)所示;如果改變后沉積速率低于改變前沉積速率,則沉積速率改變后單位寬度本征應力存在瞬時張應力增量,如圖5(e)所示。

圖5 熱蒸發鍍Cu膜沉積中斷和沉積速率變化對本征應力的影響曲線Fig.5 The influence of deposition interruption and deposition rate variation on the intrinsic stress of thermal evaporated copper film
關于Cu膜本征應力在沉積中斷或改變沉積速率時表現出的變化行為,Friesen等[20]認為這與表面吸附原子有關。沉積開始時,基底或Cu膜表面的吸附原子濃度快速升高,產生壓應力。隨著沉積的繼續,Cu膜表面粗化,產生多種表面缺陷,阻礙了吸附原子在表面的遷移,形成動態不對稱性,從而產生沉積中斷后應力弛豫過程和恢復過程的不對稱實驗結果。隨著沉積速率的增加,吸附原子濃度增加,因此沉積中斷后Cu膜的應力逆向變化量增大。
2.2 基底表面狀態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
Abermann[13]認為沉積原子在基底上的遷移率對薄膜生長過程和本征應力狀態具有關鍵作用,作者通過在生長表面引入化學吸附的O2來降低沉積Cu原子的遷移率,發現輕微增加O2分壓便可以顯著改變蒸發鍍Cu膜中的本征應力狀態。如圖6所示,隨著O2分壓的增加,成核密度提高,島合并階段向更低膜厚方向偏移,Cu膜連續后的壓應力增加,當薄膜較厚時又提高了本征應力從壓應力向張應力的增加速率。該現象的原因被認為是Cu膜-基底界面處應變場的傳遞被更多的晶界和缺陷所抑制。

圖6 在MgF2基底上熱蒸發鍍Cu膜時O2分壓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Fig.6 The influence of oxygen partial pressure on the intrinsic stress of the thermal evaporated copper film on MgF2substrate
隨后,Chocyk等[21]在研究熱蒸發鍍Cu膜的應力變化過程中發現,Si基底的不同清洗方式會導致Cu膜本征應力隨沉積時間變化過程的差異。在采用丙酮和乙醇清洗的基底上以低速率沉積的Cu膜的本征應力的變化過程為低壓應力-張應力-壓應力,以高速率沉積Cu膜的本征應力則呈現低壓應力-張應力-壓應力-張應力的變化過程,如圖7(a)所示;而在用丙酮清洗的基底上以低速率沉積的Cu膜的本征應力則表現出低壓應力-張應力-壓應力-張應力的變化過程,如圖7(b)所示。作者把在干凈基底上(乙醇+丙酮清洗)高速率沉積的Cu膜和在不干凈基底上低速率沉積的Cu膜中本征應力最后向張應力轉變的現象歸結于薄膜中的雜質,雜質抑制了由晶界或缺陷處產生的壓應力。基底表面狀態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主要是通過改變Cu原子在基底表面的遷移率來實現的,原子遷移率的改變能夠直接影響Cu膜在基底上的生長模式,不同生長模式決定了Cu膜的微觀晶體結構,Cu膜最終也表現出不同的本征應力狀態。

圖7 基底不同清洗方式對熱蒸發鍍Cu膜本征應力變化過程的影響Fig.7 The influence of substrate cleaning process on the intrinsic stress of thermal evaporated copper film
2.3 薄膜結構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
Shull等[22]報道了高真空蒸鍍Cu/Ag多層結構薄膜本征應力隨膜厚的變化關系。在多層膜生長過程中,每一個單獨Cu層或Ag層的本征應力隨膜厚的變化趨勢不變,均為弱壓應力-張應力-壓應力的過程。但是Cu層張應力產生極值時的膜厚受其下面Ag層厚度的影響,隨著Ag層厚度的增加,Cu層產生張應力極值的位置向高膜厚方向偏移。通過調整Cu/Ag多層結構實現了整個薄膜最終的應力狀態是壓應力或者張應力,展示出用該方法可以對薄膜本征應力進行調控,如圖8所示。

圖8 Cu/Ag多層膜結構對本征應力的調控圖Fig.8 Intrinsic stress modulation via Cu/Ag multilayers
3 真空濺射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因素
真空濺射鍍膜是利用荷能粒子轟擊固體靶面,將靶原子或靶分子從表面濺射出來并沉積到基底上的鍍膜過程。與蒸發鍍膜不同,濺射鍍膜以輝光放電為基礎,沉積原子從靶面到基底具有比較復雜的輸運過程。Thornton[23]提出一種磁控濺射鍍金屬膜晶體結構分區圖(Thornton模型),如圖9(a)所示,該圖基于實驗結果得出,不同于蒸發鍍膜的晶體結構僅與基底溫度有關(Movchan-demchishin模型[24]),Thornton模型給出薄膜晶體結構隨沉積氣壓和基底溫度變化的關系。隨后Messier等[25]又將磁控濺射鍍膜晶體結構分區圖進一步發展,將沉積氣壓用粒子能量代替,并引進膜厚因素,得出更全面的磁控濺射鍍膜晶體結構分區圖(Messier模型),如圖9(b)所示。根據磁控濺射鍍膜晶體結構分區圖分析:影響薄膜晶體結構的本質因素可能是基底吸附原子的表面遷移能力,由晶體結構決定的薄膜本征應力狀態也因此受到沉積氣壓、濺射功率、基底狀態等因素的顯著影響。

圖9 磁控濺射鍍膜晶體結構分區圖模型Fig.9 Models of structural zones for magnetron sputtered films
3.1 沉積氣壓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
在濺射鍍Cu膜過程中,沉積氣壓對成膜質量具有重要的影響。從微觀角度來看,沉積氣壓是影響濺射粒子平均自由程的主要參數,沉積氣壓低時濺射粒子的平均自由程長、對基底具有原子錘擊效應,能夠形成致密的薄膜,易形成壓應力狀態;相反,沉積氣壓高時濺射粒子的平均自由程短、基底存在陰影效應,形成多孔隙的柱狀晶結構,易形成張應力狀態,如圖10所示[17]。

圖10 沉積氣壓導致的錘擊效應和陰影效應對濺射鍍膜應力狀態和薄膜特征的影響圖Fig.10 The influence of atomic peening and shadowing effectresulting from different deposition pressures on the stress and characteristic of sputtering films
Entenberg等[26]曾在25μm厚聚酰亞胺(PI)柔性基底上用磁控濺射方法制備了250 nm厚的Cu薄膜,研究了Cu膜內應力(內應力由本征應力和熱應力組成,熱應力占比較低,小于8%)隨沉積氣壓的變化規律。研究結果顯示,Cu膜內應力隨沉積氣壓的升高從壓應力向張應力轉變,轉變氣壓在0.333 Pa,如圖11(a)所示。作者指出,該轉變氣壓由濺射材料的原子質量決定,在較低沉積氣壓下,沉積原子以垂直方向和較高動能入射到基底表面,原子錘擊效應使得晶粒間相互挨得很近,晶粒埋入薄膜中(如圖11(b)所示),產生壓應力;在較高沉積氣壓下,濺射原子受等離子體散射,以斜入射和低動能方式撞擊基底表面,從而產生陰影效應,在成核臺階處產生空位,導致柱狀晶生長(如圖11(c)所示),最終形成張應力。

圖11 柔性PI基底上濺射鍍Cu膜的內應力隨沉積氣壓的變化及不同沉積氣壓下Cu膜斷面的SEM照片Fig.11 The internal stress evolutionwith deposition pressure of copper films on PI substrateas well as the SEM imagesof the crosssection of copper films deposited underdifferent deposition pressures
Navid等[16]改變磁控濺射的沉積氣壓在Si基底上鍍制了Cu薄膜,不同沉積氣壓下Cu薄膜總應力(作者未對濺射過程溫度進行測試,因此未將熱應力從總應力中去除,并認為原位測量的應力基本上為本征應力)明顯表現出與沉積氣壓的強烈相關性,如圖12(a)所示。在0.3 Pa的低沉積氣壓下,Cu膜應力具有類似于真空蒸鍍Cu膜(Volmer-Weber生長模式)典型的本征應力變化特征,在膜厚10 nm處出現張應力的極大值,隨后應力轉變為壓應力并一直持續到最后。在0.7 Pa沉積氣壓下生長的Cu膜,初始時為壓應力并逐漸轉化為張應力,在膜厚100 nm時達到張應力的極大值,隨后Cu膜應力一直保持在張應力狀態。在1.4 Pa的高沉積氣壓下,Cu膜應力在整個生長階段均為張應力狀態,并在膜厚50 nm時達到張應力的極大值。用掃描電鏡對Cu膜的表面形貌進行分析,0.3 Pa沉積氣壓鍍Cu膜的表面晶粒粗大,隨著沉積氣壓增加到0.7 Pa,Cu膜晶粒細化,至1.4 Pa時Cu膜表面出現明顯裂紋,如圖12(b)所示。

圖12 不同沉積氣壓下Cu膜應力隨膜厚的變化過程以及薄膜表面形貌的SEM圖Fig.12 The stress evolution with film thickness of copper films deposited at different pressuresandthe SEM images of the topography of these copper films
Pletea等[27]利用磁控濺射方法在Si(100)基底上沉積了Cu膜,研究了沉積氣壓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將沉積氣壓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分成如圖13(a)所示的三種情形:在0.05~0.20 Pa的低沉積氣壓下,Cu膜本征應力僅在壓應力范圍內隨膜厚變化;在2~6 Pa高沉積氣壓下,Cu膜本征應力在張應力范圍內隨膜厚變化;在0.5 Pa的中等沉積氣壓下,Cu膜本征應力隨膜厚在壓應力和張應力之間變化。沉積結束后,Cu膜本征應力隨時間的變化呈現出與應力狀態相反的弛豫過程(圖13(a)右欄)。厚度為300 nm的Cu膜本征應力隨沉積氣壓的變化過程如圖13(b)所示,沉積氣壓從0.05 Pa增加到6 Pa過程中,Cu膜本征應力由壓應力向張應力轉變,該規律被認為與Cu膜微觀結構隨沉積氣壓變大從致密向疏松轉變過程有關。在低沉積氣壓下,原子錘擊效應明顯,Cu膜致密度高,隨著沉積氣壓的增加,濺射粒子被散射的現象增加,原子錘擊效應減弱,Cu膜的微觀結構變得疏松。

圖13 沉積氣壓對Cu膜本征應力變化、弛豫及狀態的影響曲線Fig.13 The influence of deposition pressure on the evolution,relaxation and state of copper intrinsic stress
3.2 濺射功率/沉積速率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
Chen[17]在研究PI基底上磁控濺射鍍Cu膜(厚250 nm)的本征應力中發現,濺射功率與沉積速率呈線性關系,Cu膜本征壓應力隨沉積速率增加而下降、本征張應力隨沉積速率增加先升高后下降,分別如圖14(a)和(b)所示。薄膜處于壓應力狀態時,提高沉積速率可以提高沉積原子在基底上的遷移能量,能夠獲得不太緊密的晶粒結構,從而使壓應力降低。薄膜處于張應力狀態時,作者借助Crude應力產生機制分析認為,沉積速率剛開始升高時能夠繼續增加原子間距至最大值,使張應力先升高至最大值,隨著沉積速率的繼續提升,原子間距又開始向平衡狀態發展,張應力反而下降。

圖14 不同沉積氣壓下制備的Cu膜的本征應力隨沉積速率的變化曲線Fig.14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insic stress and deposition rate of copper films prepared under different deposition pressures
Navid等[16]也討論了濺射功率對高氣壓下鍍制的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將1.4 Pa沉積氣壓下鍍Cu膜的濺射功率從100 W提高到200 W后發現,Cu膜晶粒變大、裂紋減少、致密度增加,高、低功率下Cu膜本征應力隨膜厚的變化基本在張應力范圍內,張應力的極值均出現在膜厚50 nm左右,高功率鍍Cu膜比低功率鍍Cu膜的本征應力整體向更高張應力方向偏移,如圖15所示。他們將Cu膜表面形貌和本征應力在不同濺射功率下的差別歸因于濺射速率的增加。

圖15 不同濺射功率下Cu膜本征應力隨膜厚的變化過程Fig.15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insic stress and film thickness of copper films deposited under different power densities
Kaub等[11]研究了SiO2/Si(100)基底上不同沉積氣壓下磁控濺射鍍Cu膜本征應力隨沉積速率的變化規律,如圖16所示。在低沉積氣壓下(0.267 Pa),本征應力一直為壓應力狀態,并先隨著沉積速率的增加而降低,這可用式(3)中的生長應力部分(即式(2))解釋,沉積速率增加使本征應力向張應力方向轉變。隨著沉積速率的繼續變大,作者認為薄膜中產生了更多的缺陷導致本征應力又轉向壓應力方向發展。在高沉積氣壓下(1.333 Pa和2.667 Pa),本征應力在最小沉積速率下是壓應力,隨著沉積速率增加單調地向張應力方向變大,最后仍然保持在飽和的張應力狀態。在相同的沉積速率下,沉積氣壓越低本征應力越傾向于壓應力狀態。這是由于沉積氣壓越低,濺射粒子的能量對應力產生的效應(稱為能量效應,可能機制是碰撞誘導致密化或粒子錘擊效應)越明顯,也就是式(3)中第二項和第三項的影響(分別對應能量效應導致薄膜晶界和晶格中的缺陷)變大。不同于高沉積氣壓,低沉積氣壓下本征壓應力隨沉積速率增加先降低后升高就是生長應力和能量效應對應力影響相互競爭的結果。

圖16 不同沉積氣壓下Cu膜本征應力隨沉積速率的變化曲線Fig.16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insic stress and deposition rate of copper films under different deposition pressures
3.3 基底表面狀態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
Abadias等[14]研究了在 a-SiO2、a-Ge、a-Si、a-SiNx和a-C五種非晶材料基底上、相同條件下濺射鍍Cu膜的本征應力隨薄膜厚度的變化關系,如圖17所示,曲線表現出對基底的相關性。在a-SiO2、a-SiNx和a-C基底上Cu膜的本征應力隨膜厚的增加呈現壓應力-張應力-壓應力的變化趨勢,而在a-Ge和a-Si基底上的Cu膜的本征應力隨膜厚的變化則明顯不同,起初(膜厚<1 nm)出現比較弱的張應力,隨后經過較為復雜的變化過程,最后(膜厚>15 nm)表現出比在其他基底上更弱的本征壓應力。研究發現,不同于其他基底,在a-Ge和a-Si基底上沉積的Cu膜,其成核階段未形成獨立的島,而是傾向于與基底形成合金,說明界面處具有較強的化學反應活性。作者認為這種比較高的界面化學反應活性,再加上濺射過程中高能粒子流對薄膜表面的轟擊作用,使在a-Ge和a-Si基底上利用濺射方法沉積的Cu膜具有特殊的晶體結構和本征應力變化過程。

圖17 在不同的非晶基底上Cu膜本征應力隨膜厚的變化曲線Fig.17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rinsic stress and film thickness of copper films on different amorphous substrates
Okolo等[28]研究了不同電壓下用Ar離子濺射清洗非晶SiO2和Si3N4基底對磁控濺射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與在未清洗的基底上鍍的Cu膜相比,基底經Ar離子清洗后Cu膜的本征壓應力明顯降低。作者認為用Ar離子濺射清洗基底能夠誘導Cu膜以柱狀晶模式生長,如圖18所示,柱狀晶空隙兩側的原子間相互作用可能產生張應力。另外發現,Cu膜中的壓應力隨著Ar離子濺射清洗電壓的增加而增加,這可能與Ar離子濺射清洗形成粗糙的基底表面有關,清洗電壓越高,基底表面粗糙度越大,越容易形成導致壓應力增長的薄膜生長平臺。

圖18 不同電壓Ar離子濺射清洗誘導Cu膜柱狀晶生長的聚焦離子束成像Fig.18 The FIB images of Ar ion sputtering induced columnar crystallization of copper films on amorphous substrates
3.4 基底偏壓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
Cemin等[29]利用高功率脈沖磁控濺射(HiPIMS)在施加有不同偏壓的Si(001)基底上沉積了150 nm厚的Cu薄膜,結果顯示,基底偏壓能夠顯著地影響HiPIMS鍍Cu膜中的本征應力,而對直流磁控濺射(DCMS)鍍Cu膜則影響不大。造成這種差別的原因可能是:DCMS中濺射出的多為中性的Cu原子,Cu原子到達基底時的能量僅為幾個電子伏;HiPIMS中80%以上的是Cu離子,到達基底表面時的能量可達20 eV以上;基底偏壓對Cu離子具有加速作用,加速的Cu離子對基底具有轟擊作用,能夠顯著影響Cu膜的生長過程和微觀結構,導致Cu膜本征應力的變化呈現出對基底偏壓的依賴性。這種依賴性體現在:(1)Cu膜最初的單位寬度壓應力隨基底偏壓增加而增加。可能的原因是更高的基底負偏壓可以增強島與基底的結合力,能更多地轉變成Laplace壓力;或者是隨著基底偏壓的增加,更高能量的Cu離子對基底具有更強的注入和刻蝕作用,從而出現壓應力增強。(2)島合并時單位寬度張應力最大值對應的膜厚隨基底偏壓增加先增加后減小。這是因為高偏壓能夠提高Cu原子或Cu離子在基底上的遷移率,使成核密度降低,島尺寸增加,單位寬度張應力最大值對應的膜厚首先隨偏壓的增加(0~-60 V)而增加;隨著偏壓的繼續增加(-100~-160 V),Cu膜生長轉變為(001)方向的外延生長方式,單位寬度張應力最大值對應的膜厚轉而降低。(3)Cu膜合并后,平均壓應力隨著基底偏壓的增加先快速降低到一個最小值(-100 V偏壓,-50 MPa),隨后再緩慢增加到-100 MPa(-160 V偏壓),如圖19所示。作者認為,無偏壓狀態的HiPIMS產生的Cu離子能量剛剛高于Cu膜原子的位移能,能夠在Cu膜表面以下幾個原子層內產生間隙原子缺陷,從而導致Cu膜比較高的壓應力;隨著基底偏壓的增加,逐漸增強的Cu離子轟擊作用對Cu膜缺陷具有消除作用,同時逐漸增大的晶粒尺寸使進入晶界的過量Cu原子不斷減少,因此壓應力逐漸降低;-100 V偏壓以后,Cu膜壓應力增加源于其在外延生長過程中晶粒內部產生缺陷而形成的微觀應變。
3.5 靶材化學計量比對Cu膜本征應力的影響
外木達也等[30]發明了一種能夠降低Cu膜張應力的磁控濺射靶材的制作方法,通過控制連續鑄造法工藝將Cu濺射靶材中的(111)取向的含量控制在15%以上,優選為25%以上。利用(111)取向含量為4.6%的靶材鍍制的Cu膜的殘余拉應力為139 MPa,利用(111)取向含量為25.7%的靶材鍍制的Cu膜的殘余應力為112 MPa,殘余張應力得到一定的消除。他們認為從(111)面濺射出來的粒子能量最高,Cu膜的致密度好,產生壓應力增量,降低Cu膜中存在的殘留張應力。
4 結論
蒸發法和濺射法是目前開展Cu膜本征應力研究的兩種主要的物理氣相沉積方法,用這兩種方法制備的Cu膜的本征應力的形成機制和變化機制既存在差別又相互聯系,并受多種沉積因素的影響。本質上講,Cu膜本征應力的變化與其微觀晶體結構的變化和特征相關,不同生長階段或不同條件下生長的Cu膜的微觀晶體結構存在差異,從而導致了Cu膜本征應力復雜的變化過程和條件敏感性。
通過對Cu膜本征應力產生、變化和影響因素的研究,為調控Cu膜本征應力提供了多種技術途徑,包括調整濺射速率、控制沉積氣壓、施加基底偏壓、調配濺射靶晶體取向、使用過渡層等,在一定程度上可用來降低Cu膜中的本征應力水平。從實際應用考慮,為整體上降低Cu膜中的殘余應力,還應盡量保證Cu膜在室溫下沉積,抑制Cu膜生長過程中由于溫度差而產生的熱應力。
降低Cu膜中的殘余應力,特別是柔性基底上Cu膜的殘余應力可提高后期的加工精度和可靠性,為柔性基底Cu膜材料在薄膜航天器、空間電池陣、柔性展開天線、柔性電纜等領域的應用奠定良好的基礎,拓展柔性基底Cu膜材料在航天領域的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