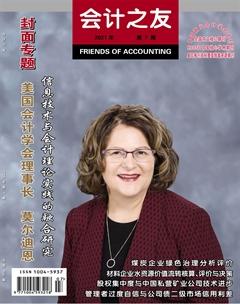財務信息列報與披露的改進研究
張巧良 程燕妮



【摘 要】 為提高財務報告的披露質量,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擬修訂《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列報》,發布了《一般列報和披露》征求意見稿。鑒于我國會計準則與國際財務報告準則的全面趨同,從以下四方面對征求意見稿和反饋意見進行了剖析和梳理:關于三大業務活動損益的列報、權益法下對一體化和非一體化的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投資收益的列報、經營費用和非正常性損益的披露、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的披露。從實質性會計政策披露、利潤表列報、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等方面對我國財務報表列報與披露提出了改進建議。
【關鍵詞】 一般列報和披露; 損益列報; Non-GAAP業績指標
【中圖分類號】 F234.5? 【文獻標識碼】 A? 【文章編號】 1004-5937(2021)07-0151-05
財務報告是上市公司信息披露的重要載體,但其依據的《國際會計準則第1號:財務報表列報》(IAS1 Presentation of Financial Statements)只是一個以原則為基礎的靈活而富有彈性的概念框架,缺乏具體的披露約束。在采用國際財務報告準則(IFRS)的國家和地區,上市公司依據IAS1列報和披露的財務信息的可比性有待提高。隨著經濟和技術環境的變化,新業態和商業模式創新不斷涌現,越來越多的公司管理層注重披露自定義的業績指標(Non-GAAP業績指標),證券國際組織(IOSCO)正努力建立更有約束力的Non-GAAP業績指標披露規則。
為改進財務報表信息的傳遞方式,提高財務報告的披露質量,增強管理層定義績效指標的透明度,國際會計準則理事會(IASB)發布了《一般列報和披露》(征求意見稿)(General Presentation and Disclosures,以下簡稱《征求意見稿》)[ 1 ]。本文對《征求意見稿》和反饋意見從以下四個方面進行了分析:(1)經營活動、投資活動、籌資活動損益的列報;(2)權益法下,對一體化和非一體化的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投資收益的列報;(3)經營費用和非正常性損益的披露;(4)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的披露。同時指出了借鑒意義。鑒于我國會計準則與IFRS的全面趨同,本文的研究對我國財務報表列報與披露準則的改進具有參考價值。
一、對IASB關于損益表結構改進建議的分析
(一)IASB對損益表結構的改進建議
《征求意見稿》提出改進后的損益表如表1所示。
從表1可以看出,IASB對損益表的改進建議主要集中在以下兩個方面:(1)對損益的分類列報,包括經營活動損益、來自一體化的聯營和合營企業的損益、投資活動損益、籌資活動損益,具體含義如表2所示。(2)對損益表中各小計項目的改進,在損益表中列報經營損益小計、經營損益以及來自一體化的聯營和合營企業的損益小計、息稅前損益、稅前損益。
(二)對IASB改進建議的分析
1.關于經營活動分類建議的分析
IASB采用排除法確定實體的經營活動損益,將所有不能分類為來自一體化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投資或融資活動的收益或費用,以及未分類為所得稅或已終止經營的收益和費用,歸類為經營活動產生的損益。IASB認為,采用排除法比使用直接定義經營活動損益更簡單,因為實體的業務活動各不相同,即使實體在同一行業,也很難得出可以一致應用的直接定義,而確定哪些收益和費用被歸類為投資或融資類別比采用直接定義經營損益需要更少的判斷。IASB建議,主體將在其主要業務活動過程中進行的投資產生的收益和費用歸類到經營損益,比如,房地產公司的經營損益中如果不包括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和租金收益,則不能忠實呈報主體的主要業務活動。如果向客戶提供融資是主體的主要業務活動,IASB建議將與融資活動相關的收益和費用、來源于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的收益和費用歸類到經營活動損益。
總體而言,IASB界定經營活動損益的努力,使主體在向利益相關者披露決策有用的財務信息方面向前邁出了積極的一步。關于融資類別中向客戶提供融資作為主要業務活動的實體進行會計政策的選擇,有助于主體提供報告其經營成果的靈活性。但是,IASB的建議也存在值得商榷之處。首先,經營活動損益是衡量績效的重要指標,采用排除法來界定似乎不夠嚴謹。其次,在經營活動的定義中引入“主要業務活動”的概念會給報表編制者造成很多復雜性,當一個主體有多個業務活動時,以什么標準來確定哪些業務活動是主體的“主要”業務活動?《征求意見稿》中的“主要業務活動”與《IFRS15源于客戶合同的收入》中的“業務活動”、《IAS7現金流量表》中的“主要創收活動”等相關概念之間有什么區別與聯系?再次,子公司的主要業務活動一般不同于控股公司,子公司的收益和費用分類與控股公司的分類是不可比的。從合并財務報表角度,控股公司是否應該基于集團角度重新評估子公司的主要業務活動?最后,如果將上述投資性房地產公允價值變動損益列報為經營活動損益,是否會影響經營活動損益的質量?
2.關于投資活動分類建議的分析
IASB建議,損益表中的“投資活動”不同于《IAS7現金流量表》中的“投資活動”。損益表中,除作為主體主要業務活動的投資外,對獨立產生投資回報且基本獨立于主體持有的其他資源的資產,主體應將對應的收益和費用(包括相關增量費用)列入投資活動損益,例如,股權或債權投資的股息或利息回報。在非一體化的聯營和合營企業的損益應享有的份額也歸類到投資活動的損益。
依據IASB的建議,雖然有助于投資者更好地理解一個主體的商業模式及其面臨的各種風險,但將損益分配到特定類別時需要相當程度的判斷,因此,在損益表中單獨列報投資活動損益將增加主體的披露成本;如果主體為籌集投資活動所需資金而產生了融資費用,應將其列示為投資活動損益還是融資活動損益?某些情況下,主體可能擁有支持主要業務活動和為股東創造價值而持有的資產池,主體是否應將這類資產池分為經營類和投資類,以反映單個資產的主要用途?
3.關于息稅前損益和籌資活動分類建議的分析
IASB建議,除以向客戶提供融資為其主要業務活動的主體外,其他主體應在損益表中列報“扣除籌資影響活動和所得稅前的損益”小計金額;將來源于現金和現金等價物的收益和費用、來源于籌資活動負債的收益和費用、其他負債的利息收入和費用,列報為籌資活動的收益和費用。
依據上述建議,利益相關者能夠以以前無法獲得的粒度水平調整財務報表所呈現的信息,有助于評估主體的長期財務業績。但也應該注意到:第一,“融資活動”的定義如何適用于《IFRS15源于客戶合同的收入》包含的“含重要融資部分的銷售交易”。第二,根據IASB的建議,主體的融資活動產生的損益可根據不同情況歸類為經營活動損益或融資活動損益,這種分類的可選擇性的后果之一是主體利用損益的分類實施盈余管理,在負利率環境下,如果主體擁有大量現金和現金等價物,則盈余管理的可能性更高。第三,如果將“投資回報”和“籌資成本”界定為強制性列報項目,將會為投資者提供更有價值的信息,因為這樣做有助于財務報表使用者獲取獨立于實體融資方式的業績信息。
二、對IASB區分一體化、非一體化的聯營企業及合營企業建議的分析
(一)IASB對區分一體化、非一體化的聯營企業和合營企業的建議
IASB建議在《IFRS12在其他主體中的權益披露》中新增對一體化、非一體化的聯營和合營企業的界定,分別披露采用權益法核算的一體化、非一體化的聯營和合營企業的相關投資信息。如表3所示。
(二)對IASB改進建議的分析
IASB區分一體化、非一體化的聯營和合營企業損益的建議,將為報表使用者提供有用的信息。這是因為,對投資方而言,這些聯營與合營企業可能具有不同的重要性,區分他們將會對主體的業務模式提供更好的洞察力。但是:第一,評估一項股權投資是對一體化的聯營和合營企業的投資還是對非一體化的聯營和合營企業的投資,需要相當程度的專業判斷,這可能降低報表所披露信息的一致性和可比性。第二,對一體化及非一體化的聯營或合營企業的厘定如何與《IFRS8經營分部》將聯營公司和合營企業識別為經營分部相互影響,如何協調與《IAS24關聯方披露》的關系?第三,在投資方個別財務報表中一體化的聯營或合營企業,是否需要重新評估其在投資方所屬集團的合并財務報表中是否屬于不可分割的部分?如果需要進行重新評估,是否會得出不同的結論?第四,將一體化的聯營或合營企業視為一個實體經營活動的一部分是否會誘發“盈余管理”?比如,當以前被歸類為一體化的聯營或合營企業的經營業績出現惡化,是否會引發重分類的問題。
三、對IASB關于經營費用和非正常損益披露改進建議的分析
(一)IASB對經營費用和非正常損益披露的改進建議
《征求意見稿》要求主體以提供最有用信息的方式為判定依據,在損益表中采用費用性質法或費用功能法對經營費用進行列報,進一步明確了選擇具體方法的標準;如果主體選擇在損益表采用費用功能法列報,則應在附注中披露使用費用性質法對其經營費用總額的分析。《征求意見稿》將非正常性損益定義為預測價值有限的收益和費用,即對非正常性的判定完全是基于對未來的預期,預計這項收益和費用在可合理預期的未來幾個會計期間不會重復發生;要求主體在附注中單獨披露非正常性損益的當期確認金額、確認原因、對應損益表項目等。
(二)對IASB改進建議的分析
《征求意見稿》關于經營費用在損益表中的列報和附注中披露方式的規定,既能夠提供給主體以選擇的余地,又能夠充分傳遞主體盈利能力主要驅動因素的相關信息。關于對非正常性損益項目進行列報和披露,雖然能夠滿足信息披露的充分性要求,但也存在一定不足。首先,實體對未來預期作出判定時,不會考慮過去是否發生過類似的收益或費用,因此,可能會連續幾個時期將類似的收益或費用歸類為“非正常性”。從這個角度講,綜合考慮過去是否出現過類似項目來判定“非正常性項目”應該更合理。其次,將非正常性損益項目進行列報和披露,不僅可能影響到同行業不同主體之間損益表中相關小計項目的可比性,而且為管理層進行經營利潤平滑創造了條件,但如果在損益表中單獨列非正常性損益項目,則可以克服此缺陷。
四、對IASB關于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披露的建議分析
(一)IASB關于引入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的建議
《征求意見稿》引入“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Management-defined Performance Measures)的概念,是指符合以下三個條件的收益和費用的小計金額:第一,用于對財務報表之外信息的公開溝通;第二,對按照IFRS獲取的總額或小計金額的補充說明;第三,向財務報表使用者傳達管理層對主體在某方面財務業績的看法。《征求意見稿》要求主體在財務報表的單一附注中披露有關任何管理層定義的績效指標的信息,包括:(1)如何計算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該指標如何提供有關主體績效的有用信息;(2)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與損益表小計或總計、毛利和類似的小計、扣除折舊及攤銷前的經營損益、持續經營損益、所得稅前損益等最直接可比的項目之間的調節過程;(3)調節項目的所得稅影響和對非控制性權益的影響。如果主體改變其管理業績指標的計算,采用新的管理業績指標或從財務報表中刪除先前披露的管理業績指標,主體要披露更改、增加或刪除的原因,重述其比較信息。
(二)對IASB引入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建議的分析
隨著新業態的不斷涌現和商業模式的創新,在會計準則規定的業績指標之外披露管理層界定的業績指標的上市公司越來越多,但此類指標存在選擇性調整、透明度和可比性低等問題,IASB對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披露的規范具有很強的現實意義。需要注意的是,要求披露每項調節項目的所得稅影響和對非控制性權益的影響,可能造成信息披露成本過高的問題。
五、研究啟示
作為關鍵性制度創新,我國科創板的設立和注冊制的實施,進一步彰顯了信息披露的重要性。高質量發展離不開高質量的會計信息[ 2 ]。高質量的信息披露是科創板完成自我檢驗、資本市場走向高質量發展的基礎。在會計準則全面趨同的背景下,密切關注IASB“促進財務報告更好地溝通”(Better Communication in Financial Reporting)的發展動向,對提升我國上市公司信息披露質量具有重要意義。根據上述分析,建議我國在進行財務信息列報和披露時應注意以下問題:
(一)披露實質性會計政策,注意準則間的協調,避免信息過載
從報表附注的披露看,我國現行的會計政策披露是基于如下假設:財務報表的主要使用者都是“會計專家”,詳盡地披露會計政策可以幫助其更好地了解公司的財務績效。現實中,上市公司年報附注中會計政策的披露只是重復會計準則對確認和計量的要求,只包含實體有限的特定信息。因此,建議上市公司首先界定會計政策的披露目標,刪除非實質性會計政策的披露,增加主體對重大會計政策應用注釋的披露。從財務報表的列報看,我國在考慮與IFRS的趨同時,應注意損益表與現金流量表中的經營活動、投資活動和籌資活動的對應關系,盡可能考慮財務報表列報的改進與其他企業會計準則之間的相互協調。
(二)規范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的信息披露
管理層定義的業績指標也稱Non-GAAP業績指標,是以非“公認會計原則”定義的計量方法來報告公司業績。某些特定情況下,GAAP的會計信息若得不到Non-GAAP信息的有效補充可能對投資者產生嚴重的誤導[ 3-4 ];股票價格與Non-GAAP收益的相關性更高[ 5-7 ];高管薪酬合同通常采用Non-GAAP的盈余指標[ 8-10 ];管理者在盈利公告中顯著地表達了對Non-GAAP盈余指標的偏好[ 5,11-12 ],并通過使用Non-GAAP盈余指標轉移分析師對公認會計準則凈收益的關注[ 13 ]。鑒于新業態和商業模式創新的不斷涌現,建議我國應鼓勵公司披露更多的Non-GAAP信息。但由于Non-GAAP信息存在諸如缺乏可比性、一致性等問題,建議我國監管當局要規范Non-GAAP業績指標的披露內容,要求公司公開披露的Non-GAAP信息與向監管當局備案的信息一致,并披露這些指標如何與高管薪酬計劃掛鉤。
【主要參考文獻】
[1] IASB(2019). Exposure draft:general presentation and disclosures[EB/OL].https://cdn.ifrs.org/-/media/project/
primary-financial-statements/exposure-draft/ed-general-presentation-disclosures.pdf.
[2] 葉康濤.會計與經濟高質量發展[J].會計之友,2019(22):2-9.
[3] 王艷林,包瑞芝.可轉可贖優先股的確認與計量:由小米集團可轉可贖優先股會計處理引發的思考[J].會計之友,2020(5):133-137.
[4] 賈建軍,張為國,王春紅.另類業績指標披露及其規則的發展和我們的對策:基于京東和蘋果案例的研究[J].會計研究,2019(5):20-26.
[5] SLOAN B R G. GAAP versus the street:an empirical assessment of two alternative definitions of earnings[J]. Journal of Accounting Research,2002,40(1):41-66.
[6] BROWN L D, SIVAKUMAR K. Comparing the value relevance of two operating income measures[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03,8(4):561-572.
[7] BRADSHAW M T, CHRISTENSEN T E, GEE K H, et al. Analysts' GAAP earnings forecas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 for accounting research[J]. Journal of Accounting and Economics,2018,66(1):46-66.
[8] BLACK E L, CHRISTENSEN T E, JOO T T, et al. The relation between earnings management and Non-GAAP reporting[J]. Contemporary Accounting Research,2017,34(2):750-782.
[9] CURTIS A, LI V, PATRICK P H. The use of adjusted earnings in performance evaluation[J/OL]. https://ssrn.com/abstract=2682652,2020-08-11/2021-
02-23.
[10] GUEST N M, KOTHARI S P,POZEN? R.Why do large positive Non-GAAP earnings adjustments predict abnormally high CEO pay?[J/OL].https://ssrn.com/abstract=3030953,2021-01-05/2021-02-23.
[11] BOWEN R M, DAVIS A K, MATSUMOTO D A. Emphasis on pro forma versus GAAP earnings in quarterly press releases: determinants, SEC intervention, and market reactions[J]. Accounting Review,2005,80(4):1011-1038.
[12] CHEN J V, GEE K H, NEILSON J J.Disclosure prominence and the quality of Non-GAAP earnings[J/OL]. https://ssrn.com/abstract=3304172,2020-12-
08/2021-02-23.
[13] CHRISTENSEN T E, MERKLEY K J, TUCKER J W, et al. Do managers use earnings guidance to influence street earnings exclusions?[J].Review of Accounting Studies,2011,16(3):501-5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