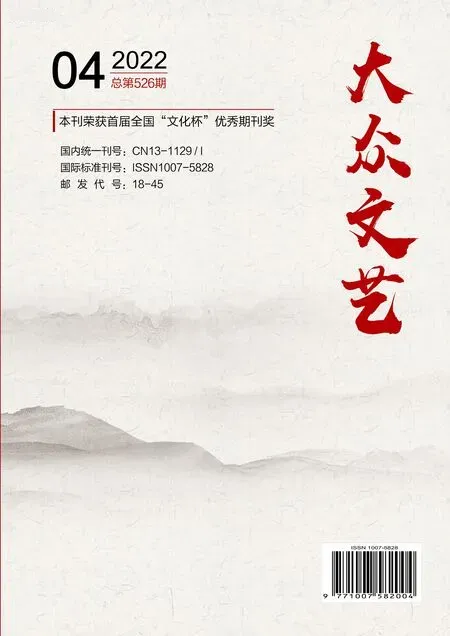淺談魏晉玄學(xué)之開篇
杜昊良
(山西師范大學(xué),山西臨汾 041004)
一、軍事:時局動亂
魏晉南北朝(220年—589年),也被稱為三國兩晉南北朝,在我國歷史上橫跨三百余年,這個時期戰(zhàn)火紛飛,硝煙不斷,兄弟相殘,父子反目,君臣相戈,禮崩樂壞,朝代更迭速度之快令人瞠目,士家大族把控朝廷,權(quán)傾朝野。同時并存多個政權(quán),互相吞并,乃是常態(tài)。設(shè)想如果我們生活在這樣的一個亂世中,又將何去何從?百姓居無定所,食不果腹,民生凋敝,連年征戰(zhàn),每天如驚弓之鳥,過著朝不保夕的生活,這樣的歷史大背景為文化的發(fā)展提供了大量的題材。也導(dǎo)致了人們心中普遍存在一種及時行樂的,今朝有酒今朝醉生活態(tài)度,聲色犬馬,縱情享樂,出現(xiàn)了大量的描繪男歡女愛,風(fēng)景如畫,舉杯對飲的詩詞歌賦。人們很少談?wù)撆c自己無關(guān)的內(nèi)容。名人隱士隱居山林,過著清心寡欲的生活。如“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結(jié)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的陶淵明,開創(chuàng)了田園詩的先河。也有士人面對家國之亂時,心思郁結(jié),境遇窘迫,如虞信的悲詩“胡笳落淚曲,羌笛斷腸歌”“枯木期填海,青山望斷河”。對生命無常的慨嘆,就連曹操,這樣的梟雄都免不了長嘆一聲“對酒當(dāng)歌,人生幾何?譬如朝露,去日苦多”。十九首中類似于這樣的情感描繪更是隨處可見,這首《生年不滿百》可能是最好的表達(dá)吧:“生年不滿百,常懷千歲憂。晝短苦夜長,何不秉燭游!為樂當(dāng)及時,何能待來茲”。用百姓的鮮血與哀腸奏響的這曲亂世離歌,成為這個時代的基調(diào)。這便是玄學(xué)產(chǎn)生的重要因素之一吧。
二、政治:士族閥閱
除卻不同國家之間的博弈征伐,外部的廝殺以外,國家內(nèi)部政治局勢也是錯綜復(fù)雜,士家大族把持朝政,門閥貴族擁兵自重,呈現(xiàn)出一種單獨(dú)分散的特征,政治上各方勢力明爭暗斗,司馬氏權(quán)傾朝野,驕奢淫逸。甚至是將一批批名門望族,名人名士都送上了斷頭臺,就更不必提那些弱小如螻蟻,任人宰割的普通百姓了。在魏晉政治制度上,值得一提的便是選拔官員,品評門第的九品中正制。從辯證角度來看,九品中正制對魏晉時期起了短短的積極作用之后,便成了加劇社會矛盾,加深士人不滿,緊張政治關(guān)系的加速劑。確乎有一個從積極走向消極的過程,我們不能忽視起初九品中正制對朝堂清明,加強(qiáng)中央集權(quán)的積極作用。但是更應(yīng)該看到它“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士族”的直接影響。門閥士族完全把控了官員選拔任用之權(quán),忽視“品性德行”的標(biāo)準(zhǔn),家庭出身則愈發(fā)重要,甚至成為九品中正制的唯一標(biāo)準(zhǔn)。想要通過仕途,報效朝廷,獲取功名來實(shí)現(xiàn)雄志,大展宏圖的士人學(xué)子失去了他們的信念。在個人價值與社會價值無法滿足時,他們便通過飲酒作樂,寄情山水來一吐胸中郁氣。失望,憂懼,憤怒,哀傷,嘆喟,種種情緒結(jié)合在一起,在相當(dāng)長的一段時間里,彌漫著整個社會。在這種社會政治的壓迫下,士人們開始重新思考人的價值,人生命真正的意義,不再以家國之名義作為自己終生的目標(biāo),而是將目光從外在轉(zhuǎn)向內(nèi)在,從社會政治轉(zhuǎn)向自然美景,從不著邊際的讖緯之學(xué)轉(zhuǎn)向客觀實(shí)在。對于整個思想精神上的轉(zhuǎn)變,這些飽讀詩書的學(xué)子通常有著更敏感的嗅覺。就在這樣的轉(zhuǎn)變中,人的主題凸顯了出來,不管是遠(yuǎn)遁田野的陶潛,還是憤慨難平的阮籍,嵇康等人。他們體現(xiàn)出的這種人的主題,是一種更加純粹的,更加深層次人生境界與思想精神。
三、經(jīng)濟(jì):莊園與寺院
此時,舊的經(jīng)濟(jì)制度隨著漢王朝的覆滅一同成了歷史的塵埃。一種以士家大族為獨(dú)立個體的莊園經(jīng)濟(jì)開始嶄露頭角,在破滅中顯現(xiàn)出新的生機(jī)與活力。上述提到,此時雖然仍有君王高高在上,但難以久坐王位,時局極其混亂,王位更替以及勢力改弦易張速度之快使得王權(quán)不穩(wěn),大大削弱了中央集權(quán)的力量,反而是士家大族把持朝政,占據(jù)權(quán)利漩渦中心。“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便是當(dāng)時最好的寫照。文中所提到的“王”與“謝”便是魏晉時期的權(quán)貴瑯琊王氏以及陳郡謝氏。再加上這些世家大族以各自的領(lǐng)地為中心,形成了自給自足的莊園經(jīng)濟(jì),和只由自己控制的武裝軍隊,這儼然成了獨(dú)立的小型社會。世族的權(quán)力過大,不受中央節(jié)制,同時他們又無心過問朝政,財富權(quán)柄皆雙手在握的這些達(dá)官顯貴們開始思考更多關(guān)于精神上的內(nèi)容。優(yōu)渥的經(jīng)濟(jì)條件與大量的空閑時間可以讓他們醉心于文藝。他們所創(chuàng)造的是一種有別于之前任何朝代的文藝,他們的創(chuàng)作觀念中幾乎沒有指向社會現(xiàn)實(shí)與國家政治的內(nèi)容,他們無心政治,兩耳不聞窗外事,他們只關(guān)注讓自己精神上純粹享受的和心理上極度愉悅的話題,這種話題便是個體的真正價值與生命存在的意義。這種主張“自然”精神狀態(tài),在亂世中明哲保身的態(tài)度,越來越向著道家思想所傾斜,于是,孕育在道法結(jié)合基礎(chǔ)之上的魏晉玄學(xué)也在茁壯成長著。
四、文化:離經(jīng)叛儒
魏晉以前,儒家思想占據(jù)著意識形態(tài)領(lǐng)域上的半壁江山。但是儒家思想更多強(qiáng)調(diào)的是維護(hù)封建統(tǒng)治,強(qiáng)調(diào)名教禮制,三綱五常,達(dá)則兼濟(jì)天下等思想,在這樣的亂世中,似乎失去了他的效力。兩漢時期的儒學(xué)背離了最原始的儒教思想精神內(nèi)涵。董仲舒“天人感應(yīng)”的世界觀散發(fā)著濃重的神學(xué)迷信色彩,禁錮天下學(xué)士思想久矣的儒家經(jīng)學(xué)不再被人接受,經(jīng)學(xué)煩瑣枯燥,缺乏活力。所以,處于裂變之時的儒學(xué)無法繼續(xù)統(tǒng)治人們的思想精神,也無法克制,掩飾它自身的弊端與不足。于是,人們長期以來對于儒學(xué)的信仰分崩離析。失去官方統(tǒng)一的思想指導(dǎo),人們心靈陷入了恐慌之中。但,愈是廢墟之中盛開的思想之花愈是光彩奪目,愈是迸發(fā)出蓬勃的生機(jī)。在對舊傳統(tǒng)的否定和對舊思想的懷疑的過程中,不斷形成了特屬于魏晉的哲學(xué)思想,他們的藝術(shù)作品中所傳達(dá)出的情緒雖是悲觀,憂嘆,感傷,頹廢,消極,但潛藏著的卻是新思潮的暗流涌動。這種新思潮中否定著傳承已久的儒家三綱五常,君臣父子,名教禮法,等級森嚴(yán)統(tǒng)統(tǒng)都成了駁斥的對象。人們開始重新思索人生的價值,生命的意義,世事的無常,自然的瑰麗。人們爭先恐后地將自己置于一種無世俗規(guī)則捆綁的世界中,將其視作對傳統(tǒng)儒學(xué)的反抗與復(fù)仇。《世說新語 德行》篇言:其時名士“皆以任放為達(dá)”。更有甚者,將這種放達(dá)轉(zhuǎn)化為為了滿足自己單純低級的感官刺激,比如“埭晉之初,竟以裸裎為高”,達(dá)官顯貴衣不蔽體,聚眾歡鬧,甚至互相玩弄女眷。這種低級的放達(dá)在當(dāng)時許多士人學(xué)子心目中也是鄙夷至極。但是從某種意義上來講,仍舊是對于禮法規(guī)則和名教思想的一種爆發(fā)式的反抗。嵇康大筆一揮,寫下“越名教而任自然”,他不是真正的視禮法于不顧。相反,他想要維護(hù)的是屬于自己心中真正的名教。而少年天才王弼,與何晏等人則認(rèn)為:“名教本于自然”。他們對名教與自然等概念進(jìn)行了重新的解釋與闡述,在道家學(xué)說的基礎(chǔ)上,不斷形成了屬于自身的玄學(xué)思想,更是為后世儒家思想與老莊哲學(xué)的糅合奠定了基礎(chǔ),為傳統(tǒng)儒學(xué)中的不足之處找到了理論上的支撐。魏晉玄學(xué)實(shí)質(zhì)上象征著人們自我意思的覺醒,這種新的人生態(tài)度,使得在傳統(tǒng)思想顛覆之后,涌現(xiàn)出大量優(yōu)秀的文藝作品,而玄學(xué)思想正是在這種文學(xué)作品中不斷地傳達(dá)出來。對儒家的反抗,對經(jīng)學(xué)的駁斥,以及名教禮法的崩潰,標(biāo)志著一個全新的哲學(xué)思想的出現(xiàn),這種哲學(xué)思想把整個時代的士人學(xué)子引向了活潑的,深邃的,放達(dá)的,展現(xiàn)出其自身勃勃生命力魏晉玄學(xué)!便言道“有晉中興,玄風(fēng)獨(dú)振”。
五、結(jié)語
魏晉南北朝在我國歷史學(xué)者看來,無疑是一個黑暗的,混亂的時代。但是在哲學(xué),文藝工作者眼中,這卻是一個偉大的,思想精神極其自由而純粹的時代。魏晉士人在經(jīng)歷了“本體意識”的覺醒后,開始著眼于自身,關(guān)注自我,反對傳統(tǒng)儒學(xué)思想的束縛,抨擊核心是維護(hù)封建統(tǒng)治,尤其是束縛人們思想行為的名教禮制。特別是玄學(xué)的產(chǎn)生對于文學(xué)藝術(shù)的發(fā)展更是起到了決定性的作用,它使人們脫離了經(jīng)學(xué)桎梏,極大地解放了士人學(xué)子的思想,不再壓抑,克制自己做為主體內(nèi)心深處真正情感的表達(dá)與釋放。不論是詩歌,音樂,甚至是繪畫領(lǐng)域上,都更加強(qiáng)調(diào)“內(nèi)在精神”的表達(dá)。東晉顧愷之更是提出強(qiáng)烈影響中國傳統(tǒng)繪畫的觀念“以形寫神,悟?qū)ι裢ā薄PW(xué)更是在特定的社會歷史時期中,通過社會實(shí)踐與高度的理論相結(jié)合,造就了中國古代士人玄遠(yuǎn)清虛的生活意境。脫離時代背景而孤立地去談?wù)撃撤N文藝現(xiàn)象,哲學(xué)思潮的誕生是不可取的,這些現(xiàn)象產(chǎn)生的原因通常不是一元決定的,而是有多種多樣的原因,共同構(gòu)成的。玄學(xué)的產(chǎn)生自然離不開當(dāng)時魏晉時期的經(jīng)濟(jì),政治,文化等等多元化的原因。這些脈絡(luò)聯(lián)系結(jié)合起來后,自然而然便推動著新的思想開篇,也可以說是魏晉玄學(xué)產(chǎn)生的必然性在這些因素中一覽無余。